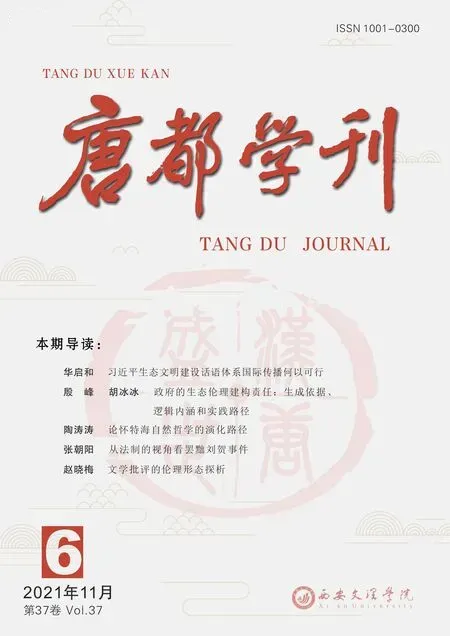河、湟歸唐與晚唐詩歌研究
傅紹磊,鄭興華
(寧波財經學院 a.象山影視學院;b.人文學院,浙江 寧波 315175)
安史之亂爆發(fā)后,吐蕃東侵,河、湟淪陷,關中與安西、北庭的聯系被切斷,失去戰(zhàn)略屏障,長期遭到吐蕃侵擾,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廣德元年(763),連長安也一度淪陷。雖然貞元、元和年間,德宗、憲宗都有復河、湟的意圖、甚至付諸行動。但是,長慶年間,隨著姑息、茍安的政治主張逐漸占據上風,唐朝與吐蕃會盟,正式承認吐蕃所侵占的唐朝土地,這種情況一直持續(xù)到大中年間。“大中三年正月,涇原節(jié)度使康季榮奏,吐蕃宰相論恐熱以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之兵民歸國……七月,三州七關軍人百姓,皆河、隴遺黎,數千人見于闕下。上御延喜門撫慰,令其解辮,賜之冠帶,共賜絹十五萬匹……八月,鳳翔節(jié)度使李玭奏收復秦州……九月,西川節(jié)度使杜悰奏收復維州……五年八月,沙州刺史張義潮遣兄義澤以瓜、沙、伊、肅等十一州戶口來獻,自河、隴陷蕃百余年,至是悉復隴右故地,以義潮為瓜沙伊等州節(jié)度使。”[1]621-629這就是大中年間的河、湟歸唐事件,在當時引起強烈反響,深刻影響到大中、甚至咸通年間的士風、文風,卻一直沒有引起學界關注,頗為遺憾。本文梳理河、湟歸唐對晚唐詩歌,特別是邊塞詩的影響,分析原因,從而為認識晚唐詩歌提供一個有價值的角度。
一、河、湟歸唐詩歌表現
河、湟歸唐以后,士人紛紛遙想盛唐,將盛唐的絢麗圖景投射到現實之中,有生逢盛世之感,從而將大中與開元、天寶相提并論,河、湟歸唐成為當時朝野內外爭相歌頌的事件。崔鉉《進宣宗收復河湟詩》:“邊陲萬里注恩波,宇宙群芳洽凱歌。右地名王爭解辮,遠方戎壘盡投戈。煙塵永息三秋戍,瑞氣遙清九折河。共遇圣明千載運,更觀俗阜與時和。”白敏中《賀收復秦原諸州詩》:“一詔皇城四海頒,丑戎無數束身還。戍樓吹笛人休戰(zhàn),牧野嘶風馬自閑。河水九盤收數曲,天山千里鎖諸關。西邊北塞今無事,為報東南夷與蠻。”馬植《奉和白敏中圣道和平致茲休運歲終功就合詠盛眀呈上》:“舜德堯仁化犬戎,許提河隴款皇風。指揮武皆神算,恢拓乾坤是圣功。四帥有征無汗馬,七關雖戍已弢弓。天留此事還英主,不在他年在大中。”魏扶《和白敏中圣德和平致茲休運歲終功就合詠盛明呈上》:“蕭關新復舊山川,古戍秦原景象鮮。戎虜乞降歸惠化,皇威漸被懾腥膻。穹廬遠戍煙塵滅,神武光揚竹帛傳。左衽盡知歌帝澤,從茲不更備三邊。”崔鉉等人身為朝廷重臣,詩歌為禮制上的應酬之作,但是,在盛情歌頌的過程中很難說沒有真情的流露。
更多的是許多士人的聲音,薛逢《八月初一駕幸延喜樓看冠帶降戎》:“城頭旭日照闌干,城下降戎彩仗攢。九陌塵埃千騎合,萬方臣妾一聲歡。樓臺乍仰中天易,衣服初回左衽難。清水莫教波浪濁,從今赤嶺屬長安。”劉駕《唐樂府十首》:“唐樂府。自送征夫至獻賀觴,歌河湟之事也。下土土貢臣駕,生于唐二十八年,獲見明天子以德歸河湟地,臣得與天下夫婦復為太平人,獨恨愚且賤,蠕蠕泥土中,不得從臣后拜舞稱于上前,情有所發(fā),莫能自抑,作詩十章,目曰唐樂府,雖不足貢聲宗廟,形容盛德,而愿與耕稼陶漁者歌田野江湖間,亦足自快。”張祜《喜聞收復河隴》:“詔書頻降盡論邊,將擇英雄相卜賢。河隴已耕曾歿地,犬羊誰辯卻朝天。高懸日月胡沙外,遙拜旌旗漢壘前。共感垂衣匡濟力,華夷同見太平年。”當時薛逢在長安任職弘文館,劉駕為應舉士人,而張祜則為布衣,雖處不同的階層,但對河、湟歸唐卻都表示出了極大的歡喜和興奮,說明河、湟歸唐影響的廣泛性。
值得注意的是,河、湟歸唐影響幾乎持續(xù)整個大中年間,《新唐書·禮樂志》:“宣宗每宴群臣,備百戲。帝制新曲,教女伶數十百人,衣珠翠緹繡,連袂而歌,其樂有《播皇猷》之曲,舞者高冠方履,褒衣博帶,趨走俯仰,中于規(guī)矩。又有《蔥嶺西曲》,士女踏歌為隊,其詞言蔥嶺之民樂河、湟故地歸唐也。”[3]478
安史之亂后,河、湟淪陷,唐朝中衰;大中五年,河、湟歸唐,對大唐士人而言意味著盛唐時期的太平盛世已經到來。
二、河、湟歸唐與晚唐邊塞詩的新變
會昌以來,隨著回紇、吐蕃的衰弱,唐朝邊境形勢逐漸發(fā)生了變化。《資治通鑒》卷247:“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zhèn)十八州。乃以給事中劉濛為巡邊使,使之先備器械糗糧及诇吐蕃守兵眾寡。”[2]7999-8000河、湟歸唐是會昌年間邊境軍事勝利的繼續(xù),是當時唐朝邊境形勢的重要轉折點,為大中、咸通年間,唐朝對黨項、南詔的軍事勝利奠定基礎,從而大大激發(fā)士人文化自信,推動邊塞詩在晚唐出現全新的面貌。
第一,歌頌唐朝武功,渴望立功邊塞的豪邁情懷再次成為主題。唐朝邊塞詩在開元、天寶年間達到高潮,在盛唐武功的激勵下,士人紛紛從軍邊塞,歌頌將士英勇,表達立功邊塞的豪情壯志。安史之亂爆發(fā),唐朝邊境大幅度收縮,軍事力量衰弱,特別是面對吐蕃強大的軍事壓力,邊塞詩不但數量銳減,而且因詩人情緒低落,厭戰(zhàn)、思鄉(xiāng)成為普遍主題。會昌以來,唐朝在邊境由守轉攻,吸引越來越多的士人前往邊塞,在頻繁的軍事勝利激勵下,邊塞詩的主題也發(fā)生了變化,馬戴《出塞詞》:“金帶連環(huán)束戰(zhàn)袍,馬頭沖雪度臨洮。卷旗夜劫單于帳,亂斫胡兒缺寶刀。”詩中石雄大破烏介可汗是安史之亂后唐朝少有的邊境勝利,在當時引起強烈反響,在詩歌語境中堪比盛唐武功。
河、湟歸唐引起唐朝西部邊境形勢劇變,直接推動唐朝對黨項的軍事勝利,而且時間與河、湟歸唐相隔不久,從而使得河、湟歸唐的影響更加持久。開疆拓土呼聲在當時邊塞詩中逐漸高漲。馬戴《關山曲二首》:“金甲耀兜鍪,黃金拂紫騮。叛羌旗下戮,陷壁夜中收。霜霰戎衣月,關河磧氣秋。箭瘡殊未合,更遣擊蘭州。”“火發(fā)龍山北,中宵易左賢。勒兵臨漢水,驚雁散胡天。木落防河急,軍孤受敵偏。猶聞漢皇怒,按劍待開邊。”許棠《送李左丞巡邊》:“狂戎侵內地,左轄去蕭關。走馬沖邊雪,鳴鞞動塞山。風收枯草定,月滿廣沙閑,西繞河蘭匝,應多隔歲還。”張喬《再書邊事》:“萬里沙西寇已平,犬羊群外筑空城。分營夜火燒云遠,校獵秋雕掠草輕。秦將力隨胡馬竭,蕃河流入漢家清。羌戎不識干戈老,須賀當時圣主明。”擊破外敵,開疆拓土,安定邊境,是晚唐邊塞詩的內在邏輯,因為河、湟歸唐讓士人有了生逢盛世的幻覺,從而順理成章地在盛唐武功的語境中形成特定的表達范式,“猶聞漢皇怒,按劍待開邊”,已經與盛唐邊塞詩相差無幾。盛唐武功主要是在西部邊境獲得,從而晚唐邊塞詩主要的地理審美空間對應的正是以河、湟為中心的區(qū)域。
第二,強烈的紀實性。會昌以來,因為邊境形勢的好轉,大量士人樂于從軍邊塞,零距離地感受邊塞,所以,晚唐邊塞詩就包含了更多紀實的價值和詩人直觀的感受。
許棠就因為身在邊塞而親身經歷河、湟歸唐的整個過程,《塞下二首》:“胡虜偏狂悍,邊兵不敢閑。防秋朝伏弩,縱火夜搜山。雁逆風鼙振,沙飛獵騎還。安西雖有路,難更出陽關。”“征役已不定,又緣無定河。塞深烽砦密,山亂犬羊多。漢卒聞笳泣,胡兒擊劍歌。番情終未測,今昔謾言和。”《出塞門》:“歩歩經戎虜,防兵不離身。山多曾戰(zhàn)處,路斷野行人。暴雨聲同瀑,奔沙勢異塵。片時懷萬慮,白發(fā)數莖新。”河、湟歸唐在長安是君臣同慶的熱烈氣象,在邊塞卻是“胡虜偏狂悍,邊兵不敢閑”。所以,身在邊塞就是在親歷真實的歷史,豪邁卻不失深沉、厚重。《題秦州城》:“圣澤滋遐徼,河堤四向通。大荒收虜帳,遺土復秦風。亂燒迷歸路,遙山似夢中。此時懷感切,極目思無窮。”河、湟歸唐突如其來,雖然是重要的軍事勝利,但是,畢竟難以在短時間里再現“太平盛世”,荒涼的邊塞有著強烈的審美感受,只有零距離面對邊塞才能夠有所感受,《春日烏延道中》:“邊窮厄未窮,復此逐歸鴻。去路多相似,行人半不同。山川藏北狄,草木背東風。虛負男兒志,無因立戰(zhàn)功。”《成紀書事二首》:“東吳遠別客西秦,懷舊傷時暗灑巾。滿野多成無主冢,防邊半是異鄉(xiāng)人。山河再闊千余里,城市曽經一百春。閑與將軍議戎事,伊蘭猶未絕胡塵。”“蹉跎遠入犬羊中,荏苒將成白首翁。三楚田園歸未得,五原歧路去無窮。天垂大野雕盤草,月落孤城角嘯風。難問開元向前事,依稀猶認隗囂宮。”當時唐朝邊境形勢頗為有利,邊塞風土人情在許棠的詩中雖然蒼涼卻不乏剛勁,將士少了幾分怨恨,多了幾分悲壯。許棠雖然在詩中還是難免惆悵,但更多的是昂揚之情,對唐朝的信心,對自己立功邊塞的渴望,這些都建立在最真實的邊塞感受基礎之上。
《舊唐書·高駢傳》:“駢,家世仕禁軍,幼而朗拔,好為文,多與儒者游,喜言理道。”[1]4703高駢作為晚唐名將,用詩歌記錄晚唐邊塞歷史,表達家國情懷。《舊唐書·高駢傳》:“會黨項羌叛,令率禁兵萬人戍長武城。時諸將御羌無功,唯駢伺隙用兵,出無不捷,懿宗深嘉之。西蕃寇邊,移鎮(zhèn)秦州,尋授秦州刺史、本州經略使。”[1]4703高駢的戎馬生涯始于在西部邊境平定黨項叛亂中表現出的高超軍事才華,從而獲得重用,拉開建功立業(yè)的帷幕,謙遜之中分明是一份躊躇滿志的自信。《言懷》:“恨乏平戎策,慚登拜將壇。手持金鉞冷,身掛鐵衣寒。主圣扶持易,恩深報效難。三邊猶未靜,何敢便休官。”咸通年間,南詔攻陷安南,唐朝南部邊境危急,高駢南征,收復安南,戰(zhàn)功赫赫,《南征敘懷》:“萬里驅兵過海門,此生今日報君恩。回期直待烽煙靜,不遣征衣有淚痕。”《赴安南卻寄臺司》:“曾驅萬馬上天山,風去云回頃刻間。今日海門南面事,莫教還似鳳林關。”《過天威徑》:“豺狼坑盡卻朝天,戰(zhàn)馬休嘶瘴嶺煙。歸路崄巇今坦蕩,一條千里直如弦。”鳳林關和海門一帶分別是高駢對黨項和南詔作戰(zhàn)的主要戰(zhàn)場,都是高駢立下赫赫戰(zhàn)功之所,天威徑對于高駢而言更是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進駢檢校刑部尚書,仍鎮(zhèn)安南,以都護府為靜海軍,授駢節(jié)度,兼諸道行營招討使。始筑安南城。由安南至廣州,江漕梗險,多巨石,駢募工劖治,由是舟濟安行,儲餉畢給。又使者歲至,乃鑿道五所,置兵護送。其徑青石者,或傳馬援所不能治。既攻之,有震碎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天威’云。”[3]6392
乾符年間,南詔進犯劍南,高駢再次出征,對南詔幾乎產生了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的威懾力。“南詔寇巂州,掠成都,徙駢劍南西川節(jié)度,乘傳詣軍。及劍門,下令開城,縱民出入。左右諫:‘寇在近,脫大掠,不可悔。’駢曰:‘屬吾在安南破賊三十萬,驃信聞我至,尚敢邪!’當是時,蠻攻雅州,壁廬山,聞駢至,亟解去。駢即移檄驃信,勒兵從之。驃信大懼,送質子入朝,約不敢寇。”[3]6392《赴西川途經號縣作》:“亞夫重過柳營門,路指岷峨隔暮云。紅額少年遮道拜,殷勤認得舊將軍。”正是因為有了長期在邊塞建功立業(yè)的親身體驗,所以,高駢的邊塞詩豪邁之中更多真切、自然。
征戰(zhàn)的艱辛、將士的悲苦、閨婦的哀怨,也都是高駢邊塞詩中常見的主題。《塞上曲二首》:“二年邊戍絕煙塵,一曲河灣萬恨新。從此鳳林關外事,不知誰是苦心人。”“隴上征夫隴下魂,死生同恨漢將軍。不知萬里沙場苦,空舉平安火入云。”《嘆征人》:“心堅膽壯箭頭親,十載沙場受苦辛。力盡路傍行不得,廣張紅斾是何人。”《寓懷》:“關山萬里恨難銷,鐵馬金鞭出塞遙。為問昔時青海畔,幾人歸到鳳林橋。”《邊城聽角》:“席箕風起雁聲秋,隴水邊沙滿目愁。三會五更欲吹盡,不知凡白幾人頭。”《閨怨》:“人世悲歡不可知,夫君初破黑山歸。如今又獻征南策,早晩催縫帶號衣。”邊塞是征人建功立業(yè)的廣闊舞臺,也是冤魂縈繞不散的無情墳墓,更是佳人黯然傷情的夢中他鄉(xiāng)。
保家衛(wèi)國的豪邁與生離死別的哀傷纏繞交織是高駢邊塞詩的最大特點,代表了晚唐邊塞詩的特點。高駢作為晚唐名將,久經沙場,屢立戰(zhàn)功,名震邊塞,深為唐朝所倚重,高駢邊塞詩創(chuàng)作將晚唐邊塞詩提高到了一個全新的境界,獲得了不同于盛唐邊塞詩的獨特意蘊。
三、河、湟歸唐與晚唐詩歌再評價
《孟子·萬章下》:“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4]孟子的“知人論世”反響強烈,逐漸與政治掛鉤,形成以政治評價文藝的范式。《毛詩序》:“情發(fā)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5]政治興衰直接影響文藝創(chuàng)作,在“治世”“亂世”“亡國”等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就有相對應的文藝創(chuàng)作狀態(tài),導致不同審美風格的形成,“詩”成為“世”的反映。《文史通義·文德》:“是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6]章學誠是在“世”與“詩”之間注意到“人”的作用,但本質上并沒有超越“知人論世”的理論范疇,只是進一步完善而已。后世對于晚唐詩歌的評價也深受“知人論世”的影響。
南宋以來,晚唐詩就受到貶抑,嚴羽《滄浪詩話》:“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歷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嚴羽所說的晚唐詩不僅是一個時代范疇,更是一個審美范疇,所以“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入晚唐者,晚唐人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當論其大概耳”[7]。嚴羽對于晚唐詩的貶抑在后世得到了廣泛的認可。黃子云《野鴻詩的》:“晚唐后專尚鏤鐫字句,語雖工,適足彰其小智小慧,終非浩然盛德之君子也。韓、柳之文,陶、杜之詩,無句不琢,卻無纖毫斧鑿痕者,能煉氣也;氣煉則句自煉矣。雕句者有跡;煉氣者無形。”[8]賀貽孫《詩筏》:“中、晚唐人詩律,所以不及盛唐大家者,中晚人字字欲求其工,而盛唐人不甚求工也。”[9]139吳喬《圍爐詩話》:“晚唐多苦吟,其詩多是第三層心思所成。”[9]591
《唐才子傳》:“觀唐詩至此間,弊亦極矣,獨奈何國運將弛,士氣日喪,文不能不如之。嘲云戲月,刻翠粘紅,不見補于采風,無少裨于化育,徒務巧于一聯,或伐善于雙字,悅心快口,何異秋蟬亂鳴也。”[10]晚唐詩人普遍苦吟,晚唐詩也就難免雕琢過甚,辛文房歸因于國運衰弱,辛文房的觀點引起后世不少學者的認同,陳子龍《安雅堂稿》:“大中而后,其詩弱以野,西歸之音渺焉不作,王澤竭矣。”[11]因為晚唐是衰亡之世而貶抑晚唐詩,屬于典型的“知人論世”,在整個唐代歷史與唐代詩歌發(fā)展史中,可備一說。但晚唐與晚唐詩之間也不可能通過政治形成籠統而簡單的關系,籠統地認定晚唐是衰亡之世所以簡單地貶抑晚唐詩而不對二者之間的關系作更為具體深入的認識,有失偏頗。
后世對于晚唐詩歌的評價基于對整個晚唐政治走向的全面認知,而晚唐士人不可能全面認知整個晚唐的政治走向,他們多是通過特定政治事件判斷自己所處的時代環(huán)境。
晚唐國運日蹙,會昌、大中年間,唐朝攘除回紇,河、湟歸唐主要原因是回紇、吐蕃的衰弱,而不是唐朝的強大,甚至對黨項、南詔的軍事勝利也并不意味著唐朝軍事實力已達至盛唐。但當時的士人不可能深究其中的原因,故順理成章地產生了太平盛世的印象,從而進一步影響到文學創(chuàng)作(1)陳銘、方然、余恕誠等人對晚唐詩歌評價更加客觀,但也是基于晚唐是衰亡之世的前提,認為晚唐詩歌代表的是不同于盛唐詩、甚至是中唐詩的具有時代衰落感、回避現實的消極的審美風格,還是“知人論世”的范式。雖然晚唐是衰亡之世,但是,因為出現了河、湟歸唐等特定政治事件,所以,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衰亡之世的特征被掩蓋,甚至在當時士人的觀念中消失,那么,對于晚唐詩歌也應該有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評價。參見陳銘《晚唐詩風略論》,載于《浙江學刊》1986年第3期;方然《關于晚唐文學發(fā)展規(guī)律的系統探討》,載于《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4期;余恕誠《晚唐兩大詩人群落及其風貌特征》,載于《安徽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2期。。河、湟歸唐等政治事件與當時的發(fā)展趨勢并不一致,士人的太平盛世的印象與當時的社會現實也有著較大的偏差,但是,卻是真實存在的歷史事實;說明將晚唐詩置于整個唐代詩歌甚至更為廣闊的文學創(chuàng)作背景中加以研究固然不錯,但是,設身處地地認識當時士人所經歷的特定的政治事件、所具有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再以此為角度對晚唐文學進行研究,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