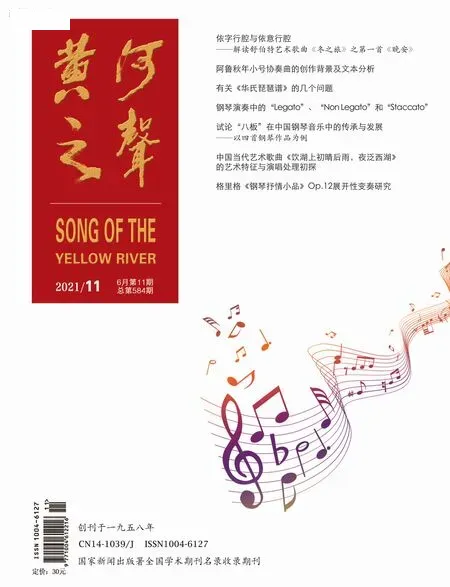同源與分歧
——法—佛蘭德作曲家與“兩種實踐”的關系論證
黃 雅
“第一實踐”(Prima Pratica)與“第二實踐”(Seconda Pratica)(統稱為“兩種實踐”),是西方音樂歷史上一對極為重要的概念觀點,亦涉及著音樂史上重要的音樂事件——“阿圖西與蒙特威爾第之爭”。這場論戰持續時間極久、所牽涉的作曲家極多、影響范圍極大,若將這一事件置于時代進程與歷史脈絡中加以探究,則可知:“兩種實踐”概念誕生的推動力不僅來自于以蒙特威爾第等人為代表的“新派作曲家”對“新的和聲與新的情感”的訴求,更是來自于與當事音樂家相關、乃至與文藝復興整體音樂進程都關系匪淺的法—佛蘭德作曲家的實踐與積累。
一、“兩種實踐”的概念梳理與分歧辨析
“兩種實踐”的觀念核心在于“音樂與歌詞”的關系問題,而這一問題一直都是西方音樂發展中糾結作曲家、理論家最深的問題之一,亦是最值得深思與探討的問題之一。詞曲關系問題可追溯到古希臘時期,哲學家柏拉圖在著作《理想國》中提出和諧和節奏應追隨歌詞的觀點。這一問題伴隨著作曲理論與實踐的發展,在17世紀初被蒙特威爾第以“兩種實踐”的概念提出,成為文藝復興向巴羅克時代更替的標志之一,并對后來西方音樂創作與審美觀念的發展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1600年,意大利音樂家阿圖西發表了文章《阿圖西,論當代音樂的不完美》(L'Artusi,overo delle imperfettioni della moderna musica)。該文章由兩部分組成,第二部分為對話集的形式。文中雖未出現真實的人物姓名,所引用的譜例亦未指明作曲家名稱,但種種蛛絲馬跡——諸如文中主要批評譜例是以蒙特威爾第《殘酷的阿瑪里利》(“Cruda Amarilli”)為代表的部分牧歌,都或明或暗地將矛頭指向了蒙特威爾第。直至1605年第五卷《牧歌集》的出版,蒙特威爾第才對此進行正式回應,這亦是他唯一一次親自的公開回應。在《牧歌集》所附信中,蒙特威爾第使用了“第二實踐”的概念,由此,“兩種實踐”的概念正式形成。
“第一實踐”,又稱為“舊音樂”、“古代風格”等,不同的稱謂表述源自于不同視角的理解與剖析,其核心定義卻始終清晰——即音樂支配歌詞。第一實踐要求作曲家注意復調對位的規則、聲部的構成與進行、協和與不協和音的安排與解決,同時只承認某種程度的不協和音,對如二度、七度的音程予以限制。“第二實踐”,又稱為“新音樂”、“當代風格”,核心定義為歌詞支配音樂,即蒙特威爾第所主張的“歌詞是音樂和聲的主人而不是仆人”。在新的風格中,作曲家可以跨越復調傳統的規則限制,使用不協和音響表現歌詞內在意象。
“第一實踐”忠實擁護者阿圖西的理論依據來自于老師扎里諾在1558年出版的《和諧的規則》(The Isitituzioni armoniche)。這本著作是扎里諾總結前人成果并結合自身實踐經驗的總和產物,正如福比尼所述一般:“扎爾林諾并不試圖闡明或者重新闡釋那些構成了16世紀復調音樂才智的大量個別規則,而是試圖進一步發現在對位藝術中所實際出現或者在他看來存在的基礎。”《和諧的規則》在當時被視為“完美的范本”,普及和建立了當時作曲系統“合理規則”,受到了絕大多數“承前”作曲家的推崇。阿圖西所作的《對位的藝術》(L'arte dell contraponto,1585)一書,便是主要遵循扎利諾的理論所編纂的一本初級教科書,該書的技法框架與體系內容基本未變。
因此,阿圖西對蒙特威爾第的攻擊并不是無的放矢。在阿圖西看來,蒙特威爾第的音樂直接違反了扎里諾的核心理念之一:“第二個必備條件是作品一定是由和諧音程所創作的;另外,它一定偶爾包括一些不和諧的音程,這發生在適當的位置以遵從我將在以后所要說明的規則。”扎里諾并不是完全反對不協和音程,而是要求其被作曲家安排和解決在合理的位置,而論戰導火索——《殘酷的阿瑪里利》正是由于作品中第12至14小節不協和音的連續進行,引來了阿圖西的批評:“我并不否認發現新的事物不只是好的,而且是必須的。但是首先要告訴我為什么你希望以人們利用它們的特殊方式來利用這些不和諧。如果你如此來做是為了說明,‘我希望他們能夠被清晰地聽到’。并且在某種意義上對耳朵造成了傷害,那么為什么你不以正常的方式來使用它們與原理……”由此可見,阿圖西反對的正是蒙特威爾第對不協和音的“特殊”運用方式,并認為這種音樂會“嚴厲而粗糙地沖擊”耳朵。
二、“兩種實踐”的美學理念與同源關系
無論是“第一實踐”還是“第二實踐”,兩者皆出于作曲家對詞曲關系的思考。兩種觀點看似針鋒相對,但實際皆未完全否定對方,這是同一出發點不同結論的美學爭論。
其一,“第二實踐”并沒有完全否認“第一實踐”的正確性,而是在原有基礎上拓寬了規則的范圍,以便作曲家們自由的使用不協和音響。正如朱利奧·茄薩萊·蒙特威爾第在《聲明稿》(Dichiaratione)中為兄長的辯護:“他稱其為‘第二’,而不是‘新’,同時他稱其為‘實踐’,而不是‘理論’……”由此可知蒙特威爾第對“第一實踐”的尊重,也說明了“第二實踐”在新派作曲家心中并沒有新概念的觀點一說,“第二”(Seconda)表明了這一概念是對原有作曲規則的拓展。
其二,“第一實踐”的“理論基礎”人物扎里諾也并不反對歌詞“可聽性”的要求,阿圖西本人亦然。他在1603年出版的《阿圖西:論當代音樂的不完美,第二部分》(L'Artusi: della imperfettione della moderna musica, parte seconda)中如此說道:“所有這些作曲家們的確允許一些粗糙的東西能夠被聽到。看到奧蘭多·迪·拉索、菲利普·德·蒙特以及加契斯·德·維爾特,你就會發現他們當中有許多人也是如此。”雖然阿圖西依然使用“粗糙”一詞來形容不協和音程,但也承認了不協和音響存在的合理性與必需性。
最后,“第二實踐”并沒有完全取代“第一實踐”,兩者并行發展。蒙特威爾第的觀點也在強調著兩者并不存在對抗性:“在舊與新、第一實踐與第二實踐、往昔音樂與當代音樂之間沒有競爭和對抗,雙方都有效。”亦如于潤洋先生所述:“在音樂創作中,這兩種常規應該是并用的。”而上述分析無論從何種角度探討,其核心本質都無法剝離法—佛蘭德作曲家對“兩種實踐”的影響。
論戰雙方的主要人物(阿圖西、蒙特威爾第、朱里奧)雖然都是意大利本土音樂家,但他們的師承關系與理論基礎均系法—佛蘭德作曲家一脈,就此可見,兩派作曲家“同宗同源”。阿圖西所擁護的恩師——扎里諾是文藝復興晚期法—佛蘭德代表作曲家維拉爾特的學生,扎里諾在《和諧的規則》中高度贊揚了老師維拉爾特的作曲手法,認為維拉爾特創作是對位寫作的范例:“他指出以精美的方法、清晰的調式來寫作音樂作品的合理次序,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向我們展示了這些東西。”因而,阿圖西對扎里諾的支持,實際上亦是阿圖西對法—佛蘭德音樂傳統的擁護。
而“第二實踐”的代表人物蒙特威爾第亦承襲著法—佛蘭德作曲技法。蒙特威爾第早年師從于克萊蒙納大教堂樂正馬克·安東尼奧·因杰涅里,這位保守派音樂家雖并未使蒙特威爾第立即獲得名聲與認可,但其趨于法—佛蘭德音樂的作曲技法風格為蒙特威爾第后期的創作奠定了一定基礎。蒙特威爾第早期的前三部作品,如《宗教牧歌》(Madrigali spirituali,1583)等都在扉頁上署名了“因杰涅里之學生”,可見因杰涅里對蒙特威爾第的影響之深。而在其后風格轉型的曼圖亞創作階段(1590-1612),蒙特威爾第與法—佛蘭德晚期代表作曲家韋爾特建立了深厚的師友之誼。在蒙特威爾第的一封信件中,他將韋爾特尊稱為“卓越超群的加切斯先生”,并表達希望效仿他創作的意愿,充分表明了蒙特威爾第對韋爾特的崇拜之意。《新格羅夫音樂與音樂家辭典》的“牧歌辭條”則以“導師韋爾特”(mentor Wert)定義兩者之間的關系,“mentor”一詞雖無直接的教師之意,但亦肯定了韋爾特對蒙特威爾第的深刻影響。兩者的相處時間雖僅達6年,但韋爾特對蒙特威爾第的影響卻是持續而深遠的。韋爾特在音樂與詩歌結合、感情的戲劇性表達等方面都給予當時不甚成熟的蒙特威爾第極大的啟發,為蒙特威爾第的半音化風格與不協和音使用等創作手法奠定了基礎。
綜合以上所述,“第一實踐”與“第二實踐”的代表作曲家“同宗同源”的關系可充分證明他們的理論實踐均基于法—佛蘭德作曲傳統。再者,無論是“第一實踐”中的典范人物——扎里諾、若斯坎、帕勒斯特里那,還是“第二實踐”陣營中的代表音樂家——蒙特威爾第、羅勒、韋爾特,都是法—佛蘭德音樂傳統的繼承者。阿圖西與蒙特威爾第在論戰之時,均例舉支撐各自觀點的作曲家名單。阿圖西分別在《阿圖西,論當代音樂的不完美》、《阿圖西:論當代音樂的不完美,第二部分》以及在論戰之前發表的《辯護信》(Lettera apologetica,1588)中列舉了多位被視為創作典范的作曲家,如維拉爾特、羅勒、韋爾特、帕勒斯特里那等;而朱里奧為支持兄長蒙特威爾第,亦例舉了一系列作曲家,如維拉爾特、羅勒、韋爾特、盧扎斯基等人。不難發現兩份名單有重合之處,且重合的作曲家大部分為法—佛蘭德作曲家,他們均為文藝復興晚期這一流派的代表性人物,即維拉爾特、羅勒、韋爾特。
三、法—佛蘭德作曲傳統與“兩種實踐”
“兩種實踐”作為概念雖誕生于文藝復興與巴洛克時代之交,但其重要的作曲實踐與積累過程早已文藝復興之初法—佛蘭德作曲家皓首窮經的創作中展開。
法—佛蘭德作曲家的前身勃艮第樂派繼承發展著馬肖的音樂傳統,以迪費等人為代表的作曲家在“新藝術”(Ars Nova)音樂革新的基礎上探索著音樂的新方向。15世紀下半葉的廷克托里斯在1477年完成了《對位藝術》(Liber de arte contrapuncti),成為最早對不協和音控制進行了系統闡述的音樂家,他認為不協和音的正確使用主要依據它的節奏和旋律的位置。此時,作曲家創作思維與技法已經逐步脫離中世紀衡定的理性和道德的抽象標準,開始為聽覺感受考慮不協和音的使用方法,進一步形成“自然主義的理性研究”。而代表“第一實踐”的佛蘭德斯音樂傳統正在被廷克托里斯所高度贊揚為“樣板”作曲家的迪費、班舒瓦及其學生奧克岡等人的作品中逐漸成型。
發展至以若斯坎為代表的法—佛蘭德作曲家一代,人文主義的影響在若斯坎的創作中浸染體現。雖然復調對位對法—佛蘭德作曲家而言尤為重要,但若斯坎對詞曲關系的思考使他的作品不再像同輩作曲家一樣注重富于裝飾而精致的復調寫作,而是更關注于如何以音樂傳達與表現歌詞,他在“繪詞法”方面的探索使作品擁有了感情的表現力。
雖然繪詞法開始被委以重任,但若斯坎的音樂卻是在多年后才得到回應;保羅·亨利·朗這樣評論道:“他的藝術走的太靠前,太個性化,沒有人立即響應他。”若斯坎感情深刻的藝術在嚴肅持重、以對位為核心的北方作曲家中曲高和寡,其音樂風格與創作觀點經由學生的傳承,終于在16世紀的意大利牧歌創作開花結果。以筆者之拙見,這種時隔多年的“回應”不僅是對于繪詞法作為音樂描繪歌詞內在的有效方法的認可,亦是作曲家們在詞曲關系中對歌詞重要性的贊同。
從微觀角度的“阿圖西與蒙特威爾第之爭”,再至自文藝復興之初開始的詞曲關系思考與實踐,法—佛蘭德作曲家的偉大之處不僅是在于對傳統的繼承與堅持,亦在于對音樂發展與時代精神的思考。世紀之末的音樂風格劇變不是朝夕之間的產物,對詞曲關系的探索早已存在于法—佛蘭德作曲家們的創作思維之中。這一探索不僅連通了自文藝復興之初傳承到時代交界的音樂傳統之脈,并回應了人文主義精神在“自我”,即主觀創作意識方面的思考,更體現了法—佛蘭德作曲家在文藝復興時期對音樂文化多維度的深刻影響。正如保羅·亨利·朗所說:“從若斯坎到加布里埃利叔侄到蒙特威爾第,所有的作曲家都受這雙重任務的啟發,這一觀念滲透在他們的音樂的每個細胞里,最后在文藝復興的靜穆氣氛轉入波瀾壯闊的巴羅克世界。”
結 語
就此,“第一實踐”與“第二實踐”并不是完全相對的概念,它們擁有著同一理論基礎。“第二實踐”的提出亦不是對“作曲傳統”的“反叛”,而是審美觀點的分歧,是原有規則尺度的擴張。“第一實踐”與“第二實踐”之爭的背后是法—佛蘭德音樂傳統另一種意義的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