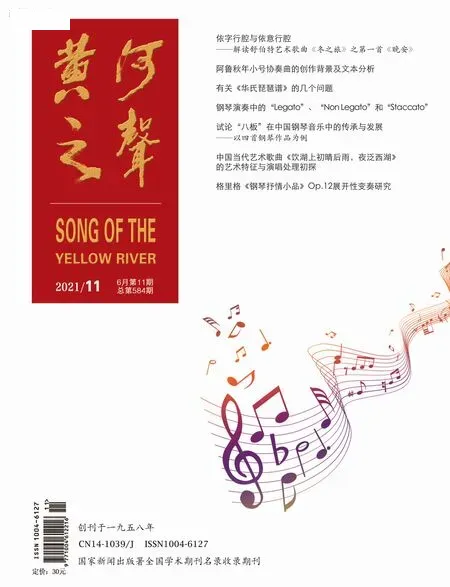試論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音樂思潮
袁鑫帥
思潮是指,某一時期內在某一階段或階層中反映當時社會政治情況而有較大影響的思想潮流。①參照上述關于思潮的定義,我們或可對音樂思潮加以如下界定:音樂思潮是指某一歷史時期內在音樂實踐中發生重要影響的思想潮流。[1]分析看來,并不是所有的音樂思想都會被稱為音樂思潮,其劃分標準應大致遵守以下幾點:一是被稱為音樂思潮的音樂思想觀念應該具有集體性,指部分或大多數音樂家所持有的共同觀點;二是被稱為音樂思潮的音樂思想應該對音樂實踐具有重要影響,在社會一段時間范圍內造成一定反響。另外,相比其他思潮,音樂思潮受一般政治、文化共性因素影響的同時,又受音樂自身發展的特殊性影響,這也是音樂思潮區別于其他思潮的所在。在探究之前我們需要明確的是,各類音樂思潮大致處于相同的時空與社會國情,因此它們之間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響、相輔相成的關系。
一、“五四”運動前的音樂啟蒙教育思潮
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的社會制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緊鎖百年的大門被迫打開,西方現代音樂文化傳入,中國傳統音樂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我國的音樂文化成分趨于多樣化。在這一時期,傳統的禮樂思想逐漸分崩瓦解,中國音樂該何去何從,引起當時眾多音樂家們的深思與討論。故而,新的音樂思潮應運而生。
(一)音樂啟蒙思潮
新的音樂思潮具體來說,又是隨著新式學校的興辦而產生,并發展為社會的音樂思潮。[2]這里暫且將這一新的音樂思潮稱之為音樂啟蒙思潮,其含義主要包括兩點:一是指通過音樂教育,使當時的人們接受西方先進的音樂文化而得到進步;二是對封建禮樂制度的批判,從而建立一種“新音樂”。
最初提出這一思潮的大多是以維新派為主的新興資產階級人士,他們希望通過音樂來培養國民的新思想,快速接納維新變法,并不是為了尋求音樂本身進步發展之道。新式音樂啟蒙教育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1903年清政府頒布《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才開始涉及音樂,卻還是以“唐宋之言絕句”“協律可歌”為主。直到沈心工、曾志忞、路黎元、高壽田等部分接受日本音樂教育的留學生回國后,學堂樂歌運動才真正步入正軌。學堂樂歌運動一方面推行和反映了音樂啟蒙思潮所帶有的政治思想屬性,另一方面也推動了中國近代音樂文化的進一步發展。
在學堂樂歌在中國全面施行的過程中,人們對于音樂本體的發展愈加重視,不乏出現以下幾種聲音:一是以匪石等為代表的激進人士提出否定中樂、全盤西化的觀點,這類觀點的確為西方近代音樂最初進入我國提供了加大幫助;二是以曾志忞、梁啟超等為代表提出西樂為主、改造中樂的觀點,這類觀點相比匪石、沈心工等人持有的全盤西化論要溫和的多,并代表了當時多數有志于發展中國音樂的知識分子;三是以孫時等為代表提出堅守中樂,抵制西樂的觀點,這類觀點更是走向了極端,為后來的國粹主義音樂觀的提出提供了范本。
綜上所述,音樂啟蒙思潮最初是以推行變法、塑造國民性為目的而興起的。但在發展的過程中,通過學堂樂歌運動,其目的逐漸由用音樂宣傳新思想、培養新風氣的政治功利性,演變為對如何吸納西方音樂文化來發展中國近代音樂的討論,雖然這一討論還僅僅處于萌芽階段。這一思潮的興起,也為“五四”運動后的各類新音樂思潮的提出奠定了基礎。
(二)音樂美育思潮
“五四”運動后,隨著學堂樂歌運動的繼續發展,音樂啟蒙思潮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以蔡元培為代表所提出的音樂美育思潮。這一思潮的提出是在新文化運動后,整個社會不再滿足于學堂樂歌式的唱“樂歌”的音樂啟蒙體驗,而對音樂教育更加細化的追求。但究其根本,仍然擺脫不了社會賦予它的功利主義色彩。這里暫借蔡元培先生在大教育背景下提出的“美育”觀點②來界定這一影響深遠的音樂思潮。音樂美育思潮的提出,是音樂啟蒙思潮在教育領域的延續,不僅為普通音樂教育的后續發展提供思想指導,更是為后來專業音樂教育的起步做出了重要貢獻。
音樂美育思潮提出后,社會對于專業音樂技能的要求愈發嚴格,于是一些新型音樂社團和專業音樂教育機構應運而生。1927年,上海國立音樂院的建立才真正標志著音樂美育思潮在專業音樂教育事業的首次成功實踐。但是我們需要明確的是在專業音樂教育領域,音樂美育思潮僅僅起到催化劑的作用,而真正使專業音樂教育事業繼續發展的主要動力,是以蕭友梅為代表赴歐美日學習音樂的留學生們的不懈努力。
二、“五四”運動后關于建設中國音樂的各類思潮
隨著新文化運動和專業音樂教育的不斷發展,對于如何建設中國音樂事業的談論愈發激烈。但究其本質,其探討中心還是在面對中西兩種音樂文化的碰撞時,如何擺正態度。這一時期各類思潮的劃分,基本延續了上一階段匪石、曾志忞、孫時等人的觀點,繼續深入論述,但卻有所不同。在對西方音樂文化逐漸客觀深刻地認識下,“全盤西化論”逐漸被音樂界各類人士摒棄,堅守雅樂至上的國粹主義音樂思潮人士卻始終沒有放棄他們的堅持。但是,當時的社會主流音樂思潮則偏重于用中西結合音樂思潮來建設我國新音樂文化。
(一)國粹主義音樂思潮
國粹主義音樂思潮是指對我國傳統音樂文化予以完全保存的觀念與主張,視西方音樂文化的傳入為“洪水猛獸”,其大肆傳播將使優秀的中國傳統音樂文化受到沖擊甚至面臨生存危機。這類音樂思潮在西方音樂文化早期傳入我國就形成了,以著名古琴家王露、鄭覲文等為代表。他們還曾公開宣揚只有我國古代的“雅樂”,才是值得提倡、值得發揚的中國“國樂”。[3]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國粹主義音樂思潮充斥著對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極度自負,他們還活在閉關鎖國的封建社會,對于不同的文化價值與藝術審美帶有強烈的排外性。
“五四”運動后,國粹主義音樂思潮迅速崛起。一是由于在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部分國人對西方的野蠻文明產生徹底懷疑;二是早年留學歐美日等國家的部分作曲家開始在國內從事專業音樂教育和音樂創作活動,從更加專業的角度向世人宣傳了先進的西方現代作曲技法,引起了國內從事中國傳統音樂的國粹主義音樂家們更加強烈地抵觸和排斥。他們紛紛開始采用各種方式復興中國傳統音樂文化,如以鄭覲文為代表的“大同樂會”,一方面培養民族器樂演奏人才,一方面還對中國古代雅樂器進行挖掘、整理與仿制。30年代,雖然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大力提倡封建禮樂制度,但在以抗日救亡運動為主的社會主流思潮影響下,國粹主義音樂思潮還是逐漸走向了衰落。
綜上所述,我們應對國粹主義音樂思潮進行客觀的評價。一方面贊揚他們對于我國優秀的傳統音樂文化的堅守與繼承;另一方面批判他們對于中國傳統音樂文化中糟粕的盲目堅持,以及對于西方音樂文化的全盤否定。他們沒有看到時代發展和音樂發展的必然趨勢,沒有看到中國傳統音樂遠遠落后于時代、落后于民眾心理的事實,沒有看到在時代變革的大洪流中音樂變革的重要性和必然性,企圖以不變之音樂應萬變之時代。[4]
(二)中西結合音樂思潮
與國粹主義音樂思潮相對應的,是認為我國傳統音樂文化不及西方音樂文化,采用以西為師、走西化道路的中西結合音樂思潮。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有蕭友梅、趙元任、陳仲子等,他們偏重于按蔡元培“兼收并蓄”的方針,主張在中國建立類似俄羅斯“民族樂派”那樣的世界音樂。
在中西結合音樂思潮提出之前,他們首先對中國音樂落后論進行了闡述。例如,蕭友梅在《最近一千年來西樂發展之顯著事實與我國舊樂不振之原因》一文中從多個方面列出中國音樂落后西方的原因。關于如何建設我國近代新音樂,蕭友梅曾在其博士論文《17世紀以前中國管弦樂隊的歷史的研究》中提出中國樂器應該依照歐洲技術加以完善,還要引入統一的記譜法與和聲等等。于是,蕭友梅在回國后創辦了我國第一所高等專業音樂學府——上海國立音樂院,一生都在致力于中國音樂文化事業的建設。
仔細探究,我國音樂文化的事業發展一直都是沿著蕭友梅先生的志愿前進,如當今西方記譜法在中國傳統器樂的廣泛使用、西方樂器和作曲技法在我國的大面積普及、西方音樂教育體制在我國的全面應用等等。但不可否認的是,中西結合音樂思潮的提出,在為我國音樂文化帶來新鮮血液的同時,卻也忽略了對中國傳統音樂的重視與繼承。
(三)國樂改進音樂思潮
“五四”運動后,在中西方音樂文化碰撞和交融中,出現了這樣一種音樂思潮。它不像國粹主義音樂思潮那樣固守舊樂,不像中西結合音樂思潮那樣“以西為師、以西為主”。它更多的是在學習借鑒西方音樂的同時,以舊國樂為本體加以改進,著手創造一種具有時代特色的、容納一定西方經驗的“新國樂”。它最早由劉天華提出,最早稱之為“國樂改進”主張,這里暫且稱之為國樂改進音樂思潮。
對于改進國樂這一事業,劉天華在國樂改進社社刊中提到:“要說把音樂普及到一般民眾,這真是一件萬分渺遠的事。而且一國的文化,也斷然不是些抄襲別人的皮毛就可以算數的,反過來說,也不是死守老法、固執己見就可以算數的。必須一方面采取本國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納外來的潮流,從東西的調和與合作之中,打出一條新路來,然后才能說得到進步兩個字……”③于是,劉天華預設了一系列計劃,前提則是國樂改進必須建立在對國樂加以研究保護的基礎上,如對古代音樂文獻加以搜集與整理,收集記錄民間音樂遺存,推行國樂教育與研究,改良民族樂器之形制等等。
國樂改進音樂思潮的提出,是在西方音樂文化傳入我國后,對中國舊的傳統音樂文化自身的反思與檢討。這讓沉睡了近千年的中國傳統音樂逐漸蘇醒,并開始快速發展。但隨著劉天華的逝世和當時社會的動蕩與需求,國樂改進音樂思潮開始降溫,并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四)救亡音樂思潮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馬克思主義即刻在中國廣泛傳播,為我國的文藝事業發展指明了方向。“九一八”事變后,抗日救亡運動在我國愈演愈烈,在“左聯”的指導下,左翼音樂運動開始發展。最早由聶耳、王丹東、李元慶等人在北平組織成立了“左翼音樂家聯盟”,接著以田漢、安娥、任光、聶耳、張曙等為代表在上海成立了“蘇聯之友社”音樂小組等等。左翼音樂組織的接續建立,標志著一個以宣傳抗日救亡思想,用音樂捍衛民族解放的救亡音樂思潮的形成。
真正使救亡音樂運動付諸現實意義的,是呂驥對于“國防音樂”口號的提出,它規定了中國近代新音樂在民族解放斗爭時期所要擔負的崇高任務。其后,為了進一步加強對音樂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領導,呂驥、周鋼鳴等人又撰文提出了“新音樂運動”的口號,并進一步闡述“新音樂運動”的性質和任務。但在實際工作中,部分人開始出現輕微的“左傾”思想。如呂驥對于冼星海、任光等人的抒情歌曲做出了批判,認為是“傷感主義”音樂,不符合現階段的“新音樂運動”宗旨;冼星海也曾嚴厲批判了劉雪庵的《長城謠》、賀綠汀的《保家鄉》等歌曲。
在對“新音樂”的界定方面,音樂界也出現了分歧,以沙梅、呂驥為代表的狹隘派認為中國的新音樂應該發端于聶耳的革命歌曲創作,中國的“新音樂”則是革命的新音樂。這得到了部分左翼音樂家們的支持,但卻遭到了中國絕大多數人的批判。這種觀點顯然是不符合社會發展軌跡的,它一方面否定了學堂樂歌運動以來我國音樂發展的累累碩果,另一方面還將不屬于無產階級革命音樂的其他音樂作品排除在外。
總的來說,救亡音樂思潮帶有鮮明的時代性和無畏的革命性,它隨著抗日救亡運動的興起而興起,隨著革命斗爭的高潮而高潮,又隨著革命的勝利而逐漸消退。救亡音樂思潮為我國抗日救亡運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使之成為中國近現代音樂發展史上的璀璨明珠。■
注釋:
① 見《新華漢語詞典》,崇文書局2006年版
② 蔡元培在《教育大辭書》提到:“美育者,應用美學之理論于教育,以陶冶感情為目的的者也。”
③ 見劉天華的《國樂改進社緣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