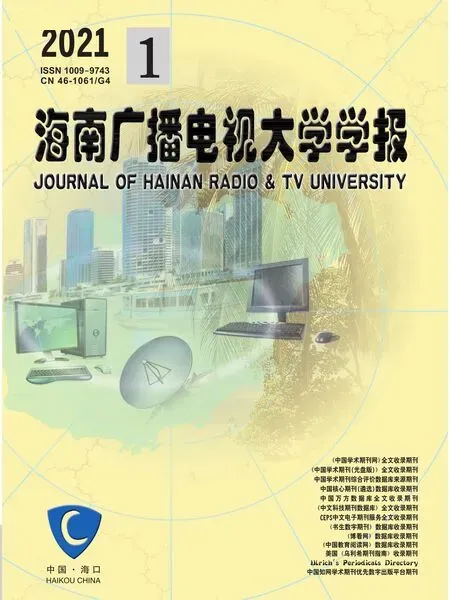楊義敘事學理論觀照下的《誤殺》敘事解讀
——兼與《誤殺瞞天記》比較
喬 慧
(山東藝術學院 傳媒學院,山東 濟南 250307)
國產犯罪電影與好萊塢同類類型片慣常著重于渲染后現代主義觀照下的暴力美學或懸疑氣氛的表現重心不同,往往是以“犯罪”這種類型作為電影方法,而將討論重點放在“黑與白”“情與法”“罪與罰”的糾結兩難。類同中國古典小說《水滸傳》,逼上梁山與招安廟堂,被動違法與主動服膺于規訓,才是國產犯罪類型片的線索與敘事走向。所以與其將其歸結為一種類型程式,弗如說是種種中式倫理道統與人文哲思在典型二元對立模式下的命題化探討。柯汶利電影長片處女作、陳思誠監制的《誤殺》,雖是改編自印度電影,但在結構設置和細節安排上體現出明確的中國敘事策略與特點,且與原名稱《Drishyam》(《較量》)或者《Visual》(《視點》)以突出其類型特征相較而言,中版英文名稱《Sheep Without A Shepherd》(《烏合之眾》)則將影片的命題聚焦于社會群體人文的深度立場。
一、倫理勢能:本體、位置與變異的親情動力
在《誤殺》這樣一部以家庭組織而成犯罪主體的電影中,金錢、欲望、權利、宣泄等常用的犯罪緣由都被摒棄于外,母親維護女兒、父親維護全家的愛與責任構成全部犯罪動機。因此倫理情感就成為影片敘事的主要勢能。《文心雕龍·定勢》說“夫情致異區,文變殊數,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情立體,體成勢,倫理體勢成為《誤殺》的敘事動力。尤其是“勢”的概念,在與印度版的比較中尤為明顯:印度《誤殺瞞天記》是以日常生活化的散漫開場,在接下來事情發生后的敘事中補述人物性格如檢察長米拉的兇暴殘忍;而中版《誤殺》則一開始就以拉韞對犯人的殘酷和對兒子的溺愛鋪墊了維杰自首的種種不可能與藏尸逃案的必要性,并以其子素察的各種作惡先科使反殺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以拉韞的多謀善斷總領全片時時處于千鈞一發的緊張氣氛,如古人寫文章“首段得勢”,又如《紅樓夢》“鳳辣子出場”,開篇推動線索結構與情緒要素向極盡貼合犯罪片類型特質的方向運轉和律動。如何在鳳頭即立起人物性格之“勢”與犯罪動機之“勢”,中版《誤殺》可算佳例。
楊義先生在其《中國敘事學》中從三個方面來細分勢能這種結構內蘊的能量或動力:本體勢能(內在)、位置勢能(外在)、變異勢能(內在和外在結合而生變異)(1)楊義:《中國敘事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頁。。本體勢能是人物本身的多構性,位置勢能是雙方相對而成的處境,而變異勢能是反轉變更。《誤殺》首先是兩個家庭“父母之愛子”的沖突,再是在情與法的沖突,后又回歸各自家庭中的父母職責承擔,人物本身的多面構成與隨事件發展境況變化產生的共時與歷時的多變驅動,共同形成影片敘事結構的曲折跌宕。
(一)本體勢能:為人之父的一體多面
“本體勢能一半來自作品中人物性格的雙構性或多構性,及其在特殊情境中能量釋放的反應(2)楊義:《中國敘事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頁。”,《誤殺》對男主人公李維杰的設定是深愛子女、愛看電影的、開設網絡公司的移民父親,不同于印度《誤殺瞞天記》中為看電影很少回家、坐辦公室里等人收錢報賬的形象,李維杰是個及其顧家的更為普通的社會中下層人物代表,影片多次展現其回家吃飯的場景卻不受大女兒喜歡,因資金緊張卻不忍拒絕女兒參加夏令營的懇求,這樣求與大女兒恢復親密的渴望,是比原印度電影中男主角疏離于家庭卻擁有和諧的父女關系,更有彌合的余地以促進情節發展的。其后這種樸實中略帶唯唯諾諾的形象在妻女遭遇危機之時呈現出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樣子:安排家人出游不在場安之若素,引導家人編造證詞機鋒百出,面對警察刑訊堅韌不移。日常狀態下的父親與危機時刻的父親判若兩人,不但順應并推進了影片敘事的進展,且豐富了人物角色自身的立體與真實。單只論日常時期的李維杰,踏實勤奮、遵紀守法、憚于示愛,放到電影中自然是乏善可陳,而護佑家庭的另一面遇到危機迸發出來,逃罪免罰種種行事就呈現出性格的雙構性特征并推動敘事矛盾走向不可遏制的強張力節點。
1.位置勢能:弓矢相搭的矛盾激變
位置勢能產生的原因是人物關系的矛盾二元對立。素察母親拉韞為警長,父親都彭為總統候選人。對手位高權重且無理溺愛,“自首連坐牢的機會都沒有”,使逃罪之舉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有了這樣的位置勢能,李維杰的舉動就處于可被同情可被理解的位置,為家人為親情為消除惡人的犯罪動機于違法之際反而占據了倫理與正義的情理優勢,所以當拉韞嚴刑逼供安安,巨大暗色的身影慢慢覆蓋幼兒小小的身軀,卻在與大部分人共情的層次上落了下乘。“位置是歷史和現實的錯綜,生存和命運的較量,偶然和必然的遇合。它給人物和事態以某種難以選擇的選擇契機,給人物和事態以選擇中的牽引力和扭曲力”(3)楊義:《中國敘事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頁。,當向來懦弱的阿玉遇見一直強勢且喪子狂暴的拉韞,愛護子女的情感之下阿玉爆發催生出原《誤殺瞞天記》電影中沒有的一場對峙,雖然此時是同為母親的勢均力敵的位置關系,但阿玉與之前性格形象的強對比反而使拉韞處于氣場上的劣勢。而原印度電影中,事先知情的母女等到維杰處理完手機和車輛之后才告訴維杰被誤殺的薩姆的身份,維杰的滅跡先于受到對手的壓制,位置勢能的不占劣勢反而使其逃罪動機找不到不得不發的理由并落于下乘。
2.變異勢能:奇正相反的對照反轉
不同于位置勢能是基于共時性的雙方參與,變異勢能則由是歷時性的反差而生。不同于印度版薩姆的直接死亡,中版添加并強調了素察吞舌窒息而死的另一種真正死因,并給出開棺移尸之時素察睜大的雙眼、染血的食指與滿是血痕的棺材板的特寫,這個情節既進一步解釋了李維杰費勁心計逃罪的另一個因素,即素察并非死于防衛過當,而是死于埋尸窒息,這就沒有了萬一減刑的僥幸可能,也以其觸目驚心的震撼為后來李維杰自首做了合理蓄勢。“所謂變異勢能,必然存在著一個原有相與一個或若干個變異相……原有相與變異相之間形成了敘事結構線索的關聯、呼應、變化(4)楊義:《中國敘事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頁。”,另一個在中版《誤殺》中被添加的變異的勢能,是二女兒安安用涂改液改過分數的試卷。案情本已塵埃落定,深愛女兒的父親看到孩子在謊言交織的前情里已經活學活用,再加上前一次變異勢能帶來的心理震動,就只能將自己送向監獄,由此掀起敘事的另一個波瀾。這兩個變異勢能以比“原有相”更不可抗拒的力量將影片的審美意義推向與印度版完全不同的方向。
二、因果預約:葫蘆格與多元隱喻
中版《誤殺》的布局,其實是非常符合中國古典小說“葫蘆格”的結構程式的。葫蘆格的范式是,前有“頭回”、后有正話故事的大小組接。這是中國敘事有別于西方敘事模式的明顯外部結構特征之一。“小葫蘆”中的幾個要素往往能夠形構為一個自具面貌的“獨聯體”,它有相對完整的情節與完足的價值觀念,與正話處于一種“并置”的狀態。“小葫蘆”里裝著豐富的信息,為正話的故事發展預先醞釀好生成環境、氛圍與輿論,預示正話的主旨,也為讀者預先調理好接受故事的期待視野(5)夏明宇:《葫蘆與雙環:宋元話本小說的空間結構》,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誤殺》開始以李維杰綜合多部電影編織的一個逃獄失敗的幻像開場交代了他豐富的閱片經歷,有閱盡電影的交代,也有“獄”的犯罪基調;然后是拉韞的審訊案例,強調其無證據而套口供的斷案能力,為后來李維杰費盡心機制造假象的壓力和拉韞幾乎數次找出真相的緊張做了很好的情緒渲染。以拉韞之能卻無能為力,以李維杰之能卻自首投案,影片的正本故事在與“頭回”正正反反的承接拓展與反轉中,為觀眾形成意料之中的期待滿足與意料之外的驚喜。
“作者早已安排好的敘事結構和敘事過程,以一種陌生的、甚至是異己的存在,和讀者的‘先在意識結構’發生相互的質疑和撞擊(6)楊義:《中國敘事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6頁。”,對于一部翻拍作品,早先的印度版本《誤殺瞞天記》形成觀眾第一次的“先在意識結構”,認為素察確實死于“誤殺”,而李維杰單純是在處理后續,還會認為結局依然是防衛者免于刑罰安然度日。而中版《誤殺》的“小葫蘆頭”即“頭回”又給觀眾形成第二次的“先在意識結構”,即身為警察長的拉韞不只會嚴刑逼供,還有精湛的業務能力,維杰一家除了會面對刑訊拷打,還會遭遇隨時被識破真相的危機。而印度電影中薩姆只有拍下安玖浴照以此威脅安玖母女就范一件惡事,在中版中則有打瞎別人眼睛卻能私了、下藥迷奸等為社會所不容的各種更惡的前科。綜上,整個觀影過程中觀眾期盼李維杰一家的罪行不被發現和擔憂其罪行會被偵破的種種情緒,交織成盼望李維杰安然脫罪的期待情緒;這種情緒行將呵成之際又被安安的作假和李維杰的投案強行扭轉,跳脫出來思考一下情與理、罪與罰的殘酷現實。楊義先生說“因此閱讀過程是作品境界的再完成和再創造,既再創造著作品,也再創造著讀者自我(7)楊義:《楊義文存》 (第一卷)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70-371頁。”,觀眾對電影作品的觀看過程也是如此,這是中式敘事獨有的、楊義先生所言“點醒靈性”的敘事承擔。
原故事雖然發生在印度這樣的佛教大國,但在《誤殺瞞天記》中印度只是一個故事發生地而無關社會與意識背景。反而是中版《誤殺》,強化了因果意蘊并以因果邏輯組織敘事線索。佛教因果循環律是佛教的人生觀,也是中國傳統的善惡觀。李維杰日常布施的時候僧侶坦然接受,藏尸之后再次布施遭到拒絕,其父母死于暴亂,李維杰引發暴亂又為了免去更大的暴亂投獄,這是電影敘事里李維杰一人的因果。拉韞因溺愛而喪子,素察因行惡而喪生,都彭因疏于對子女的教育而失權,這是二元對立中一方的因果;李維杰因為想要與女兒恢復親密而同意平平去夏令營因而埋下禍患,阿玉為了保護女兒而跟隨反擊,女兒又為了保護媽媽和自己的隱私視頻而拿起武器,李維平為了保護家人而撒謊滅跡,然后學會了撒謊的安安涂改了成績而又導致李維平自首進了監獄,這是二元對立中另一方的因果。兩個家庭的因果交織,構成犯罪與反殺,再犯罪與投案的敘事主線索。另外,李維杰踏實肯干,開設網絡公司卻是親力親為奔波于客戶公司設備井房,更近于平民,是后期“烏合之眾”的鄰人為其奔走呼吁的階層基礎;拉韞出錢擺平兒子打瞎別人眼睛,又仗權勢動用私刑審問李維杰甚至小安安,并在無證據情況下挖開百姓祖墳,導致群起而攻之后夫妻下臺,是兩個階級對抗對立的因果。及至在佛寺鐘聲里,拉韞夫妻卸下職權以單純的喪子父母的身份遇見備受煎熬的李維杰,互相道歉得知真相,所有的因得到該有的果,環環相扣的因果敘事就此完結。
很多評論將“Sheep without A Shepherd”之“羊”的意蘊放置于基督教文化下進行分析,討論其上帝缺失之義。然而作為一部數次出現佛教雕像與僧侶形象的電影,無論故事發生地是在印度或者泰國這樣的佛教國家,單從基督教場域分析也許是不全面的,反而可以試圖在佛教的文本里找到更為妥帖的隱喻。羊在不同的佛宗教義中也有不同的意指:藏傳佛教里羊是肉身的另一種生成,以羊為原型的神是值得信賴依托的對象,在《誤殺》里,桑坤越過李維杰一槍打死羊,羊在此時是李維杰的肉身之替;而開棺后拖出的羊尸,和棺材板上的血痕一起,則讓李維杰第一次意識到本該為表率的父親價值的坍塌,是為信賴信心之死。另外在《大日經》里有言“異心羝羊心”凡夫愚癡愚昧不解世理,禪宗又用“觸鼻羊”比喻不識法的昏昧學人,《大智度論》卷十二也說“牛羊眼,凡庸之眼”,如影片中牧羊人驅趕的羊群看到黃色汽車沉入水底,平平課堂上講述羊眼看不清東西,更如不明所以然的群眾紛紛為李維杰伸張所謂“正義”,這層意義上的“羊”之隱喻,才更加貼合“烏合之眾”的意思。
三、留白與“寓”:虛實共構的神韻和意味
有無“作為中國人的詩學體驗和敘事謀略,已經滲透于各種問題之中了(8)楊義:《中國敘事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5頁。”。在印度《誤殺瞞天記》中大篇幅描寫的維杰為看電影連家都不常回的愛好,到了中版李維杰在飯館的一段場景描述中就可透見他對無數電影熟稔于心;每次滅跡前剪接進去的數部電影的場景則被簡化為拉韞一個拉片名的舉動,任由觀眾自己想象電影與李維杰犯罪手法之間的關聯而不是強行科普;真正的埋尸所在地在片尾的蒙太奇里一再出現再無懸念,此為虛或者為留白;而比之印度版本,柯汶利中版《誤殺》添加的素察行兇其母私了與迷奸又為反殺補足了更為充分的理由;改安玖母女給維杰打電話無人接聽為李維杰給家人打電話無果后匆匆趕回,強調了作為一個父親與妻女深厚的感情,為后來的替罪做了更好的鋪墊;改米拉喪子之哀為拉韞之戾,也更加貼合犯罪片的氣氛營造。在原電影基礎上精心調整的有無聚焦,將原有的一二增加了之前所沒有的韻味,且將原有的一二之外的繁冗轉化為無。“中國古人很講究虛實共構與虛實互動互補的,換言之,他們是很重視聚焦和非聚焦、焦點和盲點的組合結構及其產生的審美效應的(9)楊義:《中國敘事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頁。”。
迷奸、視頻、未成年侵犯,以及隱藏于后的青少年成長、家庭教育問題是推理背后的文本厚度,父愛缺失和母愛局限都帶有批判的思辨,濫用私刑和毀人祖墳是權勢在法律之外的階層碾壓,而平民的自保和警員偵查的斗法,實際是兩個等級的博弈。官逼民暴,是《誤殺》呼之欲出埋藏不深的關于社會議題的“寓”;而烏合之眾對于自以為的真相的盲從與在法理前的迷茫,則是影片刻意揭開面紗的關于眾生“集體無意識”的無解之問。美國建國奠基文件《聯邦黨人文集》作者之一麥克利蘭認為縱觀古今對群眾的看法大致有二:一是將群眾視作應該被遏制的對象,用儀式化的方式壓制他們的能量;二是群眾力量為革命的力量源泉,使他們的力量從文明的消耗中解放出來。《誤殺》對這兩個觀點的態度其實是含混不明的,有思辨,有傾向,細而思之寓意深長。首先是李維杰利用群眾之“愚”引起群眾之暴力能量,用以反對獨裁的警局一方,是看到了其作為革命的力量源泉的力量;其次是李維杰父母喪生于之前一場不明原因的群眾暴亂,群眾又一次在當下的事件中因被誤導成為一場兇殺藏尸的包庇犯,則是需要被遏制被消解壓制的對象。其實“烏合之眾”的命題,本身是基于精英
—群眾的階級二分法,勒龐在其《烏合之眾》中抹殺了這種區分,認為群體本身就具有非理性特征,理性的個人一旦匯集成群就會轉變為歇斯底里的非理性群體。所以當被碰觸到“墳”這一代表鄉鄰親情人倫的標志物,麥克利蘭所謂“關鍵轉折點”的時刻就此來臨。電影里的群眾是熱情的,卻因目光短淺缺乏分辨真相能力而被鄰里感情和階級共情輕易帶偏,其后是否會對階級矛盾與專斷獨裁失去奮斗的勇氣,是否會對鄰里相處互相幫扶避而遠之,都在真相大白后眾人的沉默里走向沉重的未知。
李澤厚曾經指出,良心主義的德性根基既有承續演變的深厚傳統內涵,又有以公共理性為基礎的現代社會道德性的并置和調和。在基于中國倫理敘事與德性根基的人文遵循之下,《誤殺》跨文化改編后將原電影中犯罪懸疑與逃罪刺激置換成我國道德倫理與犯罪接受心理的“自我拯救”與“社會承擔”敘事,反映出我國電影對域外電影改編的策略,即對中國發展文化心理的社會而言的倫理美學與德行根基的指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