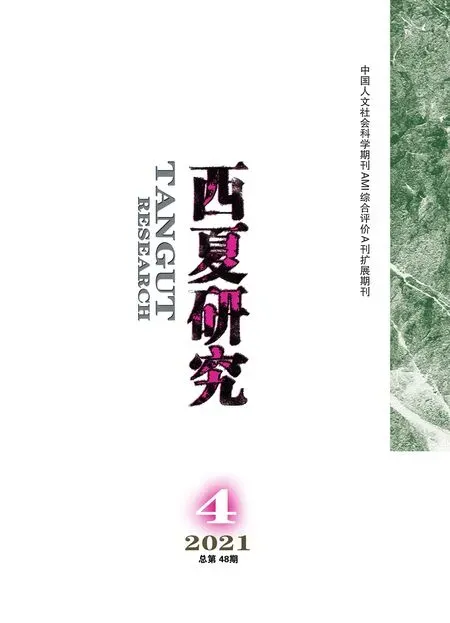從西夏文本看孫子“伐交”的本義
□彭向前 趙 軍
中國著名軍事著作《孫子兵法》西夏文刻本,為曹操(155—220)、李筌(8世紀)和杜牧(803—852)三家注本,佚名夏譯,西夏文題漢譯《孫子兵法三注》,分藏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和英國國家圖書館。俄藏乃科茲洛夫(П.К.Козлов)于1907—1908年在內蒙古額濟納旗黑水城遺址所獲,麻紙,蝴蝶裝;21.5×14.5厘米,版框17.5×12.5厘米,左右雙欄;7行,行13字,雙行小注,行21字;白口,口題西夏文“孫子”及卷次、葉次。卷中有藍絹護封。保存尚可。殘存中下兩卷6章(7—11、13),附《史記·孫子列傳》。英藏乃斯坦因(Stein)于1914年在內蒙古額濟納旗黑水城遺址所獲,其裝幀形式和行格數與俄藏一致,二者同出一本。凡兩面,另有數個殘片。殘片內容不出俄藏范圍,意義不大。兩個半葉可補俄藏之缺,為《孫子兵法三注》第六《虛實》的末尾和第七《軍爭》的開頭,在內容上恰與俄藏相銜接。綜上所述,關于這部西夏文獻的敘錄,在內容上需要改正,即以往認為殘存中下兩卷6章(7—11、13),附《史記·孫子列傳》,當改為“殘存中下兩卷7章(6—11、13),附《史記·孫子列傳》”,涉及作戰指揮、戰場機變、軍事地理、特殊戰法等方面的內容。原件照片均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刊布。[1]183-189[2]150-151
現存漢文古書及書目均不見此三家注本合刊,漢文底本久已亡佚。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出土后,學界認為對傳世版本的兩大系統武經本和十一家注本的校勘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對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譯本《孫子兵法》尚未給以應有的重視。研究表明夏譯底本與已知的各本不同,是一個我們今天不知道的“三家注本”。以往認為《孫子兵法》版本雖然繁富,但追本溯源,不外乎三大系統:竹簡本、武經本和十一家注本。西夏文《孫子兵法三注》是一個新的版本系統,可與竹簡本、武經本和十一家注本相提并論,號稱“四大系統”。
起于三國,迄于兩宋,為《孫子兵法》一書作注,代不乏人。此類注文,為好事者所輯錄而流傳至今者即宋本《十一家注孫子》①,該書為《孫子兵法》注釋之奠基者及集大成者。這十一家分別是:魏曹操,梁孟氏,唐李筌、杜佑、杜牧、陳皞、賈林,宋梅堯臣、王皙、何氏、張預。西夏文譯本《孫子兵法三注》為曹操、李筌、杜牧三家注本,在總體上是對漢文原本各個段落的解釋性翻譯,而且由于是從他者的視野來審讀的,夏譯者詮釋字詞及名物、制度,別具特色。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把該書與《孫子兵法》十一家注等注本相提并論,把它看作《孫子兵法》又一個注本,在《孫子兵法》眾多的注釋版本中占據獨特的地位。
“伐交”,即“以交伐敵”,是孫子兵學理論的重要原則之一,是孫子所闡述的對敵斗爭的一個有力手段。該詞首見于《孫子兵法》第三《謀攻》:“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轒辒,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闉,又三月而后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后世對“伐交”一詞的理解,分歧很大。有人把“交”理解為“交兵”,認為“伐交”是軍事手段;有人把“交”理解為“與諸侯結交”,認為“伐交”是外交手段而非軍事手段。后者占據上風,即大部分人都認為“伐交”就是在戰爭中通過外交手段與諸侯結盟,鞏固擴大己方陣營,分化瓦解敵人的聯盟,孤立敵人,最后迫使其屈服,以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戰爭效益。
黃樸民先生認為“外交說”純屬望文生義、主觀臆度,和孫子的本義相去甚遠,特撰文支持“交兵說”,揭示“伐交”的真實含義,即在兩軍陣勢已列、戰釁將開之際,向敵顯示己方嚴整軍容、強大實力,震懾對手,嚇阻敵人,使敵人喪失戰斗的信心與斗志,被迫退兵或無奈投降,從而以不直接進行戰場交鋒的途徑取得勝利。“伐交”類似于現在的軍事演習。其根據大致有三。一是“交”字在《孫子兵法》一書中有特定的含義,通常是指兩軍面對面相對峙,擺列好陣勢,引而不發的一種軍事態勢。如《謀攻》篇曹操注“伐交”云:“交,將合也。”這里的“將合”,指的當然是敵對兩軍“將合”,意即雙方擺列好陣勢,準備各自發起攻擊的臨戰狀態。再如《軍爭》篇“交和而舍”句下,曹操注云:“兩軍相對為交和。”杜牧注云:“交者,言與敵人對壘而舍。”可見此處的“交和”,即敵我二軍相對設營,同樣也是“對峙將合”的意思。再如《行軍》篇“交軍于斥澤之中”,此處的“交軍”,也不是兩軍進行交鋒廝殺,而是指敵我兩軍相遭遇,彼此對壘相持。二是孫子《謀攻》篇的整個邏輯關系。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描述的是一般戰爭行動的整個過程,并對不同階段的軍事斗爭原則及其優劣得失作出相應的評判。在孫子看來,通過“伐謀”(包括外交角逐)而迫使敵人屈服的,自然是最上乘的境界,故云“上兵伐謀”。如果“伐謀”不成,那就只好降格以求,進行“伐交”,將部隊擺上來,讓敵手看到我方強大的陣勢后不寒而栗、自愧不如,因而表示屈服順從。一旦列陣威懾還是沒有什么效果,敵人依舊要同我方對抗,那么就再退而求其次,只好“伐兵”,也就是野戰了,即通過野戰殲滅敵人或迫敵投降。如果敵人在野戰失敗后仍不認輸,退守堅城,負隅頑抗,那么為了達到既定的戰略目的,也只好設法攻城了。但攻城實在代價太大,純屬下策,應盡量予以避免。三是如果把“伐交”理解為外交手段,則“伐交”與“伐謀”之間實犯有同義重復之弊。通過外交手段屈敵,即運用智慧,巧假謀略以瓦解敵人之聯盟,仍屬于“伐謀”的范圍。“伐謀、伐交、伐兵、攻城”是互為關系、逐次遞進的,“外交說”會引起概念混淆、邏輯紊亂,以孫子之圣智高明,斷不會產生這樣低級的失誤。綜上所述,孫子“伐交”的本義是通過布列陣勢、顯示實力,震懾敵人而逼迫其退縮或降服。作為整個戰爭實施體系中重要的一環,“伐交”的次序和價值僅遜于“伐謀”而優于“伐兵”和“攻城”。[3]我們從西夏人的翻譯來看,“交”字沒有半點兒“外交”的含義,只有“交兵”的含義,可以從一個側面印證黃先生對“伐交”的看法,即列陣示威以迫敵屈服,而非采取外交手段。
盡管“伐交”首見于《孫子兵法·謀攻》篇的那段文字,在西夏文譯本中佚失了,但關于“交”字特定含義的描述和在其他場合對“伐交”的闡釋卻被保存了下來。以《軍爭》篇經文“交和而舍”及其注文為例:
否纅(一)候螆,
蔞繣貢:窲旺落,否旺怖;繃綆旺落,勝旺怖;苪嘻候屬窾,苪旺怖;綀嘻候屬窾,綀旺怖;舉窲候螆商絠秬譴窾,否旺怖(二)。○禔靶貢:窲碈耳篿丑城,飛倫、簕纴、瞺虙、譴紥弛,商襲趕喪,窲兩竪屬,窲候棍螆,紏槽盒盒。○呢虌貢:《成禔蒾》襲銅:“勝嘻繃綆旺屬窾,否怖。”茪減掠銅:“窲候旺魏否旺怖。舉矽勝絓嘻粄,窲綀攤誓,虃瞭膖臲。”[2]150
漢譯:
和混設營,
魏曹曰:軍門者,和門也;左右門者,旗門也;以車為營,則車門也;以人為營,則人門也;兩軍相出而面向設營,則和門也。○李筌曰:兵馬聚時,強弱、勇虛、長短、向背等,互相混合,兵力相兼,設營壘以爭勝。○杜牧曰:《周禮》中曰:“以旌為左右門,則和也。”鄭司農曰:“軍營門,亦和門也。立兩桿旗以表之,軍人出入,依次行驛。”
原典:
交和而舍,
曹操曰:軍門為和門,左右門為旗門,以車為營曰轅門,以人為營曰人門,兩軍相對為交和。○李筌曰:交間和雜也。合軍之后,強弱、勇怯、長短、向背,間雜而仵之,力相兼,后合諸營壘與敵爭之。○杜牧曰:《周禮》以旌為左右和門。鄭司農曰:“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旗表之,以敘和出入,明次第也。”交者,言與敵人對壘而舍,和門相交對也。
注釋:
(一)否纅:和混,對譯“交和”。這里對“交和”的直譯,夏譯者顯然采納了李注“交間和雜”的說法,而非曹注“兩軍相對”的說法。這里“和”為軍門,李筌的解釋是錯誤的。
(二)舉窲候螆商絠秬譴窾,否旺怖:兩軍相出而面向設營,則和門也。案本句有誤。原文《十一家注》曹注“兩軍相對為交和”,據此,“否旺(和門)”當為“否纅(交和)”之誤。
本段文字,盡管受李筌注文的誤導,夏譯文顯得有些雜亂,但通過對曹注“兩軍相對為交和”的翻譯“舉窲候螆商絠秬譴窾,否纅怖(兩軍相出而面向設營,則交和也)”,還是可以看出“交”有“設營對峙”的含義,完全讀不出“外交”的含義。
再以《軍爭》篇經文“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及其注文為例:
蹦萅繕諜矨癶吞緂窾,社兩讀翑(一)臀嘩;
蔞繣貢:萅繕落,腲謬繕怖。蹦綽娜諜矺緛吞緂窾,萅蔎兩讀翑社(二)臀帛綕?○禔靶貢:綽娜諜矺緛沏螺屬盧篎,兩讀翑社(三)八。○呢虌貢:蘦落癐簁。箿繕諜矺緛籒籑耳緂盧篎,蹦訂窲兩讀翑(四),蓯社籃。蔲矺緛吞緂窾,蓯社籃簁。[1]158
漢譯:
故不知人國謀略者,不能交兵;
魏曹曰:人國者,諸侯國也。不知敵情,豈可與人交兵?○李筌曰:知敵之情,利交兵。○杜牧曰:此者皆非。諸侯之謀先須知之,然后可交兵合戰;若不知其謀,不可戰爭。
原典:
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
曹操曰:不知敵情謀者,不能結交也。○李筌曰:豫,備也。知敵之情,必備其交矣。○杜牧曰:非也。豫,先也;交,交兵也。言諸侯之謀,先須知之,然后可交兵合戰;若不知其謀,固不可與交兵也。
注釋:
(一)社兩讀翑:字面義為“戰力結合”,即合并兵力,對譯“不能豫交”的“交”。杜注“交,交兵也”,為其所本。
(二)兩讀翑社:字面義為“力結合戰”,對譯“不能結交”的“交”。
(三)兩讀翑社:字面義為“力結合戰”,對譯“必備其交矣”中的“交”。
(四)窲兩讀翑:字面義為“軍力結合”,對譯“然后可交兵合戰”中的“交兵”。
本句經文是講“伐交”的前提,即如欲“以交伐敵”,必須先摸清對方的情況。夏譯者受杜注“交,交兵也”的影響,把本句經文“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中的“交”,翻譯為“社兩讀翑(戰力結合)”。其下曹注“不知敵情謀者,不能結交”、李注“知敵之情,必備其交矣”中的“交”,譯作“兩讀翑社(力結合戰)”;杜注“言諸侯之謀,先須知之,然后可交兵合戰”中的“交”,譯作“窲兩讀翑(軍力結合)”,大同小異,皆有“交兵”的含義,即采取軍事手段,集結兵力,示威屈敵,而沒有任何“外交”的含義。
總之,翻譯不同于閱讀,閱讀只求基本理解即可,翻譯卻必須絞盡腦汁,將原文的意思準確地表達出來。通過他者的視野,經過夏譯者的這么一番“表達”,以另一種語言形式呈現出來的《孫子兵法三注》,對今人而言,有些地方簡直就相當于“白話版”。正是從這個角度,我們說西夏文《孫子兵法三注》,堪稱《孫子兵法》十一家注外的又一個注本。無論是“設營對峙”也好,還是“戰力結合”也罷,夏譯文都表明在《孫子兵法》一書中具有特定含義的“交”,與軍事有關,與外交無關。以往學界多把“交”理解為“與諸侯結交”,有望文生義之嫌。黃樸民先生認為“伐交”即列陣示威,以迫敵屈服,類似于現在的軍事演習,而非采取外交手段,孤立敵人,以迫使其屈服,夏譯文可證。西夏文《孫子兵法三注》摻雜著西夏人自己對孫子思想的體會和見解,為《孫子兵法》訓釋材料提供了新的內容,一定程度上豐富了孫子學的內涵,對今人研讀《孫子兵法》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于此可見一斑。
注釋:
①宋本《十一家注孫子》,一般認為該書來源于《宋史·藝文志》著錄的《十家孫子會注》,由吉天保輯。之所以稱“十家”,有人認為是舉其成數而言,有人認為杜佑本不注“孫子”,其注乃《通典》之文,去掉不算,正合十家。案《通典》系典制體政書,外號“分門書”,獨《兵典》例外,并非敘述古今有關軍事組織、訓練和指揮等有關兵制的基本內容,而是以《孫子兵法》十三篇為中心,取歷代軍事成敗實例,分若干類加以敘述,如“料敵制勝”、“察而后動”、“以逸待勞”、“攻其必救”、“因機設權”、“歸師勿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