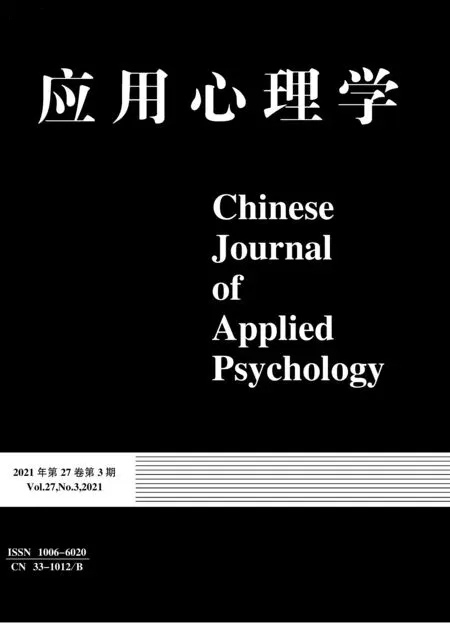從“留學熱”到“海歸潮”:海歸群體反向文化震蕩的心理與行為效應*
廖思華 丁鳳儀 徐邇嘉 胡 平 胡曉檬**
(1.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學系,北京,100872;2.清華大學心理學系,北京,100084)
1 引 言
當今新冠疫情持續肆虐全球,但是中國的疫情得到了極大的控制和極好的應對,成為目前為止唯一經濟正增長的國家,加之中國綜合國力的大幅提升和未來廣闊的發展空間,多個因素綜合起來促使了海外人才的回流現象。根據教育部發布的數據,2019年我國歸國留學人員總數為58.03萬人,回國人員數量較2018年增長11.73%。自1978年以來,我國累計出國留學人數為656.06萬人,其中86.28%在畢業后選擇回國發展。由此可見,我國海歸群體人數眾多,回歸人數呈逐年上升趨勢,加之2020年以來新冠疫情的影響,留學生在國外面臨的環境和形勢復雜多變,這意味著我國或將迎來新一輪的“海歸潮”。海歸群體通常是指從母國出發前往東道國或其他地區,停留一段時間工作或學習,最后再回到母國長期生活的群體。海歸群體人才質量較高,呈現高知化、年輕化趨勢(,2020),他們不僅擁有良好的語言能力和專業技能,更擁有國際視野,是我國以高校和民營為主的教育行業、專業服務行業不斷發展壯大、國際化趨勢加強所急需的中高端人才。因此,在理論層面上,海歸群體是多元文化的載體,對海歸群體的研究可以加深對多元文化經歷的理解,從而促進跨文化的溝通、理解和合作,并且探索其背后的內涵、機制和影響。在實踐層面上,如何助力海歸群體更好的再適應回國之后的生活和工作環境,避免因反向文化震蕩產生的負面心理和社會后果,促進海歸群體與本土群體友好相處,引導和鼓勵留學歸國人員成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生力軍,為新時代留學工作方針提供學術支持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 反向文化震蕩的概念界定和理論模型
反向文化震蕩是指個體在一個不同的文化中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后,重新適應、重新培養和重新融入自己的本土文化的過程(Gaw,2000)。它是一個多方面的具有挑戰性的文化轉換適應過程,個體通常在這期間會面臨情緒、行為和認知方面的適應問題(Szkudlarek,2010)。大量研究表明,反向文化震蕩是海歸群體回歸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環。Howard(1974)發現,由于期望差異,海歸可能會經歷收入減少、聲望和地位喪失、工作經驗不足或過時、難以找到適當的工作安置、對國內形勢失望、國內業務不足以及對同行的怨恨等負面心理現象。Chiang(2011)采訪了25位回到臺灣的年輕海歸。在采訪中,他們報告了在某些時刻經歷的典型的反向文化震蕩現象。大多數人表示,比起留在臺灣,他們更愿意搬回東道國繼續發展。Alkhalaf(2019)調查了在美國留學的沙特阿拉伯留學生,結果發現,75%的被試表示在回歸母國后經歷了反向文化震蕩,其嚴重程度與心理適應程度呈負相關,與負面情緒呈正相關。另一方面,Kartoshkina(2015)研究了美國青少年的回歸狀態,發現回歸并不只會帶來負面影響,也會帶來一種“苦中有甜”(bitter-sweet)的復合情緒,其中積極方面包括與母國的親友們相聚、與其他海歸分享出國經驗以及開發一種全新的看待母國文化的視角。Wang(2016)的研究支持了這個觀點,他們認為文化差異不僅會帶來心理不適以及文化震蕩,更能為海歸帶來一種在職場中身處“兩種文化之間(cultural in-betweenness)”的心理優勢。
反向文化震蕩是文化震蕩(culture shock)概念的拓展,兩者都用于描述個體在不同文化間切換的短期適應階段。由于個體的情緒效價隨時間發展可以畫出一條“U”型曲線,因此這一關于文化震蕩的描述被稱為U型模型(Lysgaard,1955;Oberg,1960;Furnham,2019)。Gullahorn和Gullahorn(1963)在U型模型的基礎上延伸了另一個“U”——“再入”階段,并將其定義為W型模型,用以描述個體回到母國后所需經歷的與文化震蕩類似的第二次沖擊。再入過程包括4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行前階段,通常以個體告別東道國為特征;第二階段是旅居者剛回到母國的“家鄉蜜月期”階段,海歸會體驗到回家的輕松感和成為關注焦點的愉悅感;第三階段則是反向文化震蕩階段,這是最具挑戰的階段,海歸由于告別國外的美好經歷,失去了在家鄉“明星”的角色,對本國生活產生諸多不滿,甚至想回到東道國。最后,個體逐漸重新融入母國 ,將國外經歷和國內的實踐及身份進行融合(Fanari,Liu,Foerster,2021)。
值得注意的是,支持W型模型的實證研究非常有限,并且結論大多不一致(Kim,2017),因此有學者對其提出了批評。例如,Black,Gregersen和Mendenhall(1992)指出,并不是所有海歸都會經歷反向文化震蕩的W型模型中的愉悅感階段,其中高達70%的受訪者在回歸初期就表現出了極大的不適。也有學者認為,在心理層面上,回歸過程會比出國過程更加艱難,所以不能一概而論。Furukawa(1997)表示,海歸們回歸后的6個月中可能遭受極大的情緒困擾,甚至可以達到臨床診斷標準。同時,目前大多數的反向文化震蕩研究大多在西方文化中進行,東方文化中出現了一些不同證據。Sussman(2007)表示,香港的海歸受訪者并未表現出任何關于回歸行為的負面情緒。同樣,在研究了接受西方教育的臺灣籍和斯里蘭卡籍的海歸后,Pritchard(2011)并未在被試身上發現其他學者所觀察到的回歸創傷,而是一些社會政治方面的認知失調。W模型是否具有跨文化一致性,依然需要進一步的討論,但我們可以確認的是,當海歸回到母國,面臨的困難和挑戰是真實存在的。
3 反向文化震蕩的心理與行為效應
3.1 海歸群體面臨的心理挑戰
全球化的持續深化促使越來越多的群體,比如企業外派員工、少數族裔移民、中外留學生群體等,在自身的文化認同體系中整合兩種或者更多的文化元素(Arnett,2002),進而引發由多元文化經歷而導致的復雜而動態的心理與行為后果(胡曉檬,韓雨芳,喻豐,彭凱平,2021)。在認知方面,有被試報告出國經歷讓他們對母國(美國)文化產生了批判的看法(Kartoshkina,2015;Dettweiler et al.,2015)。Wielkiewicz 和Turkowski(2010)發現,在國外學習的學生對自己的家鄉文化產生了更多的懷疑。當他們獲得了不同于本國的新的價值觀和信仰時,可能會產生焦慮感和壓力感。關于亞洲留學生的研究發現,由于自身與父母的世界觀存在較大分歧,在留學期間獲得的獨立性和孝順父母的內在要求之間的矛盾成為了家庭緊張和個人壓力的原因(Butcher,2002)。在這種情況下,個體同時還面臨著旅居者身份和本民族文化身份兩種文化身份認同的矛盾感受,這也是造成主觀心理痛苦的原因之一(Ai & Wang,2017)。
在情緒適應方面,Uehara(1986)將疏離、冷漠、失落、迷茫和孤獨的感覺列為了可能的情緒表現。Butcher(2002)認為再適應是一個悲傷的過程,這種悲傷源于對歸屬感的渴望,其中既包括對祖國文化的依戀,又包括對于具體關系的歸屬需要。此外,許多學生回國后在訪談中還談到了被剝奪感和心理緊張(Allison,Davis-Berman,Berman,2012)。Kartoshkina(2015)發現,被訪者在描述回歸的負面感受時報告了由于告別國外伙伴而產生的“喪失感”。最近一項追蹤調查表明,留學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在回歸后的第一個月達到頂峰后開始下降,在第4個月時,心理健康水平會達到最低谷(Dykhouse & Bikos,2019),這說明不良的再適應過程會給海歸帶來相當程度的心理困擾,也為W模型提供了實證支持。
在社會適應方面,個體從東道國回到家鄉,不僅是地理遷移,也是社會關系網絡的告別與重建,更是重新認識和適應家鄉文化的過程,因此面臨著巨大的心理挑戰。在參與了為期6個月的格陵蘭島探險項目后,英國學生們普遍經歷了無法與身邊的人交流、感到沒有人理解自己、無法與同輩群體做出相似的行為從而融入學校和家庭環境,以及思念旅程中的朋友的過程。他們也感到自己的經歷極為獨特,無法用語言描述,以至于無法與沒有相似體驗的家人和朋友進行交流,同時又認為沒有人對自己的經歷感興趣(Allison,Davis-Berman, Berman,2012;Pitts,2016)。這種分享和溝通匱乏的社會后果之一是關系維持的困難(Kartoshkina,2015;Butcher,2002),家人、朋友可能會期待旅居者表現出“正常”的出國前的行為,而不接受其新的行為(Sussman,1986),這反過來可能進一步加劇個體對回歸生活的融入困難,從而進一步產生負面情緒。在對中國海歸青年教師的研究中發現,中國高校海歸不僅面臨著一般性的適應問題,同時也面臨著對于缺乏支持性的組織文化、缺乏知識共享的氛圍、低工資、繁重的工作量和組織文化的適應問題(Li,Croucher,Wang,2020)。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個體在回歸時似乎都會面臨社會文化層面的心理挑戰,例如孝順父母、缺乏組織支持等。不過,對于中國的海歸群體而言,這些文化不適是否受到東道國文化的調節影響(比如北美、西歐、東亞、大洋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還是所有文化共享的過程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新冠疫情以來,海歸群體作為跨文化的旅居者,在回國過程中和回國后遇到了比以往更大的困難。首先,許多國家爆發了大量針對亞裔的歧視和仇恨犯罪,使得亞裔群體或者亞洲人遭遇了比其他族裔群體更多的心理健康問題(Wu,Qian,Wilkes,2021)。同時,全球96%的國家頒布了旅行限制和禁令,國家間航班銳減(UNWTO,2020),海歸的回國之旅變得非常困難,因此,挑戰在行前階段就開始了。第二,海歸在疫情期間回國通常是出于安全考慮,因此需要中斷學習或工作。回國后,國內外防疫政策的差異、新的社會規范的要求等,不僅與海歸記憶中的家鄉產生了落差,也與其長期居住的國外形成強烈對比,在極端情況下,海歸群體甚至因為從高風險國家返回而受到歧視。多重差距共同作用于海歸群體,會使其產生更大程度的反向文化震蕩。已有實證研究發現,疫情期間由于學業中斷回到美國的留學生在回家27天左右時就感到了反向文化震蕩和再適應壓力,而這時的壓力能夠顯著預測6個月后的孤獨感和新冠疫情相關的壓力(Fanari & Segrin,2021)。最后,疫情造成了全球經濟下行,不確定性加劇(Ozili & Arun,2020),這對本就處于就業壓力中的海歸來說,也是較大的震蕩。
3.2 反向文化適應的影響因素
3.2.1 個體差異
早期研究發現女性比男性報告了更高的回歸滿意度(Rohrlich & Martin,1991);一些研究者認為男性與女性在再適應問題上面臨的問題、對問題的看法和采取的策略是沒有顯著差異的(Cox,2004;Dettweiler et al.,2015;Sussman,2001),但也有相反的發現:相比男性,Wielkiewicz和Turkowski(2010)認為女性留學生處理焦慮的能力更弱,回歸后感受到的人際壓力和負面情緒都更嚴重,Fanari等人(2021)的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年齡因素方面,年齡與回歸后的社交困難和抑郁情緒呈顯著負相關,換言之,海歸的年齡越大,經歷的適應痛苦越小(Cox,2004;Kartoshkina,2015;Fanari,Liu,Foerster,2021)。但也有年齡與再適應沒有顯著相關的證據出現(Uehara,1986;Gray & Savicki,2015)。婚姻狀況也是值得考慮的影響因素之一。Cox(2004)發現,海歸群體中單身者比已婚者報告了更多的抑郁情緒和更少的家鄉文化認同,也就是說單身者回到家鄉后產生了更多的文化不適。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的再適應研究選取的都是方便抽樣的同質性的樣本,并未平衡被試的人口學特征,這可能是造成研究結果不一致的原因之一。另外還有一些人口學變量,例如社會階層和收入水平等,盡管在研究中被當作控制變量,其作用卻并未被充分討論,在未來的研究中需要研究者收集更多的證據。
人格特征和適應策略也是研究者關注的個體差異變量。Feldman(1991)提出,自我效能感作為個體回國后克服困難能力的重要指標,能夠幫助個體減少再適應過程中的困難。具有相似作用的是個體的堅韌性,即在面對困難挫折時保持自尊和平衡的能力。同時,以問題為中心的應對策略相比以情緒為中心的應對策略,由于能夠直接改善外部環境和移除威脅因素,因而能對回國者的再適應有更實際的幫助。Vidal,Valle,Aragón和Brewster(2007)通過郵寄調查問卷的方式,考察了一家西班牙公司外派員工回歸后的適應過程,結論支持了這一觀點,研究發現,自我效能感與員工回歸2個月和9個月后的適應程度均呈顯著正相關。Kranz和Goedderz(2020)在討論個體文化認同形成與反向文化適應問題之間的關系時,將大五人格作為控制變量,發現五個維度中僅有神經質與再適應問題顯著正相關。自我表露作為一種積極應對再適應溝通困難的策略,也被認為是反向文化震蕩和再適應的重要因素,誠實維度正向預測了反向文化震蕩的四個維度中的三個:文化、人際和情感距離,表明個體在自我表露中越誠實,他們經歷的反向文化震蕩越少。這可能是由于真誠的自我表露可以讓回歸者真實地談論和面對回國后的改變和感受。意圖維度則正向預測了反向文化震蕩階段和再適應階段面臨的困難程度,也就是說個體越是有意地自我表露,在這兩個階段面臨的困難越少。此外,深度和效價維度揭示了自我表露可能的負面影響:在模型中負向預測了情感距離和人際距離(Fanari,Liu,Foerster,2021),但這項研究并未將自我表露的互惠性維度納入考慮,因此在這一變量的解釋力上可能有所欠缺。
3.2.2 海外經歷
多元文化經歷的廣度和深度以及個體對于經歷的積極或消極評價(Maddux,Lu,Affinito,Galinsky,2020),對于個體的再適應的過程會產生影響。留學時間是個體再適應困難的重要預測變量。Wielkiewicz 和Turkowski(2010)在對669名回國留學生的調查中發現,留學三周及以下的人在反向文化震蕩量表上的得分明顯低于在國外學習一個學期或更長時間的人,說明再適應問題與在東道國逗留的時間呈正相關(Kranz & Goedderz,2020)。最近的一項追蹤調查顯示,對東道國的社會文化適應是心理健康水平下降速度和隨后回到基線的速度的重要預測因素。更適應東道國文化的人在回國后經歷了更多的心理困難,并且需要更長的時間回到基線(Dykhouse & Bikos,2019)。另一方面,留學生在國外期間與客國人民的交流更頻繁時,回國后面臨的適應困難可能越大(Rohrlich & Martin,1991)。Gray 和 Savicki(2015)發現,留學生對于自身留學經歷評價越積極,就越有可能經歷更高程度的再適應困難,研究結果支持了過多卷入東道國文化的旅居者會在返回時面臨更多的適應困難的觀點。另外,Cox(2004)在對101名去往不同國家的海歸的調查中發現,個體在國外時與家人溝通的頻率和滿意度會影響回國后的適應情況。個體在國外期間,與家人溝通滿意度和抑郁顯著負相關,但朋友關系與再適應的相關則不顯著。臺灣和斯里蘭卡的留學生在訪談中表示,由于回歸后得到了家人和朋友的理解,因此適應過程非常順利(Pritchard,2011),這表明旅居者在國外時和回國后家人朋友的社會支持都是其良好適應的重要推動因素。
3.2.3 文化認同
文化認同是影響再適應的重要方面,可以分為對東道國的認同和對母國的認同。根據對兩者不同的認同程度,Sussman(2000)提出了文化適應的四維度模型。一個人對自身文化認同改變的意識,可能是經歷這些變化的個人痛苦的來源,那些報告在國外期間與母國聯系減弱,或是與東道國關聯增強,產生身份轉換的人在回歸時會經歷更多的不適應;反之,與母國聯系增強,提升了跨文化世界觀的個體經歷的不適應則更少。隨后的實證研究證明了這一觀點:對44名回歸美國的經理的分析表明,對東道國文化認同最多、心理準備最少的人在回國后經歷了最多的心理苦惱,偏愛本國文化的海歸比融入東道國的海歸遭遇的心理困難更少。由于海外經歷導致的更普遍的自我認同的變化也與個體的心理困擾水平顯著相關(Sussman,2001),Cox(2004)提出了四種跨文化認同形成的模式:偏愛母國、偏愛客國、整合和分解。在實證研究中,被歸類為整合和偏愛本國的回歸過程比被歸類為分解和偏愛客國的回歸過程更容易重新適應,表現為整合組和偏愛本國組的抑郁得分較另外兩組更低,社會困難得分也更低。研究者認為最健康的模式是海歸在保持與本土文化聯系的同時熟練掌握東道國文化。Kranz 和Goedderz(2020)參照埃里克森的自我認同模型,研究了再適應問題與母國文化身份認同的關系。結果顯示,再適應問題與對母國文化身份認同的承諾維度呈負相關,與探索維度呈正相關,與反思維度的相關程度最高。對母國文化身份認同處于暫停狀態的參與者報告了最多的重返問題,而處于關閉狀態的參與者報告的問題最少,處于完成和擴散狀態的參與者報告的重返問題位于兩者之間。
3.2.4 文化距離
文化距離指的是兩種文化之間價值觀、生活習俗、社會規范和地理要素等方面的差異大小,測量指標可以分為個體感知文化距離和國家間文化距離指數(English,Zhang,Tong,2021;Babiker,Cox,Miller,1980)。Presbitero(2016)在研究中將被試主觀感受到的母國與旅居國之間的文化距離納入了回歸模型中,但這一變量對于心理和社會再適應的情況都無顯著影響。另一種更加客觀的方式則是使用公式計算國家間的文化距離,例如Gray和Savicki(2015)在研究中基于霍夫斯坦德的工作,計算出了留學生旅居國與母國之間的文化距離變量。他們發現,文化距離在留學經歷積極評價對再適應困難的影響中起到了調節作用,表現為在高文化距離組,無論經歷評價如何,再適應困難都較高;在低文化距離組,留學生對經歷的積極評價越高,面臨的再適應困難越低;對于在距離美國中等文化距離的國家留學的學生來說,隨著評價的積極程度的增加,再進入的困難也隨之增加。這似乎表明,引入文化變量后,原本難以解釋的結果變得更加清晰合理,提示研究者未來需要多從文化背景變量出發,例如個體主義集體主義、文化松緊性等,考察現有變量對于再適應的影響機制,加深對于再適應問題的理解。
3.3 反向文化震蕩的雙刃劍效應
3.3.1 消極心理效應
從消極的角度來看,Seiter 和 Waddell(1989)發現反向文化震蕩與一般人際關系滿意度之間存在負相關。當一個人或一個群體經歷高度的反向文化震蕩時,建立認同感和整體生活滿意度的可能性很低,良好應對日常社會生活壓力的可能性也很低(Presbitero,2016)。Gaw(2000)對美國留學生的重返經歷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經歷高反向文化震蕩的學生比低反向文化震蕩的學生更容易報告個人適應問題,其中包括疏遠、無歸屬感、孤獨、難以交朋友、自卑感、抑郁和一般性焦慮和害羞問題(包括社交害羞和演講焦慮)。報告更高適應困難的美國留學生會有更多的消極情緒,表明適應困難的留學生可能會有一個情感上重新追尋與母國文化依戀的過程(Gray & Savicki,2015)。一項對日本海歸的研究發現,那些適應不良的人感受到了更多的不被社會接納的感覺,適應良好的個體在開放問題中提到了更多接納自己的人(Yoshida et al.,2009)。Presbitero(2016)考察了文化震蕩和反向文化震蕩對個體適應的影響,發現被試的反向文化震蕩得分與心理和社會適應都有顯著負相關。但是,文化智力,即人們在與不同文化打交道時,采取有效的措施以適應新文化的能力(高中華,李超平,2009)可以作為調節變量減輕反向文化震蕩對個體心理和社會適應的負面影響,表現為與文化智力低的個體相比,文化智力高的個體的反向文化震蕩對心理適應和社會文化適應的影響都被最小化。
3.3.2 積極心理效應
文化震蕩是在另一種文化中理解、生存和成長的嘗試。雖然文化震蕩通常與負面后果有關,但它可能是文化學習、自我發展和個人成長的一個重要方面(Adler,1975),反向文化震蕩亦是如此,我們需要辯證地看待這一問題。研究發現,反向文化震蕩和文化再適應可以成為提高個體對母國文化認知和自我意識的途徑。留學生通過出國的經歷和回歸再適應的過程加深了對自身以及本國文化的理解(Uehara,1986)。同時,旅居者從國外返回時,通過與家人和朋友的接觸得到撫慰,從而變得更加感恩(Kartoshkina,2015)。文化適應和再適應的經歷也會使得海歸們更加客觀地看待事物,辯證地看待本國文化和外國文化的關系。在生活中,他們也能采取積極寬容的態度對待他人(Kartoshkina,2015;Li et al.,2020)。留學經歷帶給人們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比如建立更加多元化的視野、增加人生閱歷、擴大人生格局、提高思辨能力、積累社會資本、提升辯證思維(Hu et al.,2021)等等。
3.4 如何應對反向文化震蕩?
從海歸群體自身來看,充分的心理準備可以降低回國后面臨的再適應困難(Susaman,2001)。因此,對有回國意圖的海歸來說,參與回國前培訓非常必要。在國外留學期間,個體應當更多使用現代科技與母國加強聯結,時刻關注母國發生的變化,形成對家鄉的客觀認知和現實期待;也應更多地實時分享自己的經歷,加強與家人和朋友的相互了解。個體還應積極探索如何將母國和東道國的經歷融會貫通,產生新的火花和思想共鳴。在回國之后,個體應當正確認識自身和母國文化的變與不變,以客觀開放的態度接受當前存在的問題,給自己一段適應期和過渡期。同時也要以積極的態度面對現實和解決問題,例如主動解決矛盾、維護人際關系、尋找分享經歷的機遇、參加再適應課程等等。
從外部支持的角度來看,海歸的家人和朋友應當充分理解海歸群體在回國再適應時面臨的困難,并為其提供良好的物質和心理支持,形成友好融洽的氛圍,讓其體驗到家庭的溫暖和歸屬感的滿足。海歸團體、主管部門等應當適當組織團體輔導活動、互助會活動,邀請海歸分享經驗、相互交流,讓其在習得再適應應對策略的同時,也在團體中降低孤獨感,實現自我價值。即時充分的就業信息、心理援助渠道等也應通過微信公眾號,微博等平臺推送給海歸群體。最后,在社會層面,應當積極宣傳兼容并蓄的中國傳統文化,集體主義精神和社會主義文化,形成接納海歸氛圍的同時,也讓海歸群體能夠辯證地看待自身的多重身份,并最終形成整合的文化身份認同,將在跨文化環境中培養的能力良好運用于當下情境中,并為將來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心理基礎。
4 局限與未來展望
以往研究存在一些局限與不足。首先,反向文化震蕩的構念在不同研究中操作不一致,導致研究者無法明確研究結論、比較研究結果、得出聚合證據、提煉理論模型;其次,研究對象的身份各不相同,不僅有留學生、公司外派員工,更有回歸的移民及其后代等,這導致了分化的結論;再次,量化研究中缺乏實驗證據,難以做出因果推論和干預研究;最后,如何將海歸研究本土化是一個關鍵問題。
目前國內外心理學領域對于海歸群體的研究尚在起步階段。展望未來,仍有許多重要的研究問題值得關注:生物因素方面,多元文化經歷帶來的心理和行為改變具有哪些認知神經基礎;個體因素方面,海歸群體的動機、能力、思維、人格、文化智力等因素究竟如何影響文化再適應過程,如何挖掘個體的積極心理資源來應對反向文化震蕩;社會因素方面,西方社會和中國社會復雜多變的國際關系如何影響海歸的文化再適應過程,政府部門或者地方機構如何提供組織文化層面的指導和支持來幫助海歸群體提升反向文化適應。針對海歸群體的心理學研究仍是一片“藍海”,擁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和巨大的應用價值。譬如在理論層面如何構建中國留學生反向文化震蕩的理論模型以及在方法層面如何將行為實驗法結合追蹤研究、質性方法、大數據、計算模型和認知神經科學等技術手段,提供交叉整合的科學依據是值得未來研究探索的前沿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