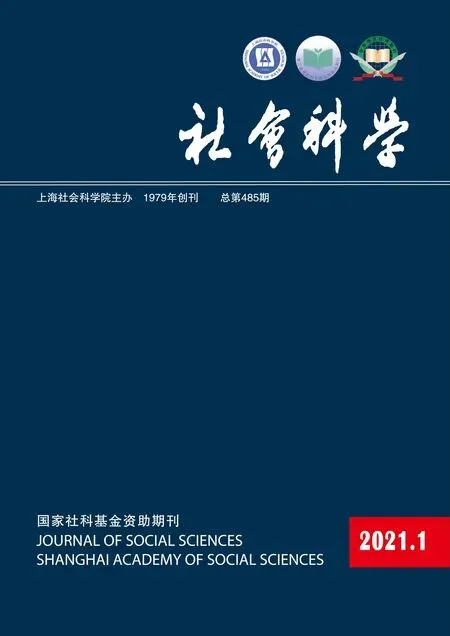“互聯網+”時代勞動關系 變革的法理分析和立法回應*
——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定性釋疑
鄭文睿
一、問題的提出: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的定性之爭
判斷一個案件是否屬于勞動爭議案件以及是否應受勞動法的調整,主要有兩條研究進路較為常見。一是傳統的研究進路,從“關系”定性的角度出發,對系爭關系是否屬于勞動法意義上的勞動關系進行討論(1)參見史尚寬《勞動法原論》,正大印書館1978年版,第2頁;謝懷栻、陳明俠《勞動法簡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頁。;二是近些年來興起的研究進路,從“主體”定性的角度出發,對系爭案件一方主體是否屬于勞動法意義上的用人單位或勞動者進行甄別(2)參見黎建飛、曾丙健《“用人單位”主體資格辨析——兼議若干新型用工主體是否是用人單位》,《齊魯學刊》2019年第1期;田思路、賈秀芬《契約勞動的研究——日本的理論與實踐》,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0—97頁。。兩種研究進路的區別僅在于判定的技術手段上,至于在價值判斷結論上并沒有差異也不應當有所差異。畢竟,如果最終判定系爭關系屬于勞動法所調整的勞動關系,那么就必然會涉及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兩方主體;如果判定案件一方主體屬于用人單位或勞動者,那么所涉及的關系就會指向勞動法所調整的勞動關系。
勞動法起源于200年前的工業社會,最適合也最能夠順暢地適用于礦山、井下等作業的勞動者。然而步入“互聯網+”的新時代后,勞動法在應對新型系爭案件時,卻顯得左支右絀、自顧不暇,無論是“關系”定性還是“主體”定性的研究進路,都不能給出一個圓滿妥當的解釋,甚至不同討論者關于“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是否屬于勞動法所調整的勞動關系”的價值判斷結論及其理由還相互矛盾。即,在勞動法規范體系和框架內,有的學者認為既有的從屬性理論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和彈性,能夠用來解釋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3)謝增毅:《互聯網平臺用工勞動關系認定》,《中外法學》2018年第6期。從而將其囊括進勞動法意義上的勞動關系范疇,但有的學者卻認為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因欠缺從屬性(4)王天玉:《網絡勞務是對勞動法的挑戰嗎》,《中國法律評論》2018年第6期。不宜認定為勞動法意義上的勞動關系(5)王天玉:《基于互聯網平臺提供勞務的勞動關系認定——以“e代駕”在京、滬、穗三地法院的判決為切入點》,《法學》2016年第6期。。出現這種狀況的實質是勞動法以有限的規則應對無限的世界所遭遇的茫然懵懂和措手不及。對此,要么需要從“關系”定性的角度,要么需要從“主體”定性的角度作出回應。進而,問題就可以被轉化為: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是否屬于勞動法意義上的勞動關系(“關系”定性路徑),或者互聯網平臺及平臺勞動者是否屬于勞動法意義上的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主體”定性路徑)。如果屬于,那么如何給出具有足夠說服力的理由闡明勞動法為什么能夠吸納和包容新型用工關系;如果不屬于,那么如何保護平臺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更為妥當。為減輕論證負擔和避免重復繁瑣,本文主要以滴滴公司與滴滴司機為例進行說明,相關的結論同樣適用于其他交通出行、家政服務、美容美甲、外賣送餐、快遞閃送、主廚料理等等新經濟帶來的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糾紛。
二、勞動關系理論在互聯網平臺用工中面臨的挑戰
新就業形態時代、數據時代、信息時代已經到來,目前主要在勞動密集型的服務行業和領域表現最為明顯。受科技驅動,為客戶回應個性化定制、滿足多元化需求、提供體驗式服務,此種服務與需求的深度融合形成了“互聯網+勞動”的有別于傳統勞動關系的新型用工模式。該新型用工模式“通過將之前未能有效利用的資產以共享的形式盤活起來,使整個經濟煥發出新的活力”(6)[日]鈴木貴博:《“AI失業”時代生存指南:未來5年在職場會發生什么》,李力豐譯,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15頁。。然而,早于“互聯網+勞動”出現的《勞動法》顯然并沒有做好應對新時代的準備,其無法預見到今天已經屢見不鮮的新型用工模式,更無妥當的協調策略來保障平臺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再加上《勞動法》本身就對其所調整的勞動關系有專門的限制與形塑,并不是所有的勞動關系都受《勞動法》所規范,因此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的定性到底如何,到底能不能適用《勞動法》來調整,均存在著極大的不確定性。
其中最突出的表現是AI算法擊穿《勞動法》中的勞動報酬、勞動時間、安全衛生、社會保險等規定,有意無意地實施著另外一套勞動力管理體系。算法管理這種有別于傳統勞動關系下的雇主對雇員直接下達指令管理員工的方式,為勞動用工帶來新的管理模式變化,因此牛津大學法學院Jeremias Adams-Prassl教授甚至將工作中的算法稱為“隱蔽雇主”,從而形象地表明新經濟業態中的平臺勞動者將面臨著更加嚴苛的、無形的“禁錮”。平臺用工需要憑借算法管理來安排指令、發布任務、執行規則,為勞動關系領域的人力資源管理帶來優化配置和高效便捷。這種科技的初衷是好的,使得算法通過智能調配能力,達到最優運力調度。不過,算法是建立在大數據的基礎上,這種“數字邏輯”關心的是經濟效益。當算法介入勞動領域,平臺勞動者就會完全被系統與時間支配,也意味著獎勵與懲罰規則一并進入到整個管理系統之中,開啟新的勞動控制模式。這種勞動控制模式一旦運行,平臺勞動者就會被算法困在系統中,陷入一個無法自拔、無限循環的“惡性”無底洞。因為在平臺經濟中,AI算法會精確地計算出平臺勞動者需要在限定的勞動時間內所應完成的勞動任務量,而且這種勞動任務量是多數普通勞動者在正常勞動里做不到的。于是,為追求平臺的經濟效益和服務效果,系統就會不斷地縮減勞動時間、增加勞動任務量。當系統第一次縮減單位勞動時間后,循環就已注定,平臺勞動者越按照平臺算法及獎懲規則抓緊時間完成勞動任務,依據大數據計算出的平臺勞動者所需要完成工作量的時間越短,就會更加縮短平臺勞動者的單位勞動時間,周而復始,循環往復。如果從《勞動法》的視野來觀察,算法以超過普通勞動者的一般勞動能力為基準設置考核標準,平臺勞動者就不可避免地會付出損害身體健康的代價,在算法面前,作為“人”的平臺勞動者被異化成了工具。技術的進步,不僅沒有帶來人類的解放,反而給平臺勞動者帶來了更加沉重的枷鎖,“視人為人”倒退為“視人為物”。這是《勞動法》所不能忍受的,畢竟“道德”和“健康”兩個關鍵詞貫穿了《勞動法》的始終。勞動法的起源就是要縮短勞動時間以維持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和保障勞動者的身體健康,但算法管理的結果是不斷增加勞動時間,突破了“道德”和“健康”的底線,也更加違背勞動法的初衷。
在算法管理之下,根本不需要平臺勞動者知曉誰是雇主,只要平臺派單、有工可做就好。但麻煩在于一旦出現事故,相關案件則難以處理,平臺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更難以得到保障。央視的《今日說法》欄目曾經報道一起“誰是雇主”的典型案件。一名滴滴代駕司機王永康在代駕過程中沖進路邊水塘身亡,王永康的家人由此陷入與包括滴滴在內的四個被告公司的紛爭之中。第一個被告公司滴滴公司明確以與王永康沒有任何勞務關系為由拒絕賠償。第二個被告滴滴接單平臺的實際運營方是杭州快智公司,第三個被告是與包括王永康在內的滴滴平臺的司機們簽訂過勞務合同的江蘇邦芒公司。這兩個被告與第一個被告滴滴公司一樣,均不認可自己是王永康的雇主,也拒絕賠償。后來又增加了第四個被告浙江外企德科人力資源有限公司,這家公司原本將王永康轉給第二個和第三個被告,但還沒來得及履行交接手續等,所幸該公司主動承認與王永康之間存在勞務關系,并提出60.5萬元的賠償方案,最終與王家人達成調解。代駕司機王永康明明在滴滴平臺上接單做業務,付出勞動,因勞動導致死亡卻不清楚到底為哪個雇主工作,1個案件至少涉及江蘇、浙江2地的4個被告。這在工業社會時代傳統一對一的勞動關系領域中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卻在新就業形態時代、數據時代、信息時代真實地發生了。
諸如此類現實發生的鮮活案件,彰顯著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定性的難度,那么“我們是否對于迎接新變化做好思想和制度上的準備”(7)騰訊研究院:《互聯網+時代的立法與公共政策》,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4頁。?這就向立法者和裁判者提出了時代之問。對于立法者而言,2011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雖然已經形成,但當時并沒有出現平臺經濟這一新生事物,以至于時至今日,與平臺相關的法律付之闕如,亟待補齊法律短板。對于裁判者而言,缺乏法律依據的指引,司法裁判對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的定性毫無頭緒,并無一個具有規律性和可操作性的確定方案。下一步立法和司法必將結合實踐經驗對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定性問題作出妥當的時代回應。
三、勞動關系理論的失能與可能
鑒于現實中算法管理及其引發的雇主困境似乎避開了《勞動法》,將傳統勞動關系下付出同樣勞動、做著同樣事情的平臺勞動者剝離了勞動法的保護,為此,針對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的定性,亟待學理上給出圓滿的解釋,并獲得大多數人的理解與認可。然而,不同的討論者圍繞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定性問題展開的討論,并不能實現圓滿解釋的目的,相關爭議繼續延續至部門規章的制定過程之中,呈現出“分歧大于共識”的狀態。
(一)學術理論分析的困境:勞動關系還是其他關系
判斷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是否屬于勞動法意義上的勞動關系,首先需要進行問題定性,才能更好地展開有針對性的研究。由于涉及到互聯網平臺與平臺勞動者的切身利益,因此本問題屬于典型的法律問題中的價值判斷問題。其次,回答價值判斷問題,需要在遵循既往價值共識的基礎上進行討論,方能達成最大限度的理解與共鳴。從勞動法學界既往的價值共識出發,關于勞動法意義上勞動關系的判定標準為“從屬性”(8)一般認為,判定勞動法意義上勞動關系的“從屬性”包括“人格從屬性”與“經濟從屬性”。當然,除了這種兩分法之外,還有學者提出了三分法,即在“人格從屬性”與“經濟從屬性”之外再加上“組織從屬性”,但也有學者認為可以將“組織從屬性”包含在“人格從屬性”之中。因此關于從屬性的二分法或三分法在價值判斷結論上沒有本質差異,僅僅是解釋選擇的差異而已。。“從屬性”標準是大陸法系國家的用法,在英美法系國家里使用的是“控制”標準而非“從屬性”標準。這屬于解釋選擇問題,二者其實大同小異,基本內涵大體相同。具體關于“從屬性”判斷標準,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的理論學說中亦相類似(參見下表)。
從上表來看,理論學說大體上認為從屬性標準包括“人格從屬性”與“經濟從屬性”,雖然還有學說提出再加上“組織從屬性”,即雇員被納入雇主的組織之中成為其中一員,但“組織從屬性”往往可以將其包含在“人格從屬性”之中,因此關于“從屬性”標準的二分法或三分法在價值判斷結論上亦沒有本質差異,依舊僅僅是解釋選擇的差異而已。無論采取哪種從屬性判斷標準,只要繼續沿用傳統的“從屬性”理論來判定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性質的話,就可能會面臨著解釋的困境。
第一個解釋困境在于勞動關系本身。從實踐表現來看,互聯網平臺公司反對其與平臺勞動者之間成立勞動法意義上的勞動關系。為乘客提供出行服務的行為,在傳統生產方式下,出租車公司與出租車司機之間可能能夠形成勞動法意義上的勞動關系。然而“互聯網+”出現后,滴滴公司與滴滴司機之間的關系卻被打上了問號。滴滴司機做著與出租車司機同樣的事情,但滴滴公司認為其僅僅是為滴滴司機和有需求的乘客之間搭建信息平臺,從而屬于平等的民事關系,不承認其與滴滴司機之間的關系定性是勞動關系(10)甚至滴滴公司在相關APP上發布的《專快車服務合作協議》第9條最后一款明確標明“本協議正文及附件受合同法等民事法律約束。我司與所有提供網約車服務的司機僅存在掛靠合作關系,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勞動關系,不適用《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社會保險法》《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互聯網平臺公司的這種觀點和做法具有一定的道理,也確實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解釋系爭關系,進而為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到底定性為民事關系還是勞動關系增添了區分的難度。
第二個解釋困境在于勞動關系主體。傳統勞動關系具有明確的“一對一”指向(即一個用人單位僅僅對應著一個勞動者),而非表現為“多對多”“一對多”“多對一”的特性。但在“互聯網+”的外衣覆蓋下,模糊了這種對應指向性,誰是雇主成為核心爭議的焦點。平臺勞動者到底是在為互聯網平臺提供勞動,還是為有需求的客戶提供勞動,抑或者是為自己提供勞動?答案如果是均為三者提供勞動,那就與傳統勞動關系中為“單一”雇主提供勞動的常識和認知明顯不符;答案如果僅僅是為互聯網平臺提供勞動,那就除了勞動關系之外還必然存在民事關系的定性爭論;答案如果僅僅是為有需求的客戶提供勞動,那勞動法將對此行為漠不關心,因為勞動關系的雇主一方必須是組織體(用人單位)而非個人,即使同一次出行的客戶有多人,那也是個人(的集合)而非組織體;答案如果僅僅是為自己提供勞動,那平臺勞動者自己就成為了雇主,在勞動法的理論上,只有為他人提供勞動的才成為勞動者,勞動法不關心雇主的勞動權益保障問題;答案如果是均不為三者提供勞動,那說明平臺勞動者像農民那樣沒有勞動所指向的“單位”相對方,從而面臨著缺失雇主主體并且不能適用勞動法的困境。
第三個解釋困境在于勞動關系內容。一是勞動報酬從過程化轉向結果化。傳統勞動關系與勞動過程相勾連,不管勞動結果如何,即使生產出來的產品賣不出去,即使打開門經營沒有一個顧客來光臨,只要勞動者完成勞動行為,就應當獲得相應的勞動報酬,但在“互聯網+”的背景下,卻以平臺勞動者的變現或現金流(即勞動結果)為前提來支付平臺勞動者的報酬。相當于用勞動者自己的勞動所得來支付其勞動報酬,而這正是勞動法最為忌諱和禁止的做法。二是勞動時間從集中化轉向碎片化。“互聯網+”勞動關系不再像傳統勞動關系那樣實施八小時工作制,而且工作時間相對自由。勞動法標準工時制禁止996,但卻可能無法禁止平臺勞動者自愿駕車載客實行996,從而難以實現勞動法通過工時控制來保障勞動者健康的目的。三是勞動地點(場所)從有限化轉向無限化。“互聯網+”勞動關系不再像傳統勞動關系那樣,勞動者無需集中在固定場所工作,由此從空間上擊穿對平臺勞動者的安全衛生保障義務。因為互聯網平臺縱使能夠采取措施保障自身的辦公大樓及工作場所的安全衛生,也難以保障每位平臺勞動者在任意道路上的行車安全。四是社會保險從實體化轉向虛置化。互聯網平臺堅持其與平臺勞動者屬于平等的民事關系而非勞動關系,于是,不提供任何保險、要求平臺勞動者自己繳納社會保險費、為平臺勞動者購買商業保險等就成為實踐中架空社會保險的多項選擇和必然做法。
難怪連黑格爾都曾感慨“最捉摸不定的首推‘關系’”(11)[美]威爾·杜蘭特:《哲學簡史》,梁春譯,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90頁。。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是否屬于勞動法意義上的勞動關系面臨著解釋困境,但其實在某種角度上,也反映出部分討論者似乎想證成“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屬于勞動法意義上的勞動關系”的傾向,不然直接作出其他關系定性即可,更何況其他關系定性也沒有形成共識。既然沒有確定性的定性學理討論結果,考慮到平臺勞動者付出勞動、接受管理、獲取報酬、養家糊口的多種事實,就不能徹底或完全排除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屬于勞動關系定性的可能,只不過需要對既有的勞動關系理論適當地改造重塑,以增強勞動關系的解釋力,對此后文將予以詳述。此外,在勞動用工中,傳統勞動法著眼于雇主對雇員進行指揮、監督、管理的從屬性支配,但若能夠洞悉新經濟背景下算法管理對平臺勞動者的派單和指令依舊體現出從屬性特征的現實表現,就為適用勞動關系理論奠定可能性。
(二)制定部門規章的波折:勞動關系以及其他關系
《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于2016年發布實施。不過,基于學理分析的意見分歧,該部門規章在出臺過程中經歷了變化,并最終刪掉了“平臺與駕駛員簽訂勞動合同”的規定事項。由此,為平臺與駕駛員之間締結“非勞動關系”,特別是“民事關系”奠定了依據基礎。
回顧這段歷程,有助于發現《暫行辦法》對平臺與駕駛員關系所達成的最低限度共識。草案征求意見過程期間(12)2015年10月10日,由交通運輸部起草的《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意見反饋截止時間為2015年11月9日。,至少召開過兩次有影響力和傳播力的專家研討會。最有影響的一次專家研討會,是由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法學會召集的。與會專家普遍認為應修改“平臺與駕駛員簽訂勞動合同”的單項唯一選擇規定。還有一次專家研討會,是由無界智庫和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召集的。與會專家建議暫緩出臺《暫行辦法》。兩次專家研討會經由新聞媒體的報導,強化了“平臺與駕駛員之間僅能締結勞動關系是不妥當”的認知,也增添了對這一價值判斷結論的份量。
作為部門規章的《暫行辦法》的出臺,為未來在法律層面制定規則調整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進行了嘗試。無論互聯網平臺與駕駛員之間是平等主體的“合作關系”“掛靠關系”“承包關系”,還是屬于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的“勞動關系”,都是作為民事案件,由民庭的法官進行審理(13)當然,對于勞動爭議案件還存在著仲裁前置的問題,以及部分法院還可能設立專門的勞動法庭審理勞動爭議案件,但這些都不影響后文對“法院司法裁判與部門規章適用的關系”論述及結論。。既然該類案件作為“民事爭議”范疇進行司法裁判,有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部門規章不能作為法院裁判的依據(14)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裁判文書引用法律、法規等規范性法律文件的規定》第4條、第5條。。更何況《暫行辦法》所積累的價值共識本身就是一道特殊多選題,哪種選擇都可能被接受,也可能哪種選擇都不被接受,并沒有明確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是否一定屬于勞動關系。誠然,政府部門在《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中流露出了“勞動關系”定性意圖,只不過最終被打了折扣,使勞動關系成為特殊多選題里可能的一個選項。
歸納而言,通過這次制定部門規章的牛刀小試,能夠發現,既有的最低限度的共識是互聯網平臺與駕駛員之間并不局限于勞動關系。種種跡象表明(15)包括但不限于互聯網平臺所公布的規則制度以及互聯網平臺僅僅為平臺勞動者購買商業保險而非參加社會保險等等。,作為組織體的互聯網平臺并不愿意與駕駛員個人之間締結勞動法意義上的勞動關系。《暫行辦法》固然為締結民事關系奠定依據基礎,但不代表就否定了勞動關系建立的可能性。滴滴司機明明做著與傳統出租車司機同樣的勞動與工作,都是將乘客安全送達至指定地點,前者卻得不到《勞動法》關于勞動報酬、勞動時間、安全衛生、社會保險的制度保障,后者卻能夠得到《勞動法》的關懷,此明顯違反“類似問題類似處理”的原則。于是,不否定勞動關系建立的可能性,再加上堅持“類似問題類似處理”,都為勞動關系的適用奠定基礎。
四、立法論維度:勞動關系的韌性與彈性
當解釋論維度中“邏輯的力量”不能達成有效的共識時,就需要通過立法的政治決斷這種“力量的邏輯”來取代“邏輯的力量”,鑒于當前并未制定或修改相關立法以調整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規劃也沒有對該問題的回應,但不妨從立法論的角度提供討論思路和建議。
(一)修改既有法律的探討:修改什么
鑒于部門規章《暫行辦法》效力層級較低,且不能作為民事案件的裁判依據,對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的定性問題宜通過法律層面的立法方式來一勞永逸式地解決,并為人民法院審理相關案件提供相應的法律裁判依據。2020年5月28日審議通過的《民法典》合同編中雖然新增了部分合同類型,但依舊沒有雇傭合同(雇傭關系)章節,亦沒有勞務合同(勞務關系)的提法。《勞動法》于1994年頒布,當時剛剛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時代背景之下,與現在互聯網新經濟的迅猛發展之間,存在著當初不可想象亦難以預料的鴻溝,新經濟業態的發展使得《勞動法》不能承受其重,可能確有修改的必要。但問題在于修改什么以及如何修改。“修改什么”指向到底是修改《民法典》合同編還是修改《勞動法》抑或者兩部法律均修改?“如何修改”指向如果確定修改《民法典》合同編或者修改《勞動法》抑或者兩部法律均修改,那么該如何修改?
針對第一個問題“修改什么”,實際上需要確定哪部法律需要修改以適應新經濟對既有規范的挑戰。根據之前制定部門規章《暫行辦法》時所凝聚的共識,當互聯網平臺與駕駛員之間屬于平等主體的“合作關系”“掛靠關系”“承包關系”等時,適用既有的民事法律進行調整即可,而且既有的民事法律亦能夠較好地規范此類關系,根本無需修改《民法典》合同編就能應對此類關系的法律調整。只有當互聯網平臺與駕駛員之間屬于或可能屬于勞動關系時,才存在由哪部法律進行調整的問題。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一方面,實際上并不是所有的勞動關系均受勞動法調整,另一方面,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的實踐已經傳遞并反映出勞動關系的難以認定,如果不能認定為勞動法意義上的勞動關系,那么勞動法對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將毫無用武之地。據統計,與互聯網相關的所謂的“勞動爭議”案件,人民法院在司法裁判時,有2/3以上的案件不認定為勞動關系,而剩余1/3能夠勉強認定為勞動關系的案件,主要是因為勞動者受傷了,其生命和健康受到了損害,如果僅是泛泛地針對解雇或拖欠工資等,人民法院往往是不認定為勞動關系的(16)黎建飛:《關于996、互聯網、工傷》,中國人民大學殘疾人權益保障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網站,http://dpls.ruc.edu.cn/show.php?contentid=5028,2019-06-18。,這就使得大量互聯網新經濟案件當中的駕駛員無法通過勞動法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17)本句是從中性的角度進行客觀描述,并沒有任何表明這些案件當中的駕駛員應當或不應當通過勞動法來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主觀價值判斷。。于是,“修改什么”的問題就可以被轉換為“要不要修改勞動法”的問題。由于人民法院要依法裁判,在沒有明確的法律規范指明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是否屬于勞動關系時,根據我國的司法體制,司法要趨向保守和被動,只能嚴格遵守上位法裁判,不能主動造法(18)即使允許主動造法,亦會帶來同案不同判的負面后果。。即“為司法官者應當記住他們的職權是解釋法律而不是立法或建法”(19)[英]培根:《培根論說文集》,水天同譯,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9頁。。所以,才能發現“2/3以上的案件不認定為勞動關系,而1/3的案件認定為勞動關系”的矛盾和割裂。當前,法院司法裁判以駕駛員是否受傷為標準來認定勞動關系,沒受傷就不認定勞動關系,受傷了就認定勞動關系,這明顯脫離了勞動關系認定的“從屬性標準”,但卻意外地彰顯了長期以來流行的“誰的娃娃誰抱走”的“組織化”關懷。反映了有困難找組織、受傷了由組織保障的計劃經濟痕跡思維,亦契合勞動法的組織化痕跡特性,這就為勞動法的適用增添微弱的理由。
有適用勞動法的可能性并不一定就真能適用勞動法。前文已經指出,既有的勞動關系理論特別是從屬性理論并不能圓滿地解釋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互聯網平臺公司堅決反對締結勞動法意義上的勞動關系,再加上法院司法裁判并沒有明確調整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的勞動法依據,因此,面臨著難以適用《勞動法》調整“互聯網平臺與平臺勞動者之間基于所謂的‘勞動’所產生關系”的困境。由此,勞動法是否能夠拓寬其調整范圍將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涵蓋進來就成為問題的關鍵。
對這一問題的回應要溯及至勞動法的起源。其實,早在20多年前勞動法制定起草過程中,就面臨著調整范圍該如何劃定的問題。當時設計了三種方案:一是“大勞動法”方案,適用于所有的用人單位和全體勞動者;二是“小勞動法”方案,僅僅適用于企業及其職工;三是“中勞動法”方案,介于第一種和第二種方案之間,以“原則適用、例外排除”的邏輯,對適宜勞動法調整就納入進來,對不適宜勞動法調整的就排除出去(20)參見黎建飛《勞動與社會保障法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71—72頁。。當時,從法政策及價值取舍的角度出發,認為農民的工作時間與作息時間不適宜被勞動法所調整進而排除了第一種方案,同時,為適應當時社會所出現的第三產業甚至第四產業,而排除了第二種方案。這就意味著勞動法的調整對象具有一定的彈性,其固然最適用于傳統的工業大生產勞動,但仍然有必要對其他新型的“勞動”關系給予關注和回應。20多年后的今天,“互聯網+”引領著新經濟,這是1994年勞動法立法時所沒有遇到過的新狀況。也就是說,新經濟背景下,針對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要不要拓展勞動法調整對象范圍依舊是一個法政策及價值取舍問題,無非就是是否需要變動“中勞動法”方案的內涵和外延而已。
對于法政策及價值取舍問題,需要在社會所凝聚的既有最大限度共識基礎上作出妥當的判斷,才可能被相關討論者所理解乃至接受。部門規章《暫行辦法》所凝聚的共識是互聯網平臺與駕駛員之間具有締結多種關系的可能性,并不排除建立勞動法意義上的勞動關系的可能性。但這種回答顯然不具有足夠的說服力。因為,社會所凝聚的既有最大限度共識僅僅是回應了選擇了什么,而沒有回應為什么這么選擇的原因。前文已指出,平等主體的“合作關系”“掛靠關系”“承包關系”等已經無需再作出回應,適用既有的民事法律進行調整足已,至于是否能夠建立勞動法意義上的勞動關系才是最需要在理論上給予回應的。其實,無論未來“互聯網+”新經濟的走向如何,其發展道路無非是兩條:要么政府實施管制手段,為滴滴公司等處于灰色地帶的互聯網平臺公司發放牌照,從而重新回到傳統出租車行業,即滴滴公司回歸傳統出租車行業;要么政府釋放“管制紅利”,不再實施出租車行業的管制,從而新經濟帶來新顛覆,傳統出租車服務轉型為滴滴服務。對于前者,勞動法本來就在發揮著調整作用(21)當然,勞動法本來就在發揮著調整作用的同時,不影響民法也能發揮著調整作用,比如針對合作關系、掛靠關系、承包關系等。。對于后者,只不過互聯網平臺披著新經濟的外衣,駕駛員做著與傳統出租車司機同樣的事情,同樣受著平臺公司算法管理和獎懲規則的制約。從這一角度來看,考慮到當前勞動力供大于求的基本事實沒有變化,平臺勞動者做著以往非“互聯網+”時代下同樣的工作,卻不能受到勞動法的解雇保護、社保待遇等制度規范。于是,本著“類似問題類似處理”的原則,合乎邏輯地,勞動法更應該對這種“隱蔽式”勞動關系甚至是“規避式”勞動關系進行調整。所以,將目光放長遠來看,一方面,勞動法比民法更具有調整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的優勢和必要性。另一方面,勞動法也更應該調整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這就意味著,20多年前的“中勞動法”方案被賦予了新的彈性,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應當置于“原則適用”而非“例外排除”中。
如果將勞動法的起源再溯及遠一些,就能夠注意到早在200多年前,前文已述的“道德”和“健康”兩個元素是資本主義國家制定勞動法的原動力。據法國、英國等歐洲國家當時的征兵資料顯示,資本家過度壓榨工人勞動,導致人口素質降低,兵源質量下降,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22)參見林嘉、范圍《用人單位員工管理指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頁。。法國的經濟學家夏爾勒·杜班曾在上議院指出了工廠無度地剝削壓榨工人,損害工人的身體健康,致使因保衛國家或參加戰斗而被招募到部隊的工人大多身體素質不合格(23)參見[法]路易·勃朗《勞動組織》,何欽譯,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54頁。。從此,資本主義國家注意到不能放任資本家肆意壓榨工人勞動,于是,勞動法隨之誕生。簡單地回顧勞動法起源的這段歷史背景,再繼續矚目今天,當前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缺乏法律調整的后果,就是平臺勞動者在平臺規則之下,為更好地完成訂單任務,有可能無法有效保障其自身的勞動安全(24)其實,關于這一點,互聯網平臺的外賣騎手表現最為突出。2018年7月,據媒體報導,廣東的外賣小哥康某有959宗違章未處理,需扣3351分,待交罰款179300元,工作人員將違章記錄用A4紙打印出來,足足有29頁,連接起來超過8米。在既有的平臺規則之下,外賣騎手送貨被投訴(送貨延遲等多種原因),會被罰款200元。相比之下,外賣騎手如果交通違法,僅有可能被處5元~50元的罰款而已。因此,受利益和價值驅動,外賣騎手寧愿存在闖紅燈、逆行、違反禁令標志等交通違法行為,以“生命送餐”的方式趕時間來防止被投訴,這種做法不僅置自身安全于不顧,更對他人(行人、機動車駕駛員與乘車人等)的安全和交通秩序產生危險。此類違反道德和損害健康的行為,居然起源于“道德”和“健康”兩大關鍵詞的勞動法卻束手無策且無法作為。對照傳統勞動關系下做著同樣工作的勞動者,有必要揭開“互聯網+”的外衣,探究隱蔽勞動關系甚至是規避勞動關系的問題。,甚至威脅到社會秩序等公共利益。而且只要立法一直缺失,這種損害平臺勞動者身體健康甚至生命的代價就會一直持續。對此,勞動法不應熟視無睹和靜默無聲。
(二)修改既有法律的思考:如何修改
第一個問題“修改什么”是第二個問題“如何修改”的前提,如果沒有必要修改勞動法,那就談不上如何針對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來具體修改勞動法。因此對第一個問題的回應是至關重要的。“修改什么”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全局性問題。與之相比,“如何修改”則是技術性問題,其實際上需要回應勞動法需要如何修改以適應新經濟對既有規范的挑戰。鑒于原有的“中勞動法”方案被賦予了新的彈性,因此有必要對傳統的勞動關系進行適當地改造重塑。
首先,適當地改造重塑勞動關系。可將勞動關系大致拆分為“傳統勞動關系”和“互聯網+勞動關系”以拓展勞動關系的包容性。前者具有極強的從屬性特征,后者則可以被認定為弱從屬性,因為互聯網平臺會通過算法管理設置一系列的獎懲規則來約束平臺勞動者,平臺勞動者要在給定的規則內接受指令、完成任務、獲取報酬。對此,可以修改《勞動合同法》第2條第一款中關于“列舉式+兜底式”用人單位的表述,要么在列舉中增加互聯網平臺,要么將“等組織”的兜底表述明確細化為互聯網平臺。無論是以列舉式還是兜底式來再次擴大用人單位的內涵外延(25)曾經,《勞動合同法》相比《勞動法》,就在關于用人單位的列舉中增加了“民辦非企業單位”,而《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就針對“等組織”的兜底表述明確細化為“依法成立的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合伙組織和基金會”。這就說明,隨著立法背景和經濟社會形勢的發展變化,用人單位呈現出擴大化的趨勢,而隨著立法背景和經濟社會形勢的再次發展變化,不妨再擴充互聯網平臺作為用人單位。,都僅僅是技術性的細節問題而已。
其次,適當地改造重塑勞動基準。勞動基準大致涵蓋勞動報酬、勞動時間、安全衛生三個核心組成部分。“互聯網+”勞動關系所指向的勞動基準這三個核心組成部分,有著不同于傳統勞動關系的特性。立法應針對互聯網用工利益共享化,進行規范并制定適合于“互聯網+”背景下的最低工資、休息休假工資、工資支付保障等制度。立法還應針對互聯網用工時間碎片化,設置總量勞動時間和單位勞動時間。比如限定滴滴司機每天最長駕駛時間,駕駛多長時間則必須休息而不能繼續派單。此外,立法還應針對互聯網用工場所無限化,為保障平臺勞動者的安全衛生,由互聯網平臺公司對平臺勞動者承擔勞動風險及雇主責任,這就對互聯網平臺提出了更高的安全衛生保障義務要求。
再次,適當地改造重塑社會保險。根據《社會保險法》第59條第二款的制度設計,其為社會保險征收改革預留了制度空間(26)參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行政法室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解讀》,中國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76頁。。社會保險“稅”“費”之爭,由來已久,而從既往的實際操作來看,就存在著部分省份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征收、部分省份由稅務部門征收的二元體制機制。基于互聯網平臺不愿為平臺勞動者繳納社會保險費的事實(27)有的互聯網平臺干脆不為平臺勞動者提供任何保險甚至還可能要求平臺勞動者自己去繳納社會保險費,有的互聯網平臺則為平臺勞動者購買商業保險。但無論哪種做法,都反映了互聯網平臺不愿為平臺勞動者繳納社會保險費的事實。以及區別于傳統勞動關系下社會保險繳費的具體操作,立法不妨設定新的適合于“互聯網+”背景下的社會保險稅種,結合互聯網平臺盈利情況、平臺勞動者數量、抽成比例、管理費金額等,由互聯網平臺為平臺勞動者承擔繳納社會保險稅的義務。此種通過征收社會保險稅的方式,有利于提高征繳力度和加大維護平臺勞動者社保權益程度。
結語:勞動法的改造重塑及優化轉型
在勞動法的視角看來,勞動者提供的勞動行為不僅可以擊穿勞動者身份的差異,還可以排斥雇主身份的差別,從而只要是在勞動力市場中被雇傭的勞動者提供了勞動行為就應當統一由勞動法調整。建立一個對所有勞動者一視同仁的勞動力市場,是法治進步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
2014年,滴滴等相繼推出的交通出行服務所引發的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法律問題,對原本就飽受勞務派遣(區分“直接用工”與“勞務派遣”不同的身份)打擊的勞動法,給予再度的重擊,同時,亦拷問著勞動法(含勞動合同法)的實踐智慧與理性思辨。梅因曾說過,“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到此處為止,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28)[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112頁。。如果說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是一種歷史的進步,那么區分“直接用工”與“基于互聯網平臺的用工”不同的身份,這種“從契約向身份”的回歸就可能是一種歷史的倒退(29)1994年出臺的《勞動法》為了破除固定工、輪換工、臨時工、合同工等身份制所帶來的不平等,堅持“打破用人單位的所有制限制”“打破勞動者的身份限制”兩個打破,將固定工、輪換工、臨時工、合同工等統稱為“勞動者”,來追求契約制的平等,真正實現了從“身份”到“契約”的飛躍。。互聯網新經濟帶來的單位乃至行業的高度裂變,有將勞動法置諸死地的危機。但“勞動法的發展并沒有結束”(30)[德]W·杜茨:《勞動法》,張國文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5頁。,勞動法如何應對互聯網新經濟妥當地作出時代回應,就成為化解適用危機的關鍵。
雖然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中并沒有修改勞動法或制定互聯網用工法之類的內容,但不妨礙本文從解釋論與立法論的雙重維度來探討是否通過修改勞動法的方式將既有勞動關系理論所不能圓滿解釋的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納入進來。拓展勞動法調整對象范圍屬于法政策及價值取舍問題,揭開“互聯網+”的外衣,將做著與傳統勞動關系中同樣工作的平臺用工關系納入勞動法意義上的勞動關系中,僅僅是豐富、拓展“中勞動法”方案的內涵和外延而已。同時,勞動法因其調整對象排除個人雇主,而屬于組織化視角的法律,“互聯網+”并沒有脫離組織化的現實構圖與法律世界,亦使得勞動法具有適用的空間與可能。將互聯網平臺定性為用人單位,借助互聯網平臺用工關系豐富勞動關系的內涵外延,“正視勞動關系多元化、彈性化的客觀需求”(31)林嘉:《勞動法的原理、體系與問題》,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3頁。,真正實現勞動法的觸底反彈與鳳凰涅槃。更何況,實體經濟作為勞動法指向和關注的重心,“互聯網只是個工具,它只能傳播價值,真正能夠創造價值的是實體經濟本身”(32)郎咸平:《互聯網經濟的未來之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80—81頁。,從價值層面不會也不足以對秉持“鼓勵勞動、創造價值”立法宗旨的勞動法造成致命的損傷。在這一認知基礎上,可以對勞動法中的勞動關系、勞動基準、社會保險等進行全方位立體式的適當改造重塑,從而實現“互聯網+”時代勞動法的優化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