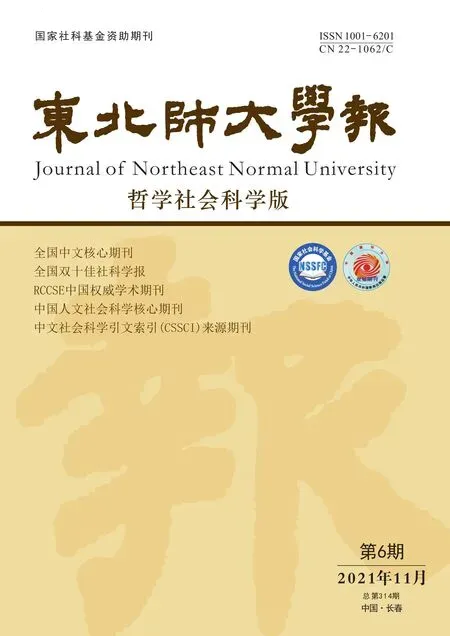老舍《駱駝祥子》英譯本的副文本研究
劉 峰,李梓銘
(1.長春理工大學(xué) 外國語學(xué)院,吉林 長春 130024;2.遼寧師范大學(xué) 外國語學(xué)院,遼寧 大連 210200)
老舍《駱駝祥子》不僅在國內(nèi)文壇享有較高聲譽(yù),被稱為“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最優(yōu)秀的長篇小說之一”[1],其英譯文自1945年首譯以來,更是引起世界文壇極大的關(guān)注和眾多美譽(yù)。在英語世界中,《駱駝祥子》是“一本感人至深、結(jié)構(gòu)嚴(yán)謹(jǐn)?shù)恼嬲龑憣嵵髁x小說”[2],“可與《悲慘世界》相媲美,在世界文學(xué)殿堂中,擁有一席之地”[3],《紐約時報》更是稱贊其為“一部偉大的小說”[4]。
迄今為止,《駱駝祥子》有5個英譯版本:King(1945),Richard and Herbert (1964),James(1979),Shi(1981/2001/2005),Goldblatt(2010)。其中,1964年英譯本是經(jīng)過改編的劇本,接受者多為觀眾而非讀者,所以此英譯版不在本文研究范圍之內(nèi)。另外,施曉菁翻譯《駱駝祥子》的三個譯本(1981/2001/2005)是依據(jù)1955年刪減修訂版《駱駝祥子》翻譯而成。從這個角度而言,譯文具有天然的不完整性,且讀者主要是中英文語言學(xué)習(xí)者和翻譯人員,對于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海外譯介研究的意義不大。其他三個英譯本分別是伊萬·金譯本、詹姆斯譯本和葛浩文譯本(簡稱“金譯本”“詹姆斯譯本”和“葛浩文譯本”),均是按照早期《駱駝祥子》未刪減單行本進(jìn)行翻譯而成。其原文具有完整性,且接受者是英語世界的讀者,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
對于《駱駝祥子》英譯本的研究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其一,英譯本在西方世界的接受與傳播研究,如孟慶澍[5],謝淼[6],金潔、吳平[7];其二,英譯本的翻譯研究,如陳曉莉、徐秋菊[8],孫會軍[9-10],黃立波[11],金潔、吳平[12],楊寧偉[13]。目前鮮有從副文本理論視角,對《駱駝祥子》英譯本進(jìn)行研究。
“副文本指任何為文本提供評論、將文本呈現(xiàn)給讀者或影響文本接受的因素。這些因素包括附加在文本上的物質(zhì)形式(內(nèi)副文本),或脫離文本的非物質(zhì)形式(外副文本)。”[14]內(nèi)副文本指封面、排版、題目、題詞、創(chuàng)作者姓名、前言、后記、注釋、插圖、出版社信息等,外副文本包括公開的作者訪談、評論等[15]。“譯文的副文本相對于文本本身來說,最先被目的語讀者所接觸,必將對文本的接受產(chǎn)生無法估量的影響。”[16]也就是說,讀者在閱讀正文內(nèi)容之前,最先從視覺、感官上接觸副文本,對文本的接受產(chǎn)生了“先入為主”的印象。副文本對于全方位、多角度發(fā)掘文本內(nèi)外的生命力具有不可或缺的輔助作用,是有效引導(dǎo)讀者參與文本意義構(gòu)建的文化場域。可以說,“副文本因素對于該譯文正文本的意義,起到了豐富、闡釋、細(xì)化、驗證的作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激發(fā)了讀者強(qiáng)烈的閱讀興趣”[17]。更為重要的是,“副文本對文學(xué)作品跨國流動,繪制出更為清晰的圖譜”[18]。本文依據(jù)副文本理論,從內(nèi)副文本和外副文本兩個視角,以老舍《駱駝祥子》的金譯本、詹姆斯譯本和葛浩文譯本為研究對象,探究歷時半個世紀(jì)之久的各個英譯本形象變遷的歷時與共時圖譜,并發(fā)掘其背后產(chǎn)生的根本原因。
一、金譯本:“美國夢”的奮斗史
老舍《駱駝祥子》第一個英譯本是1945年由美國Reynal & Hitchcock出版社發(fā)行,由筆名為伊萬·金(Evan King)(真名Robert.S.Ward)翻譯的。此譯本較之后來其他兩個譯本的最大特色是正文中收集了美國著名藝術(shù)家、插畫師塞魯斯·勒雷伊·巴爾德里奇(Cyrus LeRoy Baldridge)所畫的一系列插圖,封底介紹了插畫師巴爾德里奇生平。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巴爾德里奇曾經(jīng)在北京生活一年之久,金譯本中的插圖是巴爾德里奇描繪老北京城的真實景象。1924—1925年間,他游歷日本和中國,第二次繪畫草圖;1931年,第三次來到中國,進(jìn)行創(chuàng)作。巴爾德里奇以獨(dú)特的繪畫、海報創(chuàng)作對中國社會持續(xù)、系統(tǒng)的真實寫照,為西方打開了了解中國現(xiàn)實社會的大門。1944年,巴爾德里奇榮獲中國救濟(jì)軍團(tuán)頒發(fā)的“優(yōu)秀獎”,以此表彰他為中國事業(yè)做出的貢獻(xiàn)。可以說,在金譯本中,巴爾德里奇的插圖集是繪畫版的《駱駝祥子》,為助推故事情節(jié)發(fā)展起到了畫龍點(diǎn)睛之效果。
金譯本封面插圖節(jié)選自巴爾德里奇的插畫CamelHappyBoy。泛黃的封面極具年代感,一位年輕高大清瘦的車夫敞開著衣服,站在一輛人力車前,遠(yuǎn)處另一個車夫艱難地拉著客人,跑在空曠無人的蒼茫天地間。譯本題目為RichshawBoy,并標(biāo)出作者、插畫師和譯者姓名,以及出版社信息,特別強(qiáng)調(diào)這是一部中文小說的英譯本(見圖1)。實際上,封面插圖只展示了插畫CamelHappyBoy左半部分內(nèi)容,完整的插畫在封頁第三頁呈現(xiàn)出來。右半部分是老北京城墻外,一些拉著駱駝的商人、趕著馬車的百姓,絡(luò)繹不絕地沿著古城外墻趕集的熱鬧場景。但是,光禿的樹木、泛黃色的背景,給人凄涼頹廢之感(見圖2)。封面第二頁是彩色的北京城內(nèi)繁華擁擠的景象,猶如《清明上河圖》一般,老百姓神態(tài)各異,忙著各自的生計,但是標(biāo)志性的清朝女人頭飾暗示著故事發(fā)生的年代(見圖3),更加突出中國清末民國初期的異域文化特色。“封面設(shè)計往往通過展示刻板的異域風(fēng)情,甚至東方主義來激發(fā)目的語讀者對譯文的最初興趣。”[19]這種視覺上的副文本元素符合西方對于中國當(dāng)時社會刻板印象的想象,在文本的跨文化傳遞中發(fā)揮著協(xié)商作用,構(gòu)建了西方眼中的中國意象,成功地吸引了西方讀者的眼球,助推譯文更加順利地進(jìn)入西方世界。

圖1 金譯本封面 圖2 金譯本插圖

圖3 金譯本插圖
金譯本共二十四章,每章節(jié)開篇都配有預(yù)示本章節(jié)故事主要情節(jié)的簡筆插圖,章節(jié)段落中還配有提示本章節(jié)故事內(nèi)容的插圖。平均每個章節(jié)有兩幅插圖,但是第十一章、第二十章(每章含有三幅插圖),第十章、第二十四章(每章均有四幅插圖)除外,正文共55幅插圖。封底指出金譯本編輯Richard Ellis設(shè)計編輯了這些插圖的順序。按照內(nèi)容劃分,插圖可分為四類:第一類是人物插圖,簡單幾筆勾勒出神態(tài)各異的本章節(jié)主要人物形象,暗示著人物的不同特征和命運(yùn),如憨厚、勤勞、堅忍的祥子,好吃懶做、蠻橫撒潑的虎妞,狡猾奸詐的劉四爺,清新可人的小福子,霸道兇殘的警察和士兵等;第二類是預(yù)示故事發(fā)生背景的景物插圖,如北京城樓、四合院、大宅門、拱橋、北海白塔;第三類體現(xiàn)中國元素的圖騰,如龍、臉譜;第四類具有宗教色彩的插圖,如如來佛、彌勒佛、香爐。“文字與插圖的結(jié)合能夠使讀者對于故事發(fā)生的場景、背景和人物特征的認(rèn)知更加形象化、具體化。”[20]通過這些插圖,讀者可以推測出人物性格特征、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從而預(yù)測故事情節(jié)和主要內(nèi)容。插圖為文本提供了豐富的視覺映像,而文本又詳盡地闡釋了插圖折射的意蘊(yùn),兩者互為參照、相輔相成。西方出版社將插圖置于譯作之中,對目的語讀者的閱讀審美需要產(chǎn)生深遠(yuǎn)影響。這些插圖不僅展現(xiàn)了東方的地域特征和異域之美,同時激發(fā)了目的語讀者的閱讀興趣和“中國想象”,這是早期西方贊助人出版中國文學(xué)時慣用的策略。
封面以二百字左右介紹了《駱駝祥子》故事發(fā)生背景、人物特征、主題意蘊(yùn)以及譯者伊萬·金的翻譯經(jīng)歷。中國現(xiàn)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老舍先生選取具有一千多年歷史的古城——北京作為故事發(fā)生的背景。主人公是一位質(zhì)樸的車夫,人稱“駱駝祥子”。“面對辛酸的生活,堅強(qiáng)的祥子形象正是經(jīng)歷風(fēng)雨飄搖、遭遇苦難的中國社會真實寫照。起起伏伏、患得患失,煎熬與苦難、希望與幻滅,內(nèi)心始終埋藏著樸實的微笑。……老舍的這部小說主題意蘊(yùn)具有普適性,它可以是發(fā)生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小說,而這位令人動容的車夫與不公的命運(yùn)做斗爭,不放棄、不拋棄,則展現(xiàn)了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任何一個普通人的品質(zhì)。”[21]主人公祥子勇敢、樂觀的精神與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美國社會追求的不屈不撓、實現(xiàn)自我價值的審美文化價值觀具有一定的“同一性”。封面簡介作為內(nèi)副文本,有力地建構(gòu)了同一性。可見,“為了建構(gòu)同一性,許多出版商用兼有異國情調(diào)化和普適性的話語,強(qiáng)調(diào)外來文本讓人們看到不同的世界,也強(qiáng)調(diào)它們可能為讀者提供普適的真知灼見”[18]。這種文化“同一性”體現(xiàn)在意識形態(tài)上的“歸化”。封底在作家老舍的學(xué)習(xí)工作簡介中,指出老舍是堅毅、真摯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先驅(qū)者之一,強(qiáng)調(diào)老舍是一位自由主義作家,沒有任何政治傾向,終身為國家和人民的自由與福祉而創(chuàng)作,是一位為中國文壇所敬仰的作家。“自由”是西方社會的核心價值觀,這樣的學(xué)習(xí)工作簡介給西方讀者留下“似曾相識”之感,使讀者對文本產(chǎn)生天然的“親切”感,以拉近和讀者間的距離,引發(fā)讀者共鳴。正因為這種文化的“異質(zhì)性”與“同一性”相互交融,才使文化間的傳播、交流、借鑒成為可能。
“副文本更有益于我們深刻了解目的語歷史文化環(huán)境中的譯文呈現(xiàn)方式和接受情況,并反映出目的語特定時期的社會文化現(xiàn)象。”[22]封面簡介中將駱駝祥子稱之為Happy Boy(快樂小子)則進(jìn)一步暗示讀者,金譯文是符合美國讀者喜好的“大團(tuán)圓”結(jié)尾小說。作為在中國工作多年的美國外交官,譯者伊萬·金深知原作主人公祥子遭遇苦難、自甘墮落的悲劇形象在當(dāng)時美國社會背景下沒有市場,不能被廣大美國讀者所接受,無法喚起讀者共鳴,因此他修改了小說結(jié)尾,將祥子改寫成一位通過自己努力,排除萬難,最終實現(xiàn)夢想,并與心愛的女人結(jié)婚,過上幸福生活的美國好萊塢式小說。老舍原作中勤勞、要強(qiáng)、質(zhì)樸、善良、堅忍,但最終墮落、自私、冷血、貪財、背叛等多重復(fù)雜人性的祥子,在金譯本中變成了富有同情心、堅毅果敢、勇于追求幸福和自由的“美國夢”實踐者。可以說,金譯本的《駱駝祥子》是一部為了迎合當(dāng)時美國社會讀者的閱讀期待和獲取最大商業(yè)價值而改編的實現(xiàn)“美國夢”式的浪漫主義小說。
金譯本《駱駝祥子》出版后,立刻風(fēng)靡全美,成為最暢銷書目之一。美國主流報紙《紐約時報》《芝加哥論壇》《華盛頓郵報》等給予熱切關(guān)注,并從人物分析、主題寓意、語言藝術(shù)、審美特征等角度進(jìn)行高度評價。“祥子為了最卑微的幸福而做出最大的努力,感動得讀者們潸然淚下。人性本善的祥子最終戰(zhàn)勝苦難的命運(yùn)。可以說,這部令美國讀者陌生的中國作家小說,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杰出的作品之一。”[23]譯者對小說悲劇性結(jié)尾的改寫,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目的語讀者對人物形象的認(rèn)知。為了迎合1940年代中期美蘇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激烈爭奪,1946年美國官方邀請老舍訪美。譯者伊萬·金將老舍小說悲劇性結(jié)尾改寫成“美國夢”的奮斗史,更有益于美國讀者對陌生的中國產(chǎn)生“親近感”和“認(rèn)同感”,順應(yīng)了當(dāng)時美國社會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需求。實際上,譯者除了對小說結(jié)尾進(jìn)行改寫外,基本上還原了原作的語言藝術(shù)和審美感受。“《駱駝祥子》最為寶貴的是小說中大量的民間諺語和含蓄的隱喻,就如同中國流通幾千年的銅錢一樣,這些語言對中國人來說,普通無異,但是對于我們外國人來說卻是鮮活生動、價值斐然的瑰寶。”[24]“寒冬夜里,茶館擠滿喝茶取暖的車夫,熱鬧的祝壽和奇特的春節(jié)場面,無知貧困的社會底層民眾封建迷信、愚昧致死,各種中產(chǎn)階級家庭生活百態(tài)等等,在我們(目的語讀者)記憶中留下深深的烙印。”[25]金譯本不僅滿足了美國民眾對異國情調(diào)的文化獵奇,也使一些美國評論家認(rèn)識到小說的社會批評價值。“小說的主題蘊(yùn)意比故事更為重要。它揭露和控訴中國當(dāng)時社會和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體系,腐蝕了人的身心與道德,使人墮落成無情可怕的野獸。”[3]金譯本在美國產(chǎn)生巨大影響,不斷再版,并且以此為藍(lán)本翻譯成其他語種。由此,老舍的文學(xué)作品在世界文壇廣泛傳播開來。此時,美國對中國文學(xué)的認(rèn)知處于初級階段,僅限于中國古詩研究。海外對于金譯本《駱駝祥子》研究比較少,僅有Cyril Birch《老舍:幽默中的幽默家》(LaoShe:TheHumouristinhisHumour)[26]和C.T.Hsia《近代中國小說史(1917—1957)》(AHistoryofModernChineseFiction1917—1957)[27]在闡述老舍的政治生活背景和小說創(chuàng)作的社會背景時,提及《駱駝祥子》主要內(nèi)容和人物形象分析,并指出金譯本結(jié)尾與原作大相徑庭[26],但是對于老舍小說的藝術(shù)價值分析不夠深刻。
簡而言之,封面、插圖、創(chuàng)作者信息(包括作者、譯者、插畫師、編輯)、出版社信息、目的語讀者評論等譯文內(nèi)外副文本的主要因素,不僅啟發(fā)讀者進(jìn)一步探索文本之意義,更加詮釋了譯者伊萬·金對老舍小說《駱駝祥子》的改寫,成功塑造了通過自身奮斗實現(xiàn)“美國夢”的“美式英雄”形象,不僅對于老舍作品在西方世界廣為傳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也成為西方了解中國社會、中國文化、中國元素的重要渠道。
二、詹姆斯譯本:了解中國社會的“窗口”
1972年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訪華及隨后中美建交等一系列重大國際事件,使美國及西方社會急需了解中國社會政治經(jīng)濟(jì)的真實狀況。另外,20世紀(jì)50年代,中國大量現(xiàn)代文學(xué)作品翻譯成英文,加深了美國乃至西方世界對中國文學(xué)的整體認(rèn)知,尊重文學(xué)的“異質(zhì)性”成為西方的主流話語。再有,很多美國讀者發(fā)現(xiàn)金譯本與老舍原作內(nèi)容相差甚遠(yuǎn),“我非常震驚地發(fā)現(xiàn),譯者為了迎合西方讀者閱讀口味,竟然將悲劇《駱駝祥子》改寫成歡樂大團(tuán)圓式結(jié)尾,這真是令人難以接受”[28]。多重社會背景和諸多因素促成了忠實于原作的詹姆斯譯本出版。
1979年,美國夏威夷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了譯者珍·詹姆斯翻譯的《駱駝祥子》,英文名為Rickshaw:thenovelLo-t’oHsiangTzu。詹姆斯譯本封面(見圖4)是由Yue Tin Mui于1978年所畫的黑白水墨中國畫,封面中一位車夫拉著母子二人急速奔跑,紅色大字Rickshaw位于書頂中央顯赫位置,下方是作者和譯者名字。封面最右側(cè)從上至下以行草書寫“前進(jìn):步不停,錢前錢后,錢老孤丁。莫天(Yue Tin Mui筆名)一九七八年”。封底是其英文翻譯。第二頁封頁(見圖5)除了書名、作者和譯者名外,書正中央從上至下印有書法“東洋車”字樣,封頁底端標(biāo)出版社信息。

圖4 詹姆斯譯本封面

圖5 詹姆斯譯本封頁
封底內(nèi)容包括老舍小說《駱駝祥子》創(chuàng)作背景、祥子人物特征分析、小說語言風(fēng)格,并特別指出此譯本完全忠實于原作內(nèi)容,未刪除、未修改任何信息(omits nothing and alters nothing)[29],可作為東方學(xué)者或?qū)懽鲪酆谜邊⒖佳芯渴褂谩4送猓€附有作者老舍生平簡介以及譯者詹姆斯學(xué)習(xí)和翻譯工作經(jīng)歷。詹姆斯是愛荷華大學(xué)文學(xué)博士,多年來一直從事中國文字和中國文學(xué)研究工作,翻譯老舍兩部作品《駱駝祥子》和《二馬》及大量中國詩歌,在中國小說和詩歌翻譯方面造詣頗深。再有,封底標(biāo)出封面設(shè)計師Roger Eggers以及封面中國水墨畫家Yue Tin Mui的名字。詹姆斯譯本沒有對水墨畫家有過多介紹,這與金譯本插畫師的詳細(xì)信息形成鮮明對比。封面畫家的地位弱化,凸顯原作者和譯者的主體地位,能夠吸引目的語讀者更加關(guān)注作者、譯者和文本內(nèi)容。無論是中國水墨畫封面,還是中國毛筆字題詞,這些充滿濃郁中國元素的副文本與金譯本插畫有著相似的“異質(zhì)性”,對喚起目的語讀者的閱讀興趣起到重要作用。
詹姆斯譯本與金譯本最大的區(qū)別在于,前者有譯者序,而后者沒有。彼得·紐馬克(Peter Newmark)認(rèn)為,沒有譯者序的翻譯小說應(yīng)該成為歷史。“譯者通過副文本,在文本的客觀物質(zhì)空間里,證實自己的存在。”[30]譯者序是非常重要的譯文副文本因素之一,能夠傳達(dá)譯者的翻譯動機(jī)、翻譯策略、翻譯思想以及個人的意識形態(tài)等等,是凸顯譯者身份的重要場域。詹姆斯在譯者序中首先指出,金譯本與詹姆斯譯文均是按照老舍原作未刪減版本作為藍(lán)本而進(jìn)行的翻譯活動,彰顯了詹姆斯譯本的權(quán)威性。其次,詹姆斯認(rèn)為,金譯本存在一些不足,如譯者伊萬·金大量刪減、修改原文內(nèi)容,并且創(chuàng)造出原作沒有的人物形象,這使金譯本與原作大相徑庭。而詹姆斯譯本從形式上忠實于原文,沒有刪減或修改任何內(nèi)容。即使有些必要的信息增補(bǔ),也是為了方便目的語讀者更好地理解原文涵義而有意為之。
詹姆斯不僅是譯者,更是一位讀者和評論家。可以說,詹姆斯的譯者序是一篇學(xué)術(shù)價值頗高的文學(xué)評論。在社會文化學(xué)視域下,詹姆斯從文化、社會、政治等維度對語言風(fēng)格、人物形象、主題意蘊(yùn)等方面做出價值判斷。在詹姆斯看來,老舍的寫作風(fēng)格更富有感染力。小說《駱駝祥子》使用了大量活靈活現(xiàn)、極具地方色彩的北京方言,而譯者詹姆斯竭盡所能在譯文中將此呈現(xiàn)給讀者,使讀者身臨其境感受到異域文化的語言魅力。詹姆斯認(rèn)為,老舍對老北京城的描寫手法深受狄更斯影響。小說《駱駝祥子》處處體現(xiàn)著狄更斯式詼諧與幽默、辛辣與諷刺的語言藝術(shù)。比如,小說主人公“祥子”名字本身含有“好兆頭”“好運(yùn)”之意,然而祥子身上卻發(fā)生一系列出其意料的“霉運(yùn)”,最終走向悲劇式的窮途末路。
詹姆斯將老舍與查爾斯·狄更斯相提并論。他認(rèn)為,二者不僅是社會小說家,更是地方志編纂者。在某種程度上來講,狄更斯的小說是倫敦志,而老舍《駱駝祥子》則是老北京城里社會底層苦難生活的真實寫照。詹姆斯推測小說《駱駝祥子》故事大概發(fā)生在1934—1937年左右,正值國內(nèi)軍閥混戰(zhàn)、日本入侵中國內(nèi)憂外患之亂世。在詹姆斯看來,《駱駝祥子》是中國現(xiàn)代小說對社會底層勞動者的首次正式關(guān)注。作者老舍對小說人物祥子沒有贊譽(yù)、嘲弄,甚至指責(zé),而更多的是懷著絕望之情深刻剖析其人物特征,指出祥子最大的人性弱點(diǎn)就是“自私”。他只為自己考慮,正是這種“自私”的本質(zhì)最終毀滅了自己,而并沒有獲得絲毫的“自利”。從這個角度而言,祥子不是病態(tài)社會的受害者,而是舊社會的產(chǎn)物和代表。人,具有社會屬性,不能脫離社會而單獨(dú)存在。盡管這座沒有溫度的大城市以中立的姿態(tài)對待祥子,既沒有給予祥子過多的幫助,也沒有妨礙其個人發(fā)展。但是,與鄉(xiāng)下惡劣環(huán)境比較而言,老北京城能夠給予他更多的庇護(hù)和生存空間。換言之,處于亂世的老北京城還是為祥子提供了一些發(fā)展機(jī)遇,甚至可以說改變其命運(yùn)。但是,自私、自負(fù)、貪婪的本性使他拒絕小福子的愛,因為害怕承擔(dān)起照顧其兩個年幼弟弟的重任。小福子最終因貧困和絕望而自殺,她的死深深刺痛了祥子,成為壓倒祥子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從此,祥子自甘墮落,走向毀滅。祥子“行尸走肉”般毫無希望地活著,正是這個毫無希望的社會造成的惡果和產(chǎn)物。祥子是無望的北京城里最無望的普通人。相比之下,妓女小福子才是這個病態(tài)社會的真正受害者,她無處可逃,深深陷入絕望無助的人間煉獄之中,最終被邪惡的黑暗社會所吞噬。
在詹姆斯看來,老舍對社會底層百姓懷有深厚的憐愛之情,卻無法寄希望于他們。北京城里的人們麻木冷漠地活著,艱難求生,醉生夢死般地消遣,對任何事情不抱有希望,也不期待任何事情發(fā)生。可以說,這部小說里沒有真正的英雄人物。當(dāng)人們已經(jīng)習(xí)慣踩著他人的身軀向上掙扎,努力抓住活著的機(jī)會時,他們勢必淪為看客,冷漠地圍觀政治犯阮明被處以極刑,并以此為樂。詹姆斯指出,小說結(jié)尾處歇斯底里呼喊的人,不是祥子,而是作家老舍從內(nèi)心深處發(fā)出的憤怒的吶喊,這與魯迅《狂人日記》何其相似!詹姆斯以為,二者均是對“吃人”舊社會的強(qiáng)烈控訴,所不同的是,老舍并沒有像“狂人”一樣,將期望寄予“孩子”,他并沒有將希望寄托于未來。《駱駝祥子》除了譏諷和絕望,讓人看不到一絲光明和希望。在詹姆斯看來,老舍的憤怒和絕望源自于根深蒂固的罪惡舊社會。小說處處清晰地表明了作者的政治愿望:車夫老馬以螞蚱為例告訴祥子,一只螞蚱成不了“蝗災(zāi)”,單打獨(dú)斗成不了大器。只有窮苦大眾團(tuán)結(jié)起來,才有力量挽救自己的命運(yùn)。
譯者序末尾附有兩幅地圖(見圖6、圖7),一幅老北京城地圖,另一幅則是祥子逃離部隊返回京城的地圖。這兩幅地圖不僅表明譯者詹姆斯對祥子生存環(huán)境的深切關(guān)注,同時也直觀展現(xiàn)出中國20世紀(jì)30年代的社會地理風(fēng)貌。我們看到,詹姆斯譯本中形象直觀地注入視覺化元素,豐富了文本結(jié)構(gòu),增強(qiáng)了文本的立體化呈現(xiàn)方式,為讀者解讀文本、更好地理解小說情節(jié)起到有效的引導(dǎo)作用。“譯者序能夠幫助讀者更好地接受源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之間的差異。”[31]最為難能可貴的是,譯者詹姆斯在譯者序中介紹作者老舍與老北京城地理、歷史、人土風(fēng)情等情況時,向讀者推薦了相關(guān)專業(yè)書籍。從這方面來講,詹姆斯的譯者序具有一定的學(xué)術(shù)性價值,適合學(xué)術(shù)研究人員深入探究。正如封面賓夕法尼亞大學(xué)遠(yuǎn)東歷史系教授Hilary Conroy評價此書時談道:“隨著中美文化交流不斷發(fā)展和深入,老舍小說《駱駝祥子》應(yīng)該成為研究中美文化關(guān)系方面的書目,同時將這本小說推薦給廣大讀者,相信他們會有更多的收獲。”[29]

圖6 祥子從部隊逃跑返回北京城路線圖

圖7 老北京城地圖
詹姆斯譯本被譯者和贊助人界定為學(xué)術(shù)研究讀物,在一定程度上,引起諸多海外學(xué)者關(guān)注并展開了深入研究,由此拓展和豐富了國內(nèi)外老舍作品的整體研究。其中兩篇海外博士論文對老舍《駱駝祥子》研究較為顯著。Leung在博士論文CharlesDickensandLaoShe:AStudyofLiteraryInfluenceandParallels中以歷時和共時相結(jié)合的雙視角,從文本內(nèi)對比老舍與狄更斯寫作手法的異同,指出:狄更斯的《博茲特寫集》《霧都孤兒》《尼古拉斯·尼克爾貝》與老舍的《老張的哲學(xué)》《離婚》《駱駝祥子》均生動形象地刻畫了城市與鄉(xiāng)村的社會面貌,挖掘出城市冷漠無情、罪惡累累,鄉(xiāng)村危機(jī)四伏的社會本質(zhì),所不同的是,狄更斯認(rèn)為外部環(huán)境不會腐蝕人的善良本性,而老舍則揭示出外部社會環(huán)境對人的內(nèi)部屬性的巨大影響。在Leung看來,《霧都孤兒》中的奧利弗是從社會底層不斷向上的演變過程,即從一個貧困潦倒、被拋棄的私生子,到學(xué)徒小子,再到竊賊團(tuán)伙頭目費(fèi)金的“搖錢樹”,偷竊富人財物的共犯,最終被中產(chǎn)階級紳士收為養(yǎng)子,結(jié)束苦難的生活,繼承父親遺產(chǎn),開啟幸福的幸運(yùn)兒。相比之下,祥子如同過山車一般從一個誠實、單純、努力上進(jìn)的車夫,墮落成一個游手好閑、無惡不作的京城流浪漢。小說《駱駝祥子》中的一條隱秘線索則是祥子不斷與外部惡劣環(huán)境做斗爭的艱難過程。然而,祥子并沒有奧利弗的好運(yùn),因為奧利弗幸運(yùn)地遇到好人布朗洛和梅麗夫人,他們的關(guān)懷與照顧一直溫暖著奧利弗,激發(fā)了深埋在他靈魂深處的人性善的種子。反觀祥子僅憑借自己有限的社會資源,獨(dú)立面對殘酷的人生,最終被黑暗的社會所吞沒。Leung認(rèn)為,祥子本性為善,沒有傷害過任何人,而摧毀祥子的正是邪惡的外部因素[32]。可見,詹姆斯和Leung對于祥子的人性本質(zhì)認(rèn)知存在很大分歧。在詹姆斯看來,外部邪惡環(huán)境誘發(fā)了祥子原罪的欲望,而Leung相信人生而向善的本性,將祥子的悲慘命運(yùn)歸咎于黑暗的舊社會。二者均認(rèn)識到外部環(huán)境對人物命運(yùn)的影響,但是Leung認(rèn)為,這種外部環(huán)境影響具有決定性,也就是說,外因決定了內(nèi)因,本質(zhì)上夸大了外因的作用。
另外一位海外博士生李英俊(音譯)在博士論文Context,TranslatorandHistory:AStudyofThreeTranslationofLuotuoXiangziintheUSA中對比分析了伊萬·金、詹姆斯和施曉靜三個譯本,并將詹姆斯譯本定性為:“教材,具有一定的學(xué)術(shù)價值和研究價值。”[33]老北京城不僅具有神秘的東方異域文化的吸引力,更是讓目的語讀者感受到一只看不見的“命運(yùn)之手”操控著蕓蕓眾生的命運(yùn)。祥子的命運(yùn)與其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說,被其左右或控制。我們看到,老北京城的傳統(tǒng)婚姻習(xí)俗——劉四爺生日慶典推動了祥子與虎妞的結(jié)合,火辣炙熱的太陽和疾風(fēng)驟雨的糟糕天氣慢慢消磨了祥子的健康,軍閥混戰(zhàn)中士兵搶奪祥子的第一輛人力車等等,一種隱秘而不可抗拒的強(qiáng)大力量在每個關(guān)鍵時刻影響著祥子的抉擇和命數(shù)。祥子在老北京城的夾縫中苦苦掙扎,而罪惡的外部環(huán)境卻慢慢腐蝕了他的身軀和靈魂,使其淪落為“非人非鬼”的京城棄兒。李英俊與Leung觀點(diǎn)相似,認(rèn)為:祥子是無產(chǎn)者,是舊社會的受難者和受害者,代表窮苦大眾,慘遭病態(tài)社會蹂躪,盡管自身有些缺點(diǎn),但是應(yīng)該值得同情。
在李英俊看來,首先,詹姆斯譯本忽視了文學(xué)的想象,夸大了《駱駝祥子》的社會批判性,將小說人物并置于具體社會歷史環(huán)境中,向讀者展示了這一時期民族和文化歷程的持續(xù)性和復(fù)雜性[34]。甚至可以說,詹姆斯譯本是中國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紀(jì)實文獻(xiàn)。但是,我們也應(yīng)該看到,詹姆斯譯文中的譯者序?qū)⒅袊囟〞r期的歷史、社會、文化介紹給西方讀者,為解讀和接受文本提供了更加寬廣的詮釋空間。顯然,在這方面,此譯文優(yōu)越于金譯本。其次,詹姆斯譯文盡管語言沒有原作生動,且缺乏感染力,忽視了老舍原作中的語言藝術(shù)和審美力量,卻能夠從形式上完全忠實于原文,將原作內(nèi)容完整傳達(dá)給目的語讀者,能夠使西方世界真正了解老舍作品原貌及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的魅力,這是金譯本所欠缺的部分。
西方文壇依據(jù)詹姆斯譯本,對老舍《駱駝祥子》人物和環(huán)境的辯證關(guān)系展開激烈的爭論,實質(zhì)上并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文學(xué)的社會功能,期望通過文學(xué)來解讀中國社會歷史問題,將文學(xué)視為了解中國社會的窗口。詹姆斯譯本出現(xiàn)在中美建交之后,得益于政治環(huán)境的有力推動,越來越多的西方讀者開始關(guān)注中國文化。
三、葛浩文譯本:關(guān)于苦難與人文關(guān)懷的世界經(jīng)典文學(xué)
葛浩文以為,金譯本改寫原作結(jié)尾,完全歪曲了作者老舍的寫作意圖;而詹姆斯重譯老舍《駱駝祥子》,雖然勇氣可嘉,但是詹姆斯過度追求文本形式忠實于原文,結(jié)果造成誤譯頻出,且存在很多不符合英語習(xí)慣的表達(dá)方式。另外,詹姆斯譯文使用大量過時的中文拼寫,嚴(yán)重破壞了原文的語言風(fēng)格和審美藝術(shù)。再有,譯者施曉靜1981年譯本最后一章僅翻譯了原文一半內(nèi)容,完整性欠缺;而施曉靜2005年香港中文大學(xué)出版社的譯文是英漢雙語版,主要服務(wù)于翻譯學(xué)習(xí)者[4]。基于此,葛浩文重譯老舍經(jīng)典作品《駱駝祥子》,期望在完整性、忠實性及可讀性方面超越以往其他四個譯本。
2010年,美國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團(tuán)(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出版發(fā)行葛浩文翻譯的老舍《駱駝祥子》譯本,英文名為RickshawBoy,封面是由Bettmann/Corbis拍攝的車夫拉客照片(見圖8)。葛浩文譯本沒有對照片和攝影師有過多介紹,僅從封面照片來看,實際上無法判斷車夫的年齡和國籍。這種人力車為了吸引游客觀光旅游,甚至在當(dāng)今的美國曼哈頓大街也隨處可見。照片中建筑物墻壁上的廣告牌隱約可見漢語繁體字“飯館”字樣,給讀者留下無限想象空間。封面照片下,白字紅底印著書名RICKSHAW BOY,以及作者LAO SHE名字。較之金譯本和詹姆斯譯本,葛浩文譯本封面設(shè)計弱化了異國風(fēng)情,沒有刻意突出中國元素,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目的語讀者的陌生感,有利于中國文學(xué)更好地融入世界文學(xué)。封底從文學(xué)性和哲學(xué)視角介紹該書內(nèi)容:“作者老舍是一位深受愛戴的中國作家,他的小說《駱駝祥子》描寫了一位窮苦的北京車夫悲慘的一生。可以說,《駱駝祥子》是二十世紀(jì)中國文學(xué)史上最重要、最受讀者喜愛的文學(xué)作品之一。小說主人公祥子是一個充滿爭議的人物,一個堅韌、勤勞的車夫,在黑暗的社會邊緣痛苦掙扎,最終墮落成一個滑稽可恥的悲劇人物,這是一部強(qiáng)烈控訴個人主義哲學(xué)的社會現(xiàn)實主義小說。”封底對作者老舍和譯者葛浩文做了簡單介紹,強(qiáng)調(diào)了作者和譯者的社會地位和名望,進(jìn)一步肯定原作和譯作的文學(xué)價值,并指出葛浩文譯本是“最新最完美的《駱駝祥子》譯作”。

圖8 葛浩文譯本封面
與詹姆斯譯本相同,葛浩文譯文也有譯者序。所不同的是,詹姆斯的譯者序是比較專業(yè)的學(xué)術(shù)類文學(xué)評論,而葛浩文的譯者序則從譯者身份角度出發(fā),向目的語讀者展示了譯者的翻譯動機(jī)、翻譯策略、翻譯方法等。葛浩文在譯者序中,大篇幅詳細(xì)介紹了作者老舍的求學(xué)、工作、寫作經(jīng)歷,以及主要作品。“譯者序不僅是譯者顯身發(fā)聲的重要渠道,也是更好地促進(jìn)人與人之間、不同文化之間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重要場域。”[31]作為莫言作品首席翻譯家,葛浩文對作者老舍的介紹在西方世界更具權(quán)威性和可靠性。這些副文本信息為西方讀者接近和了解作者老舍和作品《駱駝祥子》提供了有價值的信息和資料,促進(jìn)了老舍和《駱駝祥子》在西方世界的傳播,提高了老舍在世界文學(xué)中的地位,為老舍爭取了更多的象征資本。
葛浩文強(qiáng)調(diào),為了保障該譯本的權(quán)威性,選取小說《駱駝祥子》未刪減版本作為翻譯底本,也就是1939年人間書屋出版的《駱駝祥子》版,并參照1941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版本,在最大限度上保證譯文的完整性。葛浩文嚴(yán)謹(jǐn)?shù)闹螌W(xué)態(tài)度還表現(xiàn)在對小說題目和故事發(fā)生地點(diǎn)翻譯方法的考究上。在葛浩文看來,如果采用意譯方法將中文“駱駝祥子”翻譯成fortunate son,不如直譯成Camel Xiangzi更恰當(dāng)。祥子是一個年輕的車夫,而非男孩。葛浩文將“人力車夫”翻譯成Rickshaw Boy,是因為boy在英語中通常指代服務(wù)員、侍者,或社會地位較低的勞動者,與年齡大小無關(guān),只是特殊語境中對特殊人群的稱呼而已。因此,葛浩文繼續(xù)沿用金譯文題目。再有,中國首都北京,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稱呼。1928—1949年期間,稱為北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改名為北京。作者老舍稱之為“北平”,葛浩文忠實于原文,將故事發(fā)生地點(diǎn)也翻譯成北平。葛浩文在譯者序中,沒有詳細(xì)解讀文本,也沒有對其進(jìn)行主觀性的價值判斷,而是向讀者展現(xiàn)作者波瀾壯闊的一生,側(cè)重“作者本位”,充分體現(xiàn)了譯者葛浩文對作者老舍生命歷程的人文關(guān)懷。
“譯者是一個獨(dú)特的角色,發(fā)揮著文化大使的作用……譯者向?qū)υ凑Z文化了解甚微或持有刻板印象的目的語讀者傳播他們對不同文化的理解,而譯者序是傳播的最佳場域。”[31]老舍《駱駝祥子》不同英譯本的譯者序言反映出譯者的翻譯動機(jī)、倫理道德立場,以及個人的文學(xué)審美觀念的差異性。譯者主體積極參與到文學(xué)和文化的構(gòu)建過程中,對于老舍作品在世界文學(xué)語境中生長出新的生命力具有一定的推介作用。
西方世界對于葛浩文譯本的解讀呈現(xiàn)多元化、系統(tǒng)性、綜合性特征。對于小說《駱駝祥子》人物分析,不僅限于男主人公祥子,而且開始關(guān)注女性人物命運(yùn)。Selvi認(rèn)為,小說兩位主要女性人物虎妞和小福子的悲劇,深刻詮釋了20世紀(jì)20年代中國城市女性的命運(yùn)多舛[35]。實質(zhì)上,虎妞是20世紀(jì)初期中國大多數(shù)女性的真實寫照。在當(dāng)時具體歷史和社會風(fēng)俗背景下,女性只有結(jié)婚,才被世俗認(rèn)可。虎妞非常害怕成為人人唾棄的未婚女人,很大程度上,這種心態(tài)是虎妞不顧父親反對,執(zhí)意嫁給祥子的最大動因。盡管虎妞能力很強(qiáng),甚至超過男人,能夠把車行經(jīng)營得很好,但是在父親劉四爺眼里,或者說,在當(dāng)時社會風(fēng)俗里,作為女性,虎妞的個人能力往往被忽視,女人的價值只能體現(xiàn)在嫁給男人、傳宗接代的惡俗上。虎妞難產(chǎn)而死不是個別現(xiàn)象,而是當(dāng)時殘酷的社會現(xiàn)實:舊中國新生兒死亡率高,尤其是貧困的城市底層階級。在Selvi看來,盡管虎妞的個人命運(yùn)被當(dāng)時的社會風(fēng)俗所左右,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有能力又有點(diǎn)積蓄的虎妞可以自己做主,決定自己的命運(yùn)。相比之下,貧窮的小福子完全沒有能力選擇自己的命運(yùn),唯一的希望也寄托于婚姻來解決生存問題。當(dāng)婚姻無望時,小福子只能靠出賣自己的身體來維持生活,養(yǎng)家糊口。Selvi以為,《駱駝祥子》揭示了貧困女人的無能無助以及被現(xiàn)實所迫只能寄予婚姻來維持生存的悲慘狀況。Selvi從歷史發(fā)展的角度,縱向?qū)Ρ确治觥恶橊勏樽印泛汀恫桊^》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指出:盡管《茶館》中女性人物王小華,作為茶館掌柜的孫女,有條件上學(xué)接受教育,不再以婚姻作為謀生的唯一出路,但是從女招待丁寶、小心眼的出現(xiàn),可以窺見20世紀(jì)40年代女性在中國社會的地位仍舊十分低下,相比較20年代虎妞與小福子而言,沒有根本性改變。實質(zhì)上,《茶館》與《駱駝祥子》向讀者清晰地展現(xiàn)了20世紀(jì)初葉中國百姓,尤其是女人的苦難。可以說,城市女人的生活暗無天日,外部環(huán)境沒有給她們提供改變苦難的可能性,更沒有給予她們足夠的空間和權(quán)力來創(chuàng)作生活的可行性。金錢,也許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改善她們的處境,然而多數(shù)女性缺少金錢,她們的生活更多是以丈夫為中心,所以她們沒有機(jī)會掙得更多的財富。20世紀(jì)是中國社會發(fā)生巨大變革的時代,然而這種變革具有不均衡性,尤其是對于女性在經(jīng)濟(jì)上、精神上的不公待遇。盡管女性在老舍作品中處于輔助、增色作用,但是老舍沒有忘記女性的苦難,他在作品中淋漓盡致地展示了那些堅忍、不屈不撓掙扎在艱難時世的女性形象。
隨著中國文學(xué)被大量翻譯成為各國文字,中國文學(xué)開始走向世界,成為世界文學(xué)的一部分。Thomas認(rèn)為,老舍作品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作為世界經(jīng)典文學(xué)的代表之一,小說《駱駝祥子》為豐富世界文學(xué)中城市工人階級人物形象做出了一定的貢獻(xiàn)。Thomas從世界經(jīng)濟(jì)學(xué)角度出發(fā),深入解讀《駱駝祥子》中的語言風(fēng)格、人物形象、主題涵義等,同時闡釋Rickshaw的來源。Rickshaw 一詞來源于日語,意思是“人力車”。二戰(zhàn)時期,隨著日本對亞洲國家不斷侵略擴(kuò)張,很多文學(xué)作品出現(xiàn)該詞,譯成漢語為“洋車”,寓意來自日本東洋的車。在Thomas看來,小說題目Rickshaw暗示日本對中國武力和精神的侵略。祥子的悲慘命運(yùn)是由社會、政治、經(jīng)濟(jì)等外因與人性內(nèi)因共同作用下產(chǎn)生的結(jié)果。當(dāng)時,中國進(jìn)步作家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主要在于農(nóng)村窮苦大眾的生活狀態(tài)。可以說,《駱駝祥子》的最大貢獻(xiàn)是開始關(guān)注城市工人階級狀況,并發(fā)現(xiàn)了城市工人自身的“個人主義”矛盾沖突。即,一方面祥子只考慮自身利益,冷漠地對待周圍一切人和事,最終無路可走,這種自私的“個人主義”是造成祥子悲劇的主要動因。另一方面,我們應(yīng)該看到,當(dāng)祥子放棄理想,不再堅持“個人主張”的獨(dú)立和自立精神時,就迅速墮落成可恥的社會混子。“個人主義”哲學(xué)的利弊關(guān)系,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小說矛盾沖突的張力。
在Thomas看來,《駱駝祥子》中描述的世界是一個出生死亡率高、濫用童工、封建愚昧、酗酒成性、家庭暴力、濫交性病的病態(tài)社會。小說甚至暗示虎妞與父親有過親密關(guān)系。嚴(yán)格意義上來講,這不是一部自然主義流派小說,而是以自然主義的某些元素反映出中國當(dāng)時社會的現(xiàn)實主義和作者的虛無主義世界觀的主題意蘊(yùn)。老舍的北京方言自成一個流派,很難被翻譯成其他語言。甚至,老舍自身帶有的對地方文化的熱愛與認(rèn)知的標(biāo)簽,也很難在譯文中體現(xiàn)出來。簡而言之,小說的語言藝術(shù)、人物形象、敘事結(jié)構(gòu)方面,都顯示出作者老舍超凡的寫作能力。在西方世界眼中,《駱駝祥子》是20世紀(jì)初葉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比較稀有的佳作,老舍不僅是地域色彩濃烈的北京作家、優(yōu)秀的中國作家,更是具有崇高地位的世界現(xiàn)代作家[36]。
全球背景下,老舍《駱駝祥子》翻越語言藩籬,走向世界,成為展示中國元素的文化符號、解讀中國故事并豐富其他理論知識的世界經(jīng)典文學(xué)作品。Vandertop從經(jīng)濟(jì)學(xué)的非均衡理論視角,比較老舍《駱駝祥子》和印度作家安納德小說《苦力》,探討發(fā)展中國家小說作品中的邊緣城市化和發(fā)展不均衡帶來的危機(jī)問題。非均衡理論從歷史角度,以形式主義方式,為解讀現(xiàn)代主義涵義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該理論揭示了20世紀(jì)初期世界經(jīng)典文學(xué)反射從民族到全球化發(fā)展過程中非均衡的經(jīng)濟(jì)因素阻礙國家終極發(fā)展的根本原因。Vandertop認(rèn)為,人力車,作為交通工具,暗喻一種拖垮、碾壓主人公命運(yùn)的“歷史車輪”。人力車是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流動與固定、手工與機(jī)械的混合物象征,它不僅推動故事情節(jié)發(fā)展,也暗示著全球背景下城市現(xiàn)代性的不平衡發(fā)展[37]。新時代,西方讀者在世界文學(xué)張力場中透視《駱駝祥子》,與之展開對話,發(fā)掘出人類苦難與人文關(guān)懷的主題意義,使其煥發(fā)出新的生命力,奠定了《駱駝祥子》世界經(jīng)典文學(xué)的地位。
自老舍《駱駝祥子》第一個英譯本問世以來的70多年里,不同譯本的副文本“反映出文本所處社會時代的復(fù)雜意識形態(tài)爭奪,以及意識形態(tài)對文本的影響與控制”[38]。《駱駝祥子》三個英譯本形象經(jīng)歷了由“美國夢”式的浪漫主義小說到世界經(jīng)典文學(xué)的曲折變化過程。譯本封面的中國元素信息也經(jīng)歷了由繁到簡、由多到少的過程。“封面不僅是傳遞譯文主題的關(guān)鍵場域,更是意識形態(tài)爭奪的臨界點(diǎn)。”[39]譯本封面異域風(fēng)情的歷時變化,說明西方對中國文學(xué)“東方主義”凝視的變化。20世紀(jì)初葉,西方從“他者”角度,對中國文學(xué)充滿明顯的歐洲中心主義偏見,譯本形象設(shè)計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西方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需求。改革開放后,中國文學(xué)被大量翻譯成外文,世界文壇開始出現(xiàn)“中國聲音”,由此改變了中國文學(xué)“缺席”的局面,并逐漸在世界文學(xué)殿堂中展現(xiàn)出獨(dú)特的“中國之美”。西方世界“撥開云霧”開始正視中國文學(xué)的內(nèi)核與價值,這也是老舍《駱駝祥子》三個英譯本封面的“中國風(fēng)”逐漸減少的原因。
老舍《駱駝祥子》多次重譯,反映出西方對中國文化認(rèn)知的不斷深入,這一認(rèn)知變化從譯者序言的有無以及序言的內(nèi)容上得到了最直接、最充分的體現(xiàn)。金譯本沒有譯者序,本質(zhì)上是為了滿足西方讀者獵奇心理的“美國夢”式浪漫主義小說;詹姆斯譯本中的譯者序是服務(wù)于學(xué)術(shù)研究的文學(xué)評論;而葛浩文譯者序讓位于“作者”,從尊重作者、尊重原作角度出發(fā),將寬廣的解讀空間留白給讀者,使目的語讀者積極參與世界經(jīng)典文本的意義建構(gòu)。此外,譯者聲音的“無”與“有”,這一變化不僅表明“隱身”的譯者以更直接的方式“顯身”并積極參與文本形象建構(gòu)與意義生成,更揭示出譯者序作為副文本,浸透微觀的個人“先驗”,以及折射出譯本所在年代的社會規(guī)范、意識形態(tài)和詩學(xué)特征等一系列歷史語境因素。
在過去的70多年里,三個英文譯本越來越忠實并完整地將老舍《駱駝祥子》呈現(xiàn)給英語世界讀者,為西方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國經(jīng)典文學(xué)創(chuàng)造了條件。在異域文化的傳播過程中,譯文不斷被解讀和評論,通過與文本對話,其意義不斷增值,生成新的意義闡釋空間。金譯本改寫原作結(jié)尾,在很大程度上有悖于原作的主旨。這一時期,海外評論順應(yīng)了西方社會政治意識形態(tài),相對忽略了老舍小說的藝術(shù)價值,但有些讀者對金譯文的改寫效果產(chǎn)生質(zhì)疑。接受者“所持的意識形態(tài)及審美立場往往影響或決定著譯文對原文的調(diào)整策略”[40]。新時期,西方掀起多元文化、尊重“異質(zhì)性”熱潮。詹姆斯重譯老舍《駱駝祥子》,從形式上忠實于原文,企圖再現(xiàn)小說原貌,再現(xiàn)作者創(chuàng)作意圖,海外老舍研究也開始脫離早期的意識形態(tài)控制。海外研究者從思想藝術(shù)、宗教文化等角度,開啟了文學(xué)性研究的先河。當(dāng)歷史的車輪進(jìn)入新時代,中國經(jīng)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社會經(jīng)濟(jì)文化等各方面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引起西方世界的極大關(guān)注。正視中國的崛起、了解中國文化成為當(dāng)今世界的熱點(diǎn)與焦點(diǎn)。葛浩文譯本從形式與內(nèi)容兩方面,最大限度地忠實于原文,為海外研究提供了可靠、權(quán)威的譯本。基于此,老舍《駱駝祥子》的海外研究由感性認(rèn)識走向理性分析,呈現(xiàn)微觀與宏觀相融合的綜合型、系統(tǒng)性、多元文化向度的研究趨勢。“譯作評論不僅可以總結(jié)歸納出譯作的成功之處,亦可以指出譯作中的問題,反作用于譯者以提高新譯本的質(zhì)量,進(jìn)而促進(jìn)譯作在目的語讀者中的接受。”[41]海外學(xué)者有著不同于中國學(xué)者的語境和學(xué)術(shù)背景,其獨(dú)特的異域身份、新穎的研究視角,即從“他者”跨文化視角觀照作家和作品,通過文本意義的發(fā)掘,激發(fā)了文本內(nèi)在的生命力,使文本內(nèi)外的價值得以有效銜接和連貫,不僅營造了良好的接受環(huán)境,更是與國內(nèi)研究互補(bǔ)互動、交相輝映,構(gòu)建“學(xué)術(shù)共同體”,從而真正實現(xiàn)了中西文化交流。
文本在翻譯、傳播、接受過程中衍生出來的封面、譯者序、評論等副文本因素,在某種意義上成為文本建構(gòu)的新成分,從而成為闡釋空間不斷生長、意義不斷增值的“星星之火”。《駱駝祥子》三個譯本見證了譯本在英語世界從“美國夢”式的浪漫主義小說到世界經(jīng)典文學(xué)作品的歷時演變過程。由此可見,積極思考和研究翻譯副文本之于中國文學(xué)走出去的意義,積極開展翻譯的副文本研究,剖析文本和語境之間的辯證關(guān)系,考察其折射出的復(fù)雜意識形態(tài),不僅有利于拓寬譯文闡釋緯度,推動跨文化交流,而且擴(kuò)展和豐富了正文本研究,對中國文學(xué)走出去的主動譯介有著深刻的啟發(f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