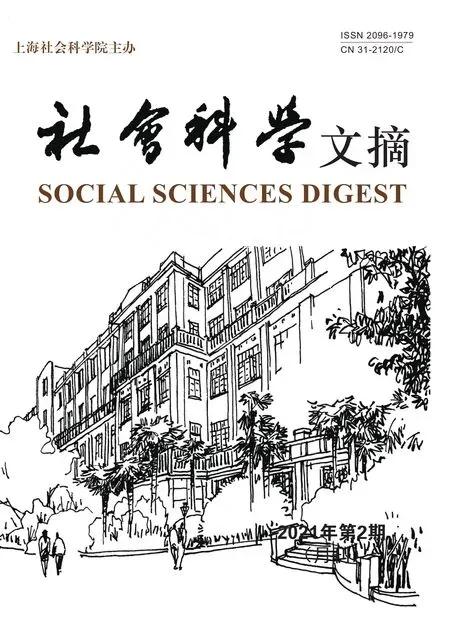中國小說的“中國性”管窺:以汪曾祺為例試駁“葛浩文之問”
文/歐陽燦燦
美國漢學家葛浩文曾批評中國當代小說受傳統章回體小說的影響,偏好描寫與情節無關的場景而顯得過于冗長。他從結構嚴謹的角度來評價中國小說,認為以《紅樓夢》為代表的中國小說沉迷于描寫瑣屑的生活場景,情節不夠緊湊,因而小說有喪失文學性與審美性而變成“百科全書”之嫌。我們認為,葛浩文所說的與情節無關的生活細節描繪,源于中國文學的“文”“人”以及“世界”相融合的表現傳統,體現的正是中國小說的“中國性”,亦即“中國特色”。中國當代作家汪曾祺繼承了中國古代文論傳統,自稱“不喜歡布局嚴謹的小說,主張信馬由韁,為文無法”,甚至因喜好描寫從表面看來與故事情節“無關緊要”的地方風俗而被稱為“風俗畫作家”。我們將以中國當代作家汪曾祺為例進行管窺式考察,以期回應葛浩文先生所質疑的問題。
文學能否獨立于世界與人
汪曾祺在其文章《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中明確表達了對中國古代文論的推崇。他并沒有明確解釋現實主義與中國古代文學之間的關系,但是他將兩者并舉,很明顯地表現出了他對中國古代文學重視真實、表現現實這一特點的察覺。但是,“現實主義”這一標簽掩蓋了汪曾祺所繼承的中國傳統文論與西方文論之間的諸多差別,對此我們尚需細心加以甄別。
西方文論的重要傳統,是理性地處理、制作文學作品,重視作品形式本身的美。前蘇格拉底時代,畢達哥拉斯就把美歸因于事物各部分的對稱與合適的比例,從事物的“數理形式”的角度闡釋美。亞里士多德認為悲劇情節的組合形式要有邏輯性,要具有整一美,這樣才能客觀真實地表現出對象超越個別的、真理性的意義,情節因其形式的整一美而獲得內容上的概括性,憑此作品才得以獨立于現實甚至獲得超越于現實的價值。康德提出美具有無利害性的特點,試圖使藝術擺脫社會現實的附庸地位,從藝術本身的形式要素如色彩、線條、音響來認識藝術的美。黑格爾強調真正的藝術品是內容與形式的密切結合,理念內容須呈現為感性的外在形狀,形式本身的美感問題不容忽視。20世紀俄國形式主義、新批評、結構主義等理論流派,把形式提升至文學的本體,挖掘文學作品的形式規律,并希望以此來概括文學生成的原因。敘事學理論更是認為文學作品的意義完全來自其形式結構,文學是獨立于社會人生的理性意識制作品。
西方文論家要求作品在形式上“合目的性”,根本原因是認為文學只是對自然或“理念世界”的摹仿,缺乏自明的獨立性、自足性,因而作家要以其主觀意志介入創作甚至作品,使作品的形式具有獨特的美感,從而擺脫對模仿對象的依附。具體到與我們的論題相關的現實主義文學,不僅重視文學的形式與結構,還力圖使文學在內容上成為現實生活的“理念”表征,具有類似真理一樣的概括力與表現力,從而如科學一般具有認識論的價值。18世紀的啟蒙文學把現實世界明確為理性主導的世界,并試圖引導人們以理性精神,即從科學的角度來認識這個世界。19世紀司湯達、巴爾扎克、哈代等諸多現實主義作家受到各種科學思潮的影響,更是致力于建構科學認識論為原型的文學世界。作者從廣延的維度想象、創造虛構的文學世界,從科學與理性的角度去思考人物性格與情節結構是否清晰合理,正如人們從牛頓力學與達爾文進化論的角度去認識日常生活世界。在其后遵循并著力表現遺傳學與生理學等自然科學知識的自然主義文學中,科學性取代審美性成為文學的第一性,可以說是現實主義理性精神進一步發展的結果。現實主義文學以科學世界觀與認識論為理論原型,目的是使文學獲得獨立的地位與價值。
汪曾祺在創作上受到歸有光和好述“因文見道”之言的桐城派的影響,因此他的現實主義創作論可溯源至文道論。雖然在“道”是什么,文學作品是不是應該表現“修、齊、治、平”之道等問題上,汪曾祺與歸有光及桐城派的看法不盡相同,但對于“文”“道”之關系,也就是文學與現實世界的關系,他們的看法是一致的。
首先,文道論表現了文論家對文學與世界關系的思考,從根本上推定了“文”對“道”的依附以及貫通關系,因此他們從不認為“文”能脫離現實生活而獨立存在,也不認為“文”有獨立于“道”的價值與意義。明代王祎在《文原》中言:“妙而不可見之謂道,形而可見之謂文。道非文,道無自而明;文非道,文不足以行也。是故文與道非二物也。”“道”無“文”表現,則無法為人所明,“文”離開“道”也無以立。文學因其與真實世界相關聯而具有價值。
其次,中國古代文論家承認“文”與“道”的合一性關系,他們并不著意探究“文”的獨立性與區分性價值,他們所側重思考的問題是文學作品如何抓住并表現心靈對“道”的感悟與體驗。中國古代文論中的文意、事辭、肌理、華實、文情、文理、情采、辭理等范疇都是探究如何用真誠細膩的“心”去感受體驗“道”,然后用適當的文辭表現出來。在中國古代文論家看來,文學要表達真實的事理情感,是毋庸置疑的先決條件,他們從不質疑優秀的文學作品與作者及世界的關聯性,也從不懷疑作品在表達情感體驗與社會生活經驗方面的真實性,而是特別關注如何巧妙地使“文”“道”“心”融合為一。“道”“心”“文”之間具有同構同感的關系,“心”能夠感知領會“道”,“文”也能表現“心”感知的“道”。這既是中國文論家思考問題的起點,也是彼此共享的不言自明的前提。
再次,是否偏好強調文學作品的形式從而突出其獨立的地位與價值,還體現在汪曾祺與西方作家對小說情節結構的不同看法上。18世紀英國小說興起之時,作家們致力于通過描寫大量的物質生活細節以使這種表現普通人的體裁獲得“現實感”,但他們逐漸認識到,作品的意義要通過建構因果序列的情節結構表現出來,因此,18世紀英國后期的小說情節結構逐漸走向了整一與緊湊。19世紀現實主義小說更是重視表現有因有果、首尾呼應、脈絡清晰的行為事件,以此構建統一完整、疏密有致的情節結構。小說中的日常生活細節描寫必須“掛”在情節上,指向通往結局的情節,為展示人物的行動服務,這些細節因指向人物行動的結局而表現出了某種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小說中的日常生活描寫由此克服了描寫對象的個別性、或然性與庸常性,獲得了高度的必然性與概括力。
這似乎讓熟悉外國文學的汪曾祺感到不安。我們從其創作談文集《晚翠文談》中,也能感受到他以外國小說的要求審視自己“結構尤其隨便”的小說時所隱約表現出來的焦慮。但他還是確信小說的意義來源于與現實生活、真情實感的關聯,而非其整一的形式結構。
建構“真”與“美”的“日常生活美學”
在文學文本與世界、人的關系上,西方文論普遍認為應該對文本進行理性“制作”,追求文本的獨立性價值,而中國傳統文論強調三者的合一性、同構性與合作性關系,倡導文學作品要真實自然地表現現實。但是,如果在表現現實時完全遵循生活的邏輯與常態,又該如何使得瑣碎平凡的生活具有美感?汪曾祺繼承了中國文學傳統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在處理“真”與“美”如何結合的問題時展現出了濃厚的“中國特色”。
汪曾祺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學中不是唯一但也十分重要的一脈傳統,即以審美的眼光看待人生但又不脫離現實,發掘并表現凡俗人生的“不凡”之處,建構日常生活的美學。
首先,凡俗生活中的人物可能社會地位卑微,沒有剛毅果敢、斗志鮮明的意志,缺乏朝向目的、強有力的行動,但他們不乏在平凡生活中尋找、發現、表達情致與趣味的傾向與能力,從而使凡俗的生活充滿溫情與滋味。汪曾祺不僅多次表明了要在凡俗人生中尋找樂趣和情味的人生態度,更認為這種人生態度具有真實地面對現實卻又不被現實打敗的強大韌性,是中華民族普遍的品德。
其次,這樣的生活是在直面現實生活的庸俗、痛苦甚至因死亡所帶來的虛無的基礎上,尋找發現人的智慧及“生”之樂趣,其人生態度依然是真誠地面對真實的人生。尋找理想生活與生命的意義,并不意味著對現實生活的全盤否定,更不是在直面現實生活的痛苦與虛無時徹底喪失活著的勇氣與尊嚴,而是清醒地活著,踏實地活著,感受活著的力量與趣味,因此能夠療愈人心,彰顯小人物存在的意義。《受戒》十分有代表性。這部小說完全剔除了宗教超越抽離于日常生活的維度,直面真實的人性需求,并且通過對各個人物的生活細節尤其是小英子一家吃穿住行的描寫,淋漓盡致地展現了日常生活的美好。小說以宗教為起始,在日常生活與宗教的兩極所構成的張力中,通過對各種生活細節、風俗人情的描寫,悄悄地消融了宗教壓抑欲望、遠離日常生活的冷漠與疏離的刻板印象,盡情開掘綻放出了人性以及日常生活溫暖美好的光輝。汪曾祺的文學創作一方面真切地表現了凡俗人生的經歷及體驗,對其不作“英雄主義”的拔高,小說情節的發展因此而遵從日常生活的邏輯,另一方面又試圖大力發掘并表現日常生活中非功利性的詩意、趣味與溫情,由此超越生活的瑣屑、平庸甚至虛無。汪曾祺小說中的日常生活描寫也因此有著獨立于情節敘事的審美價值。
再次,如何能夠發現“生”之樂趣與美好,主要憑借的是前文述及的能夠感知“道”、“貼著”人物、與他人同情共感的“心”。對生活的熱愛以及心中的溫情,使得汪曾祺小說中的人物既不回避現實,又能夠在現實生活中尋找到存在的樂趣與生活的意義。世俗生活中充滿溫情、能同情共感的“心”是汪曾祺日常生活美學的基礎,它既非巴爾扎克小說中追求“典型性”的物質描寫所體現出來的認識論價值,也非《包法利夫人》中展現物品之美卻受控于商品邏輯的消費主義。緊貼現實生活的同時以審美的方式對待生活,我們認為汪曾祺的創作體現了真正的“日常生活的美學”。
葛浩文批評中國當代小說受傳統章回體小說的影響,偏好描寫與情節無關的場景而顯得過于冗長,把小說變成文學百科全書,使得敘述不夠流暢。我們認為,西方文學自古希臘起以摹仿論為基本理論模型,在人物行為動作意志的沖突中提煉高度濃縮的意義,思考對人性的認識與探究,以嚴謹的結構形式傳達具有普遍性的象征意義,體現文學超越生活的獨立性價值。但中國古代文學重視作品、世界與人之間的同構性與合一性關系,強調作品以合宜的方式與分寸表現人與世界的融合性關系,在那表面看來無關緊要的、瑣碎的細節描寫中,其實包含著人的眼光、人的情感、人的體驗,這使得作家在對凡俗生活的描寫中建構起一種“日常生活的美學”。中國小說中許多在表面上看來與主要情節無甚關系的“瑣碎細節”與“生活記錄”蘊含著人的情感甚至是人情世故的“韻味”,充分體現了中國小說植根于日常生活的美學追求與對“原生態生活”中人的理解。而葛浩文過于拘囿于西方小說的審美標準,未能很好地察覺到這一點。在文學批評實踐中,這些特點實際上也是中國明清小說評點家津津樂道的小說妙處,當然也是小說中不可分割的重要內容,具有鮮明的審美性與文學性。
作者與語言、讀者的關系
與真實自然的審美內容相一致的是,汪曾祺作品中語言的平淡、自然與真實。他十分重視小說的語言,認為“寫小說就是寫語言”,要以日常化的語言真實、貼切、自然、自由地表達平凡的生活世界。他說,“寫小說決不能做文章,所用的語言必須是活的,就像聊天說話一樣”。這句話清楚而又巧妙地解釋了中國古代文論對文學語言形式的要求與目的,即強調文學與日常生活的貫通而非隔離,以及二者所用語言的貫通而非隔離。這句話也表明了強烈的“朋友式”讀者意識,即把讀者設定為彼此平等而又心意相通的朋友,以“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含蓄方式感動讀者,而不是以充分有力的說理以及緊湊清晰的形式去說服、征服、啟發讀者。
中國傳統文論家雖然認為文學形式技巧很重要,但又認為文學形式的最高境界是自然,形式應該消融于意蘊之中,其實也就是認為文學形式不具有完全獨立于內容之外的價值,語言形式應與所表現內容合一。他們雖講究形式與技巧,但是認為它們只是通達意蘊美的手段,在熟練掌握技巧之后,就要巧妙自然地運用技巧,自如地表達心靈世界。因此最好的文學作品渾然天成,沒有斧鑿的痕跡。宋代葉夢得在《石林詩話》中說:“詩語固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妙,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他還對比了“魚躍練波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與唐代詩人杜甫《水檻遣心》中的詩句“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認為兩者同為寫景,但是有造作與自然之別。前兩句是葉夢得根據晚唐和宋初西昆派的詩歌風格自己擬作的,意在諷刺只重形式、矯揉造作的詩風。而杜詩雖似平常,實十分工巧自然,每一字都非虛設。春天的細雨落在水面上,小魚兒常常會浮上來,如果是大雨,則不會有此情景。燕子的身體輕弱,非微風則不能借助風勢,以輕盈的身姿飛在空中。此詩句對仗工整,流暢自然,而又入情入理,渾然天成。追求自然和諧之美的文學家占據了中國古代文學創作界的主流。
汪曾祺所說的“寫小說決不能做文章”,其實就是葉夢得所言“不見刻削之痕”。語言既是形式,又是內容。在生動、活潑、富有生命力與表現力的日常語言中,“人”“道”“文”自如地結合在一起。它既真實地表現了世界,又意趣天成,渾然一體,巧妙自然地體現了“人”“世界”“文”的同構性與合作性關系,以及文學內容與形式的合一性。
汪曾祺強調小說語言“就像聊天說話一樣”,體現了他“朋友式”而非“受啟式”的讀者意識。“世界”“人”與“文”彼此依存、彼此同構合一的關系,不僅體現在作者與世界的關系上,還體現在讀者與作者的關系中。作者要對讀者身臨其境、感同身受的能力有足夠的信任與尊重,不能居高臨下地教育、告知與啟示讀者。汪曾祺相信,讀者與作者一樣有在日常生活中發現美與詩意的要求與能力,而文學創作的樂趣與意義就在于以含蓄、簡練、生動、形象的語言,激發調動起讀者的這種能力。因此文學創作不能過分直露地表達作者的觀點與思想,而應該以含蓄自然平淡的狀物摹情,達到與讀者交流的目的。
綜上所述,汪曾祺繼承了著意于“世界”“人”與“文”彼此依存、彼此同構合一的關系的文學傳統,而西方探索文學的獨立性價值。葛浩文對中國小說大量描寫與情節無甚關系的日常生活場景的質疑與不解,實際上反映了中國文學具有無法被西方文學及其詩學審美慣例拘囿的“中國性”。此外,如何重新認識并深入挖掘中國古代文論的現實意義,把它廣泛有效地應用于當下的文學批評實踐中,使它積極地介入當代中國文學理論的重建,在這方面,汪曾祺建構“日常生活美學”的文學創作實踐及創作論具有典型案例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