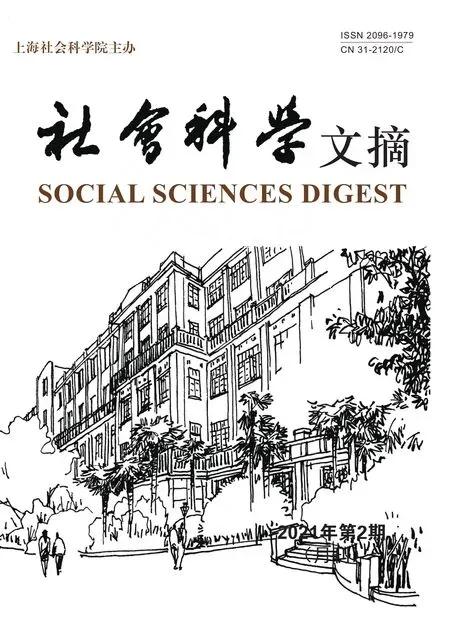農地政策調整的民情基礎
文/狄金華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之后,中國農地的整體性制度變革雖未發生,但圍繞具體的經營制度卻發生了諸多調整。要把握這些政策調整的內在機理,既要理解農地制度在中國體制中所具有的獨特地位,并以此為基礎,洞悉國家在農地制度調整中的實踐機制與治理邏輯;同時也必須理解不同時期民情的變化,要把握具體的民情如何影響農地政策,并與體制性的力量相互作用,共同推進農地制度的調整。
民情:理解農地制度變遷的視角
體制與民情、規制與順從構成了圍繞社會秩序達成的一切治理都需要面對的問題:作為理想狀態,體制與民情可以處在一種良性的互動結構之中,然而在實踐中,體制總是試圖對民情進行引導和規制,而民情卻不總是按著體制所規訓的方式來實踐;當民情與體制不匹配,而民情以公開或隱蔽的方式來“抵制”體制時,體制要么陷入“空轉”的困境,要么進行自我調整以順應民情。
體制與民情間關系的復雜性不僅表現在外部環境的變化會擠壓體制與民情之間的互融空間;同時也表現在民情本身并不是一個固定的、一成不變的樣態。民情自身的復雜性在于:在橫向上表現為其在不同的地域文化具有不同的秉性;在縱向上表現為時勢變動而致使它隨之發生改變。
在中國的語境中來理解農地政策的民情時,首先需要洞悉農地對于農戶的意義:一方面,農地既是農戶的生產資料,也是政府賦予他們的一種福利保障;另一方面,農業生產作為一種勞動過程,農戶總有勞苦規避的動機。追求勞苦規避與農地收入的最大化構成了圍繞農地民情中最為關鍵且又相互矛盾的部分,二者的此消彼長則構成民情變動的核心,民情的結構往往因不同地區經濟社會文化條件(如非農就業機會的多寡等)的差異及其變化而發生改變,進而形塑出一個變動的民情譜系。
農地制度實踐的體制性空間
20世紀70年代末,中央對農村的整體性政策仍是“以糧為綱”。在自上而下的體制性壓力下,地方政府必須保證糧食產量,而它們又不得不面對集體化經營方式效率低下的困境。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所能進行的“制度創新”只能是在不改變土地生產經營方式的前提下,改變組織內部的結算方式,以形成對農戶的激勵。真正促成地方政府在農地經營方式上做出調整的則是自然災害。安徽省肥西縣山南區作為最早實施“包產到戶”的區域,于1978年春推行這一經營制度調整的誘因即是當地遇到了大旱。換言之,正是體制性壓力加大,促成了地方政府釋放了民情實踐的空間。
因為工業化建設的過度投資、政府提高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減輕部分地區農村稅收負擔等原因,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社會的積累率大幅度下降,政府財政赤字增大,由此形成了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的“內源性的經濟危機”。作為危機應對,中央政府在體制層面做出調整來順應“包產”的民情,“開口子”允許在“地廣人稀、經濟落后、生活窮困的地區,索性實行包產到戶之類的辦法,讓他們自己多想辦法,減少國家的負擔”。
雖然農地制度的改革具有“甩包袱”的功利主義訴求,但因為農地制度及其治理本身具有極強的外部性,因此無論是在農地的集體所有制屬性的延承上,還是在整體耕地規模的穩定上,中央政府都設置了底線與紅線,一旦農地經營產生負外部效應(如誘發干群沖突),中央政府就會進行干預。正是顧及其外部性,所以政府一方面強調要將農地經營權交給農戶,但另一方面又強調要讓分發到農戶手中的農地產出更有效率。因此,在農地制度的變遷過程中,個體的保障與農地資源的優化配置、自治與官治就形成了一對相互影響的邏輯,彼此之間的空間也影響著農地制度實踐探索的路徑,以及民情得以實踐的空間。
“讓土地承包起來”:“單干”訴求與農地分配
包產到戶因為將生產經營單位重新調回到了中國傳統的家戶層面,加之其采取定額租的合約體系,因而激發了農戶生產的積極性,但同時它也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與農民平均占有農地訴求相對應,社區內農地因為水利、交通、地理等因素造成農地產出不均。為了實現農民的平均占有,包產到戶的制度導致農地在各家庭之中的占有呈現細碎化特點。
對于當時的農民而言,土地均分雖然會對水利、耕作帶來一定的沖擊,并使勞苦程度有所增加,但它卻滿足了農戶對于公平占有的訴求。換句話講,在分田到戶之初,農戶在農地分配之中,對公平占有的偏好是勝于對勞苦規避的偏好。形塑這種民情結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包產到戶政策實施之初,由于各種非農就業機會缺乏,導致農戶只能通過無限勞動力的投入來保障家庭所占有的土地收益最大化。
包產到戶政策實施之初,農地分配所面臨的民情基礎表現為,以村莊共同體的社區成員為邊界,以“家戶”這一中國傳統的生產生活單位來分配土地和組織生產,其中土地分配中的公平觀勝于耕作的便利觀,農戶對土地收益的追求重于對勞苦的規避,且這種民情結構在各地之間存在著高度的一致性。而上述民情特征的形成正是以農村非農就業機會缺乏、農戶異質性不高為前提的,而一旦這個前提發生變化,民情就會隨之發生變化,同時亦引起農地制度的調整。
“讓地權模式豐富起來”:農戶差異化需求與地權多樣化實踐
伴隨著包產到戶制度實施時間的延長,這一制度所產生的激勵效應和邊際收益逐漸下降,而外部結構的變化也使得民情本身發生了改變。
在政策層面,成員的變動導致附著在成員權上的農地亦隨之變動,由此要求通過農地的動態調整來應對社區成員的動態變動,在此過程中,農地調整與分割導致細碎化的程度不斷加深。在“生不增、死不減”的框架之下,政策將社區成員設定為分田初期的社區成員,并允許其在家庭內部傳遞,則令人口增長等原因使家庭間的農地占有產生巨大分化。另外,隨著20世紀80年代社隊企業和鄉鎮企業的發展,部分地區的農民有了從事非農就業的機會,這一部分農戶要求減少農業勞動力的投入。民情的發酵與演變同政策對糧食產量的徘徊不前共同構成了體制力量改變農地政策的決心。
1987年,中共中央提出在農村建立改革試驗區,其中圍繞農地制度建設,中央層面建立了三種地權模式的探索,即貴州湄潭的“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模式,明確土地集體所有權的有償承包使用,切斷了人口增長與土地再分配之間的關系;山東平度“兩田制”模式,在農地整治和田塊連片的基礎之上區分出按人口均分的“口糧地”和按競爭招標承包經營的“責任田”,并配套進行地力管理、農業服務等制度探索;蘇南、北京順義和廣東南海以土地規模經營為主要特征,試圖“利用大量勞動力轉移到非農就業的現實條件,運用經濟、行政和法律手段,實現土地相對集中和規模經營”。這種多樣化的地權探索背后是因為各地因其區位、非農發展及各種土俗不同而形成了農戶對農地的不同訴求。
20世紀90年代,當全國各地的農村都自主地進行農地政策調整之時,“兩田制”被廣泛采納;同時,“兩田制”的制度設計在被其他地方學習時,其他地方也依據自身的民情特征進行了一定的“改編”。這種“創造性的轉化”自然是地方社會基于地區性的民情特征進行的調整。然而由于“兩田制”制度實際上是將農地調整的控制權分配給村集體,而其他地區在引入“兩田制”時既沒有平度配套的對村集體的制度監管,又沒有相應的社會結構對村干部的謀利行為進行鉗制。這種制度實踐自然引發民眾的反抗,由此而引起干群關系緊張以及地方治理的沖突化。考慮到“兩田制”因為放權給村集體而造成代理人成本增加,中央政府出面壓縮了“兩田制”的制度空間,同時將有助于限制村集體自由裁量權的“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農地制度納入到中央主推的地權模式之中。
縱觀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農地政策實踐,其本質上是分化的民情結構誘發了多種樣態的地權模式。當這些地區模式“自由”地進行擴散時,由于不同地區的民情結構存在差異,具有“選擇權”的利益主體則可能選擇合乎其自身群體利益而悖于民情的地權模式。當多樣化地權模式“自由”地擴散導致基層社會矛盾沖突時,體制性力量便再次進入其中,“干預”地方社會對地權模式的選擇。
“讓土地流動起來”:體制與民情雙重作用下的土地流轉
隨著湄潭模式上升為全國主導性的地權模式,該模式背后運用市場機制來配置農地資源的訴求也隨之在全國推開。但與體制設計及體制的治理訴求不相匹配的是,起初農民并沒有強烈的農地流轉訴求。這一格局的形成既與長期以來形成的戀土情結相關,同時也與農戶從土地中所獲得的收益相關。
這種農地流轉民情發生改變首先是發生在1998年。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使中國已經建立的龐大的工業生產能力因無法向外出口而使得生產過剩問題首次在中國出現。作為應對,“當時中央的做法是推出農業產業化,為已經處于過剩階段的工業資本找到進入農業拉長產業鏈的機會”。當城市的工業資本進入農業領域,它必然需要土地進行流轉與集中,這形成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波農地流轉的訴求。第二波農地流轉的訴求則始于21世紀之初,隨著農業稅費的取消,以及政府對于農業生產的補貼加大,農業生產的獲利性增加,加之農業機械化及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農業生產的勞苦程度有所下降。在此背景之下,小農戶、家庭農場、合作社及農業公司等不同主體的農業生產積極性都有所高漲,而此時仍然延續自包產到戶以來的細碎化地權結構,就越來越不能滿足他們的訴求,改變這種細碎化的地權樣態就成為當下農村民情的核心。
農戶對因地塊分割、細碎化所導致的耕作不便(尤其是因為地塊分割而限制機械化使用)形成普遍不滿,這也形成了此一時期農戶針對農地經營的民情特征。這種民情在地區之間亦存在一定的差異:相對于平原地區而言,丘陵地區因地形地貌及水資源分布而在包產到戶初期,農地分級級別更多,故農地的細碎化、“插花”程度更高,當前進行按戶連片和按片耕種的訴求更高,進行相應實踐創新的動力也越強。
體制治理與民情回應:農地政策調整中體制與民情的互動
(一)體制的壓力與民情的訴求
農業與農地政策所具有的外部性特征決定了體制對于其民情考量的特殊性。中國農地生產經營的基本特點是:第一產業的收益弱于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在第一產業內部糧食作物的收益又弱于經濟作物。因此,無論是農民還是村集體或是地方政府,都有足夠的動力與熱情將農地非農化或是從糧食作物轉向其他高附加值的作物;但對于中央政府而言,它卻不得不考慮整體層面的糧食安全問題。劉守英、卡特和姚洋的研究業已指出,對于土地使用權和土地流轉限制最多的地區主要是國家糧食采購依賴的重點糧區,而在非主要糧食產區,國家對農民的自發選擇則予以了高度的彈性空間。
整體性的體制性壓力并不總是以犧牲局部的民情為代價;相反,它亦可能成為釋放局部民情的契機。20世紀70年代末農村改革的啟動雖然最終是體制對民情作出了讓步,賦予了民情得以實踐的空間,但這一體制變革的結構背景恰恰是體制治理所面臨的整體危機需要釋放農村的民情來予以化解。換言之,當民情與體制之間存在一定張力,且這種張力逐漸累積誘發成體制治理的困境時,它則需要釋放民情來化解這一困境。
(二)體制內部的張力與民情實踐的空間
中央在農地政策的設計中總是試圖限定代理人的自由裁量權,“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制度被中央“吸納”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此。此一時期民情的主導是希望地權結構能契合農民對于農地靈活、多樣化的占有,但當這種靈活占有的處置權交由村集體時,村集體的自利行為反而傷及了農戶的利益,并誘發了農村社會的沖突,構成了社會不穩定的因素。這種農地政策實施的“非預期后果”使得農村社會的主導民情從“配置農地資源求發展”轉向“配置農地求穩定”,而“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政策由于有助于約束村集體的自利行為受到中央政府的青睞,該政策的推廣與“主流化”背后顯然是基層治理的民情影響了中央,并主導了農地政策的走向,但這一政策與農民農地配置的訴求相比卻相去甚遠,農民通過農地配置謀求發展的民情被掩蓋和擱置。
除此之外,中央與地方的張力也可能使得地方得到“授權”以釋放民意實踐的空間。在自上而下的壓力型體制之下,地方政府為了完成自上而下的治理任務,尤其是這一任務需要釋放民情來完成時,地方政府則可能在體制內進行釋放,并引導政策以順應民情的方式來發展。只是這種地方政府的努力有時候是顯性的,有時候則是隱性的。
(三)民情的變動與體制性的回應
民情的生成機制決定了它與特定自然、社會條件及時勢特征是相關聯的,因此民情并不是一個單數,而是一個復數,而且是一個動態的復數。圍繞農地的民情,在平原農村與丘陵山地農村,以農業生產為主的農村與兼業化程度高的農村,農戶在農地訴求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用一種統一性的農地政策很難回應這種多樣化的訴求。同樣,由于土地分配所依憑的社區成員的權利既源自于法律的授權也源自于社區情理的認同,因此不同地區對于“成員權”的界定亦可能存在差異。這些差異反過來也要求中央政府在農地政策的設定上應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以給予地方政府結合具體民情特征進行選擇執行的空間。
民情亦會隨著時勢的變動而發生相應的改變。在包產到戶之初,圍繞農地的訴求表現為農戶對于公平性追求為主,而隨著非農就業機會的增加以及農業收入在家庭總收入中比重的下降,農戶對于農業生產經營的便利化訴求逐漸上升,成為民情的主導。民情的變動意味著雖然政策最初與民情相匹配,但隨著時勢的發展,其與民情則可能出現張力,此時政策必須隨著民情結構的變動而變動。
小結
本文以農地政策的變動為線索,分析了包產到戶之初,均分土地所帶來的規模不經濟及相互性困境,發現民情中存在兩股反向的力量——通過盡可能公平地占有土地而獲得家庭受益的最大化以及因農地平均分配導致細碎化后勞苦程度增加而無法有效進行勞苦規避。在包產到戶之初,由于非農就業機會有限,農戶對農地收益的追求勝于勞苦規避,這導致土地的細碎化;隨著非農就業機會增長及農業機械化運用,農戶對勞苦規避的訴求勝于對經濟收益的訴求,進而導致對土地連片的政策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