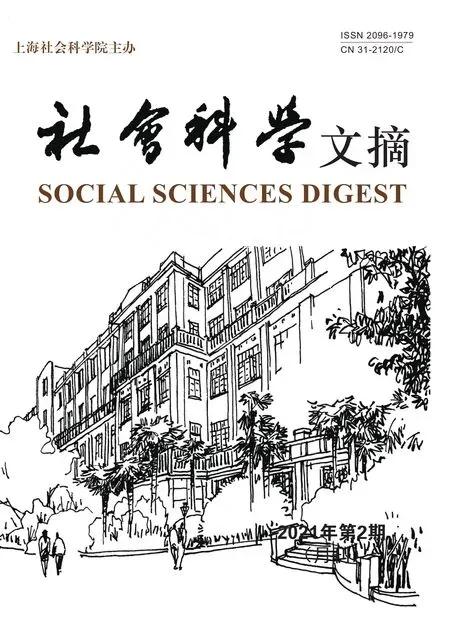美國戰略界為何沒能預見蘇聯解體
——基于認知相符理論的解析
文/吳大輝 王洋
本文嘗試使用羅伯特·杰維斯(Robert Jervis)的認知相符理論,解析美國戰略界對蘇聯解體的誤判。杰維斯是認知學派國際政治理論的領銜學者。“錯誤知覺”是杰維斯引入國際政治理論的一個心理學術語,指由于決策者對接收到的信息作出了誤判,其決策和行為隨之偏離了實際,導致的結果與決策者的原本意愿不相符。杰維斯認為,導致錯誤知覺生成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認知相符(cognitive consistency)在認識過程中的呈現。所謂“認知相符”,是指人們在理解和認識客觀世界時會有保持自己原有認識的趨向,當接收信息時,總是下意識地使新獲得的信息與自己原有的認識保持一致;如果接收到的信息與自己原有的認識不一致,他們就可能對新的信息視而不見,或是曲解誤斷,使其能夠與自己原有的認識一致起來。
美國戰略界對蘇聯經濟增速判斷中的認知相符
對于蘇聯經濟增長率的預測失誤,是美國戰略界沒能預見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美國的蘇聯學領域經濟學家們忽視了一些重要的現象,包括經濟增速的持續下降、軍費在國民經濟中的畸形地位、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經濟后果,以及1980年后的貨幣性不均衡,這些現象構成了“蘇聯解體的經濟因素”。美國經濟學家對蘇聯經濟預測中的集體錯誤,歸根結底是基于歷史類比的認知相符。本文認為,可以從研究者使用的預測方法、數據來源,以及他們所處的特殊社會環境中探尋原因。
(一)忽視蘇聯的特殊性加劇認知相符
美國經濟學家對蘇聯經濟制度的特殊性認識不足。縱觀西方經濟史,自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確立之后,經濟增速均呈現周期性波動,這一現象得到現實的反復印證,成為西方經濟學家的普遍共識和基本信條。問題在于,市場經濟和指令式經濟在經濟活動的組織中占據著兩個極端。由于美國經濟學家將西方市場經濟增長規律應用于蘇聯經濟增速預測,保留了對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強烈信念,而未能注意到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特殊性。這種信念讓他們在預測模型使用和數據詮釋中,有意無意地對蘇聯經濟增速進行高估,并選擇性地忽視20世紀70年代的預測失敗,在80年代繼續一路狂飆。可以說,對研究對象(蘇聯經濟體制)的認識不足,是經濟增速預測失敗的重要原因。延伸來看,研究者的預測和判斷均以歷史經驗和常識為基礎,而歷史經驗和常識源于研究者的過往經歷和所見所聞。加之,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第一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蘇聯是一種嶄新的存在,亦是美國社會科學家既有知識邊界之外的全新領域,這也增加了預測難度。
(二)長期存在的高估傾向加劇認知相符
當兩個國家處于持續且激烈的對抗時,高估對手而加緊防備帶來的額外代價,遠比因輕視對手而慘遭失敗要低得多。因此,在美國,當時存在著大眾對蘇聯經濟高增長的預期,美國戰略界對蘇聯的研究有意無意地在此問題上形成認知相符。當時美國民眾、學者及政府官員都傾向于相信蘇聯前途光明,堅不可摧。只有極少數美國的蘇聯學界經濟學家,在蘇聯解體前夕清醒地指出了蘇聯經濟存在的問題:蘇聯的資源可能會限制經濟的發展、工業界的經理人缺乏運作市場所必需的知識、長期的國家命令限制了工廠對市場作出快速反應的生產能力。但多數美國的蘇聯研究者在蘇聯解體前仍然認為其經濟形勢遠未達到導致國家解體的境地。處于這樣的輿論氛圍和情感傾向之下,如果經濟學家對蘇聯經濟前景作出悲觀判斷,其個人要承擔輿論壓力甚至利益風險,還有可能被指責因為低估競爭對手而誤導政策的重大風險。因此,無論是從個人利益角度出發,還是以美國國家利益為考量,對蘇聯經濟增速作樂觀判斷,都是合乎時宜、符合“戰略清醒”原則的明智選擇。
(三)蘇聯的數據虛高加劇認知相符
美國經濟學家進行經濟數據預測的第一步,是獲取并處理數據源。對于處在冷戰狀態下的美蘇兩國而言,獲取對方經濟數據的唯一可靠渠道,便是彼此發布的官方數據,然而,美蘇兩國在經濟統計指標、價格計量方法等方面均不相同,這給雙方學者造成了新的挑戰;與此同時,一旦數據源本身的質量存疑,即使數據經過糾偏和格式化,也無法產生可靠的預測結果。英國統計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對蘇聯數據的評價是:總是低估通貨膨脹因素,而夸大增長水平。對于統計數據虛高的情況,蘇聯國內的學者和官員也是承認的。
美國戰略界對蘇聯軍政關系判斷中的認知相符
戈爾巴喬夫上臺以來,蘇聯的軍事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在美蘇緩和的大氛圍下,蘇聯進行了大規模的軍隊裁撤,并逐年縮減軍費和軍備生產,使資源分配格局發生了重大轉變。面對大規模的裁軍計劃、軍費縮減以及聲譽損失,蘇聯軍隊的利益受到了從上至下的嚴重損害。美國戰略界對此非常敏感,密切關注軍隊高層人員的動向和表態,預測蘇聯發生軍事政變的可能性,考量戈爾巴喬夫對軍隊的掌控能力。
美國戰略界對蘇聯軍隊是否會在大規模裁撤之后發動軍事政變的判斷,本質上探討的是蘇聯的軍政關系、決策機制,以及戈爾巴喬夫對蘇聯軍隊的掌控能力。總體而言,美國戰略界對蘇聯軍政關系作出了正面評價,認為蘇聯軍隊實現了政治中立化,服從于文官統治,并不構成獨立的政治力量來影響國家的政治進程。換言之,戈爾巴喬夫領導的蘇共牢牢掌控著蘇聯軍事決策權,其對蘇聯軍隊的掌控力毋庸置疑,發生軍事政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美國戰略界對蘇聯軍政關系狀況的誤判,在于高估了戈氏領導的蘇共對蘇聯軍隊的掌控力,低估了蘇聯軍方人員在政治過程中的自主性和影響力。美國戰略界對蘇聯軍政關系判斷中存在嚴重的認知相符,充分相信蘇聯軍隊從始至終都是一個令行禁止的統一整體,是蘇聯政權最后的守護者。這種認知相符產生的原因,在于對蘇聯憲法關于蘇軍行動范圍的限制、蘇聯軍人不針對平民的信念、戈爾巴喬夫與軍隊關系的破裂等政治規制與現實,缺乏足夠系統的了解。因此,他們始終將規模龐大的武裝力量視作拱衛蘇聯政權的政治資本。
美國戰略界對東歐劇變判斷中的認知相符
蘇聯的解體,首先源于其帝國外部的叛離。因為東歐國家的政治進程是對蘇聯模式的徹底否定,在意識形態層面對蘇聯造成極大挫傷。在實踐層面,東歐的改革浪潮向蘇聯回流,加速了蘇聯國內的改革進程;東歐國家的和平分離,則鼓舞了蘇聯國內的分離主義。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加盟共和國的分離主義,均是造成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在某種意義上,東歐劇變是蘇聯解體的前哨戰。
作為與蘇聯纏斗了數十年的對手,美國對蘇聯在東歐的戰略布局和考量了如指掌,能夠感知東歐之于蘇聯的戰略地位下降、維系成本攀升,因此同蘇聯高層一樣,將東歐視作“包袱”和“火藥桶”,認為東歐的和平劇變對蘇聯而言不失為一種可喜的解脫。這是美國戰略界對蘇聯外交最嚴重的認知相符。這種認知相符的最大問題,在于它在進行精明的收益-成本分析時,忽視了東歐政治劇變的外溢效應,尤其是東歐政治進程與蘇聯國內改革之間的“影響循環流”(circular flow of influence),以及東歐成功脫離蘇東集團對蘇聯國內民族分離主義的鼓舞作用,未能預見蘇聯國內的改革進程和分離主義將被催化加速,最終也未能成功預測蘇聯因此解體的可能性。
美國戰略界對東歐劇變判斷中的認知相符源于兩個方面。其一,忽視戈爾巴喬夫個人的作用,這使美國戰略界無法理解蘇聯在東歐劇變過程中所作出的反應。對于戈爾巴喬夫拱手讓出東歐的行為,評價呈明顯的兩極分化。但無論戈爾巴喬夫在東歐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克制是出于對“全人類共同價值的追求”,抑或“對自身聲譽的渴求”,東歐劇變都是蘇聯解體的第一聲喪鐘,由戈爾巴喬夫本人敲響。其二,選擇性漠視東歐劇變的影響力。僅僅專注于東歐劇變后的“民主化”“市場化”和“西化”,就已經完全契合美國的利益與期待,這讓美國忽視了蘇東關系破裂對蘇聯政體安全產生的破壞性影響,陷入將有大批國家加入“第四波民主浪潮”的盲目樂觀之中。東歐演化方向符合理論期待所導致的盲目樂觀,是美國戰略界在東歐問題上產生認知相符的重要原因。
美國戰略界對蘇聯意識形態判斷中的認知相符
意識形態這一隱蔽卻又極為重要的問題,在反思蘇聯解體原因時容易被忽視。當國家尚存之時,要準確識別意識形態的崩壞程度及其對國家肌理造成的腐蝕,更是難上加難。另外,蘇聯末期百病叢生,經濟、民生、民族、軍事等顯性問題不斷浮現,美國戰略界的注意力幾乎全部集中于此,這進一步加劇了意識形態因素的隱蔽性。
回看美國戰略界的蘇聯研究,經濟和民族問題始終是關注焦點。當戈爾巴喬夫宣布以“公開性”和“民主化”作為政治改革目標之初,蘇聯的報紙雜志開始公開批評政府,諸多政治家公開宣布退黨時,美國的蘇聯問題專家卻始終沒有注意到這場毅然決然的政治倒戈背后,蘊藏著意識形態的徹底轉向,也未曾意識到對于蘇聯這樣一個依靠意識形態立命的帝國,意識形態的崩潰有何致命影響。
蘇聯突然活躍的政論氛圍的確引起了部分美國人的注意。然而,由于價值體系的不同,觀察人士無法將“言論自由”與“亡黨亡國”聯系起來,反而以贊賞的眼光看待蘇聯的這一新變化。美國戰略界并非全然沒有注意到蘇聯意識形態的新動向,但由于這一新變化與其信奉的價值觀——公開、自由、民主——完全相符,與其所期待的“和平演變”也基本契合,因此忽略了“蘇聯是一個意識形態帝國”這一基本事實,無法準確理解意識形態對于蘇聯政權安危的極端重要性。如此一來,即使有識之士觀察到蘇聯意識形態的松動,也難以預見這一問題的災難性后果。
美國戰略界之所以會忽略和誤讀這一重大現象,是出于兩個原因。其一,對“軟因素”的忽視。意識形態問題具有天然的隱蔽性,加上蘇聯時值多事之秋,意識形態的衰落成為“房間里的大象”,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除此之外,冷戰時期的國際關系理論集中關注經濟、軍事等可量化因素,而忽視意識形態等難以量化的“軟因素”,也是重要原因。其二,美國戰略界犯了“由己推人”的錯誤。美國戰略界未能認識到蘇聯意識形態衰退所帶來的嚴重后果,對蘇聯的社會狀態作出誤判,也是因為這種變化符合美國的期待,由此產生認知相符。在蘇聯解體前夕,意識形態衰退已經有十分明顯的跡象,美國戰略界看到了這些變化,卻不以為意,并不認為意識形態管控的放松會給蘇聯帶來災難性后果。意識形態方面的新舉措,對蘇聯政體而言是一種危險嘗試,但美國戰略界在對其進行判斷時產生了基于本國價值體系的認知相符,認為這是朝著“新聞自由”前進,是增強活力的體現。美國戰略界當時尚無法將“言論自由”“取消書報審查”與“亡黨亡國”聯系起來。
結語
美國戰略界對蘇聯解體預測中的認知相符,呈現出全面性的特征,并導致對蘇聯解體預測的集體失敗。
在經濟方面,蘇聯經濟于20世紀70年代達到峰值,從此之后陷入漫長的停滯。美國經濟學家意識到蘇聯經濟增速的放緩,但將其與“蘇聯經濟發展整體向好”的固有認知掛鉤,對經濟放緩的嚴重程度估計不足。
在軍事方面,借用技術情報手段,美國戰略界對蘇聯軍事實力有準確和翔實的認知。但對于蘇聯的軍政關系,尤其是戈爾巴喬夫與軍隊的關系,美國戰略界卻始終缺乏了解。美國戰略界忽視了蘇聯軍政關系的惡化,高估了蘇共對蘇聯軍隊的掌控力,低估了蘇聯軍隊在政治進程中的自主性,認為軍隊是保衛蘇聯制度最后的守護者。
在外交方面,美國戰略界低估了東歐劇變對蘇聯國內政治進程的影響,將東歐視為蘇聯的“包袱”,認為東歐劇變事實上幫蘇聯減輕了負擔,是為蘇聯帝國減負。然而,東歐劇變在本質上是對蘇聯模式的否定,彌漫于蘇東陣營的改革氛圍加速了蘇聯國內的改革進程,同時極大地鼓舞了蘇聯國內的分離主義。
在意識形態方面,美國戰略界忽略了“蘇聯是一個意識形態帝國”這一重要事實。意識形態問題本身不易被察覺,蘇聯末期經濟、政治、社會的種種劇變吸引了觀察者的注意力,在這些顯性議題面前,意識形態因素過于隱蔽而被忽略。即使有人注意到蘇聯社會的意識形態變化,但也相信這種變化是蘇聯政府掌控下的變化,意在增加蘇維埃國家的政治活力,因為這與西方國家通過“公開”“自由”“民主”保持政治價值活力的做法基本相符,因此無法準確理解意識形態對于蘇聯政權安危的極端重要性。
美國戰略界對蘇聯解體預測中出現了全面的認知相符,這導致對蘇聯解體預測的集體失敗。究其原因,有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基于固有思維的研究方法催生認知相符。蘇聯學界的研究方法過于強調抽象性而忽略單元主體特性,過于強調科學性而忽略蘇聯領導人的個人角色。冷戰時期的國際關系理論重視體系研究,認為國家個性將服從于體系結構。美國戰略界對蘇聯軍政關系的誤判,就是出自對國家特性的忽略。如果美國戰略界的研究者們將鏡頭拉近,從體系結構的宏觀視角轉向國家具體的獨立單元,便會注意到蘇聯憲法對軍隊行動范圍的約束、蘇聯軍隊的榮譽觀,以及戈氏與軍隊的齟齬,從而對軍隊維護蘇聯政權的意志與能力持謹慎態度,對蘇聯解體的可能性多一份想象。如果對俄國路標轉換陡然性規律有所認識,美國戰略界在面對蘇聯解體時也許不會如此錯愕困惑。
其二,蘇美互動中的國家信號與傳遞不暢催生認知相符。蘇聯政治過程的黑箱特質極大地壓縮了外界對于蘇聯的可觀測空間,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而且時常有意誤導,統計數據的失實給美國戰略界評估蘇聯真實狀況設置了很大的障礙。這導致對蘇聯“寧可高估、不可低估”成為美國戰略界普遍持有的心理,因高估對手而加緊防備帶來的額外代價,遠比因輕視對手而慘遭覆滅要低得多。在這種心理的作用下,盡管蘇聯疲態盡顯,美國仍然把它視為最具實力的對手,無法客觀準確地評估其實際狀況。加之蘇聯演化方向符合美國戰略界的期待,這一事實也強化了美國的樂觀態度。
其三,在美國的蘇聯學界,對意識形態問題研究的缺失催生了認知相符。當冷戰時期的兩大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均追求理論的科學性時,意識形態這一“不那么科學的”“軟因素”被徹底忽略了,而意識形態崩潰現已被越來越多的學者認定為蘇聯解體的終極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