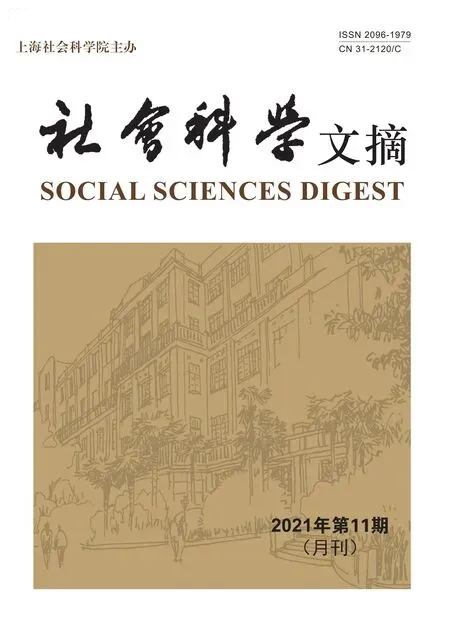論歷史認識的檢驗標準
文/喬治忠
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基點,就是主張歷史事物的客觀性,強調歷史學的社會科學屬性,歷史科學的目標乃是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為此,必須從理論上解決歷史認識檢驗的標準問題。
歷史認識檢驗標準的理論闡釋
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居于主導地位的語境中,多數學者在整體取向上恪守唯物主義歷史觀念。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一個基本原理,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談到歷史認識的檢驗,很自然地會首先思考怎樣運用“實踐”標準的問題。這存有一個困惑,就是如何闡釋“社會實踐”這一概念的內涵與實質,如何講清“社會實踐”檢驗歷史認識的內在機理。于是人們就一方面不承認“社會實踐”能夠直接檢驗所有的歷史認識,因而提出不同的分層次檢驗方式,析解出多種檢驗標準、檢驗方法,但析解后又試圖將各項層次性檢驗收斂、統一,“歸根結底”地納入“社會實踐”的“唯一”標準。如此一分一合,相關的解說十分勉強甚至自相矛盾。
實踐,在本義上就是指人們的實際行為,只要具備一種公共社會領域和行為指向的群體性活動,都成為整個社會運動結構的組成部分,都可稱之為“社會實踐”。毛澤東在經典的著作《實踐論》中指出:“人的社會實踐,不限于生產活動一種形式,還有多種其他的形式,階級斗爭,政治生活,科學和藝術的活動,總之社會實際生活的一切領域都是社會的人所參加的。”此處舉出“科學和藝術的活動”為例,顯示出社會實踐不限于物質的生產,而要點在于“社會的人所參加的”一切領域內的活動都是社會實踐。社會實踐的產出有物質產品也有精神產品,但作為人們群體活動的實踐,都是物質性的社會實踐。
在辯證唯物主義哲學中,“社會”是一種高層次的物質,人們的社會活動是物質性的運動。因此,學術研究、政治宣傳、文化傳播等等,從進行這些運作的人們角度來定義,都是實實在在、不打折扣的社會實踐。史學研究即史學實踐,是社會實踐的一種形態,不應當將之稱為“間接社會實踐”,不必劃分“物質實踐”與“精神實踐”。史學研究作為整個社會許多學者工作的總和,不能再看成是精神性的活動,而是人的活動、是人們被社會機制組織起來的物質性運動,其產出的歷史著述,才屬于精神性的范疇。將學術實踐排除于社會實踐之外的觀點,是保守、落伍、不正確的觀念。
毛澤東說:“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這不僅確定藝術活動、科學活動屬于“實踐”,更深切的意義是指明一個具體門類認識上的是非、正誤問題,要由與之相對應的實踐來驗證,而不是所有人、所有行業的實踐都來參與。在史學界許多涉及歷史認識檢驗的論說中,諸如“作為檢驗歷史認識真理性標準的實踐,應當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總實踐”“歷史研究的結論……最終要由全體社會成員參與的過去和現在的歷史進程的社會實踐來檢驗”等類似的說法屢見不鮮,實乃大言無當。試想工廠中制造飛機、汽車、服裝、食品、農藥等等生產活動,加上所有政治活動的實踐,怎么能夠檢驗我們對王夫之的歷史評價?怎么能夠檢驗我們對《明史》的評價呢?這是根本做不到的。直接檢驗歷史認識的實踐,總會是歷史學學術性質的實踐。因此在歷史認識檢驗標準的問題上,可以得出高度概括而又準確的命題:
史學界共同進行的歷史學學術實踐,是檢驗歷史認識的唯一標準。
所謂“史學界共同進行的歷史學學術實踐”,這里的“史學界”,是說當代進行歷史研究和歷史認識檢驗的成員,主要應當由專業的史家承擔,但“史學界”不是一種身份的固定畛域,任何人參與學術性的歷史研究,皆等于加入了史學界,是其中平等的一員。而“共同進行”的實踐,是每個學者研究活動的總括,其中必然充滿不同見解的爭論。如馬克思指出的“真理通過論戰而確立,歷史事實從矛盾的陳述中清理出來”,學術論辯正是在學術實踐中檢驗以往認識是否準確的重要機制,是現代學術實踐的固有內容,是推進認識向真理邁進的動力。
在近現代社會,學術已經形成相對獨立的運作系統,并且逐步擴大在整個社會生活中的所占份額。人類社會的一切問題,人類的所有重要行為之是非、得失,以及人們的價值觀等等,最終或早或遲都將在學術研討中予以審視和判斷。學術要審視的對象在原則上沒有限制,人為的學術禁區總會打破。學術性審斷的自身是發展的、不容易最終定論,而對比于其他非學術性審斷,則帶有最終審斷的性質。
在不少的論著中,提出歷史認識的史實檢驗、史料檢驗、邏輯論證等等,其實這些也都是歷史學者在學術實踐中的檢驗方法,是歷史學者將之運用,而不是史實和邏輯自動出來檢驗歷史認識。歷史學者是能動的主體,其在知識結構和方法之掌握上,需要包含以下各種要素:經過核實的史料證據,人類理性認識所積累和升華而來的邏輯思維,史學以及各個學術門類的知識積累與前沿探討,處于先進地位的歷史理論,各門類的先進學術理論和方法。總之,史料、邏輯思維、研究方法、歷史理論及各種前沿理論都可以被史家帶入學術實踐之中,對歷史認識的檢驗發揮作用。
歷史認識的檢驗是不斷推進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檢驗進程也同時是歷史的再認識進程。真理不可窮盡,歷史認識總體上沒有頂峰和終點,但不是所有問題都得不到最終的解決。在史學發展中,事實上已經解決了很多問題。許多史實得以考證,許多歷史評論得以確立。這切實顯示了相對真理向絕對真理靠近的步伐,那種對歷史認識持悲觀和消極的態度,是毫無根據的。史學實踐產生歷史認識,歷史認識再回到學術實踐中予以檢驗,這個進程不斷反復,實踐與認識的水平都在提高,歷史學從而實現發展和深化。
以歷史學的學術實踐觀破解歷史相對主義的挑戰
近代以來,從西方興起歷史相對主義的流派,從理論上表現為試圖否認歷史認識可以檢驗并且消解客觀的歷史事實。這對國內史學界有相當大的影響,造成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亂。
相對主義的歷史理論,其立說主要有兩大支點:第一,聲言歷史事件一去不復返,無法復制歷史研究的對象,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做反復實驗來檢驗,因而不能成為科學;第二,認為歷史往事以及相關的記載,如果不能被史家選擇,就毫無意義,進入史家頭腦并且通過思想中重新構建的歷史才是真歷史,但經過選擇和重構的材料,已經被史家的主觀思想所重建,成為主觀上認可的事實,就無法驗證也無須驗證是否符合原有的歷史事件。歷史相對主義的這兩個支點,我們應當以歷史學的學術實踐觀予以破解。
現在先看第一個問題。中國歷史學自產生以來對求真、實錄理念的堅持與貫徹。西方古希臘、古羅馬的史學產生之后,也立即確立了以如實記載為最根本準則。中國史學產生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執政者記錄史事的出發點就是保存史實以作備案,當時處于政權與社會大動蕩之后,也無法不如實地記載時事。至春秋時期,已經樹立了“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后嗣何觀”、“良史”的標準為“書法不隱”等理念。盡管這種記史求真觀念有時與統治者的欲望沖突,但其道義地位從未動搖,官方和私家都標榜所修史書為實錄,將“善惡具書,成敗畢記”“君舉必書,盡直筆而不污”列為規范。我們不要因為先前史籍未能達到完全真實,就輕視這種“求真”理念,有此理念為共識,即大大遏制了記史失實的現象。
西方古典史學從希羅多德《希波戰爭史》開始,希羅多德每每說明他所記述的某些情節,他自己也不能相信,顯示出一種求真意識。到修昔底德撰《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作者即聲明“這些事實是經過我盡可能嚴格而仔細地考證核實了的”。美國史學家J.W.湯普森指出:修昔底德“相信歷史家的首要責任就是消滅那些假的事實”,他的著述中沒有任何神話的成分。修昔底德真正建立起西方史學的著述規范,就是嚴格的求真態度。發揚修昔底德撰史傳統的史學家波里比阿(約公元前204—122),更富于嚴格的批判性,他認識到,“在歷史作品中,真實應當是凌駕一切的”。這種理念,在后來的博學時代的文獻匯編與鑒定、理性主義的史學思潮與德國蘭克客觀主義史學的暢行中得到發揚。
在記史求真理念的引導和制約下,中國、西方乃至整個世界,長時代的歷史學運行積累了豐富的成果,產生了大量的基本如實記述的史籍,歷史的宏綱大線基本確立,構成大體上符合客觀史實的系統認識。歷史的大事件、大線索基本得到如實的再現,這是相對主義、后現代主義的無稽之談所不能抹殺的。這里不是說史學遺產中不存在失實之處,不是說歷史敘述中沒有人們主觀因素的滲入,更不是說歷史研究中不遺留未能認清和未能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都是需要在不斷的歷史學學術實踐中逐步解決的。但即使有些終歸不能考察清楚的問題,也不能動搖歷史認識的總體架構,可以說是無傷大體。
當然,上述所有對歷史學文本能夠大體上符合客觀史實的樂觀性解析,無論中國還是西方,都是指史學正式產生之后,進行規范性記載的那個時間段,至于史學產生之前的傳說,則另當別論。
夸大歷史學與自然科學的不同,也是不正確的,我們試結合事例予以分析。例如點燃一塊木材,直到燒成灰燼,我們得出木材具有可燃性的認識。為了驗證這個認識,我們再次尋得一塊木材,仍然燃燒直至灰燼。在這個檢驗之中,是重復了認識的對象即木材嗎?第一塊木材其實已經燒盡而不可復制了,第二塊木材與第一塊不會完全一致,那么實驗所重復的只是人所進行的研究實踐。客觀歷史固然不可復現,但同一歷史問題的認識卻可以反復進行,我們所要檢驗的是歷史認識而并非歷史研究的對象,那么有什么必要總是強調歷史不能重復出現?為什么竟然不注意歷史認識的實踐可以反復進行呢?
歷史不可再現,人所共知,但如果我們假定歷史事件可以重現,也不能作為檢驗歷史認識的根本方式,因為歷史認識不單單表述歷史事件的實況,更重要的是予以分析、概括、總結、評價和置于整個歷史進程中的綜合論斷。例如關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事件,有許多不同的評價,都屬于歷史認識。假如重現這一歷史事件,至多增加一些直觀場景的感性認識而已,這對于檢驗該歷史問題的某種理性認識是無效的。諸如“焚書坑儒”是否屬于文化專制主義行為,是否是維護政權的必要舉措等等,該場景重現的意義其實不大,最終還是依靠學術實踐中研究和論辯來解決。
另一問題的要害,是相對主義的歷史理論強調:歷史認識是史家選擇材料在思想中重新構建而成,不被選擇和不能得知的歷史事件毫無意義,從而消解了客觀歷史的意義,只有經過思想重構才是真的歷史,真歷史是當代人構筑的。這就是克羅齊“一切真歷史都是現代史”命題的含義。后現代主義史學觀念流行之后,相對主義傾向更加徹底,通過將歷史理論的“語言學轉向”,干脆將客觀史實剔除于史學的話語之外。如美國學者海登·懷特說的,“歷史首先是一種言語的人工制品,是一種語言運用的產物”,“歷史總是我們猜測過去也是某種樣子而使用詩歌構筑的一部分”。因此他堅持認為歷史學與文學、藝術完全一致,都是充滿想象力而用語言構造的文本。這種說法盡管形成自我循環的封閉體系,倘若將之引出其自我話語的圈子,它能夠禁得住歷史學實踐的檢驗嗎?
第一,歷史撰述中固然存在主觀因素的加入,但自史學產生以來的歷史學實踐,反映在系統史學史研究的成果中,顯示了人們的主觀因素遠未淹沒對客觀史實的考訂和梳理。這種史學史反映的基本狀況,上文已述。要之,“求真”“求是”理念成為歷史學的共識,這是最大最根本的“主觀”意識,遏制了其他干擾史學的想象。歷史相對主義思想,不符合自古以來歷史學的實踐及其成果。
第二,馬克思主義不否認歷史認識中的主觀性因素,恰恰相反,而是十分重視認識上的主觀能動性。在尊重史實,維護“求真”這個歷史學底線上發揮歷史認識的主觀能動性,就會在歷史學學術實踐中更多地揭示具體的歷史真相,而且能夠獲得更深層次的抽象性宏觀認識。
第三,靠想象構筑的歷史敘事,在史學未曾萌生的遠古、上古時間段也曾存在,后來也被納入系統的歷史敘事之中,例如中國的“三皇五帝”傳說。但這恰恰是歷史學質疑和否決的對象,從宋代的歐陽修到清代的崔述,有力的批判持續深化,近代“古史辨”派的研究,更是作出較全面的清算。古人出于某種學術外的目的把這種傳說納入歷史敘事,乃是將之指認為真實可信,內在理路依然順從于歷史敘述需要真實的理念,與歷史相對主義理論認可歷史想象、想象之外無他物的說法并不一致。至于近現代,隨著考古學與基因人類學迅速發展,人類社會的遠古狀況正逐步揭開,這一久遠逝去的歷史時代,也具備了豐富的客觀資料,是可以被研究、可以被認識的,不是靠想象來構建。歷史相對主義理論在這一領域,也沒有立足之地。
第四,歷史相對主義的理論家,大多沒有做過歷史研究,大多沒有嘗試美國史、歐洲史或任何一處具體歷史問題的研究。同時他們對于系統的史學史的知識體系不甚了了,特別是對于中國史學史的系統知識,甚至是一片蒙昧。史學理論本應當在總結自古以來歷史學實踐狀況中、在學者自身的史學實踐中得出,歷史相對主義的理論家則在這方面一切缺如。那么,歷史相對主義這種什么實踐基礎都缺乏的理論從何而來呢?也許是靠收集某些哲學思潮、文藝思潮的泡沫,再經過想象加工、推衍發揮而成。這種活動如果也算是一種實踐,那也不是歷史學的實踐,其結論不應該當作史學理論。
綜上所述,歷史相對主義理論,與古往今來歷史學的實踐完全脫節,它自身也沒有學術實踐的基礎。因此,這種理論猶如海潮上的浪花和泡沫,雖然容易被看到也比較引人注目,但只能即生即滅,并不能融入歷史學大海的深層內容及結構。只要堅持歷史學學術實踐觀,就不難解決歷史認識論上的難題,不難破解形形色色主觀主義、相對主義歷史思想的沖擊。
在根本的意義上,人的認識緣起于人類的實踐,而認識又回到實踐中被檢驗,此為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本觀點。歷史認識論是史學理論的核心內容,做這項研究的學者,不能只是在中外歷史學理論“文本”的圈子里打轉,應當把自己的認識聯系歷史學的實踐:第一是深入了解以往的歷史學實踐及其成果,即掌握系統的中外史學史知識;第二是關注和梳理當下的歷史研究狀態;第三是擁有自己切實研究歷史問題的體驗。否則難以抵制各種錯誤史學觀念的影響,難以做出史學理論建設的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