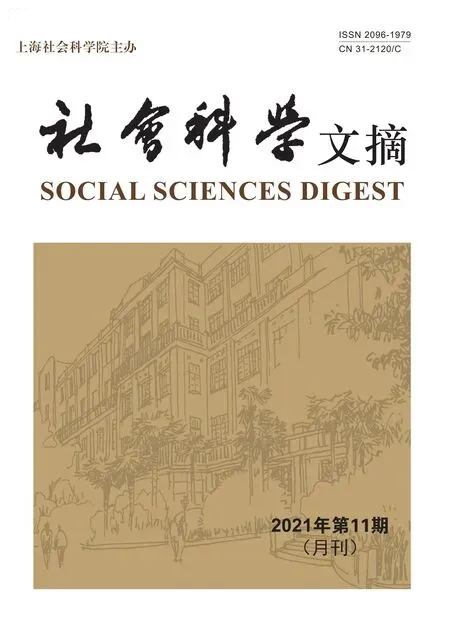互聯網使用如何影響居民社區融入?
文/周驥騰 付堉琪
(作者單位系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摘自《社會學評論》2021年第5期;原題為《互聯網使用如何影響居民社區融入?——基于“中國城市居民生活空間調查”的分析》)
問題的提出
隨著移動互聯網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和智能手機的普及,互聯網已經成為當代中國人民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網絡社會的崛起使人們的社會生活發生了空前復雜的變化,缺場的網絡空間與在場的地理空間之間的融合、并立與分化是這一進程中的核心問題。在城市社區中,這一問題突出表現為互聯網與在地社區的關系,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現有研究大都圍繞互聯網使用是否促進了社區融入這一問題展開討論,卻對互聯網究竟通過何種機制影響居民與社區之間的關系關注度不足。只有對這些中間機制進行探究,才能更好地揭示移動互聯網時代互聯網與社區深度融合的社會事實,理解網絡化背景下的交往行為以及空間整合模式。
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一)互聯網與居民社區融入研究述評
互聯網信息技術的發展給人們的經濟生產、社會交往與社會認同帶來了深刻的影響,推動了人類社會從群體社會向網絡社會的變遷。雖然許多學者對互聯網會導致社區失落的問題表示了擔憂,但更多的研究顯示,網絡信息技術對社會關系的影響機制具有雙重性:互聯網一方面使社會交往擺脫了對在場時空條件的依賴,但同時又與基于地方空間的社會參與息息相關,在不同情境中,二者可以分別或同時發揮作用。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地理空間與網絡空間之間的邊界是模糊的,人們在地理空間建立聯系,在網絡空間繼續展開交往,反之亦然。
并且,現有研究多基于互聯網發展早期的社會狀況,而隨著互聯網對社會的影響越來越深入,尤其是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之后,互聯網對鄰里社區的積極作用被廣泛證實。因此,本文認為互聯網使用會對居民的社區融入有顯著的積極影響,并提出假設1:互聯網使用會對居民的社區融入產生積極影響,且互聯網使用頻率越高,居民社區融入程度越高。
(二)互聯網對居民社區融入的影響機制
人們在網絡空間中,既有超越特定身份、場所和環境限制的缺場交往行為,也有基于特定組織、團體、地域的在場活動。對中國社會的網絡群體而言,人們雖然活躍在缺場的網絡空間中,但他們的存在根基與活動內容卻與地方空間有不可分離的內在聯系。網絡群體本質是地方群體的網絡化,是社會群體實現的地方空間與網絡空間的融合。故要回答互聯網如何影響居民社區融入這一問題,必須將居民的互聯網使用行為置于網絡空間得以有效展開的社會情境中,考察地理空間中的城市社區居民借由互聯網建立社會聯系、形成社會群體的具體路徑。
現有互聯網與社區的研究多從互聯網的媒介與關系屬性兩個基本視角展開,前者認為互聯網是社區媒介系統的一部分,是居民現有信息來源的補充,后者側重于強調互聯網為居民搭建社區關系網絡提供了新的途徑。此外,在網絡空間與線下空間的互動過程中,社區生活中缺場與在場的融合有著生動的體現。據此,本文沿著關系、媒介與空間三個視角,考察在線社區交往、社區信息傳播、線上線下轉化三種機制對居民社區融入的影響。
第一,在線社區交往。通過互聯網,社區居民借助在線社交工具展開社會交往,從而增加社區認同,促進社區參與。以社區論壇、QQ群、微信群等代表的在線社區網絡快速發展,成為居民日常交流的重要平臺。通過在線社區交往,居民逐漸形成了具有凝聚力的社會紐帶和情感認同,進而增進了社區參與。據此,本文提出假設2:在線社區交往在互聯網使用與居民社區融入之間起中介作用。
第二,社區信息傳播。除了提供線上溝通交流的平臺,互聯網還是當今社會重要的信息媒介之一。根據傳播基礎結構理論,促進社區歸屬感、集體效能感和公民參與的最重要因素是要有一個活躍的“故事講述網絡”,網絡社區媒介豐富了居民獲取社區信息的渠道,提升了居民在故事講述網絡中的參與度,利用網絡社區媒介獲取社區信息,是居民增加社區社會資本、促進社區認同、提升社區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徑。據此,本文提出假設3:社區信息傳播在互聯網使用與居民社區融入之間起中介作用。
第三,線上線下轉化。線上的交往行為往往嵌入線下社會空間之中,反過來也對線下空間產生著影響。這一線上向線下轉化的動力同樣成為互聯網促進居民社區融入的路徑之一。已有研究顯示,城市居民社會網絡線上向線下的轉化率約為25%。不僅如此,網絡空間還為社區生活開辟了新的公共空間,線上互動與線下交往的融合動員了社區集體行動,培育了社區公共生活。據此,本文提出假設4:線上線下轉化在互聯網使用與居民社區融入之間起中介作用。
根據上述討論,本文建立如下研究框架(見圖1),嘗試從網絡空間分化與整合的視角出發,探討互聯網影響居民社區融入的具體路徑。

圖1 互聯網影響居民社區融入的分析框架
數據、變量與方法
(一)數據
本文使用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于2018—2019年開展的“中國城市居民生活空間調查”的京津冀十城區數據進行分析。剔除重要變量的缺失值后,本文選取2003個樣本進入分析。
(二)變量
本文將因變量社區融入操作化為社區認同與社區參與兩個部分。社區認同包括社區功能認同和社區情感認同兩個維度,得分越高,表示社區認同感越強。社區參與包括公共事務參與和鄰里交往參與兩個維度,得分越高,表示社區參與度越高。
本文的核心自變量為互聯網使用和互聯網使用頻率。
本文選取在線社區交往、社區信息傳播和線上線下轉化作為中介變量。在線社區交往方面,考慮到微信是當代中國居民最重要的線上交往工具,而微信群是居民在線社區交往最重要的途徑,本文用受訪者加入的與本小區相關的微信群的數量來測量居民在線社區交往的廣度和水平。社區信息傳播被操作化為兩個維度,第一個維度是網絡信息渠道,本文將“關注了與社區相關的微信公眾號”的樣本賦值為1;第二個維度是網絡信息信任。線上線下轉化方面,問卷詢問了被訪者過去一年參加本小區論壇、微信群、QQ群、公眾號等平臺組織的線下活動的次數,本文將參加過線下活動的樣本賦值為1。本文的控制變量包括兩部分:社會人口特征和居住特征。
(三)方法
本文選擇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對互聯網使用對居民社區融入的影響進行分析。此外,由于互聯網使用存在自選擇問題,為檢驗多元線性模型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采用傾向值匹配法(PSM)來解決樣本選擇性偏差問題。通過穩健性檢驗之后,為了考察互聯網使用對居民社區融入的影響機制,即檢驗在線社區交往、社區信息傳播、線上線下轉化是否在互聯網使用與社區融入之間起中介作用,本文采用了依次檢驗和Sobel檢驗的方法。
研究結果
(一)互聯網使用與社區融入
社會人口學特征方面,男性居民社區情感認同、公共事務參與水平更低;年齡越大,社區情感認同、公共事務參與水平更高,但年齡二次項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年齡對社區情感認同、公共事務參與的影響存在邊際遞減效應;有配偶的居民鄰里交往頻率越高;受教育年限越長,社區功能認同水平越高,鄰里交往參與水平越低,公共事務參與水平越高;年收入越高,鄰里交往參與水平越高,公共事務參與水平越高。居住特征方面,居住時間越長,社區情感認同、鄰里交往參與、公共事務參與水平越高。住房產權變量主要作用于社區功能認同和鄰里交往,社區功能認同方面,從高到低依次為租房、商品房、回遷房、單位房居民,而鄰里交往方面則恰好相反,從高到低依次為單位房、回遷房、商品房和租房居民。
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是否使用互聯網與居民社區融入各指標之間的關系表明:使用互聯網的居民在其他三個指標上均顯著高于未使用過互聯網的居民。且互聯網使用頻率越高,居民社區融入狀況顯著更好。除了社區功能認同之外,使用互聯網的居民在社區融入其他三個指標上的得分均顯著高于不使用互聯網的居民,這與多元線性模型的回歸結果一致。傾向值匹配分析的結果表明,在控制了樣本選擇性偏誤的情況下,互聯網使用仍然對居民社區融入有著積極影響,這證明了結果的穩健性,假設1得到證實。
(二)互聯網影響居民社區融入的中介效應檢驗
1.在線社區交往中介效應檢驗
互聯網使用頻率顯著增加了居民在線社區交往的頻率。社區功能認同方面,在線社區交往對社區功能認同的影響不顯著,因而不存在中介效應;而在社區情感認同、鄰里交往參與和公共事務參與方面,中介效應均顯著,Sobel檢驗亦通過,中介效應分別占總效應的6.06%、9.34%、8.60%。分析結果說明居民互聯網使用頻率越高,在線社區交往越頻繁,進而促進了社區融入。由此可見,除了社區功能認同外,在線社區交往在互聯網使用和社區融入其他各指標之間起到中介作用,從而支持了假設2。
2.社區信息傳播中介效應檢驗
本文將社區信息傳播操作化為網絡信息渠道和網絡信息信任兩個維度。網絡信息渠道的中介效應檢驗的回歸結果顯示,在控制了其他變量之后,互聯網使用頻率顯著提升了居民通過網絡信息渠道接受社區信息的概率,并且網絡信息渠道提升了居民的社區功能認同、情感認同以及鄰里交往、公共事務參與水平。模型納入網絡信息渠道的中介變量之后,總效應互聯網使用頻率的系數和顯著性水平明顯下降。網絡信息信任的中介效應檢驗的回歸結果顯示,網絡信息信任對互聯網影響社區功能認同、社區情感認同、鄰里交往參與和公共事務參與的中介效應均顯著,且都通過了Sobel檢驗,中介效應分別占總效應的17.72%、29.86%、30.26%和34.85%。
以上結果說明居民互聯網使用頻率越高,從社區網絡媒介就獲取了更多有效信息,進而促進了社區融入。由此可見,社區信息傳播在互聯網使用和社區融入各指標之間起到中介作用,從而支持了假設3。
3.線上線下轉化中介效應檢驗
線上線下轉化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顯示,在控制了其他變量之后,互聯網使用頻率顯著提升了居民線上線下轉化的概率。線上線下轉化提升了居民的社區功能認同、情感認同以及鄰里交往、公共事務參與水平。模型納入線上線下轉化變量之后,總效應互聯網使用頻率的系數和顯著性水平明顯下降。由此可見,線上線下轉化在互聯網使用和社區融入其他各指標之間起到中介作用,從而支持了假設4。
上述對三類影響機制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表明,除在線社區交往對社區功能認同外,在線社區交往、社區信息傳播和線上線下轉化在互聯網使用頻率對社區情感認同、鄰里交往參與和公共事務參與四個社區融入指標的影響中均發揮著中介作用。
(三)不同互聯網使用行為的影響差異
為檢驗不同互聯網使用行為對居民社區融入的影響差異,本文選取了兩類典型的互聯網使用行為,交往行為(用“社群交往”行為的頻率來測量)和信息行為(用“獲取信息”行為的頻率來測量)分別進行回歸。結果顯示,交往行為提升了居民的社區情感認同、鄰里交往參與和公共事務參與水平,對社區功能認同的影響不顯著;信息行為提升了居民的社區情感認同和公共事務參與水平,對社區功能認同和鄰里交往參與的影響不顯著。這一結果表明,不同的互聯網使用行為對居民社區融入水平的不同維度的影響是有差異的,相較于信息行為,交往行為作用于居民鄰里交往的效應更為明顯。網絡交往行為與信息行為都未提升居民的社區功能認同,可能的解釋是社區功能認同反映了居民的居住滿意度,與居民互聯網使用行為的關聯并不緊密。
結論與討論
本文基于網絡社會空間分化與整合的視角,探究了互聯網使用對城市居民社區融入的影響機制。首先,在場的社會空間構成了居民社區融入的社會基礎,不同社會人口特征和居住特征的居民社區融入狀況存在差異。其次,互聯網使用對居民的社區情感認同、鄰里交往參與和公共事務參與發揮著積極作用。再次,影響機制方面,互聯網使用通過在線社區交往、社區信息傳播和線上線下轉化三種中介作用機制促進居民的社區融入。最后,不同互聯網行為對社區融入的影響具有異質性,交往行為促進了居民的社區情感認同、鄰里交往和公共事務參與,信息行為對鄰里交往的影響則不顯著。
許多研究都強調網絡社會的崛起使社區的地域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個人為中心的跨越空間的社會網絡,但此類研究大都只關注了缺場的網絡空間對傳統社會的在場空間的替代作用。本文則聚焦于互聯網與地方社區的連接環節——在場的網絡空間,指出網絡化條件下社區的地域性不僅沒有消失,反而促進了居民在地的社區融入,研究結果表明互聯網能夠為對地域性社會網絡的構建提供更豐富的渠道。特別是在當今移動互聯網高度發達的城市社會中,在線的網絡空間和地域性的社區空間相嚙合,人們在網絡空間中展開社區交往,獲得社區信息,建立情感連接,融合線上與線下的在場網絡空間的社會意義將進一步凸顯。
網絡化時代信息媒介及內容的極大豐富使人們社會交往的方式帶有越來越強的符號化、游戲化特征,不僅降低了人們連接與組織的成本,也推動著感性經驗的傳遞和認同性資源的集聚。隨著互聯網在居民社區交往、參與、認同中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網絡社會背景下的社區建設與社區治理也正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基層社區治理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環節,在治理實踐中不能僅局限于利用互聯網技術展開更精密的社會管理,還應當轉變思維方式,發揮互聯網的信息媒介和社交網絡的功能,建設社區新媒體,整合數據資源,拓展應用場景,積極促進居民鄰里交往與社區參與,打造服務型、智慧型的“互聯網+社區”“互聯網+基層治理”的社區治理新模式,推動城市社區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