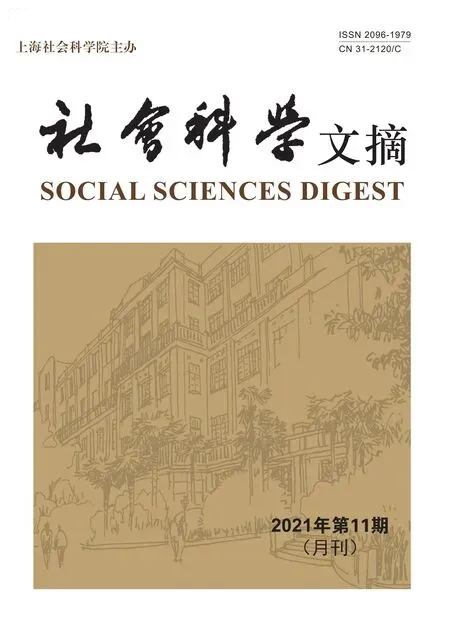十年“新子學”:從學術構想到文化引領
文/曾建華 蘇詩悅
(作者單位系揚州大學文學院;摘自《管子學刊》2021年第4期;原題為《古今學問事,十年“新子學”:從學術構想到文化引領》)
通常學界認為子學即諸子之學。狹義的子學乃指著書立說自成一家的原創性學術;廣義的子學則將后人對歷代諸子及其著作的研究也納入子學系統中。就文獻層面看,子學是相對于四部分類中的經學、史學與集部之學而言;就思想層面看,子學乃是士人對其所處時代困境的反思與爭鳴,是超越于元經學思想的知識體系和學術理念,也是士人觀念得以確定和發展的內在力量。而當前所謂“新子學”,主要是指基于傳統“子學”與現代“西學”所提出的新的學術理念、方法路徑和文化觀念,乃是作為一種多元、開放的“新國學”構想,試圖打破經學(儒學)主導下所造成的中西對立的“舊國學”觀念而出場。然而,由于“新子學”尚未建構出“新”(有別于傳統學術)的思想體系和方法理論,因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理論困境,不斷徘徊于“新國學”與“新哲學”的兩端。故此,筆者于“新子學”十年創構之際,再度梳理“新子學”之發生理路,并嘗試將“新子學”構思為一個反思傳統學術、實現文化引領的新型知識譜系。
從爭論走向共識
2012年,方勇先生終于向學界拋出醞釀已久的“新子學構想”。其認為,子學產生于文明勃興的“軸心時代”,是以老子、孔子等為代表的諸子百家汲取王官之學精華,并結合時代新因素創造出來的新學術,具有與時俱進的革新品質,比之經學更具有開放、多元、平等的現代性意義。因此,方勇先生希望借助傳統學術資源的現代詮釋,不斷從元典中攝取創生性、開放性、多元性和對話性的學術思想,以逐步破除經學思想所主導的封閉、專制的舊國學理念,從而為加快傳統思想資源的創造性轉化,實現民族文化的新變革、新發展,最終為中華之崛起提供思想資源。正是從這一刻起,方勇先生驟然以“莊學專家”的身份,開啟了心之所向的學術“通人”的理想之途,由此引發了文史哲諸多領域的廣泛討論。
北京大學中文系張雙棣便強調,新子學要著眼于創新,廣泛借鑒雜家寬容平等、兼收并蓄的思想理念,發展諸子多元的思想觀念;廈門大學新傳學院謝清果則認為,新子學之“新”在于子學對“禮崩樂壞”時代問題的回應意識,其既回應了在當代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進程中提升文化自信的需要,又回應了中國向世界貢獻建構和諧世界思想資源的使命;東南大學哲學系許建良則進一步將“新子學構想”解讀為一種思想認識的革命,而將儒家回歸為諸子百家之一,以期突破偏重儒家的現實局限,從而進一步推動我國學術的轉型;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宋洪兵則著眼于未來中國信仰體系的多元、包容、平等、對話的新趨勢,力陳“新子學”構想在未來中國社會結構中的重要作用。盡管各家之言各有偏重,然而均基本認同“諸子學”作為國學之主體,具有多元、開放與包容的學術精神,因此,其本質便是與時俱進、日用而日新的“新子學”,必然在未來中國學術文化的構建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隨著探討的深入,“新子學”到底新不新,其理路是否正確、是否重要已不言而喻。而學者們關心的話題也從對“新子學”現實作用的宏大構想,轉向其本質屬性的詮釋與切實可行的理論創構。比如,華中師范大學高華平便將詮釋的重點從“新子學”之“新”,轉向了“新子學”之“子”,認為“新子學”之“子”即當代具有獨立人格精神的知識個體(知識分子),而他們的學術活動和成果就是所謂“新子學”。其時筆者也有類似的思考,認為“新子學”務必將子學研究與士人傳統進行合理的關聯,并通過對子學發生、發展及其文化建構與士人傳統之變遷的復雜關系的考察,進一步揭示子學向“新子學”化生的內在動力,從而確立新子學命題的合法性和超越于個案研究的有效路徑。
不過,“新子學”最初的“構想”雖稱宏大,但多著重于概念框架的設置而缺乏思想史的梳理,因而很難深入到子學發生、演化及其文化創生的層面,更難從本質上區分新、舊子學之淵藪,進而明確“新子學”的理論構建與方法路徑。因此,“新子學”只有對新時代所面臨的新問題給出建設性的具體方案,才能真正實現傳統與現代的對接,開創一個新的百家爭鳴的時代。正是這一系列的問題,逐漸引發了筆者對傳統中國學術之弊的進一步反思。
中國傳統學術之弊
在中華文化的傳統中,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思想世界里,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情結:即渴望一種基于權力關系而形成的觀念秩序,“經學化”的儒家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中應運而生的。于是,本作為一種社會倫理而存在的“三綱五常”,便逐漸被漢儒內化為一種具有神圣性的精神秩序與觀念結構,進而確立為儒術獨尊的思想格局,由此主宰了古代中國人幾乎全部的精神生活、禮儀規范與學術傳統。哪怕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與長達百年的現代性啟蒙,其依然頑固地存在于國人的思想世界之中,在社會文化的各個層面均占據著重要的位置,發揮著“經學”的主導作用,這便是“新子學”所指斥的“經學思維”。
經學主導的時代容不得新銳的思想,從而阻斷了中國社會的科技創新與良性循環。而“經學思維”的核心特征乃是強調永恒的中心與不變的秩序,由此營造出一個極具優越性的“自我”,并試圖以這個“自我”的意志去主導社會、政治和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而當下中國已然處于一個科學、民主、平等、公正、開放、多元、包容、進步的全球化格局之中,并對未來世界之進程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如果再以經學化的儒家思想去接洽當下的世界,抑或試圖以此去建構當下的學術生態,進而期求借助這一學術生態去解決未來世界的相關問題,其結果無異于緣木求魚、刻舟求劍。
吊詭的是,當今學界(本文所涉及的“學界”與學科僅指人文學科領域)雖已廣泛接受了現代性的洗禮和學科專業的分工,但由于經學思維的根深蒂固,而趨于不同程度的偏執、僵化、封閉甚至內卷,其直接表現便是學術的圈層分化與學者的代際割裂。
所謂圈層分化,主要是指不同學科以及同一學科的不同方向,由于問題導向與視野差異而產生的學術分化與話語阻隔,從而使各個領域的學術研究不同程度地呈現出碎片化、項目化與煩瑣化傾向。尤其是項目化,本是為了促進學術繁榮,但卻迫使學術研究呈現出日益嚴重的行政性、應時性與依附性的特征。所幸,面對傳統人文學術愈演愈烈的“精耕細作”式研究,學界已有較為客觀的認知與反思,一些前沿學者甚至已經嘗試提出某些可行性的解決方案。比如,早在2005年,葛兆光、楊念群等人文學者,便開始積極尋求突破傳統人文研究范式的良性發展之路。2020年11月22日,張江、周憲、朱立元、丁帆、鄧安慶、曾軍、成祖明、李紅巖等人文社科的知名學者,更紛紛呼吁以當代闡釋學理論破除學科藩籬,進而建構一種整體性的研究視野和跨學科的學術范式。這次論壇的召開,對于反思當下學界之弊端,重構人文學術之使命無疑具有方法論性質的指導意義,對我們“新子學”之未來發展自然也就具有不可忽視的啟示作用。
至于學者的代際割裂則主要是指,學者從事學術工作的方法、思維與問題隨時代變革而出現代際性錯位,由此造成了主觀、僵化、封閉與悖謬的傾向。經學思維主導下學者所面臨的代際割裂,難以借助傳統學術的方法、理論去維系,因此現代學術的代際延展,只能借助學術圈層的大循環才能規避可能出現的學術內卷化傾向,否則很難從根源上切除經學思維的毒瘤。因為,經學思維強調基于經學文本所構建的師承、門戶與問題意識,所以它既不強調學者的獨立性與創新意識,更不在意千差萬別、與時俱進的現實問題,而是試圖以一套自以為完美的理論體系——經學模型去建構和規范現實秩序。這必然導致學者在自以為清醒、獨立的情況下出現思想的僵化與空懸,日益步入邏輯的怪圈,造成荒謬的代際割裂。以當下最為主流的“(新)古典學派”(以現代“史料”派為主流)為例,此派學者多注重對知識材料的整理和完善,主張以經典文本作為知識材料,追求知識材料的“原始”性,同時有意識地排斥宏觀、化約的理論建構,且往往以占盡資源的“知識貴族”的高傲姿態,睥睨通俗的知識傳播或“空疏”的理論建構。于是,傳統文化便成了圈子內的文化,而不同圈層又容易形成某種荒謬而隱形的鄙視鏈,使學科交叉的訴求成為葉公好龍式的、不切實際的口號。
有鑒于斯的“新子學”,乃力求破除中心、僵化與封閉,強調多元對話與觀念的嬗變,要求將儒家經學文本還原為子學的有機構成,建構一個兼容并包的子學文本體系,進而從歷代諸子的觀念中抽離出具有現實指導意義的知識、范疇、方法和理論,以此作為建構中國學術話語體系和知識譜系的基本信息庫。進一步以此為內核形成一個多元對等的思想體系,最終在現代價值與文化身份的建構中發揮積極的作用。按照“新子學”的此種構想,我們確有可能從思想根源上破除經學思維,從而改變古典學術因圈層分化與代際割裂而日益內卷化的傾向。然而,在“新子學”發揮作用的同時,我們又不得不考慮“新子學”自身的“國學”屬性以及對新的“諸子”的培養。這就要求“新子學”不能只是一味強調其“新”,而應切實地創造新的思想,形成新的話語,應對新的問題,進而以全新的學術范式推動整個文化事業的返本開新,以獨立的姿態,去擔負通過學術文化之重構,以實現參與時代進程、鏈接世界文明的使命。
文化引領的可能進路
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人類知識信息的溝通與傳遞能力正在經歷指數級的增長,而人類大腦的功能則越來被超級計算機所取代。面對席卷全球的數字革命浪潮,人文學術的發展存在著困惑。也即,面對“超級智能”這一全新“宗教”所建構起來的虛擬“幻象”,我們的人文學術究竟該何去何從?是積極應對去尋求“預流”之途,還是坐視“人文”的枯竭而接受文化消解的命運呢?如果存在“預流”的可能,那么我們古老的“諸子”是否仍能提供某種新創性的思想資源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們又將如何在古老的“諸子”中獲取應對困境的知識與智慧呢?對此,“新子學”勢必給出具有哲學方法論性質的預判和應對方案,以哲學的高度去思考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的現實問題與相應的學術構建,這就必須提及當下方興未艾的數字人文思潮。
所謂“數字人文”,乃是以計算機技術和“數字化”文獻為基礎的橫跨人文社科與自然科技領域的交叉學科,其研究方法更多涉及電子信息的調查研究、分析、綜合與表達,同時指向人文主義的思維與價值。因此,“新子學”首先要思考的就是,在數字時代,人文學科的存在形態、傳播路向、接受方式與創作研究等相關問題及其所引發的知識譜系與思維方式的重要變革,尤其是古典學在數字化時代的知識重構與文化塑造等問題。
對此,筆者不得不重申從“新子學”到“新古典學”的建構路徑:觀念—方法—話語—知識譜系。借助大數據分析,從傳統經典文本中提煉出核心語詞范疇,并對其進行觀念史的梳理與現代性闡釋,從而超脫歷史時空所帶來的思維局限,最終將古典文本從沉寂、封閉、僵化的經學闡釋中喚醒,賦予其鮮活的歷時性意義。基于一系列觀念鏈條的通道,我們便可著手中國學術話語的建構,直到形成完整的具有現代學術意義的中國文化的知識譜系——包括新觀念、新方法、新理論和新話語體系的古典知識譜系。“新子學”視域下的古典學研究,并非要從經典中獲得指導當下生活的準則,更不是通過古典的研究來尋求預測未來的“智慧”,而是試圖通過盡可能精確地了解我們的古典世界,從而跳出當下生活的局限,尤其是觀念上的局限,最終促使我們得以確立某種既具有中國文化特質,又面向現代文明的適時、多元、開放的話語體系、精神訴求和思維方式。
當然在此建構過程中,我們須借助人工智能與大數據分析以解決相應的技術難題,但更為重要的是基于技術而進行的傳統文化反思與對現實的人文關懷。首先,要合理借鑒數字人文理論,構建專業的學術數據庫系統,這或許是實現傳統“子學”甚至是整個古典學轉型和持續發展的必然進路,同時也是避免重復研究和碎片化研究的最優選擇。其次,要基于準確周備的數據網絡與觀念體系,讓學者超出單一文本和學科藩籬所造成的片面、主觀、僵化、滯后與封閉的碎片化認知,逐步形成適時互動與集體協作的學術生態,最終構建一個生發、流變、融通的新古典學的“知識譜系”。對此,陳成吒先生基于“新子學”視域所進行的“小說觀念”探索無疑具有典范性的實踐意義。其指出,過去經學思維主導下所建構的中國學術文化生態是人為修飾的秩序井然的花園幻象,而“新子學”所展開的則是一個全新又原生態的學術文化森林,諸子及其文化是重要組成部分,“小說家”也在其中,而且“小說”理念不斷走向通俗、潮流的特征正是子學開放性、大眾化這一根本特質最集中、最前沿的呈現。
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通過多元、并包的“諸子”話語譜系打破學科專業的瓶頸,去全面觀照我們的中華文化,比如在“新子學”的視野下,李贄、唐甄、袁枚等離經叛道者,不再為文學、哲學或歷史研究所局限,而是傳統思想脈絡中一個個獨具創新意義的“新子”,是當代思想文化建構的重要資源。由此,修修補補的饾饤之學,自然就升級為既深入傳統又關懷當下且能面向未來的經世致用之學,此方為當代學術之大視野、大格局、大趨勢與大氣象。
總之,“新子學”十年的探索,讓我們逐漸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必須以有機的觀念結構為脈絡,對諸子文本進行跨學科的系統研究,在整個世界的文明譜系中觀照先秦諸子這些最具原創性與思想性的經典文本,從而真正實現文化與文本的返本開新、當代轉化與世界鏈接,進而為培養新時期的“諸子”與“元話語”性質的知識信仰建構一個相對堅實的、具備現實性與操作性的學術范式,最終開創一個真正具有中國話語特色與理論深度的學術新時代。與此同時,“新子學”還需要撫今追昔,實現文理交融,即立足當下生活,合理利用科學革命的最新成果,以跨學科、跨文化的方式,重新審視古代經典及其學術,最終建構一個價值性、功能性、科學性、身份性的“新古典學”。而這樣一種基于道義與犧牲精神的“新古典學”,或許可以被人類賦予“超級智能”的未來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