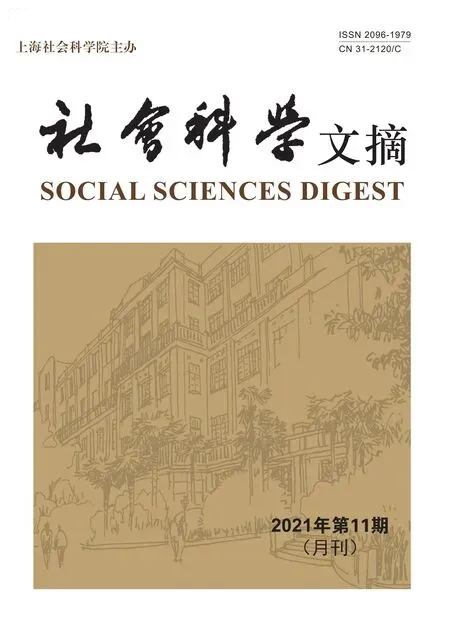中國特色西方哲學研究的歷史發展和未來走向
文/馮俊
(作者單位系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摘自《哲學研究》2021年第5期)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召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回顧中國的西方哲學研究和教學的發展歷程,總結中國特色西方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和發展成就,正視存在的問題,展望未來發展前景,讓我們更加堅定了學術自信和文化自信。
西方哲學在文化啟蒙、解放思想、推動中國社會變革中發揮重要作用
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有三種資源:馬克思主義資源、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國外哲學社會科學資源。這三種資源在交融互動中各自發揮著獨特作用,同時又共同推進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和發展。
西方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學說一起,通過三個途徑進入中國:第一個途徑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赴日本留學生對馬克思主義和西方哲學的傳播;第二個途徑是赴歐美留學生對它們的傳播,最早是嚴復等留學英國的學者,后來主要以赴法、德等國勤工儉學的學生為主體,此外還有來華的英美和歐陸學者如杜威、羅素、杜里舒等來中國講學,直接傳播相關思想;第三個途徑是留俄、留蘇的學生與共產國際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和西方哲學。盡管馬克思主義是在西方哲學的文化土壤中生長出來的,但是西方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幾乎是同一個時期傳入中國的。沒有西方哲學和各種社會政治思潮的大量引進和輸入,中國人也沒有機會發現馬克思主義。
從百年來哲學發展的歷程看,西方哲學和馬克思主義一起參與中國文化啟蒙、解放思想和社會變革運動,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包含兩個重要的歷史時期。
第一個歷史時期是,20世紀初西方各種學說和思潮開始在中國傳播,到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前后達到高潮,產生的重大歷史事件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在20世紀初,戊戌維新變法的康有為、梁啟超為西方哲學在中國的傳播作出過貢獻。嚴復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與此同時,嚴復對于穆勒哲學和黑格爾哲學的介紹,王國維對于康德、叔本華和尼采哲學的研究,馬君武對于黑格爾、斯賓塞、穆勒、狄德羅、拉美特利、托馬斯·莫爾、圣西門等人思想的研究,章太炎對于古希臘哲學、經驗論和理性論哲學、德國古典哲學諸多哲學家的研究,蔡元培對于康德哲學尤其是美學的研究,張頤對于黑格爾哲學的研究,馮友蘭、梁漱溟等人對于柏格森哲學的研究等,都起到了“西學東漸”的作用。他們對于西方哲學的大量翻譯、引證和論述,使西方哲學在中國文化界和知識分子中得到廣泛的傳播。
五四運動之后,在陳獨秀、李大釗滿腔熱情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為建立中國共產黨而奔走的同時,蔡和森、瞿秋白、陳望道和李達等也在翻譯介紹和研究傳播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的《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等著作。除李大釗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長文之外,蔡和森的《社會進化論》、瞿秋白的《社會科學概論》、李達的《現代社會學》也先后發表,對于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唯物史觀起到很大的作用。中國就是在引進西方哲學各種學說和社會思潮的過程中,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20世紀10年代到20年代引進西方哲學和思想文化以來取得最為重大的歷史性成果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馬列主義被共產黨人確認為真正能改變中國命運的真理。
西方哲學在文化啟蒙、解放思想、推動中國社會變革方面的第二個歷史時期是從70年代末開始的。西方哲學思潮的引進推動了中國解放思想的大討論,讓中國人再次開眼看世界,產生的重大事件是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
1949年以后,中國的哲學界受到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受蘇聯哲學教科書和來華蘇聯專家影響,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向蘇聯學習,使哲學成為意識形態斗爭的工具,將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斗爭政治化和教條化;另一方面受冷戰和“文化大革命”等極左思潮的影響,西方哲學被當作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成為批判的對象。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掀起了解放思想的大討論。思想解放助推了中國的西方哲學研究和教學的興盛,反過來中國的西方哲學研究和教學的繁榮又助推了這個時代中國的文化啟蒙、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的發展。
1978年在蕪湖召開的“全國西方哲學討論會”、1979年在太原舉行的“全國現代外國哲學討論會”是中國西方哲學界具有歷史意義的兩大事件。“蕪湖會議”和“太原會議”在外國哲學研究和教學中突破“語錄標準”和“蘇聯標準”的“禁區”,放棄了50年代以來蘇聯那種簡單化和教條主義地批判資產階級哲學的做法,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開始對西方哲學史上和現代西方哲學的各種流派、人物、著作、學說和觀點進行深入的而不是膚淺的、客觀的而不是貼標簽式的研究和教學。
80年代人們迎來了“尼采熱”“薩特熱”和“存在主義熱”,“弗洛伊德熱”和“精神分析熱”,“生命哲學熱”“結構主義熱”“法蘭克福學派熱”和“哈貝馬斯熱”,波普爾、庫恩和“科學哲學熱”;繼而90年代興起了胡塞爾、海德格爾和“現象學熱”,“分析哲學熱”和“語言哲學熱”,羅爾斯和“政治哲學熱”,福柯、德里達和“后現代主義哲學熱”等,相關哲學家的著作被大量翻譯和介紹,大學里的此類課程十分熱門和搶手。廣大學生與社會青年之所以熱衷于學習和了解西方哲學,不僅是要補足以往我們哲學研究和相關知識的缺失,而且是希冀能從中找到推動中國社會變革的理論和方法。
中國特色西方哲學研究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
中國的西方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在百余年的發展中,尤其是在改革開放40多年來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并仍在不斷發展和完善。
1.學科體系建設
中國特色西方哲學研究的學科體系建設體現在三點上,一是學科自身的體系化,二是學術機構和學科點的設置,三是該學科提出和發現的新問題。
一是西方哲學學科自身的體系化。西方哲學學科自身的體系化有兩個快速發展階段:一個是從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一個是改革開放以來40多年的時間。
在第一階段,一方面是經過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文化啟蒙之后,學者們對西方的哲學開始進行成體系的翻譯引進和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在抗日戰爭開始后,中國知識分子有一種喚醒國人民族獨立意識、振奮國人精神的愛國情懷,因此開展大規模的文化和新思想的啟蒙,對西方的主流哲學進行更加全面系統的翻譯和引進。從古希臘哲學、經驗論和理性論的哲學、18世紀啟蒙思想和法國唯物主義哲學、德國古典哲學到20世紀初的現代西方哲學,幾乎都有譯介。隨著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在西方留學的學生學成回國后,他們開始從單純翻譯介紹轉為用中國人的文化視野研究西方哲學,產生了可觀的新理論成果。
中國的西方哲學學科體系化的第二個階段是改革開放時期,這是一個快速發展階段,經過中國學人40多年來的努力,可以說西方哲學的所有流派、重要哲學家和主要學說、主要著作幾乎都被引進到中國,都有人在研究。
從研究的領域來看,從改革開放之初單純重視德國古典哲學特別是黑格爾哲學,而發展到古希臘羅馬哲學、中世紀哲學、近代經驗論和理性論哲學、啟蒙運動哲學、德國浪漫主義哲學、孔德實證主義哲學、叔本華和尼采的意志哲學、柏格森生命哲學、現象學和存在主義哲學、分析哲學、語言哲學、邏輯實證主義、實用主義哲學、科學哲學、結構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解釋學、過程哲學、精神分析哲學、心靈哲學、后現代主義哲學、政治哲學、文化哲學、分析的和生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應用倫理學,以及大數據與認識論、人工智能哲學等。另外,還有猶太哲學、印度哲學、伊斯蘭哲學等廣義的西方哲學,都成為我們研究的對象。可以說,凡是西方學術界研究到的領域,中國的西方哲學界也都已涉獵,并從“跟跑”逐步接近“并跑”狀態。例如,苗力田、汪子嵩、葉秀山、姚介厚、范明生、陳村富等人對古希臘哲學的研究,付樂安、趙敦華、段德智、王曉朝、黃裕生等對中世紀哲學的研究,陳修齋對經驗論和理性論哲學的研究,馮俊對笛卡爾和法國近代哲學的研究,周曉亮對休謨和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研究,張世英、王玖興、楊祖陶、王樹人、楊壽堪、錢廣華、鄧曉芒、李秋零、張志偉、謝地坤、韓水法等對德國古典哲學的研究,江天驥、夏基松、涂紀亮、劉放桐等對現代西方哲學的研究,靳希平、龐學銓、倪梁康、陳嘉映、孫周興等對于胡塞爾、海德格爾等人現象學的研究,洪漢鼎、何衛平等對伽達默爾哲學和闡釋學的研究,姚大志對西方政治哲學的研究,俞吾金、張一兵等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韓震對西方歷史哲學和社群主義的研究,高宣揚、杜小真、尚杰、馮俊、莫偉民、汪堂家、錢捷、孫向晨、楊大春、汪民安等對現代法國哲學的研究,王路、江怡、陳波、韓林合、葉闖、陳亞軍、陳真、費多益等對分析哲學的研究,傅有德對于猶太哲學的研究,高新民對心靈哲學的研究,王齊對克爾凱郭爾的研究,等等。
二是學術機構和學科點的設置。從北京大學1912年設立“哲學門”開始,中國就有了專門的哲學學科點。1952年國內院系調整,只有北京大學一家有哲學系。從1956年開始,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中山大學等先后開始建設或恢復重建哲學系。1955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成立了以賀麟先生為組長的西方哲學研究部,這是國內研究西方哲學的重要學術機構。1964年設立的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也是研究西方哲學的專門機構。此外,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復旦大學等校的外國哲學教研室都是研究西方哲學的重鎮。改革開放后,在恢復哲學研究和教學的過程中,哲學一級學科下面劃分出八個二級學科,外國哲學為其中之一,與其他七個二級學科即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邏輯學、倫理學、美學、宗教學、科學哲學并列。在八個二級學科中,中國哲學、外國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俗稱“中、西、馬”,它們是哲學學科的主干。據教育部高教司的相關報告稱,2020年全國現有98個哲學專業點,有哲學專業的地方基本上都會有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三個教研室。中華全國外國哲學史學會和全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這兩個學會在推動中國的西方哲學研究、構建中國特色西方哲學學科體系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是該學科提出和發現的新問題。學科體系是否成熟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能否提出本學科特有的問題。中國特色西方哲學學科在引進和傳播西方哲學的過程中,除了引入西方哲學提出的一些問題外,也開始對西方哲學進行中國式的解讀,或者運用西方哲學來研究中國哲學問題,形成了中國語境下的“問題意識”,提出了中國的西方哲學學科獨有的問題。趙敦華教授曾經歸納出十個問題,包括西方哲學研究方法論問題、西方哲學術語中譯問題、中世紀哲學性質問題、康德與黑格爾的重要性和相互關系問題、中西哲學會通問題、西方哲學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關系問題、啟蒙與現代性的是非功過、后現代主義的哲學評價問題、政治哲學中“左”“右”之爭、海德格爾與納粹關系問題。其實,問題遠遠不止這十個。韓震教授講道:“歐美哲學界學術研究的論題,都被中國學者們給予有中國視角的研究,有些西方命題通過我們新的解釋轉換成為中國當代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江怡教授也概括了40年來中國對于分析哲學的四條研究路徑:歷史路徑、視角路徑、問題路徑、方法路徑。
2.學術體系建設
中國特色西方哲學研究的學術體系建設方面,最重要的有三點:一是學術翻譯,二是教材建設,三是師資隊伍建設。
一是學術翻譯問題。翻譯西方的原著原典是西方哲學研究的基礎。40年來,除了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中的哲學類圖書已經累計出版了282種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上海譯文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等出版機構也出版了很多外國哲學家的著作,其中包括一些重要哲學家的全集或選集,如《亞里士多德全集》《柏拉圖全集》《盧梭全集》《康德著作全集》《費希特著作選集》《杜威全集》《維特根斯坦全集》《薩特文集》《列維-斯特勞斯文集》《拉康選集》《布爾迪厄作品集》《海德格爾文集》《克爾凱郭爾文集》等,正在翻譯出版的有《謝林著作集》《黑格爾全集》《胡塞爾文集》《尼采全集》《舍勒全集》《梅洛-龐蒂文集》《羅蘭·巴爾特文集》等。
二是教材建設問題。從新中國70年的學術發展來看,我國西方哲學的教材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改革開放后譯介出版的哲學史著作有葛力先生翻譯、梯利著的2卷本《西方哲學史》,賀麟和王太慶等翻譯、黑格爾著的4卷本《哲學史講演錄》,何兆武和李約瑟翻譯、羅素著的2卷本《西方哲學史》,羅達仁翻譯、文德爾班著的2卷本《哲學史教程》,馮俊等翻譯、帕金森和杉克爾主編的10卷本《勞特利奇哲學史》,周曉亮翻譯、托馬斯·鮑德溫著的2卷本《劍橋哲學史》;有代表性的單卷本哲學史有童世駿等翻譯、G.希爾貝克和N.伊耶著的《西方哲學史——從古希臘到20世紀》,洪漢鼎等翻譯、D.J.奧康諾主編的《批評的西方哲學史》,韓東暉翻譯、安東尼·肯尼著的《牛津西方哲學史》,馮俊等譯、安東尼·肯尼著的《牛津西方哲學簡史》等。由中國人自己編寫的西方哲學史最早是由洪謙等人編寫的《哲學史簡編》,以此為基礎汪子嵩等改寫了《歐洲哲學史簡編》,后有朱德生和李真編寫的《簡明歐洲哲學史》,李志逵編寫的《歐洲哲學史》,劉放桐等編《現代西方哲學》,陳修齋和楊祖陶著的《歐洲哲學史稿》,夏基松主編的《現代西方哲學教程》,冒從虎等編著的《歐洲哲學通史》,全增嘏主編的《西方哲學史》,于鳳梧等人主編的《歐洲哲學史教程》,苗力田、李毓章主編的《西方哲學史新編》。新世紀以來有趙敦華著的《西方哲學簡史》,張志偉主編的《西方哲學史》,鄧曉芒、趙林著的《西方哲學史》與由趙敦華和韓震主持編寫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西方哲學史(學術版)》。大部頭多卷本哲學史主要有:葉秀山、王樹人主編的8卷本《西方哲學史》,劉放桐、俞吾金主編的10卷本《西方哲學通史》,馮俊主編的5卷本《西方哲學史》,還有汪子嵩等的4卷本《希臘哲學史》,涂紀亮的3卷本《美國哲學史》,黃見德的2卷本《西方哲學東漸史》,等等。我國西方哲學的教材體系建設取得了很大成就,而且與時俱進。根據目前狀況,中國大概是世界上非西方國家中編寫《西方哲學史》最多的國家。
三是師資隊伍建設問題。我國老一輩的西方哲學學者如賀麟、洪謙、任華、嚴群、龐景仁、全增嘏、熊偉、王玖興、江天驥等有出國留學經歷的老師,和苗力田、王太慶、陳修齋、汪子嵩、張世英等沒有出國留學經歷的老師,他們都既有很好的國學功底,又有很高的外語水平,既能翻譯西方哲學的原著原典,又能產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在50年代至70年代接受大學教育的一代,由于政治運動的影響,都沒有機會系統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和外語,但還是出現了像楊祖陶、葉秀山、梁存秀、劉放桐、夏基松、姚介厚、王樹人、陳啟偉等出類拔萃的學者。80年代之后,隨著國民教育體系的逐步健全和對外開放,中國學習西方哲學的學者又有機會出國讀學位或做訪問學者,使我們的西方哲學師資水平得到了整體提升。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國內著名大學和研究機構的西方哲學師資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從世界名校哲學系畢業的優秀博士陸續歸國任教,很多高校還直接招聘海外師資。國際化交流活動日益頻繁,國內的學術研究和國際上幾乎是同步的,世界哲學舞臺上的中國聲音越來越大。另外,中國的西方哲學界創辦了《外國哲學》《哲學分析》《中國現象學與哲學評論》《德國哲學》《法國哲學》等學術刊物,還有英文版的《中國哲學前沿》雜志。
3.話語體系建設
中國特色西方哲學研究的話語體系建設,包括西方哲學在中國產生的標識性概念,西方哲學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中國哲學的影響,西方哲學研究的國際話語權問題。
首先,西方哲學引入中國后產生了中國原本沒有的一些標識性概念。中國學者通過翻譯西方哲學原著,讓西方哲學說現代漢語。在中國出現了本體、理念、形式、質料、主體、理性、知性、感性、直觀、意志、自由、現象、先驗、超驗、絕對、異化、純形式、生存、沉淪、應然、概然、此在、證實、證偽、身體、他者、解構、延異等核心概念,這些術語被引入現代漢語。它們是中國譯者們不斷思考、研究的結晶,既深刻、準確地表達了西方哲學的原意,也極大地豐富了漢語的表達,形成了中國特色西方哲學研究的話語體系。
其次,中國的西方哲學研究促使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改變了面貌。例如,價值論、人道主義、異化問題、意識形態的馬克思和科學的馬克思之爭、主體性問題、社會批判、日常生活批判、后現代主義和解構主義、發展觀問題、公共性問題、生態問題、現代性問題、全球化問題等,成為今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界討論的熱門話題。波普、庫恩、羅爾斯、查爾斯·泰勒、桑德爾、利奧塔、布爾迪厄、鮑德里亞、德里達、福柯等人的名字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論文中出現的頻率甚至超過了在西方哲學論文中出現的頻率。西方哲學對于時代性問題的思考、許多重要的哲學范疇和研究方法、很多概念和話語,已經被馬克思主義哲學界吸收借鑒、轉換融通,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理論視野,提升了理論思維水平。
再次,中國的西方哲學研究促使中國哲學改變了面貌。這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20世紀上半葉,以胡適、馮友蘭為代表,運用西方哲學的體系、概念和方法建構起中國哲學史的框架;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圍繞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學界也展開了討論——到底是哲學在中國,還是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到底是跟著講、照著講還是自己講、講自己?這些討論增強了中國哲學的主體意識和文化自信。二是運用西方哲學的概念和方法研究中國傳統哲學問題。例如,楊適對東西原創文化的研究、王樹人對“象思維”的研究等。再如張世英晚年思考中西哲學的結合問題,以世界性的視野,創立了新的哲學體系“萬有相通論”。陳來就本體論、生命哲學、價值理念等在中西之間進行比較,吸收了西方哲學的一些理念,創建了“仁學本體論”等。三是對中西方哲學進行比較研究,例如,張祥龍、張汝倫、倪梁康、王慶節等一批學者從不同角度致力于中西哲學的比較研究,這些西方哲學的學者也成為研究中國哲學的重要力量。
最后,中國的西方哲學研究的國際話語權問題。中國的西方哲學研究者們要在世界哲學舞臺上發出聲音、占有一席之地。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陳康先生就曾自信地說,要讓西方研究希臘哲學的人以不懂中文為遺憾。洪謙、金岳霖、沈有鼎、王浩等中國哲學家在分析哲學、邏輯學等領域作出了貢獻。邱仁宗考察了波普爾對卡爾·馬克思思想的批評,陳波關于克里普克的只存在“后驗偶然命題”、不存在“先驗偶然命題”和“后驗必然命題”的批評意見等在國際哲學界引起了關注。江怡還被推選為國際分析哲學史學會執委,這些都是國際影響力的證明。
中國特色西方哲學研究面臨的問題和未來走向
中國特色西方哲學研究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已經取得長足進步,成就蔚為大觀。然而,中國特色的西方哲學研究在發展中也存在一些問題。
首先,中國特色的西方哲學研究在發展繁榮的同時也存在著趕熱點、趕時髦現象。研究和教學存在著“冷熱不均”,這些反映出學術的浮躁之風。
其次,中國特色的西方哲學研究在日益專業化職業化的同時形成了新的學術壁壘,彼此隔絕、自說自話。學術領域越分越細、越來越專,研究英美哲學的不懂大陸哲學,研究大陸哲學的不懂英美哲學。在英美哲學內部,研究邏輯哲學、語言哲學、科技哲學、心靈哲學的互相也不懂;大陸哲學中,研究德國現象學的人不了解法國現象學,研究現象學的也不懂社會政治哲學。西方哲學研究的一些領域已經出現支離破碎、畫地為牢的現象。
再次,中國特色的西方哲學研究正日益脫離社會現實。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哲學工作者要觀照現實、參與現實,要關注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我們研究西方哲學,不能單純以西方人的問題為問題,不是為了幫西方人發展他們的哲學,而是要從哲學上回答中國當代面臨的問題,發展中國人自己的哲學。我們反對政治化、標簽化、簡單化、公式化等錯誤傾向的同時,在一定程度又產生一種“去政治化”傾向,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在西方哲學的研究中幾乎失語、失蹤了。
最后,中國的西方哲學越來越被社會邊緣化。一方面,有些學者用一些生僻甚至怪異的名詞概念將自己變成了讓圈外人聽不懂、社會大眾望而生畏的“洋學問”,將自己與社會大眾隔離起來;另一方面,大眾文化、商業文化和以新媒體為代表的流量文化也遠離和遺忘了西方哲學,使西方哲學越來越被邊緣化。
但是,即使如此,仍然有一些學者為中國特色西方哲學研究的發展和繁榮作出進一步努力,對中國特色西方哲學研究的未來前景充滿希望。從目前中國學者關注的問題看,中國特色西方哲學研究的未來走向有這幾個方面:
第一,生活世界。胡塞爾在20年代到30年代提出哲學要回歸“生活世界”。從30年代中期開始,列斐伏爾提出“日常生活批判理論”。哈貝馬斯認為,生活世界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相互交往的舞臺,生活世界又是在交往活動的實踐中形成的。20世紀后半葉,存在論現象學、精神分析學、闡釋學、社會批判理論、政治哲學、倫理哲學等都重視生活世界,認為哲學必須要解決人類生存所面對的問題,應該面向現實生活。中國特色西方哲學研究為了克服學術壁壘,突破哲學日益脫離社會現實、被社會邊緣化的現狀,也開始提出哲學向生活世界回歸,強調哲學應該關注現實,研究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當代社會生活條件,思考人及其生存的環境,人自身的創造性活動、生存意義及現實中提出的種種哲學問題。
第二,未來哲學。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尤其是人工智能和生物技術的迅猛增長,使人類文明進入了一個重大的歷史性變革之中。人類對未來的關切前所未有,所以有些學者提出我們要注意研究“未來哲學”。在哲學史上,費爾巴哈第一個提出“未來哲學”概念,尼采的《善惡的彼岸》一書,副標題就是“一種未來哲學的序曲”。孫周興教授提出具有世界性的“未來哲學”應該研究三個問題,那就是文明對話問題、人類政治問題、技術困境問題,其中最核心的是技術問題。
第三,漢語哲學。近幾年來,在中國的西方哲學圈內展開了關于漢語哲學可能性的討論。中國的西方哲學研究者提出了“讓哲學說漢語”的口號。這種漢語哲學,不是簡單延續中國古代哲學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模板”,不是西方哲學史的“再版”,也不是現代西方哲學的“翻版”。這種漢語哲學,不是西方哲學的漢語翻譯,但是它吸收了西方哲學的豐富內涵;漢語哲學不是對中國傳統哲學的簡單重復,但它包含了中國傳統哲學的優秀成果;這種哲學是說漢語的,但它是世界性的、是可以翻譯的。建立這種漢語哲學的任務靠單純研究中國傳統哲學的學者或靠單純研究當代中國現實問題的學者是完成不了的,它需要以精通西方哲學和世界哲學的學者為主體、結合其他哲學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來完成。
第四,翻譯、教材和研究的統一。在今天我們仍需要翻譯,翻譯仍然是西方哲學研究的基礎性工作。在今天,西方哲學的教材還需要寫,任何哲學史都是當代史,隨著研究的深入和學術視野的擴展,我們要寫出這個時代新的哲學史和哲學教材。有的學者認為,哲學史要不斷地被重估,哲學史的敘事總是以一定的哲學觀點為視角的,哲學的反思又總是以一定的哲學史敘事為基礎,并為自身重新確立思想坐標。所以說,哲學史和教材是常寫常新的。還有學者正在進行“21世紀西方哲學史編纂學研究”,認為哲學史編纂學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西方哲學研究的未來走向一定是讓翻譯、教材編寫和研究統一起來,而不是三者的分離。
第五,中、西、馬哲學的對話和會通。中國當代哲學的發展要發揮中、西、馬哲學的對話和會通的優勢。在中國研究西方哲學應該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它能給我們分析評價西方哲學提供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這是中國特色西方哲學研究得天獨厚的條件,這也是中國特色的重要體現。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并存,是中國當代哲學的基本格局,也是中國當代哲學的特色與優勢。這三種哲學形態中的任何一種,都沒有能力獨立完成建設中國當代哲學這一艱巨的任務。中國傳統哲學需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西方哲學需要“中國化”,與中國哲學交流融匯,而馬克思主義哲學也需要在用好中、西哲學資源的基礎上,在中國的實踐創新中不斷地推進理論創新。“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中、西、馬哲學的對話和會通必將能夠產生出無愧于這一時代的當代中國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