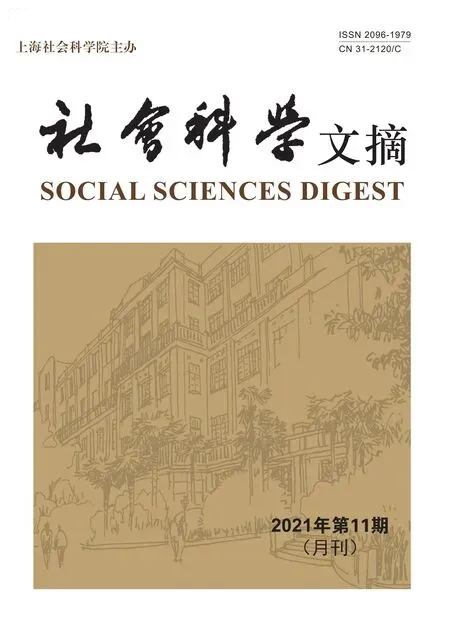西方政治學轉向歷史的三個層次及其啟示
文/郭臺輝
(作者系云南大學民族政治研究院政治學教授;摘自《教學與研究》2021年第10期)
轉向歷史是中國政治學發(fā)展的必由之路。從歷史視野開拓新的政治學研究領域,需要進一步承接到社會科學的歷史傳統(tǒng),在更普遍范圍的學理意義和學術史來討論政治學轉向歷史的基本分途,辯證地認識到其中的可能面向與困境及其超越的可能路徑。本文立足于西方社會科學傳統(tǒng)的歷史反思,關注歷史研究與政治學研究之間的結合方式,歸納出三種層次性的關系及其缺憾。
第一種結合方式是把歷史視為方法,歷史研究為政治學的知識生產(chǎn)提供更豐富的論證材料,這種實證主義的理解遭到來自闡釋學傳統(tǒng)的批判;第二種結合方式把歷史作為一種意識、認知和思維,將政治學的研究議題置于歷史過程的具體闡釋,對政治學理論、概念與命題的知識生產(chǎn)施加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性條件,但帶來知識碎片化和歷史想象力的詬病;第三種結合方式是把歷史視為本體的存在,而政治學的知識生產(chǎn)是論證普遍歷史進程和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視角或手段,這恰恰為世俗化的后形而上學傳統(tǒng)所拋棄。中國嘗試發(fā)展歷史政治學,需要合理定位歷史研究與政治學之間的關聯(lián)機制,尤其需要為第三種理解提供中華文明連續(xù)統(tǒng)一的歷史觀念,使之成為前兩種結合方式的前提假設與哲學基礎。
歷史作為方法
在歷史作為方法的層次上理解歷史研究與政治學研究的結合,意味著歷史研究為論證材料之“用”,服務于政治學研究之“本”,旨在探索與發(fā)現(xiàn)在現(xiàn)實政治領域具有普遍適用性的概念、理論、命題等知識范疇。把歷史研究視為社會科學的一種主要研究方法,需要滿足兩個前提條件:其一,把歷史視為經(jīng)驗事實的文獻材料,可以直接或間接拿來論證社會科學研究追求的基本命題、因果規(guī)律和法則;其二,政治學與社會學和經(jīng)濟學一樣,成為實證社會科學傳統(tǒng)的一個重要分支,并且對應自由主義國家意識形態(tài)劃分政治、社會、經(jīng)濟領域,而政治學的任務是探索國家、政府、政黨等政治領域,解釋當下國家正在運行的政治現(xiàn)象與規(guī)律。但這兩個前提條件并非同時發(fā)生,各有不同的形成時間與方式。歷史研究與政治學研究之間之所以“體”“用”結合,得益于一部分政治學者不滿政治科學的既定研究狀況而轉向歷史方法,為當代政治學學科開辟新的研究領域,也同時打開政治研究的歷史視野。其中,歷史研究可以成為社會科學的重要方法,得益于兩個基礎。其一是笛卡爾開創(chuàng)的哲學基礎,認為歷史材料需要有利于當下知識生產(chǎn)的論證,因當下問題的解決而探討過去,即“以古觀今”是為了達到“以今觀古”的現(xiàn)實主義目的。其二是開始于孔德的社會科學基礎。孔德在笛卡爾基礎上,進一步把歷史與觀察、實驗、比較并置為科學研究方法,旨在通過過去發(fā)生的歷史事件來檢驗當下的結果。結果,消除其唯心主義影響的德國“蘭克學派”迅速擴展到歐洲其他國家,在法國發(fā)展成為“實證史學派”以及后來的“歷史學方法論派”,并且到19世紀后期的涂爾干時代,史料編纂的歷史研究成為社會科學發(fā)現(xiàn)“社會事實”的主要場域與論證材料來源。然而,西方現(xiàn)代政治學研究更晚接受歷史方法。政治學直到20世紀20年代之后發(fā)展出美國政治科學之后,才獨立建制為一門現(xiàn)代學科。但歷史成為政治學的研究方法,恰恰是作為“批判的武器”,抵制美國以功能論和系統(tǒng)論為主導范式的政治科學。在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20年代,美國政治科學全然關注當下政治過程與生活,尤其是選舉與投票的政治行為與心理,采用問卷調查、定量和數(shù)理模型化的實證分析,尋找變量之間因果關系的“硬科學”規(guī)律。雖然主流的政治科學依然強勁地追求數(shù)理模型和理性選擇,但一批非主流的社會學家率先以“歷史社會學”為名,在歷史作為方法的層次上行使“歷史政治學”之實,復興19世紀政治研究傳統(tǒng)的關鍵議題。
當今政治學需要尋找那段時期轉向歷史方法的知識資源,進而接駁在19世紀之前的學科傳統(tǒng),必須關注相鄰學科的學術史,尤其是社會學與歷史學之間的親密結合。其一,重新探討19世紀經(jīng)典作家關注的現(xiàn)代性議題,關注傳統(tǒng)至現(xiàn)代的斷裂與轉型;其二,充分運用比較歷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圍繞沖突與變遷的重要政治議題,進行跨時間、跨空間與跨語言情境的大范圍比較,試圖為大轉型提供結構主義的合理解釋,或者重新解釋宏大歷史的帝國與文明過程,或者分析具體主題的因果關系機制;其三,既充當歷史學家,親自收集充分的一手檔案史料,又扮演社會學家,對數(shù)據(jù)進行量化分析,對具體研究的問題提供因果關系的理論解釋。
然而,歷史作為方法的政治學也最容易遭到詬病。其中,這種建立在實證史學基礎上的理論研究,需要經(jīng)受來自史學的批評,因為史料派理解的歷史可能喪失歷史個體的生命體和主體性,況且這種唯政治史的歷史掩飾了社會、經(jīng)濟、文化的歷史多面性與復雜性。因此,轉向歷史方法的社會科學普遍得不到史學界的認可。同時,主張歷史方法的政治學往往以超歷史的理論問題先入為主,試圖發(fā)現(xiàn)一個所謂外在于歷史自身的非歷史命題。他們難以進入那些運用當下數(shù)據(jù)并追求普遍解釋力的主流社會科學視野,只能擠壓于歷史特殊性與理論普遍性的夾縫之間。結果,轉向歷史方法的政治學研究如果不是被政治學的主流范式所拋棄,就可能成為其中一個獨特的子學科或研究領域,自娛自樂,自謀發(fā)展。
歷史作為認知
在認知層次的歷史研究看來,歷史有其本質的規(guī)定性。其一,所發(fā)生的一切都有其唯一具體性,不可復制,必須嚴格遵循時間發(fā)生的先后次序安排;其二,歷史過程充滿偶然性與復雜性,并沒有超越時間次序和歷史情境的命題、概念、理論和普遍發(fā)展規(guī)律;其三,歷史上的人物、制度、事件及其發(fā)生過程都是整體涌現(xiàn)的,并且同時在各領域、各層次以及不同的社會政治群體中造成不同后果。這意味著,歷史整體是被人為劃分并建構為局部不同的領域史,而再現(xiàn)真實的歷史需要一個整體的歷史意識和具體的關聯(lián)機制。相應地,在歷史認知層次上來理解政治學的歷史轉向,其任務有三:其一,政治學的所有概念、理論、命題必須受制于時間次序與歷史情境的條件約束;其二,政治學當下關注的任何議題與問題都必須有其歷史形成和路徑依賴的意識,現(xiàn)實的政治生活與制度帶有歷史痕跡,是歷史過程漸變或突變的延續(xù)或結果;其三,政治學轉向歷史,其任務不僅是闡釋與分析歷史過程中的關鍵發(fā)生機制,而且需要關注推動其變遷的社會、經(jīng)濟、文化等條件以及結合機制。換言之,歷史認知層次理解的政治學轉向歷史是歷史研究與政治學研究雙方都需要同時反思,之后的再結合才得以可能。在當代西方學術史上,認知層次的歷史研究是在反思與批判方法層次的基礎上提出來的。轉向歷史方法的社會科學為了達到理論建構的目的,只能人為裁剪歷史材料,運用社會科學“講道理”的語言替代并重組歷史學“講故事”的語言,這既違背歷史重現(xiàn)的真實性,又不符合社會科學追求價值中立的客觀標準。歷史研究必須“按其真實發(fā)生的方式來敘述的歷史”,因此,“真實發(fā)生”(時間次序)與“敘述”(敘事語言)構成社會科學轉向歷史時必須面對的兩個前提條件,相應也迫使“政治學轉向歷史”之“歷史”從歷史方法層次上升到歷史認知層次,之“政治學”能接受敘事語言的表現(xiàn)方式。因此,轉向歷史的社會科學既反思實證社會科學自身的“硬科學”范疇,又充分吸收歷史學的傳統(tǒng)特征,超越歷史方法的層次,把社會科學與歷史研究在認知上結合在一起,并且充分體現(xiàn)在四個方面:在語言上采取分析性敘事;性質上以過程闡釋取代因果解釋,嚴格遵循時間的先后次序來理解歷史;時間序列上遵從歷史原本真實發(fā)生的起因與結果;重視歷史事件發(fā)生的偶然性、過程的整體涌現(xiàn)性與后果的不可預料性。
然而,政治科學即使轉向歷史,也存在三種明顯缺陷:其一是“歷史即研究往事”,為政治史中的特定結果提供經(jīng)驗性的因果解釋;其二是“歷史是收集例證性的材料”以證明普遍命題;其三是“歷史是產(chǎn)生案例的場所”,利用小樣本展示大命題。這三種或經(jīng)驗性或策略性的歷史轉向,只是政治學與歷史學之間“主”“仆”關系的結合。在歷史認知層次上理解的政治學研究也面臨問題:其一是知識碎片化問題;其二是歷史成為想象;其三是打破傳統(tǒng)主流學科的霸權地位。當所有研究議題都有著時間意識,相應也找到自身的歷史合法性,無須從母體學科尋找知識資源的支持,也不為母體學科增強解釋力和知識創(chuàng)造力時,傳統(tǒng)主流學科難以有新的生命力。簡言之,政治學從認知層次上轉向歷史,既缺乏普遍歷史的基礎性支撐,又作為政治學傳統(tǒng)學科體系的離心力,帶來研究議題的泛化與知識構建的主觀化。
歷史作為主體
歷史本體論是對歷史意識與觀念的普遍假設,假定歷史整體作為一種生命體,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之間存在一種本質、普遍的統(tǒng)一關聯(lián)機制,任何時期所發(fā)生的一切社會政治現(xiàn)象甚至自然現(xiàn)象都源于并服務于某種特定的普遍歷史規(guī)律。顯然,歷史本體層次意義上的歷史研究與政治學研究之間的關聯(lián)恰恰是歷史方法層次上的關系“倒轉”,即以歷史研究為“本”,政治學研究為“用”。然而,歷史研究分歧最嚴重的層次恰恰是歷史的本體論問題。因為這種“何為歷史”的形而上學問題處于歷史觀念領域的最高層次,屬于人之理性不能把握的信仰范疇,卻是知識建構與理性論證之先驗預設。雖然西方社會科學有五種時間性的理解,但西方的歷史觀念傳統(tǒng)主要是循環(huán)論與進步論兩種競爭性的歷史本體論假設,各自對政治學研究的歷史本體論有著截然不同的影響。歷史循環(huán)論從古希臘的修昔底德與波利比烏斯、近代的馬基雅維利與孟德斯鳩,至現(xiàn)代的斯賓格勒與湯因比,都把人類文明視為生命周期循環(huán)的興衰歷史。修昔底德從人性不變的假設出發(fā),認為所有外在社會政治事件的發(fā)生都是內在人性的反映,因此歷史必然周而復始地循環(huán)發(fā)展。這為古希臘史學奠定了觀念基礎。到近代之后,馬基雅維利與孟德斯鳩復興古希臘史學的“實用主義”傳統(tǒng),從人性不變的假設出發(fā),把人類歷史視為政治史,并從政治經(jīng)驗領域總結出對當下現(xiàn)實有直接效用的歷史教訓。后來的斯賓格勒與湯因比則從文明史比較的更大視野來強調歷史循環(huán)論,試圖以悲觀筆調來超越樂觀自信的進化論。孟德斯鳩重視經(jīng)驗分析,延續(xù)古希臘至馬基雅維利的經(jīng)驗—實用歷史觀念傳統(tǒng),為現(xiàn)實政治的君主制國家提供治國藝術,旨在發(fā)現(xiàn)政治與道德領域共同的正義標準及其制度落實。這意味著孟德斯鳩不僅僅停留在特定語境條件的實用主義史觀,而是突破了傳統(tǒng)的政治史范疇,探討推動歷史變遷與社會運轉的“原因之原因”,即更為穩(wěn)定的普遍法則。為此,涂爾干把孟德斯鳩視為社會科學的先驅。這恰恰是遵循培根開創(chuàng)的近代經(jīng)驗主義哲學傳統(tǒng),認為歷史材料是逐步提煉客觀知識的基礎,而知識“金字塔”頂端是自然法意義上的普遍法則,通過“一列通到準確性的循序升進的階梯”,由特殊和具體的歷史研究上升到普遍的規(guī)范哲學。從此,自然法的理性主義與感性現(xiàn)實的經(jīng)驗主義兩種哲學傳統(tǒng)達成統(tǒng)一,與其說終結了古希臘以來據(jù)于實用主義原則的政治史,不如說歷史循環(huán)論在18世紀之后受制于歷史進步論。
進步論在近代西方之后成為一種強勁的歷史觀念,恰恰是始于中世紀基督教傳統(tǒng)的上帝神學假設。近代宗教改革與啟蒙運動把人的理性精神抬高到上帝位置,確立人類中心論的世界觀,但中世紀的共相/殊相、人/自然等二分法假設依然有效,只是表現(xiàn)為歷史進化論、發(fā)展主義、現(xiàn)代化等方式。奧古斯丁確立中世紀基督教傳統(tǒng)的信仰體系,把“圣父”“圣子”“圣靈”視為“三位一體”不同“位格”的整體,統(tǒng)一解釋永恒上帝與普遍歷史的存在,形成神學體系的形而上學假設,共同推動人類歷史進步的普遍進程。然而,從中世紀后期開始,三“位格”對世界、上帝、歷史的解釋出現(xiàn)分歧,逐漸形成理性神、自然神、意志神三種世俗化的神學假設,奠定近代西方不同的歷史哲學傳統(tǒng),尤其是從意大利維科到德國赫爾德以降的歷史主義傳統(tǒng)和法國以伏爾泰為代表的理性主義傳統(tǒng),雖然英國并沒有明確提出經(jīng)驗主義的歷史哲學,卻依然堅持普遍歷史進步的普遍假設。
當然,歷史本體論假設在近代西方由進化論取代循環(huán)論,三種世俗化的神學假設以科學與理性精神之名義,實現(xiàn)上帝的普遍意志。不同的是,培根的經(jīng)驗哲學與實驗科學方法把人、自然、歷史、社會納入自然神假設的統(tǒng)一整體與時間序列進程,當然,到洛克之后的經(jīng)驗主義史學則是否認自然神的假設,更重視長期積累的感性實踐與經(jīng)驗知識,而休謨把歷史研究視為整理感性記憶和記錄的歷史材料,旨在形成因果關系鏈條的論證過程。但法國以理性神假設的歷史哲學傳統(tǒng)以理性精神為核心,旨在發(fā)現(xiàn)理性精神在人類歷史普遍進程中的決定性作用,在眾多具體、偶然、個別的歷史事件中尋找本質性存在的普遍規(guī)律與永恒法則。因此,普遍性的命題需要歷史作為論證材料,同時也是解釋復雜歷史進程的關鍵機制。在這個意義上,從伏爾泰、孔多塞、孔德對宏大變遷的人類文明進程都劃分不同的歷史發(fā)展階段,也是人類精神不斷理性化與世俗化的普遍歷史進程。到19世紀之后歷史進步論大獲全勝,雖然德國歷史主義傳統(tǒng)在19世紀末走向衰落,但進化論和發(fā)展主義依然是西方主導性的歷史本體論假設。進入20世紀,歷史進步觀念蛻變?yōu)楝F(xiàn)代化理論、趨同論、依附論、歷史終結論等,主宰西方社會科學研究的價值觀念。
但是,歷史進步觀念的根本問題在于,帶基督教神秘色彩的歷史觀念有著強烈的目的論、宿命論與終結論,假定了人類歷史普遍趨同的未來,忽視文明進程的多樣性,容易為各種意識形態(tài)所操縱。此外,統(tǒng)一時間進程的歷史進步觀念帶來虛幻的、浪漫的、盲目的樂觀主義,缺乏對人類生活的憂患意識與自我反思。
結論與啟示
19世紀之后,作為社會科學重要組成部分的政治學與歷史研究之間的關系一直充滿爭議,在轉向歷史過程中存在三個層次的性質差異,即歷史作為方法、作為認知與作為本體。其中,歷史作為方法立足于當下,歷史作為認知把過去與現(xiàn)在關聯(lián)一體,而歷史作為本體是放眼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的連貫性。首先是歷史作為方法。西方社會科學的實證主義方法論傳統(tǒng)糅合經(jīng)驗主義與理性主義兩大認識論傳統(tǒng),一方面,歷史成為可以觀察感知和經(jīng)驗歸納的“試驗場”;另一方面,感性、具體、復雜的歷史現(xiàn)象背后有著本質性存在的因果聯(lián)系與普遍規(guī)律,因此歷史可以作為方法和材料服務于社會科學研究。其次是歷史作為認知,對于關注過去的歷史研究與關注當下的社會科學研究而言,二者從來都是相容為一個整體而不可分離,“以古觀今”與“以今觀古”都把歷史與現(xiàn)實聯(lián)系在一起,旨在共同理解當下問題的歷史成因與歷史變遷的當下后果。最后是歷史作為本體。社會科學與歷史研究的彼此平等融合并非穩(wěn)定不變,歷史在本體層次上的價值或信仰預設不僅影響到歷史研究自身的意義,還關系到社會科學的價值與意義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