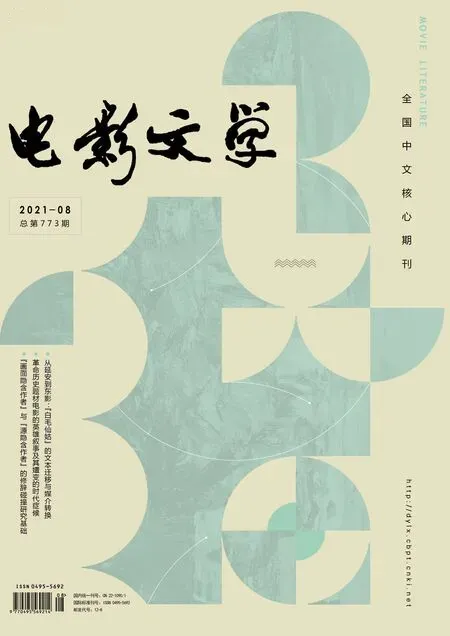《氣球》:超現(xiàn)實(shí)場(chǎng)景中的多重對(duì)話解讀
陳蓓蓓
(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傳媒學(xué)院,江蘇 南京 210013)
萬瑪才旦是藏族本土導(dǎo)演之一,他的上一部作品《撞死了一只羊》是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風(fēng)格的初次嘗試,獲得了第75屆威尼斯電影節(jié)地平線單元獎(jiǎng)最佳影片提名獎(jiǎng)、第13屆亞洲電影大獎(jiǎng)最佳電影提名等一系列榮譽(yù)獎(jiǎng)項(xiàng)。新片《氣球》也在第76屆威尼斯電影節(jié)上引起了關(guān)注,該片主要講述了因傳統(tǒng)信仰與現(xiàn)實(shí)生活的沖突而引發(fā)來自靈魂深處的思考。影片風(fēng)格整體上偏向現(xiàn)實(shí)主義,但其中出現(xiàn)的三個(gè)超現(xiàn)實(shí)場(chǎng)景對(duì)命運(yùn)、生命、人性進(jìn)行了更加深刻隱喻性的詮釋。
第一個(gè)超現(xiàn)實(shí)場(chǎng)景出現(xiàn)在兩個(gè)弟弟讓江洋脫衣服看背上的痣時(shí),這顆痣與他們過世的奶奶身上的痣長(zhǎng)得一樣,所以江洋被認(rèn)為是奶奶的轉(zhuǎn)世,在超現(xiàn)實(shí)場(chǎng)景中,弟弟拿下哥哥背上的痣當(dāng)玩具,透過江洋的視角我們進(jìn)入了一個(gè)江洋追逐著兩個(gè)弟弟的場(chǎng)景;第二個(gè)超現(xiàn)實(shí)場(chǎng)景出現(xiàn)在爺爺意外去世后,依舊是從江洋的視角中我們進(jìn)入了他尋找爺爺?shù)氖澜纾谶@個(gè)場(chǎng)景中,所有的畫面都是從水的倒影中呈現(xiàn),他最終還是沒能追上爺爺,但在道路盡頭他與一只羊相遇;第三個(gè)超現(xiàn)實(shí)場(chǎng)景出現(xiàn)在卓嘎送妹妹離開前,在卓嘎的視角中出現(xiàn)了她與長(zhǎng)發(fā)妹妹溫馨幸福的場(chǎng)景,但顯然妹妹已經(jīng)深深受到情傷而選擇在寺廟剃發(fā)當(dāng)尼姑,現(xiàn)實(shí)中不再可能出現(xiàn)如此歡快的場(chǎng)景。還有兩次一閃而過的超現(xiàn)實(shí)場(chǎng)景分別出現(xiàn)在達(dá)杰去朋友家借種羊喝醉之后,隨著外面的電閃雷鳴他看到窗外的奇妙景象,奠定了影片中達(dá)杰的情緒基調(diào);卓嘎在得知自己懷孕后徘徊于信仰與生活中不知該如何抉擇,她看向水中的自己,迷茫而恍惚。
在多個(gè)超現(xiàn)實(shí)場(chǎng)景的視覺語言上,導(dǎo)演均采用升格畫面、非正常色調(diào)影調(diào)以及模糊等手法來表現(xiàn)特殊情境,這種情境可以視為故事中人物的“夢(mèng)境”,也可以是一種導(dǎo)演為了營(yíng)造相應(yīng)的氛圍而使用的技巧。在聽覺語言的運(yùn)用上,沒有對(duì)話,沒有一切外界聲音,只有迷幻而悠遠(yuǎn)的音樂,與其他現(xiàn)實(shí)場(chǎng)景中的自然音響、人物對(duì)話、幾乎沒有背景音樂鋪陳形成鮮明對(duì)比,一方面渲染了悲涼莊重的場(chǎng)景氛圍,另一方面更加突出這幾個(gè)超現(xiàn)實(shí)場(chǎng)景,且迅速帶觀眾進(jìn)入其中。好萊塢商業(yè)片中超現(xiàn)實(shí)場(chǎng)景通常依托于特效等科技手段呈現(xiàn),帶給觀眾巨大的視覺沖擊力,以博取觀眾眼球。而萬瑪才旦導(dǎo)演《氣球》中的超現(xiàn)實(shí)場(chǎng)景,則是另一種不同的表現(xiàn)。《氣球》在運(yùn)鏡上十分平穩(wěn),也沒有人物間的對(duì)話,升格鏡頭與空靈平緩的背景音樂凸顯出超現(xiàn)實(shí)場(chǎng)景的特殊性,符合影片整體營(yíng)造出來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氛圍,也同時(shí)是萬瑪才旦本人的鏡頭語言風(fēng)格。
萬瑪才旦導(dǎo)演一向聚焦于書寫小人物的身世命運(yùn)的迂回輾轉(zhuǎn),借助自己藏族本土導(dǎo)演的優(yōu)勢(shì)描繪著一系列藏族人獨(dú)有的民俗、儀式,《靜靜的嘛呢石》刻畫古老的世俗文明與新興的外來文化的沖突下人們的不同迷茫狀態(tài);《尋找智美更登》以藏戲?yàn)橐v述尋找自我的故事;《老狗》則通過賣不賣純種藏獒這一問題引發(fā)了一系列對(duì)商業(yè)利益驅(qū)使下人們的原始信仰也受到?jīng)_擊這一問題的思考;《塔洛》深刻探討著物欲橫流的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對(duì)純粹藏族身份、靈魂的吞噬與裹挾。在《氣球》中,他再次直擊藏族人靈魂深處的痛楚,加入超現(xiàn)實(shí)元素,并且采用氣球這一多重意象性指代的物質(zhì)為線索講述藏族現(xiàn)實(shí)故事。
一、人類對(duì)話生靈:命運(yùn)的映射
英國(guó)著名藝術(shù)批評(píng)家約翰·伯格指出:“動(dòng)物的生命不會(huì)與人互相混淆而被視為和人類生命平行。因此只有在死亡狀態(tài)下,這兩條平行線才互相交疊,或者再因互相交疊而再度平行;這就是‘靈魂轉(zhuǎn)世’這種普遍的信仰之由來。由于二者的平行生命,動(dòng)物能提供給人們一種互相為伴的感情。”在影片《氣球》中,除了“氣球”本身之外,“羊”作為另一個(gè)重要的元素貫穿故事始終,首先種羊作為男性力量的代表,去選擇自己滿意的母羊作為交配對(duì)象。而不能繼續(xù)下羊崽的母羊被拽出羊群,被人類所拋棄。在江洋視角下的超現(xiàn)實(shí)場(chǎng)景中,他跟丟了去世的爺爺卻在道路盡頭與羊相遇,一方面印證了約翰·伯格所說的人類與動(dòng)物兩條平行線交疊,另一方面也隱喻著生靈對(duì)于人類命運(yùn)的投影與映射:無法掌控自己而被支配的命運(yùn)。在影片體現(xiàn)的現(xiàn)實(shí)世界中,羊有兩種命運(yùn):其一,作為物種延續(xù)的生產(chǎn)者,被迫配種;其二,被人類宰殺成為食物或者被販賣維系生活。動(dòng)物不僅在自己的世界中,存在著競(jìng)爭(zhēng)與選擇,同時(shí)它們還面臨著人類的控制與掌握。羊尚且如此,人類也并不例外,要忍受同類與傳統(tǒng)道德規(guī)范夾持的雙重壓力。在卓嘎身上,沒有“氣球”照樣被丈夫達(dá)杰逼迫著與自己結(jié)合,意外懷孕之后又被逼著留下孩子,不能去墮胎。達(dá)杰認(rèn)定這個(gè)孩子是死去父親的轉(zhuǎn)世,而卓嘎出于身邊人的勸阻及對(duì)現(xiàn)實(shí)生活困境的考慮,不想留下這個(gè)意外得來的孩子。達(dá)杰所代表的觀念是傳統(tǒng)信仰下的轉(zhuǎn)世輪回觀,而卓嘎則立足現(xiàn)實(shí)試圖拋棄傳統(tǒng)。但卓嘎并不是堅(jiān)定的,在醫(yī)生反復(fù)勸阻下,她沒有自己決定選擇與丈夫商量,刻意避開遠(yuǎn)道而來的醫(yī)生不想面對(duì)這一現(xiàn)實(shí)狀況。
同時(shí),卓嘎在發(fā)現(xiàn)自己懷孕前告訴達(dá)杰自己做了一個(gè)夢(mèng),夢(mèng)見那只不能產(chǎn)崽的母羊突然下了一只濕漉漉的羊羔。這段情節(jié)雖然沒有用超現(xiàn)實(shí)場(chǎng)景表現(xiàn),但在卓嘎的敘述中,也十分具有說服力。在人類與生靈的對(duì)話中,生靈任人宰割沒有自我話語權(quán),此時(shí)生靈命運(yùn)是人類命運(yùn)的映射,兩者都無法自己掌控。與此類似,在萬瑪才旦導(dǎo)演的《老狗》中,老狗作為傳統(tǒng)藏民精神的依托,以生靈老狗的命運(yùn)為引,老人拼命想要留下作為牧人朋友的純種藏獒,而兒子在利益驅(qū)使下要將藏獒賣到小販?zhǔn)种校趥鹘y(tǒng)與現(xiàn)實(shí)的較量中,老人選擇親手結(jié)束老狗的生命。“在影片中,父子對(duì)比、沖突與和解始終貫穿影片,老人出現(xiàn)時(shí),總是騎馬,而兒子總是騎摩托車;老人抽煙袋,兒子抽香煙;兒子喝酒、打臺(tái)球,老人手持念珠念經(jīng)”。現(xiàn)代文明對(duì)于藏族文化的沖擊體現(xiàn)為摩托與馬兩種交通方式互不相容,兒子不想面對(duì)不能生育的事實(shí),藏獒被老人親手扼殺,老人最終顯然是沒有向現(xiàn)代文明妥協(xié)的,所以將藏獒留存在過往的文化中。
約翰·伯格在《看》中還提到:“若說動(dòng)物是最原始的隱喻,那是因?yàn)槿撕蛣?dòng)物之間的基本關(guān)系是隱喻性的……無論何處,動(dòng)物提供我們以解釋,或者更確切地說,借它們的名字或性格來讓我們形容某些特質(zhì)。”藏族得天獨(dú)厚的地理優(yōu)勢(shì)使其孕育著牛、馬、羊等這些動(dòng)物,萬瑪才旦在《氣球》中通過對(duì)動(dòng)物生靈命運(yùn)的書寫,映射著人類自身的命運(yùn)走向。
二、生者對(duì)話亡靈:生命的延續(xù)
《氣球》中出現(xiàn)的第一個(gè)超現(xiàn)實(shí)場(chǎng)景就體現(xiàn)了生者與亡靈的對(duì)話,兩個(gè)弟弟拿下了江洋身上象征著奶奶轉(zhuǎn)世的痣當(dāng)玩具,江洋在后面追逐著兩個(gè)弟弟跑向山坡盡頭,隨著兩個(gè)光著身子的弟弟消失在山坡上,江洋停下了腳步。這個(gè)超現(xiàn)實(shí)場(chǎng)景暗示著江洋是奶奶生命的延續(xù),在爺爺和爸爸的日常對(duì)話中,也在反復(fù)感嘆與強(qiáng)調(diào)著這場(chǎng)生命的輪回。兩個(gè)小孫子問到爺爺他們是誰的轉(zhuǎn)世,得到的回復(fù)是暫時(shí)不知道,但一定是某個(gè)生命的轉(zhuǎn)世。在這個(gè)超現(xiàn)實(shí)場(chǎng)景中,兩個(gè)小孫子沒有穿衣服隱喻著他們暫時(shí)沒有受到生命輪回轉(zhuǎn)世的牽絆,無憂無慮,甚至去任意拿下奶奶轉(zhuǎn)世的標(biāo)志性象征。而在故事后面,父親去世,達(dá)杰從上師處得知他會(huì)轉(zhuǎn)世到自己家中,碰巧達(dá)杰的妻子卓嘎懷孕,故而達(dá)杰認(rèn)定這個(gè)孩子就是自己父親的轉(zhuǎn)世。
另一個(gè)超現(xiàn)實(shí)場(chǎng)景是江洋追逐著已經(jīng)去世的爺爺,所有的畫面都在水的倒影中呈現(xiàn),在道路盡頭爺爺消失。在這場(chǎng)生者與亡靈的對(duì)話中,生者是被選擇的一方,生來就是某一生命的延續(xù)。生命的輪回轉(zhuǎn)世觀體現(xiàn)著藏族人民深刻的宗教信仰,他們認(rèn)為一個(gè)人的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終結(jié),只是在另外一個(gè)新生的生命中繼續(xù)生存。卓嘎基于現(xiàn)實(shí)生活狀況,試圖反抗傳統(tǒng)信仰的行為被達(dá)杰深深抵制,他寧愿生活極度困難也不愿拋棄信仰。伴隨著這種轉(zhuǎn)世觀念而來的是藏族人民自我認(rèn)同的身份困境,他們與生俱來的“他者轉(zhuǎn)世”身份,賦予了他們一場(chǎng)特殊的使命:生來就是另一個(gè)人生命的延續(xù),要帶著另一個(gè)人的信念生存下去。
張楊導(dǎo)演作為非藏族本土導(dǎo)演以他者言說的“外視角”來闡述藏族故事,在《岡仁波齊》中也印證著生命的輪回轉(zhuǎn)世:一心想要替哥哥洗去罪過的楊培老人在朝圣岡仁波齊的路途中安靜離世,新生命丁孜登達(dá)的誕生仿佛就是老人生命的輪回。“現(xiàn)在的西藏,早已不是過去神秘且封閉的世外空間,而是一個(gè)逐漸被外來的現(xiàn)代文化改變著的新的西藏,關(guān)于西藏身份的體認(rèn)又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外來的文明并沒有要求藏族人摒棄原有的傳統(tǒng)宗教信仰,而是希望他們基于傳統(tǒng)信仰的層面上,尋求與自我身份認(rèn)同兩者間的平衡。萬瑪才旦的另一部?jī)?yōu)秀作品《塔洛》同樣在探討身份缺失問題,塔洛身邊的所有人甚至想不起他的名字,只稱他為“小辮子”,為證明自己的社會(huì)身份被迫辦理身份證。他的記憶力極好,能清楚記住自己什么時(shí)間養(yǎng)了幾只羊,甚至完完整整地背誦出毛主席《為人民服務(wù)》段落。但隨著愛上了鎮(zhèn)上的一個(gè)姑娘,他剪掉了小辮子,被姑娘欺騙丟失了一切財(cái)產(chǎn),因發(fā)型與之前辦好的身份證不一致被要求重新拍照補(bǔ)辦身份證,他徹底迷失自我,成為現(xiàn)代文明的犧牲品。
“羅蘭·巴特在闡釋愛森斯坦的電影時(shí)講到所謂‘第三意義’。他把一個(gè)場(chǎng)景的意義分為三個(gè)層次:信息層次、象征層面和第三層面。在第一個(gè)層面上,意義通過參照必要的事實(shí)和現(xiàn)象產(chǎn)生。在第二個(gè)層面上,意義通過聯(lián)想來獲得。第三個(gè)層面通常由突兀的結(jié)構(gòu),奇怪的表征和過度的形式構(gòu)成,意義很難明確。”在這里提到兩個(gè)超現(xiàn)實(shí)場(chǎng)景,信息層次即我們所看到的江洋追逐弟弟、尋找爺爺;象征層面則是他們都是不同的亡靈的轉(zhuǎn)世,死亡即意味著新的開始;第三層面指代生命輪回轉(zhuǎn)世觀這一藏族的傳統(tǒng)信仰毋庸置疑,凡違抗都是有悖于傳統(tǒng)道德的行為。
三、本我對(duì)話超我:人性的救贖
在卓嘎視角下的超現(xiàn)實(shí)場(chǎng)景中,妹妹香曲卓瑪恢復(fù)了往日的長(zhǎng)發(fā),笑容天真爛漫,整個(gè)畫面充斥著歡快與自由,而這種場(chǎng)景也正是現(xiàn)實(shí)生活中不可能出現(xiàn)的。萬瑪才旦的原小說《氣球》中,并沒有以妹妹為線索再展開一條故事線,影片在有關(guān)妹妹的這部分故事中增加了很多書寫空間。雖然影片中并沒有直接闡述發(fā)生在妹妹身上的往事,但我們從身邊人與她的對(duì)話以及影片中的中學(xué)老師為她寫的《氣球》一書等種種行為下,可以推斷出妹妹曾經(jīng)所犯的過錯(cuò)導(dǎo)致她選擇當(dāng)尼姑來彌補(bǔ)。影片中刻意強(qiáng)調(diào)了妹妹痛徹心扉的愛情經(jīng)歷這條線索,用來增加卓嘎這一人物形象的戲劇性,卓嘎對(duì)于那位中學(xué)老師來找妹妹這件事的態(tài)度是堅(jiān)決反對(duì)的:不允許妹妹再對(duì)過去有絲毫留戀。與此相反,她在自己意外懷孕對(duì)于是否墮胎的選擇上卻徘徊不定,這也體現(xiàn)了卓嘎這一女性角色的矛盾性:既迫于世俗深受傳統(tǒng)道德觀念的影響,又想要從中試圖反抗獲取一絲女性的自由。
弗洛伊德提出三重人格理論的概念:“一是本我,指最原始的、與生俱來的潛意識(shí)的部分。基本由性本能組成,代表人的本能欲望。二是自我,是理性的代表,是來自本我經(jīng)外部世界的影響而形成的知覺系統(tǒng)。三是超我,代表社會(huì)道德準(zhǔn)則和倫理觀念方面的要求,它要努力達(dá)到的是完善而不是快樂或現(xiàn)實(shí)。”在《氣球》中的兩位主人公卓嘎和達(dá)杰身上,本我體現(xiàn)為兩人對(duì)彼此的欲望,在原始的沖動(dòng)下,他們?cè)跊]有找到避孕套的情況下仍然選擇彼此結(jié)合,拋卻了一切可能發(fā)生的后果選擇當(dāng)下的歡愉。卓嘎意外懷孕后,在達(dá)杰身上,自我是缺失的一部分,他根據(jù)傳統(tǒng)信仰的要求當(dāng)機(jī)立斷覺得孩子是父親的轉(zhuǎn)世并執(zhí)意留下孩子,正因?yàn)樗裱^往經(jīng)驗(yàn)得出了如此判斷,故而與擁有自我的妻子產(chǎn)生劇烈的沖突矛盾。由于家里已經(jīng)有了三個(gè)孩子,再生第四個(gè)孩子不僅會(huì)被罰款,給本不富裕的家庭帶來更大的困難,而且會(huì)影響現(xiàn)有三個(gè)孩子的成長(zhǎng)進(jìn)程。卓嘎的自我體現(xiàn)在她既考慮到了傳統(tǒng)信仰下的倫理規(guī)范,又結(jié)合當(dāng)下情況做出了進(jìn)一步判斷,而她身邊的人對(duì)墮胎一事有支持有反對(duì),更加阻礙了她最終抉擇的方向。最后的超我在卓嘎身上也有所體現(xiàn),影片最后卓嘎躺在手術(shù)臺(tái)上準(zhǔn)備墮胎的剎那,被慌忙趕來的丈夫和大兒子所阻止,她跟隨妹妹一起去寺廟生活一段時(shí)間后,最終導(dǎo)致了自我的迷失。
雖然影片設(shè)置了開放式結(jié)局,沒有呈現(xiàn)出卓嘎究竟是否仍選擇墮胎,但在丈夫、妹妹、兒子的態(tài)度中,觀眾能夠想象到更可能的結(jié)局,這里萬瑪才旦在慣用的水面表現(xiàn)空間中映射出卓嘎孤立無援的復(fù)雜心境。卓嘎是希望遵從內(nèi)心追求個(gè)體自由的,但她卻始終在被迫著選擇傳統(tǒng)信仰下的道德規(guī)范,被動(dòng)實(shí)現(xiàn)所謂的“超我”,進(jìn)而達(dá)到人性的救贖。在這個(gè)超現(xiàn)實(shí)場(chǎng)景中,她與妹妹的歡樂互動(dòng)場(chǎng)景與現(xiàn)實(shí)困境形成鮮明對(duì)比,虛幻場(chǎng)景使得擁有原始快樂的本我和面臨現(xiàn)實(shí)困境的超我相遇,最終在他者的指引下得到了救贖。關(guān)于人性的救贖是藏族題材影片一直在探討的主題,松太加導(dǎo)演的《太陽總在左邊》中的主人公意外將母親碾死車下,在朝拜拉薩的路上完成自我心靈的救贖;張楊導(dǎo)演的《皮繩上的魂》中,塔貝在護(hù)送天珠去往蓮花生大師的掌紋地路途中放下過去,尋找真正的自我,完成生命的輪回與人性的救贖。在人性救贖這一永恒主題下,藏族題材電影提供了一個(gè)典范,也深刻地彰顯出民族精神與時(shí)代文化。
《氣球》中三處超現(xiàn)實(shí)場(chǎng)景的作用更偏向于增加影片對(duì)于命運(yùn)、生命、人性的刻畫程度,展現(xiàn)了故事中人物在現(xiàn)實(shí)場(chǎng)景無法實(shí)現(xiàn)的另一種結(jié)果,從而上升到對(duì)影片主題的書寫:傳統(tǒng)信仰與現(xiàn)實(shí)生活產(chǎn)生劇烈沖突的情況下藏族人民的不同抉擇。除了頗具想象力的超現(xiàn)實(shí)場(chǎng)景,對(duì)于影片本身來說,其中的“氣球”意象第一層面指的是兩個(gè)兒子的玩具氣球;第二層面指的是避孕套,為了遏制本我欲望沖動(dòng)所產(chǎn)生的后果,同時(shí)也意外地被兩個(gè)小兒子當(dāng)作玩具;第三層面體現(xiàn)在精神上,在傳統(tǒng)的意識(shí)觀念中,由于避孕套作為“性”的象征成為藏族人民不可言說的一部分,也使它變得神秘而不可觸碰,所以在兩個(gè)小兒子當(dāng)玩具玩的時(shí)候才會(huì)立刻被父親扎破,因其本身特定的功能成為藏族人民遵守傳統(tǒng)信仰的精神符號(hào),當(dāng)這種精神符號(hào)消失時(shí),留在原地的人就會(huì)與現(xiàn)實(shí)生活產(chǎn)生難以協(xié)調(diào)的矛盾。與此同時(shí),“氣球”這一意象在電影中并不少見,在楊德昌導(dǎo)演的電影《一一》中,洋洋在老師面前拿出“氣球”,此時(shí),洋洋眼中的玩具與老師眼中的避孕套形成電影的戲劇張力,體現(xiàn)了兒童世界和成年人世界的巨大差異;姜文導(dǎo)演的《陽光燦爛的日子》中,由于調(diào)皮的馬小軍不小心扎破了父親藏在抽屜里的避孕套而感到格外害怕,描繪出中國(guó)20世紀(jì)七八十年代社會(huì)對(duì)于性的遮蔽;在2018年德國(guó)同名電影《氣球》中,紅色的熱氣球是帶領(lǐng)主角一家人逃離黑暗走向光明與自由的唯一希望。由此可見,“氣球”本身所具備的象征含義也是極其豐富的。
萬瑪才旦導(dǎo)演說:“我并不拒絕現(xiàn)代化,我的作品呈現(xiàn)的也并不是現(xiàn)代和傳統(tǒng)之間的二元對(duì)立,而只是一種現(xiàn)實(shí)的狀態(tài)。”他用現(xiàn)實(shí)主義敘事方式來表現(xiàn)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shí)的沖突這一主題早在《靜靜的嘛呢石》《老狗》《五彩神箭》等作品中就有所呈現(xiàn),新片《氣球》融入了超現(xiàn)實(shí)場(chǎng)景和藏族女性試圖爭(zhēng)取自由的反抗意識(shí)兩種新元素,使得藏族題材影片不僅在畫面風(fēng)格、視聽語言上有了進(jìn)一步的發(fā)展,在藏族故事的主題及敘述上也取得了較大的突破。新世紀(jì)以來,藏族題材電影發(fā)展迅猛,呈現(xiàn)主題多元化、視聽語言多樣化的趨勢(shì),一批優(yōu)秀的藏族題材影片導(dǎo)演也應(yīng)運(yùn)而生。萬瑪才旦的多部影片在國(guó)際電影節(jié)上獲得關(guān)注,他用這種方式拉近藏族故事與世界各民族觀眾的距離,加之松太加、拉華加、張楊等多位導(dǎo)演不同視角下對(duì)藏族故事的書寫,彰顯著藏族文化的獨(dú)特魅力,這對(duì)藏族本土文化走入全民族視野無疑是意義重大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