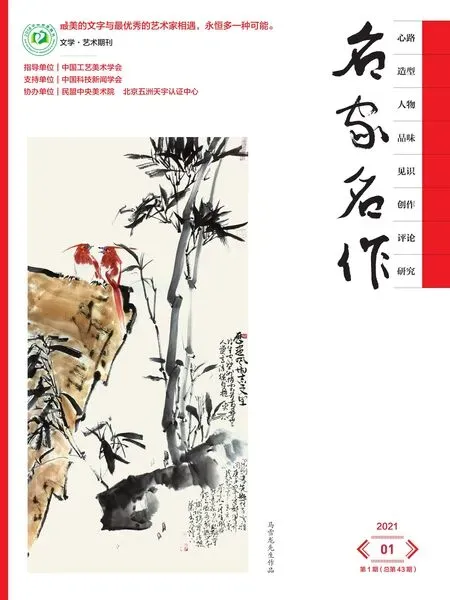淺談人物畫的造型與筆墨關系
閆超杰 鄧益民
繪畫是一種造型藝術,對于中國人物畫而言造型更是至關重要的,只有生動準確的人物形象才能傳達出畫面的“氣韻”來。中國傳統繪畫以“形”來代指造型,相關的說法有“以形寫神”“形神兼備”等,中國畫作為一種似與不似、寫實與寫意之間的繪畫,其“形”偏重于二維平面的線面造型,并以線為基本造型因素;而西方繪畫力圖在畫布上呈現出人和物在空間中的真實存在,其造型藝術是在平面之中虛構一個空間,通過對縱深的處理和人體結構的理解,繪就寫實的造型,其造型藝術偏重于體面造型。
20 世紀以來,徐悲鴻引進西方科學的素描和造型體系對人物畫進行改造,再加上蔣兆和的教學實踐和改良,美術學院中國畫學科形成了較為科學嚴謹的“徐蔣體系”。這個體系成就了一批優秀的人物畫家,如蔣兆和、周思聰、劉國輝等,但出現的問題是筆墨關系在較大程度上為人物造型服務,失去了文人畫筆墨力透紙背、一波三折的書法性用筆“寫”的特性。“中西融合”絕不應該僅僅是用筆墨和宣紙去畫造型準確的人物素描,而應當較大程度地保留中國筆墨精神和審美價值的前提下,吸收、融合西方科學的造型體系,以創作出具有時代風格特征的新作品,這種有機的結合從來都是艱難的,但藝術之所以能夠不斷發展并呈現出新面貌,關鍵就在于不同文化、地域,不同藝術門類之間的吸收綜合。因此,總體來說,對于西方科學的造型體系尤其是素描的輸入要給予肯定,而現在面臨的如何處理傳統筆墨與西方造型之間關系的問題也需要解決。
對于這一問題,為了“形”的合乎比例以及動態準確而犧牲“筆墨”,或讓利于“筆墨”而失去對“形”的創造,還有為了畫面整體需要,“形”和“筆墨”都做減法,這樣的做法都是不成熟且無奈的選擇。上文提到,中國畫以線為基本造型因素,不妨從傳統的“線”和“白描”入手,看是否有一些新的可能性。
中國早期的人物畫用線條勾勒而成,到后來才慢慢發展出了簡筆和潑墨,即使發展到現在,線條仍然是學習人物畫最初必要的基礎練習,原浙江美院的潘天壽先生在教學中就對學生強調人物畫線面造型的重要性,倡導在寫生中通過“線”聯系起體面和筆墨,并把它貫徹到日常速寫的訓練中。速寫生動活潑且快速,與中國畫中的線關聯較大,習畫者可以以線為基礎,力求“骨法用筆”地抓住對象的神態、比例和特征,一方面抓住了中國畫的線條因子,一方面又兼顧了客觀造型和人物。但在長此的寫生和創作中,如果要發揮其筆墨的審美趣味的話,就不能在深入塑造形象時使線消失在體面轉折中,成為“體”的一部分。這就要求我們要充分發揮人物畫中線的雙重作用,即實現造型和筆墨關系兩者的有機結合,同時也要根據畫面對象和畫家的思想情感來具體實施。
崛起于20 世紀50 年代中期的“浙派人物畫”,如方增先、周昌谷等人,他們的藝術實踐就很好地體現了這種結合,墨色點染、線墨結合,筆中有墨、墨中有筆,線條更加自由奔放,少了素描的感覺,多了傳統水墨的韻味。另外,在“線”的運用上有較大突破的還有“以速寫入畫”的黃胄、葉淺予等畫家,他們將速寫與水墨相結合,拋開素描的光影關系,用靈活的線條表現生動的人物形象,同樣體現了中國水墨語言的魅力。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兩條藝術實踐的道路上,他們進行的造型與筆墨語言的結合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浙派”內化了人物造型并外現了中國水墨的韻味,在科學造型的基礎上表現了意象特征,而“以速寫入畫”這一路則以繪畫中的“生動性”為連接點,將速寫造型與筆墨語言連接并置,融合之后呈現在畫面上,實現了精彩的藝術效果。
無論是在上述兩類藝術實踐中還是在更多的人物畫畫家作品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降低明暗光影”和“平面化”的特征,這和中國畫的特點有關,中國畫的媒介材料不適用于表現三維立體的真實人物形象,而對西方造型體系中科學的人體結構、速寫的活力、色彩的表現、構圖的特點等倒是可以借鑒吸收,將它們和傳統筆墨語言進行恰當的結合,或許可以發展出新的面貌。
下面來談一談筆墨語言。中國人物畫中的筆墨,一是為了塑造形象,即造型,作為一種輔助手段,“筆以立其形質,墨以分其陰陽”;二是作為一種符號,皴擦點染,濃淡干濕,或是點線交織,它們具有獨立的審美價值,不依存于客觀對象,作為抽象形式可以被復制和重組;三是體現出畫者的情感思考和美學趣味,豐富的筆墨圖式和技法表現是一種與畫家心靈相通的“有意味的形式”,也正因為如此,不應當為了造型的科學合理或者人物的動態準確而犧牲“筆墨”,筆墨一皴一擦之間滲透著中國人的思想觀念和人生情懷,筆墨與傳統文化,與中國哲學、文學等有著深刻的內在關聯。
就目前來看,人物畫中的筆墨作為造型手段,必須保留;筆墨作為一種審美形式和符號,要從其豐富的語言中加以提取,使之與科學的人物結構和造型相適應;最后,筆墨仍然要體現出畫者的思想情感和美學趣味,雖然當代畫家的思想、意識和情懷等與古代文人畫家的思想情懷相差巨大,但它們有著一個共同的思想基礎——中國文化,在傳達古人精神的筆墨語言基礎上如何變化才能更符合當下人的審美觀念?對于這個問題,要細細研究,反復琢磨和比較并進行大量實踐。
筆墨落在宣紙上,會產生不同的筆跡效果,因此,國畫用筆可以產生很多表現技法,如中鋒、側鋒、頓挫、順逆、皴擦、渲染,除了要根據畫面對象恰當地運用這些技法外,應用到人物畫上主要是對衣紋進行組織安排和取舍,體現出形式美和舒適感,古人的這套體系已十分成熟,但當代人物衣紋服飾的用筆、用線則需要進一步地探索和完善,同時也要根據客觀對象來安排筆墨語言,比如畫老人可以用墨干澀,用焦墨、重墨,畫女性則相應濕潤,不宜過多皴擦。用墨的技巧也很重要,傳統有墨分五色的說法,用墨既要注意濃與淡的強烈對比,也要注意濃淡的細微起伏。墨的聚散、墨色平衡、墨色深淺等要在實際操練中逐漸體會和把握,積墨法、破墨法也要合理地表現人物的體積、服飾的質感等。除了用筆和用墨外,筆墨組織其實更為重要,它不但關乎技法,更關乎審美的內在理解,是對秩序、和諧、律動關系的總的理解和看法,一幅優秀的人物畫必定有著良好的筆墨組織。
筆墨在傳承的過程中,形成了許多程式與規范,這種規范有利于筆墨語言的沿襲繼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畫家的個性表達,這種約束其實在明清就已有體現,而對于經歷過戰爭和革命洗禮的現代中國社會而言,舊的筆墨程式已經非常不適用于描繪和表達新的社會氛圍、人物面貌等,這要求人物畫的筆墨語言必須打破以往的規范,走上新的發展之路。事實上,20 世紀中國人物畫的實踐已經取得了很大成果,對于西方造型的引入所帶來的問題,前文提到的一些大家已經做出了一番探究和梳理,這對我們而言是值得借鑒的經驗,但也應當更往前一步,去發揮更多的自由和創造力,但這并不意味著不再有問題和限制,它會隨著人物畫中筆墨和造型的深入而逐漸凸顯出來,而通過對這些問題的解決會形成新的規則,新的規則會構成新的筆墨形態或程式,筆墨就是在這樣回旋演進的過程中體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和豐富的可能性的。
人物畫中造型與筆墨關系的問題,歸根結底在于當代生活中的實踐。一方面,在人物畫寫生與創作中,要有“骨法用筆”的意識,用線不僅要貼合人物造型,也要根據對象的特征發揮自己的感受,用筆要變化多樣,在表現人物的各種形象和動態時,可以用皴擦、渲染、輔線、復線等方式來塑造形體,從而增加線的表現力。線本身是抽象的,畫面中的線是畫家通過對衣服褶皺及其明暗投影的分析組織而形成的,這種能力需大量寫生和反饋才可獲得。同時,也應當將主觀的認識、感受、思考及平日的修養融入畫面之中,所謂繪畫的時代性并不是去刻意追求的,而是在真誠的思考和實踐中潛移默化地體現出來的。“氣韻生動”“以形寫神”等法則仍然可以作為我們追求的目標,中國文化強調天人合一,客觀原則和主觀心靈是可以一并呈現出來的,人物畫的造型和筆墨語言當然也可以實現良好的結合,在今天多元化的生活中,要發揮中華文化擅長吸收綜合的特點,要學會“架橋”,面對這個轉型的世界,要將古今中外有價值的藝術要素進行簡化與新的綜合,在繪畫面貌上闖出一片“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