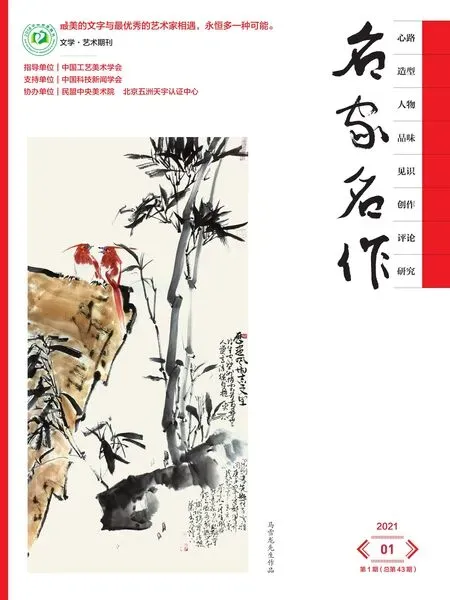愛是靈魂的花朵
——試評郭卿的愛情詩
王立世
沒有靈魂的生命,僅僅是核酸和蛋白質。沒有愛的靈魂,無異于荒漠和廢墟。
我曾經說過,一輩子沒有寫過愛情詩的詩人不可想象。從古至今,那些優秀詩人,總有幾首愛情詩讓人陶醉。還有一些詩人,如歌德、葉芝、普希金、莎士比亞、倉央嘉措、白朗寧夫人、徐志摩等,一生創作了大量的愛情詩。一般而言,詩人最早的創作離不開青春和愛情這兩大主題。在女詩人的創作中,愛情詩占比更大,因為愛情在她們生命中至關重要,靈魂的香氣主要來自愛情的花朵。她們的愛情詩寫得細膩、溫潤、深情、飽滿,如林徽因的《別丟掉》、舒婷的《四月的黃昏》、戴濰娜的《悖論》、燈燈的《我的男人》、張琳的《我的愛情觀》、玉珍的《愛和骨頭有關》、施施然的《想和你在愛琴海看落日》等。從這些優質的愛情詩中,可以讀出她們生命的靈光和靈魂的秘密。
郭卿在社會闖蕩多年以后,步入中年時與繆斯在伊甸園不期而遇。青春寫作靠的是激情和靈感,中年寫作靠的是閱歷和感悟。她的詩,像歲月的流水緩緩漫過心靈的堤岸,有了中年的從容、沉著和智慧,但不時翻卷起情感的浪花拍打著你,讓你體味到從容中的窘迫、沉著時的忐忑、智慧外的疼痛。她的詩,既不是激情似火,又不是冷若冰霜,而是冷中有熱、靜中有動、苦中有甜。情感既單純又復雜,既明朗又迷蒙,既真誠又凝重。讀她的詩,可能不會一下子叩響你的心弦,但最終會引爆你的內心世界。她的詩一開始就有別于他人,因為她寫的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體驗、自己的甘苦,不是千人一面、眾口一詞,而是風格獨特、辨識度極高的那類。
郭卿的愛情詩呈現過去、現在和未來三種時態,對應的空間是養育她的故土和安身立命的都市。時空交錯,展現出個體的真實存在,搖曳著靈魂的美麗光影,其精神境界僅靠文字是無法完成的,離不開人生豐富的歷練和情感長期的積淀。在某個角度看,是多舛的命運成就了她的詩歌,反過來詩歌又在撫慰著她帶傷的生命。
《一棵開花的樹》寫的就是過去的愛情,早已逝去且無法挽回的愛情:風吹,整整一晚/天亮了落紅滿地/那天你娶了鄰村的滿花/散了,一對青梅竹馬//一曲鄉謠,唱斷春風流水/今天我回來/看你碩果累累/在山野長成一棵老樹/開滿唐詩宋詞//紅袖添香的/卻不是我。
詩人借“一棵開花的樹”寫一段青澀、美好而又悲傷的愛情。從“整整一晚”可以體悟到詩人對風的憎惡和內心的無助,也不難想象詩人輾轉反側、一夜難眠的痛苦情狀。這“落紅滿地”有秋風掃落葉的蕭瑟凄涼。“你”為什么一改初衷“娶了鄰村的滿花”?是誰拆散了“一對青梅竹馬”?一看寫的就是“有情人難成眷屬”的無奈和失望,表面的平靜難以掩飾內心的波瀾。詩人只寫事實和結局,背后的原因只字不提,給讀者留下了廣闊的想象空間。讀到此,方才明白,寫落花就是為了寫愛情的凋謝,這風就像陸游《釵頭鳳》中的“東風惡”一樣,制造了一出人間愛情悲劇。
“一曲鄉謠,唱斷春風流水。”什么樣的鄉謠不得而知,很可能就是婚禮上的唱詞,但在詩人聽來卻是如此的尖利。一個“斷”字大煞風景,春風不再。詩人用的是通感,隱喻內心失落的蒼涼。就像“東邊日出西邊雨”一樣,有人歡喜有人悲。悲的人是真悲,歡喜的人卻不一定真歡喜。時光匆匆,大半的人生一晃而過。“今天我回來/看你碩果累累/在山野長成一棵老樹/開滿唐詩宋詞”。詩人以樹喻人,用樹的蒼老隱喻歲月無情,用樹的碩果累累隱喻曾經心儀的人已經兒孫繞膝。塵世滄桑,青春難覓。寫樹“開滿唐詩宋詞”,內心一定是五味雜陳。“我”花落誰主?過得如何?又是一個謎。蒼老的“你”遇到曾經年輕的“我”,內心會翻江倒海嗎?詩人故意省略了許多,就像畫畫一樣,布下大片的留白讓人想象,這才是詩的凝練和彈性。
“紅袖添香的/卻不是我”。對逝去的愛情念念不忘,一聲短嘆飽含著無盡的遺憾和惋惜,真是哀音不絕、苦味無窮。
人和樹交錯著寫,情趣頓生。寫樹是為了寫人,而且抓住了共同特征,處處形成對比,悲喜交集,明暗映襯。情感表達得含蓄委婉,把控又適中。以浪漫寫現實,不失為一大特色。通感運用自如,極大地增強了情感的張力,將詩歌的審美有效地擴容。
青春期的愛情浪漫如云,雖自由舒展,但說變就變,具有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寂靜》《天梁河》《證據》寫的就是中年的愛情。詩人已經從青春的夢中醒來,扎根于現實豐厚的土壤,情感生長得枝繁葉茂,思想不再左右搖擺。愛需要從一點一滴做起,經歷細微而堅實的過程,不像做廣告那樣張揚。《寂靜》就是這樣的一首詩,但內心一點也不寂靜:一棵是棗樹/另一棵也是棗樹/秋天里/你看見樹上綴滿了青果/你沒看見的是/春天的夜晚,那些翠綠的小花朵/一點一點地開,像我對你/一點一點的愛。
這首詩開頭巧妙地引用了魯迅《秋夜》中的名句,卻一點也不突兀,感覺自然、貼切。詩人的棗樹沒有魯迅那樣深刻的社會內涵,只是表達生活的平凡與寂靜。往下寫就更不相同了,意象的捕捉不同,情感的色彩不同,思想的深淺不同。郭卿寫得風輕云淡,委婉而細膩地展現出一個普通女子真摯而美好的心靈世界。詩中寫到的人物“你”,只看到秋天的青果,卻忽略了春天的花朵,重結果不重過程。女詩人的關注點正好相反,她更在意那些翠綠的小花朵“一點一點地開”的過程,因為“像我對你/一點一點的愛”。讓我想起李敖“不愛那么多/只愛一點點”的情詩。郭卿也不同于李敖,而是一點一點地積攢,有水滴石穿那般的堅韌,直到結出香甜的果實,量變發生了質變。如此輕柔而執著的愛卻被所愛的人忽略,內心難免生出淡淡的憂傷,證明了再好的愛情也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如果一直寫景,寫得再好也有局限。郭卿出其不意地寫到愛,而且用花開作比,情與景在寂靜的狀態下像水乳一樣交融于一體,有一種無言的美、傷感的美、人性的美。好些詩歌敗在結尾,前功盡棄,這首詩結尾加分不少,它沒有破壞寂靜的氛圍,還傳導出愛的溫情脈脈,平淡中閃耀出絢爛,庸常中陡現崇高。
《天梁河》是詩人的代表性作品。著名詩歌評論家呼巖鸞先生認為“這首詩像白話唐詩,既古典,又現代 ”。中年的散淡、人生的滄桑盡現筆下,但對愛堅不可摧的信念令人感動:有時候,我們慢慢地走著/誰也不說話/遠處是危崖,腳下/大雨之后的碎石之間 /叢生的那些草,散漫而安靜/仿佛我們的一生/可以被踐踏,可以被埋沒/而從不被所愛的人忽略。
這首詩不同于舒婷凸顯女性思想獨立的《致橡樹》,也不同于伊蕾宣泄女性生命意識的《獨身女人的臥室》,是屬于郭卿自己的《天梁河》,寫得從容不迫,又玲瓏精致。開始寫“我們慢慢地走著”“誰也不說話”,愛情不能靠激素速成,也不能靠誓言約束,往往是欲速而不達,它是無言的心有靈犀,是“潤物細無聲”的精神滋養。接下來由遠到近的危崖、亂石、雜草層次感特別強,象征著人生不同時期的艱難處境,也是“慢慢地走著”的客觀原因。人生有時確實無法繞過被踐踏和埋沒的蒼涼命運,對塵世的一個弱女子更是如此,詩人的理解、隱忍、寬容和承受讓人感慨不已。“而從不被所愛的人忽略”,一下感到柳暗花明,環境的艱難更反襯出愛情的溫暖和力量。雖然沒有具體展開寫,但讓人回味不絕,像閃電一樣照亮了全詩。“從不被”語氣堅定,有生死相依的感覺。結尾這幾句,確有米沃什的味道和風范。
愛情不是逢場作戲,而是人生一樁嚴肅的事情。郭卿為自己也為讀者留下了剛中有柔的《證據》。她對環境柔弱的反抗和對愛情真摯的憧憬交織于一起,凝結成人生輝煌的太陽,照亮自己云霧繚繞的天空:我在這荊棘叢生的人間等你/做一只刺猬,保護著自己/有時我想向你靠近,可我又擔心/這滿身的刺,這滿身的刺/會讓我流淚/黑夜里,荊棘開始瘋狂/我與荊棘對抗,甚至想丟盔棄甲/做一只溫順的小狐貍/我不想讓你看到血染的黎明/用滿身的刺去迎接新的自己/如果哪一天你忽然會想起我/哦,這滿身的刺,這滿身的刺/會令我哭泣/我總是羞于承認,我有一顆向狐貍而生的心為你盛開/而這些秘密被兩只麻雀/在古寺門的空曠處跳躍的麻雀/和寺里打坐的菩薩/心知肚明/如果哪一天/我為了你而放下一切/讓這荊棘叢生的人間普照慈悲的色彩/群山撼動,萬物本真/我的這首詩會成為詆毀的證據。
浪漫的愛情往往使人沉溺于不切實際的幻想,削減了現實的嚴酷和沉重。郭卿卻把理性的美和情感之旖旎結合起來使愛情散發出奇異的光芒。詩人“等你”,不是在花前月下、桃紅柳綠旁,而是在“荊棘叢生的人間”,情感氛圍一下莊重起來。魯迅在《傷逝》中借涓生的口說出:“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如果長時間沉醉在溫柔鄉里,這樣的愛注定沒有遠方。從這個意義上看,郭卿是一個清醒的現實主義者,這個現實不是急功近利的物質至上,而是對生存環境的理智逼視。為了不受傷害,卡夫卡變成一只甲蟲以逃避現實。郭卿卻變成一只刺猬,去對付瘋狂的荊棘,這在女詩人中并不多見,也是郭卿最具鋒芒的比喻。可“向你靠近”的時候,又擔心傷害了愛情,內心充滿矛盾。為此而“流淚”“不想讓你看到血染的黎明”,甚至想“丟盔棄甲”“做一只溫順的小狐貍”。善不是停留在口頭,而是在心尖發顫,是愛的至純結晶。閻志說:“詩人是離善良最近的一群人。”郭卿在愛情生活中體現出人類最本真的善良和東方女性的含蓄內斂之美。詩人假設“如果哪一天/我為了你而放下一切”。為了愛情放棄了與環境的對抗,雖然群山都會被撼動,但“我的這首詩會成為詆毀的證據”。是否放下?放下后誰在詆毀,詆毀什么?詩人點到為止,其深刻的人生哲學留給讀者去思考。詩人如果再詳加描述,這首詩可能就會事倍功半。現在沒有完全說出來,只露出冰山一角,卻事半功倍。如果老怕別人讀不懂、弄不明白,就會擠兌和破壞詩歌潛在的審美空間。懂得節制,才是詩的藝術和藝術的詩。
從上面三首詩,可以清晰地看到女詩人對愛情的格外珍惜和為愛情所做的英雄般的努力,愛情有了不同于青春歲月的質量和重量,逐漸實現了從夢幻向現實靠近,但依然不失浪漫情懷,實現了浪漫與現實的完美結合。如果愛情一味追求現實,就會變得俗不可耐,必然走向反面。如果愛情一味追求浪漫,人生就會變成空中樓閣,肉體和靈魂無處安放。愛情離不開物質基礎,但物質不等于愛情。愛情是靈魂的花朵,溫婉美麗,又光芒四射;晶瑩純潔,又馨香襲人。
從辯證思維來看,愛情不可能一成不變。在物質極度貧乏的時代,不可否認物質更容易轉化為精神,產生愛情也就不足為奇。在市場經濟時代,愛情變得光怪陸離,被欲望牽著鼻子走,脆弱的愛情輕易就向物質投降,存在變色、變味、變質的異化現象。作為追求精神生活的詩人,對愛情的期望成了市場經濟時代不可多得的風景。郭卿憧憬什么樣的愛情呢?《炊煙里的家》是她繪制的最美愛情藍圖:碹幾孔窯洞/添置一桌一椅一燈,幾卷書/還有一個喊我小名的男人/會腌制酸白菜,會做南瓜餅/與我晨點炊煙,夜枕松風/門前種花,房頂看星星//削根竹,做個簫/吹給他一個人聽/他寫詞,我譜曲/日子旖旎/歲月雍容。
這簡單的“幾孔窯洞”,類似于劉禹錫的陋室,充滿煙火氣息和高雅情趣。詩人鐘情的不是貴族富豪,而是“會腌制酸白菜,會做南瓜餅”的那個男人。她渴望的不是錦衣玉食,而是“他寫詞,我譜曲”的心靈和諧與歲月靜好。粗茶淡飯,讀書吹簫,種花看星星,一幅其樂融融的愛情畫卷,正是國泰民安的一個縮影。這是一塵不染的鄉村愛情,仿佛陶淵明的世外桃源,寄寓著詩人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旨趣和生存理想。
郭卿的《山中尋月》,尋的是故鄉明月,也是心中明月般的愛情和人生。“那清暉/在草蟲低鳴中錯落有致/再高的山,再矮的草/平分秋色,甚至暖陽/甚至這中秋的月色”。像王維的山水畫一樣靜謐,但巧妙地融入了詩人平等、自由的愛情理想。她的愛情已經由小我抵達大我,由私密性轉化為社會性,借此表達對弱小事物的人文關懷和共享文明成果的社會期望。
郭卿在多首愛情詩中展現了愛情的美。《俗塵》不同于李清照的“沉醉不知歸路”,而是:“把你的笑容當作杯酒飲盡/我就可以迷離、恍惚地看你/看你獨善其身,看你疏離紅塵的背影”。對詩人而言,“獨善其身”的品質是贏得愛情的重要砝碼,愛情不是物質與物質的碰撞,而是在一個精神頻道上的同心共振。其在《草木斷想》中寫道:“像你這樣的花/大片大片地開就成了詩經/一朵一朵地遺世獨立/就成了情竇初開的女人/太陽是如此的博愛/而你不忘初心/把愛孕育成千顆萬籽/再也抬不起相思的面容”。一般是用花來比喻女人,郭卿卻反其道而行之,用女人來比喻花,奇思妙想,既有相思的嫵媚,又有成熟的美麗。其在《桃花謠》中寫道:“我趕著春風去看你/趕著鳥啼去看你/趕著一路的山山水水一樹梨花一溪月去看你。”借助自然風物為愛情站場,節奏越來越快,情感越來越濃,愛情像春風一樣暖人、鳥啼一樣悅耳、山水一樣起伏、梨花一樣純潔、月一樣明亮。她心中的愛情有色、有形、有聲、可感可觸,趨于完美,但最后歸結到純潔上,這是她對人類愛情最美好的憧憬和展望。
郭卿受儒家思想影響較深,永遠都是溫柔、敦厚的樣子。她喜歡以平和的心態面對紛繁的世界,具有《詩經》中“淑女”的傳統美德和東方女性的知書達禮,生活中雖有太多的風寒和霜雪,多數時候表現出息事寧人和忍辱負重。她不同于那些強悍的女權主義者,向愛情要獨立,和生活要自由,而是恪守傳統的道德和美學,不管處境怎樣艱難,每天依然迎著朝陽出發,匆匆走向美好的明天。她的詩屬于典型的女性寫作,正如著名詩人李琦所言:“女性詩歌會有那種微妙的、纖細的、無法準確描述出的奇妙、憂郁和冷暖。女詩人作品里自然呈現出的那種愛與美,恒久的包容或者獨到的尖銳,芭蕾舞者般的輕盈或者陶罐那樣的厚重,讓女性詩歌質地獨特,在詩歌領域中會經久散發著不可替代的、月光般的銀輝。”可以說,除了尖銳,其他都具備。詩歌是她的避難所,也是她的精神家園。不論在生活中還是在詩中,她都想做最好的自己,以期達到至善至美的人生境界。她寫的不是雕欄玉砌,而是小橋流水;不是雷鳴電閃,而是蒙蒙細雨。留給讀者的印象不是姹紫嫣紅,而是冰清玉潔;不是胭脂口紅,而是蘭質蕙心。在現實生活中她處處與人為善,在自身舉步維艱的困境下,對弱者仍然心懷悲憫,經常伸出友愛之手,施以人道主義的幫助。每個漢字在她筆下都變成謙謙君子,在傳承著一個民族的道德、文明和文化。她的詩具有真正意義上的純粹性,靈魂一塵不染,情感發自內心,思想明朗健康,語言返璞歸真。在藝術上,她以自然為美,面對茫茫宇宙,總像一個人在自言自語,有時又好像有心儀者站在面前。她迷戀人間煙火,又保持適度的疏離,貼近澎湃的內心,又懂得有效地節制,不拘泥,又空靈,總是恰到好處、游刃有余。在寫作時,她只聽從內心的召喚,沒有興趣咬文嚼字,但常常出其不意地打破語言上的慣性和陳舊的修辭,營造出堅實而新穎的意象和別具一格的詩情畫意,避免了空洞的說教和同質化的抒情。愛使她的生命變得愈來愈明媚、純凈和美麗,當然,我們也不能回避她明媚中的暗影、純凈中的孤獨、美麗中的柔弱。詩歌在弘揚真善美和核心價值觀的同時,也應提升鞭笞假丑惡的信心和斗志,除了陽光和鮮花外,也需要魯迅那樣的“匕首和投槍”,溫婉中確需增加一點犀利,為有尊嚴的愛和生活掃清前進道路上的一切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