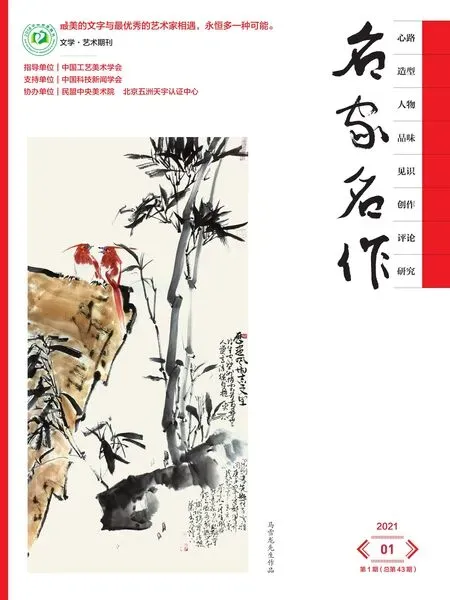奧尼爾《毛猿》的喜劇與人的悲劇
2021-11-13 00:52:33劉辰
名家名作
2021年1期
劉 辰
文藝復興以來,人們總是從積極意義上去描繪、展現和歌頌人性之美,更多意義上的人性之美被賦予了勤勞、善良,有著堅定的信念和無窮的創造力。然而,隨著工業革命暴風驟雨式地席卷歐洲大陸,隨即波及整個世界,一切都變得不一樣了。當時的美國在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迎來了工業革命后的第二個春天,大發戰爭橫財,壟斷資本迅速膨脹,資本家為了攫取高額的利潤,不斷增加工人勞動強度,勞資關系不斷惡化,兩大階級對立所產生的矛盾沖突成了當時的美國乃至整個資本主義“帝國”共同面臨的難題。生活在這個時代背景下的普通人,在絕望中找尋著自己的精神家園,又在現實生活中掙扎著度日。千百年來撫慰人們痛苦心靈的上帝不再存在,到處彌漫著的是知識界的理性缺失和美夢的一再破滅。
“一戰”前的四五十年間,在美國戲劇舞臺上到處都上演著奢侈華麗的情節劇、荒誕的滑稽劇和壯闊的音樂劇,而素有以通俗風格為主流的浪漫主義傳統的美國戲劇卻舉步維艱,無處不透露著當時的戲劇作家對人生和人性的某種半官方的態度。
從19 世紀80 年代開始,現代主義成為歐洲又一場藝術運動。隨著“社會的不斷系統化、社會化、城市化和拜金化,藝術家們越發疏遠主流社會”。其中一個本質特征就是“反對現代社會這些享樂主義和權力主義”。“大眾社會要求其公民遵守死板的職業道德”,現代主義者提倡從“這些對人性的侵蝕”中逃脫。……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