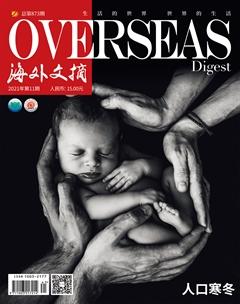空巢東歐:揮之不去的人口焦慮
讓·巴蒂斯特·查斯坦
羅馬尼亞的奧內什蒂市在共產主義時期曾是石油化工重鎮。如今,在這里的幾家被遺忘的巨型工廠中,卻只剩默默生銹的設備。待你繼續往市區里走幾個小時,和行人攀談幾句后就會發現,這座城市和羅馬尼亞腹地的其他城市一樣,患了一種病,病名為“人口大規模外流”。
奧內什蒂的許多公寓樓都是60年代蓋的,而夜幕降臨時,亮燈的卻沒有幾家,許多房子都沒人住。一名市政府工作人員說:“查一下我們樓的水表,你就會發現65戶中只有20來戶有人住。”他接著緬懷了一番城市上空濃煙滾滾的時代,是有污染不假,但也有許多工作機會。然而,那個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自1990年以來,已經有一半居民離開了。圖書館空無一人,體育場和游泳館也早已停業。人都去哪兒了?市長尼古拉·齊奧塞斯坦率地說:“他們都走了。”
2007年,羅馬尼亞加入歐盟,西歐勞動力市場的大門自此向這個國家敞開。羅馬尼亞人都盼望過上更好的生活,因此,西歐市場對他們意味著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事實上,奧內什蒂自1990年就開始衰敗,但2007年之后,城市的頹勢變得更為明顯。在長途汽車站,喇叭一遍又一遍的響聲仿佛在喊著那些理想去處的名字:德國、比利時、荷蘭、法國、丹麥……這些無一不是西歐國家。
| 和平時期,人口降幅創新高 |
人口形勢危急的奧內什蒂在羅馬尼亞絕非個例。雖然沒有人能給出準確的數據,但保守地說,至少有300萬羅馬尼亞人在國外生活。1989年,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垮臺那一年,羅馬尼亞的人口為2300萬,到了2017年,這個數字下降到了1970萬。
聯合國列舉了人口流失情況最嚴重的十個國家,其中就有羅馬尼亞。根據聯合國的估算,到本世紀中葉,羅馬尼亞人口可能會降到1600萬左右。保加利亞、克羅地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摩爾多瓦、塞爾維亞、烏克蘭等國的情況也與羅馬尼亞類似,這些中東歐國家的人口問題已經危及到了它們的立國之本。
人口統計學家托馬斯·索伯特卡指出,1990年到2017年,歐盟15個老成員國的人口增長了12%,但2004年以來,新加入的13個成員國的人口下降了7%。索伯特卡依據自己掌握的信息,估算出如今有1500萬到1800萬的中東歐公民在西歐生活。人口問題在政治上是敏感話題,沒有一個政府官員愿意看到本國公民大規模涌向國外。“在歐洲,一個國家的人口數量決定了它的政治話語權。”索伯特卡說,“在匈牙利和捷克,政府給出的人口流出數據分別比實際要低1/3和1/5。波蘭的人口統計數據甚至會將不在本國生活的波蘭人算進來。”
| 僑民資金回流 |
奧內什蒂市長給不出市民的具體人數,他一開始說:“根據最新統計,是5.1萬。”不過,羅馬尼亞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卻顯示,2011年,奧內什蒂只有39172名市民。看到統計局的報告后,他又改口說:“從城市每日產生的垃圾來看,現在的人口應該在3.5萬到3.6萬之間。”但倘若聯系一下當地收垃圾的清潔公司,我們就會發現,這數字還得往下降一降,因為登記在冊的用戶有3.6萬人,而真正交錢的只有2.7萬。
奧內什蒂周邊的情況更糟。拉多亞就是一例,鎮上只有一條坑坑洼洼的小路,路上更是看不到人,只有一家雜貨鋪開著門。“這很正常。”小店老板說,“80%的人都出去打工了。”路上偶遇的一名建筑工人說,他回來主要是看望祖母。“我在英國一天就能賺174歐,但在羅馬尼亞,一個月才能賺232歐!”他感嘆道。
雖然這些人出去打工了,但他們卻把錢帶了回來。公共基礎設施年久失修,而居民自己的住所看上去卻挺華麗,有些已經蓋好了,有些還在施工。
近些年,羅馬尼亞的最低工資大幅度上漲,盡管如此,它的平均工資卻在歐盟墊底。每年都有20萬羅馬尼亞人出國打工,相當于每小時就有23人離開祖國。羅馬尼亞人口外流問題專家杜米特魯·桑都表示:“貧窮國家的公民到周邊富有國家打工是再正常不過的了。沒有什么舉措能真正阻止這一趨勢。”
歐盟的人口可自由流動政策隨著1992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生效而落地,歐盟成員國公民自此可在歐洲任一角落工作和生活。此前,歐盟成員國的發展水平相近,但自2004年東歐國家相繼加入歐盟以來,發展水平就變得參差不齊了。2019年的統計數據顯示,20%的羅馬尼亞勞動力人口在歐盟發達地區打工,立陶宛和克羅地亞的數據則分別為15%和14%。
| 勞動力短缺 |
“波蘭水管工”這樣的話題經常在法國引起論戰,但這在歐盟并非主流。多年以來,波蘭等國的勞工都很受意大利、西班牙、德國、英國的歡迎,因為他們價格合適、靈活度高,而且為各國建筑業、農業和醫療行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當然,這也引發了政治上的爭端,英國脫歐也多少與此有關。
羅馬尼亞人口統計學家瓦西里·格陶說:“人口大規模外流,挽救了羅馬尼亞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就業市場的壓力一下子減少了許多,失業率也跟著降低了。2010年以來,在外打工的人口往國內輸入了270億歐元。他們數以百萬計的親人因此過上了好日子,還有數百萬人買了房、做起了生意。”
但這一現象也引發了極大的焦慮。他繼續說道:“如今,中東歐國家的勞動力缺口非常大,并且形勢在進一步惡化。以羅馬尼亞為例,流失的高素質人口越來越多。這樣下去,這些國家未來會吃大虧的。”醫療衛生行業就是重災區,若本地的醫生都跑到西歐就業,其后果可想而知。
| 縮水的學校 |
卡尤蒂學校離奧內什蒂不遠,走進教室,孩子們在高興地畫著歐盟旗幟。不過,這里1/3到1/2的孩子的父母都在國外打工。這些父母大多經濟條件有限,無力帶孩子一起出去,他們多數會讓爺爺奶奶或親戚幫忙照看孩子。
羅馬尼亞政府長期對留守兒童問題不聞不問,直到2015年,政府終于意識到了這一點,要求凡是出國打工的父母都要向政府申報。46歲的加布里埃拉·托薩是卡尤蒂學校的校長,她說:“我們學校只有26個孩子的父母申報了,但你隨便和學生聊幾句就會發現,真實數據要比這個多得多。”
托薩認為,父母不愿申報的原因是擔心社會服務部門會跟他們提要求。托薩的家人基本都在國外,但她卻選擇留在國內。她如今在攻讀博士學位,研究的就是父母長期不在身邊會對孩子造成何種心理影響的問題。“自卑、輟學、祖父母對孩子缺乏鼓勵、學校作用發揮不足……”她將負面影響一一列了出來。2017年到2018年,在她的學校就有40名學生輟學。
30歲的瑪麗安·達莫克在一家專為該地區學校提供硬件援助的非政府組織工作。她說:“不少班級都被砍掉了,老師們也被校長叫到辦公室商議調整工作崗位的事。”她的許多朋友都在國外,但她畢業后卻選擇留在國內,“大家都問我為什么要留下來,我也跟他們解釋不清楚。”她很憂心,因為人們對出國工作已經習以為常,長此以往,國家能否繼續存在下去都是個問題。
| 解決人口危機的最大障礙 |
奧克塔維安·里斯特亞是一家工廠的老板,他說:“20年前,來應聘的人能在工廠門口排起長龍,但如今,我們得從各個方面滿足工人的需求,這樣才能留住他們。”他給工人開出的月薪是440歐元,已超過了國家最低工資。這樣的現象在中歐也很普遍。匈牙利的奧迪工廠也給工人漲了工資,漲幅高達18%。
然而,企業家擔心,即使漲了工資,外出打工的人還是少有回來的,生產力難以提升。那能否吸引外國勞工呢?這些國家幾乎沒有這一傳統,提這樣的建議甚至會觸碰禁忌。
匈牙利總理維克托·歐爾班是極端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在2019年2月的一次講話中,他說道:“如今,歐洲的生育率越來越低。西歐的對策是吸引外來人口,但我們不能走這條路,我們關心的不是數字,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土生土長的匈牙利孩子。接受外來人口,對我們而言無異于繳械投降。”他進而提出了一攬子促進生育的政策,其中包括對育有四胎的媽媽終生免個稅。
不過,依然有國家開始考慮吸引外來人口。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三國工作的烏克蘭人和巴爾干半島人就有數十萬之多。這些外來人口并非歐盟成員國公民,但他們還是能輕松地拿到工作簽證。
有的國家將目光投向了更遠的地方。羅馬尼亞就在近期出臺了提升非歐盟國家公民工作簽證配額的政策。如今,羅馬尼亞的工廠和賓館中已經有不少尼泊爾人和越南人了。
安德烈·巴比什除了捷克總理的身份外,還有個身份:農業大亨。根據德國之聲的報道,他的做法頗具諷刺意味,雖然口頭上高調反對外來人口,但一到自家的屠宰場,他又毫不猶豫地雇用了越南工人。在索伯特卡看來,捷克確實也別無選擇。
索伯特卡說:“90年代,西班牙和愛爾蘭成為了移民國家。再過一二十年,東歐國家也會走上這條路。”他認為真正值得關注的大問題在于是否會有大批俄羅斯人涌入這些國家。俄羅斯人與非洲人或中東人相比,在文化上更容易融入這些國家,并且俄羅斯有1.4億人口,可提供充足的勞動力。但蘇聯曾控制過東歐,這些國家對此還有陰影,它們能否接受俄羅斯人還是未知數。
東歐的人口焦慮愈演愈烈,過去想都不敢想的想法,近年來都相繼浮出水面。2018年底,羅馬尼亞財政部長提議,將歐盟居民出國生活的上限設為五年,用他的話講:“這或許限制了大家,但這都是為了社會和諧。我們不能一味地發展西歐,犧牲東歐。”2019年6月,克羅地亞總統科琳達·格拉巴爾–基塔羅維奇明確表示:“歐盟的人口自由流動政策是解決人口危機的最大障礙,人口能流動固然是好的,但前提是他們得能回來。目前來看,克羅地亞的人口形勢不容樂觀。”面對鋪天蓋地的斥責聲,二人很快就收回了他們的話,但他們的發言也確實反映了這些國家當政者的難處。
| 人口危機與民主危機 |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拉脫維亞裔歷史學家烏娜·伯格曼認為,想要找到解決方案絕非易事。近年來,她的家鄉拉脫維亞和它的波羅的海鄰國一樣,也面臨大規模人口外流。
“不論哪種人口政策都無法填補人口外流所造成的缺口。拉脫維亞政府想依靠政策吸引在國外的30萬拉脫維亞人回國,這太理想化了。而吸引外國人來拉脫維亞務工又是一個敏感話題,提都不能提,因為自蘇聯時期以來,拉脫維亞就一直有身份認同危機。”伯格曼說。
東歐的政府官員內心也很糾結。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他們都將人口外流看作好事。一方面,它可以降低失業率;另一方面,出去的往往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這些人喜歡批評當政者,他們走了正好。而留在國內的多是受教育程度偏低和生產力較低的人,他們對社會援助的依賴更強。以羅馬尼亞為代表的國家就常常利用社會援助左右選舉。
這些國家近年來身份僵化、貪腐嚴重,對法治的攻擊也越來越多,這些現象就像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迫使更多的高學歷人才走出國門。這一情況足以說明人口危機和民主危機緊密相連。愛沙尼亞近來興起了一個民族主義黨派,他們拿人口外流做文章,攻擊執政黨,稱執政黨鼓勵人口外出打工和外國人口流入。2019年3月3日,議會選舉,該黨派獲得的票數非常多,令人震驚。
2018年11月,《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文章,稱在前東德地區,女性比男性更愿意出去闖蕩,導致該地區男女比例失衡,加之2015年以來,大批難民涌入前東德地區,生活在那里的白人男性更覺得自己的飯碗被搶了,于是許多白人男性為此將選票投給了極右翼民粹政黨AfD(意為“德國的選擇”)。
倫敦、布魯塞爾、柏林等地的東歐僑民也在近年來成立了許多公民組織,遠程對抗祖國的保守勢力。捷克裔的索伯特卡就發現,捷克僑民更愿意將選票投給自由黨派候選人。不過,境外投票手續麻煩,正因如此,僑民在選舉中的存在感很低,沒有人對接觸了西歐社會的他們及其政治立場的變化進行過詳細研究。可以說,僑民總生活在邊緣地帶,不被認可。他們的祖國和他們生活的國家都不拿他們當回事,在選舉中也很少有人替他們發聲。
僑民的種種做法或許并不只是為了自由本身,而是在對祖國的當政者表達不滿,他們認為國家之所以留不住人,正是當政者執政不力造成的。在匈牙利,有一個叫“動量運動黨”的新黨派,由許多國外回來的高學歷年輕人共同創辦,目標就是讓歐爾班下臺。不過,在2018年4月的議會選舉中,該黨僅獲得3%的選票。由此可見,該黨成員雖然在西歐的大都會闖蕩過,體驗過各地的多樣性,但他們依舊無法改變國內的政治形勢。
[編譯自法國《世界報》]
編輯:侯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