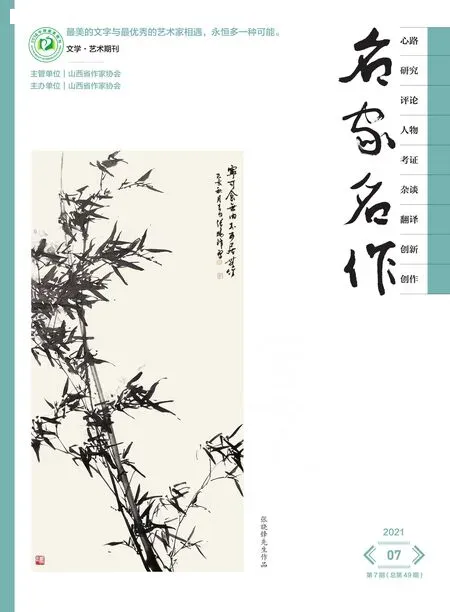論松尾芭蕉俳句中的“寂”
張曉恒
一 、引言
“寂”這個日本特有的美學術語是在中世時代流行起來的。它經由鐮倉時代貴族文學的沒落和室町時代禪宗的世俗化,最后定型為“空寂”和“閑寂”的狀態。其中,“空寂”更多地被認為是與平安時代流行開來的“物哀”一脈相承,以“幽玄”為基調,更有個人情緒意味的表達,而“閑寂”則多與風雅聯系,更突出一種以自然為主體的審美體驗。“寂”這個概念的成熟,離不開“俳圣”松尾芭蕉的俳句創作和理論研究。
二、松尾芭蕉俳句中的“風雅之寂”
(一)對“寂之聲”“寂之色”的表達
松尾芭蕉俳句中的“寂”可以分為三個層面:一是“寂之聲”,來自漢字“寂”的本意,是追求“有聲比無聲更加安靜”,類似于“以動寫靜”;二是“寂之色”,是視覺上的,在《去來抄》中記載松尾芭蕉在他的俳論中用過“寂色”一詞,與現在所說的“陳舊的色彩”相類似;三是“寂之心”,和“寂之聲”“寂之色”相比有些抽象,是更深一層的概念,也是最核心的概念。正因為有這種“寂之心”,才能夠體悟到“寂聲”“寂色”。所以,在“寂心”之外,又有“寂聲”“寂色”的表達。
首先是風雨聲。作于天和元年(1681)的“大風吹芭蕉,夜聽漏雨滴木盆”,用短短12個字把屋外的風聲和屋內的漏雨聲融合在一起,內心之寂寥呼之欲出。“蜘蛛隱隱作何聲?秋風陣陣過。”[延寶八年(1680)]把蟲鳴和秋風呼嘯放在一起,突出了秋天的凄涼蕭瑟。“寒風入竹松,靜默不作聲。”[貞享二年(1685)]寫寒風吹入竹林,明明有風聲,但卻“靜默不作聲”,恰恰是以有聲來寫無聲之“寂”。“梅雨連綿,撐裂木桶,夜里一聲響。”[貞享四年(1687)]用寂靜夜晚中木桶突然撐裂的脆響來突出夜晚的安靜。“春雨沙沙,屋頂上的漏雨,順著蜂窩滴答答。”[元祿七年(1694)]也是用這種細密微小的雨聲來襯托環境的安靜。
然后是蟲鳴。“來聽聽蓑蟲鳴吧,寂靜草庵中。”[貞享四年(1687)]“撞鐘聲,仿佛回響耳邊,蟬鳴不絕。”[貞享五年·元祿元年(1688)]“一片寂靜,巖石里,滲進蟬叫聲。”[元祿二年(1689)]“黑夜里,歸巢迷路,千鳥聲聲悲。”[元祿四年(1691)]這些鳥蟲之聲并不是中國傳統詩歌中“自在嬌鶯恰恰啼”那種歡快,而是一種悲涼、空明的聲音。蟬因為生命短暫,所以“蟬鳴”的意象又多了一分對生命無常的感傷。但偶爾也有新意,像著名的“古池旁,青蛙一躍遁水音”[貞享三年(1685)]。正岡子規將這首俳句稱為“平淡”,但對于《古池》的評價,大多評論家還是認為它著重于描寫松尾芭蕉聆聽青蛙入水的聲音,不著閑靜二字而寫閑靜,實在高超。
還有人工的聲音也不容忽視。“寂靜夜,月侘齋人獨自吟,奈良茶歌。”[延寶九年·天和元年(1681)]“年終歲尾,搗制年糕回聲響,伴我伶仃睡。”[延寶九年·天和元年(1681)]“汲水儀式上,面無表情眾僧侶,蛩音不絕響。”[貞享二年(1685)]“花云繾綣,鐘聲響自上野,還是淺草?”[貞享四年(1687)]這些都是非自然的聲音,但因為松尾芭蕉的處理,這些人工之聲并沒有使俳句失去“寂之聲”,相反,因為“月侘齋人”“年終歲尾”“伶仃睡”這樣的詞語,讓整個環境更加幽寂起來。
與較為容易理解和捕捉的“寂之聲”相比,“寂之色”就與俳句中的景物意象更加融為一體。寂色是與明艷的大紫大紅相對的,以黑、白、灰為主的顏色,如果用季節來比喻,那就應當是秋冬之色。“烏鴉停枯枝,秋日入黃昏”[延寶八年(1680)]就體現了這種對于視覺上的蕭瑟秋色的推崇。“中秋明月,圍著池塘轉,通宵達旦。”[貞享三年(1685)]“初秋,滄海綠田,一片青。”更突出了這種秋天的“寂色”。但值得注意的是,松尾芭蕉的“寂色”并不是一味地寫秋冬之衰敗,并不只是一味地哀傷,也有明快的調和,例如:“走累了,正要投宿時,預見紫藤花。”[貞享五年·元祿元年(1688)]這更加說明芭蕉的“寂之色”不是來源于外在的衰敗秋景,而是來自內在的“寂之心”。
(二)對生命無常的感慨
在松尾芭蕉的俳句中,對于生命無常的感嘆也是特別值得單獨討論的。在延寶四年(1676)的時候,松尾芭蕉就寫下了“生命,僅僅是斗笠下的,一塊陰涼”的俳句,在表達對生命短暫的感慨之余,也有幾分“滑稽”的趣味。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松尾芭蕉對于生命的思考逐漸沉重了起來。“曝尸荒野,心已決,秋風入骨寒。”[天和四年·貞享元年(1684)]他的俳句中開始出現“曝尸”這樣極端的死亡意象。“墓冢也動容,我的哭聲,化秋風。”[元祿二年(1689)]這首《墓冢也動容》用12個字表現出無比強烈的悲痛。大西克禮的《幽玄·物哀·寂》認為它是非常直接的主觀表達。雖然在真實性上有夸張之嫌,但“在外在的文字上加以極端化的直接表現,而將間接的、客觀的余裕之心包含于其中”。在之后的俳句中,有“生命何其短,四季變化不得知,蟬鳴聲不絕”和“拔掉白發,藏枕下,蟈蟈吱吱叫”,結合這些生命短暫的昆蟲的鳴叫,來表達對生命短暫的感慨。
(三)松尾芭蕉俳句中對中國儒學、禪宗的吸收
俳句本身就經歷了一個由中國古詩逐漸“日本化”的過程。在平安時代的末期,隨著中華文化特別是佛教文化和禪宗隱逸思想的傳入,當時的漢詩文創作掀起了一個高潮。但因為貴族政治的瓦解和武士階級的掌權,從鐮倉幕府時代開始,佛學的影響稍稍勢弱,而儒學和禪宗在日本文學和生活中的影響逐步增強。于是在這一歷史時期產生了“佛儒合一”“禪凈一如”“佛儒不二”等觀念。
中國禪宗帶去的“隱逸”“山居”等觀念順勢轉移到了日本的文學中,影響了后世的創作,特別是俳偕的創作。在松尾芭蕉的俳句中,這種源自中國儒學和禪宗的思想很多。
(四)松尾芭蕉的漂泊創作對其俳句和俳句理論的影響
在松尾芭蕉成為“芭蕉”之前,松尾宗房已經在34歲左右達到了一定的俳句創作高度。也正是在此時,他改俳號為“桃青”,開始收徒。但當時的談林俳偕雖然具有嶄新的滑稽之風,但新意并不能長久。面對這種困境,他在38歲的時候“斷然從俳偕宗匠的榮譽中抽身出來,在江戶深川的隅田川對面結庵而居”。后來因為其弟子贈他一株芭蕉于門前,遂把草庵命名為“芭蕉庵”,也將自己的俳號改為了“芭蕉”。松尾芭蕉的創作風格也發生了變化,逐漸脫離了瑣碎,在形式上使“發句”從俳偕中獨立出來。
離開俗世在草庵中隱居那個時代的流行。這就不得不提到日本的“隱遁”思想。隱遁是“建立在佛教基礎上的隱棲,在日本的隱逸中占據著最重要的位置”。換句話說,就是在戰亂的鐮倉幕府時代,想要逃離社會的危難,但又要讓信仰與美并行不悖的情況下的遁世。這種遁世與中國傳統語境中的“歸隱”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從來源上看,日本的“隱遁”不能回避中華傳統文化給予它的胚芽,但是生長于日本這個先天缺乏反對權力體制的文化環境之中,“隱遁”就更是一種個人的修行。修行場所就是“草庵”,修行途徑就是“漂泊”“孤獨”“寂寥”,從而達到一種內心自由的狀態,最后生發出了“閑寂”這個高度抽象的審美理念。于是松尾芭蕉的“芭蕉庵”就是他的修行,在修行中他得以不斷體悟俳句的精妙之處。
三、結語
綜上所述,松尾芭蕉的俳句以“寂之心”作為基調,用“寂之聲”“寂之色”來表現其俳句理論——“風雅之寂”。松尾芭蕉在俳句中表現出來的寂是“閑寂”與“空寂”的結合。他對于“寂”這個概念的理解和對俳句本身的感悟并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建立在對于前代俳偕特別是談林派的基礎之上。而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之下,隱逸之風盛行,松尾芭蕉的三次長途旅行也為他的俳句理論的形成提供了養分。除此之外,松尾芭蕉對于中國的佛學、儒學和禪宗的借鑒也是他的俳句呈現出不同于以往的特色的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