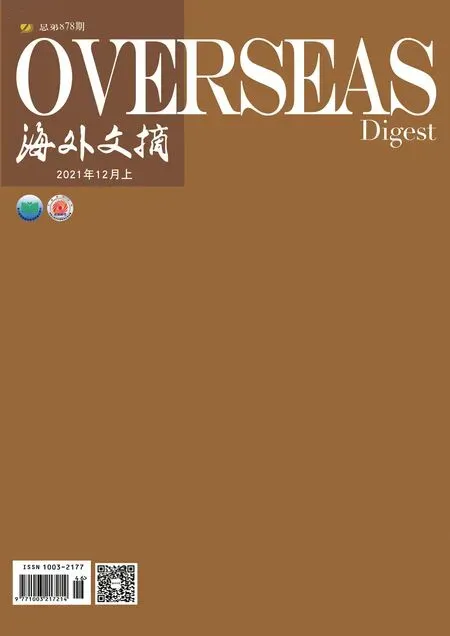論交通肇事罪中“逃逸”的應為含義
夏銘
(華東政法大學,上海 200042)
在我國刑法法條與司法解釋中,共規定了具有三種不同意義的逃逸行為,其性質、含義錯綜復雜,不僅在理論上引發了重大爭議,在司法實踐中也是莫衷一是,甚至發生同案異判的情況,嚴重損害了司法公信力。面對此種困境,分析有關法律規定與司法解釋,辨析交通肇事罪中逃逸的含義、明確定罪量刑時逃逸行為的性質與影響,對于改善現狀,確保司法的公平公正,促進法院正確適用法律,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
1 解釋“逃逸”的體系限制
交通肇事后逃逸由兩個行為構成。第一個行為是肇事行為,構成交通肇事罪;第二個是在構成交通肇事罪后,進一步實施的逃逸行為。只是由于法條的特別規定,才在特殊情況下將肇事與逃逸行為結合成一個加重的交通肇事罪。將肇事和逃逸看作當然的一個行為的觀點,“根本上是對交通肇事后逃逸場合所涉及的行為個數作了錯誤的判斷,沒有看到逃逸行為具有獨立于交通肇事行為的性質。”同樣,也可將司法解釋所規定的逃逸入罪分解為過失致人重傷行為和逃逸行為的結合。
那么,法律及司法解釋中規定的三處逃逸行為的含義是什么?它們的含義是相同的嗎?很多學者通過有力的論辯主張幾處逃逸的含義各不相同:“對交通肇事后逃逸的三種情況而言,立法目的各不相同。”“……一是單純交通肇事后逃逸,這是基于行為人逃避法律責任而加重處罰;二是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這是基于行為人對被害人不及時救助而加重……”也有學者更進一步,提出作為義務的位階性:不僅各個逃逸之間的含義不同,甚至同一規定中的逃逸含義,也要根據具體情況的不同有所變化。例如,根據此種主張,肇事產生受害人死亡風險時的“肇事后逃逸”,和沒有產生死亡風險時的“肇事后逃逸”的含義是不同的,構成逃逸所需的行為方式也不同。
此類對逃逸含義進行多樣化解釋的觀點,雖然在不同程度上兼顧了逃逸行為可能涉及的各種作為義務,符合防止被害人損害擴大的規范保護目的,但卻忽視了一個最基本的要求:對法條的實質解釋必須限制在形式解釋的范圍之內。具體到交通肇事罪,就是對“逃逸”進行目的解釋時,不能逾越“逃逸”通常含義的界限。遺憾的是,許多理論觀點一味關注立法目的的辨析,而無視了過度強調救助義務的“逃逸”早已突破了形式理性的界限,無怪乎被人批評“規范目的解釋論者以實質解釋名義,拋開文義解釋而徑直采用了規范目的解釋方法。他們往往不是討論逃逸本身的問題,而是在猜測和推知立法者或者法律想達到什么目的。”想要對“逃逸”的含義作出正確解釋,就不能直接訴諸于立法目的,而應該先從對相關規定的形式入手。
首先,在解釋逃逸含義時,不宜對數個逃逸作不同解釋。確實有對刑法中同一詞匯做不同解釋的情況,但那是以同一詞匯處于不同法條、不同語境下為前提的。交通肇事罪的特殊之處在于,《刑法》第133 條直接連續規定了“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的刑罰加重,“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再次加重,中間以分號間隔。法條規定明顯呈現出一種肇事-肇事逃逸-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遞進式思維。“第2 檔規定的‘逃逸’,是沒有致人死亡的逃逸,它專指‘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的說法雖然在邏輯上更加合理,但恐怕不能為社會常識所認同。兩條互有遞進關系的規定中,作為遞進關系中介而存在的兩個“逃逸”意思卻大相徑庭,這種解釋路徑未免過度關注實質,而忽略了詞語可能含義的形式界限。這里的形式界限,并非通常意義上的對詞語內容的形式限制,而是根據前后文與法條結構,對詞語關系的形式限制。刑法第133 條的法條結構,蘊含著“兩個‘逃逸’的解釋須協調一致”的隱性形式界限和要求。
2“逃逸”規定的應有之義
就“逃逸”詞語含義本身而言,本文認為,基于三方面理由,“逃逸”應當解釋為“逃離現場以逃避法律追究”。
司法解釋明確指出,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是指“在發生交通事故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解釋中清晰闡明了肇事逃逸所包含的兩個關鍵要素:逃逸的動機應當是“逃避法律追究”,逃逸的表現形式應當是“逃跑”。如果說“逃逸”尚有一絲爭辯的空間,那么司法解釋中明確化了的“逃跑”則沒有任何歧義的余地,只能是指物理性地離開事故現場的行為。
這里引用的是最高法于2000 年的交通肇事司法解釋,由于存在許多與刑法理論沖突之處,遭受諸多批評,甚至有學者直接拒絕承認司法解釋中某些規定的有效性。雖然這些批評正確指出了司法解釋無權立法,相關規定沒有理論基礎、不應在實踐中適用等問題,但就其性質而言依然是“立法論”層面上的批評,而沒有司法層面上的意義。這是因為學理解釋在司法實踐中的影響力相對有限。與德國司法人員高度重視學習法學家的意見,法學家能對法律作出權威解釋的“精英話語體系”不同,中國學者的意見,在基層司法活動中完全無法抗衡國家機關的權威指導。自顧自地否定最高司法機關的指導文件,把希望寄托于基層法院在實踐中主動推翻的司法解釋而聽從學理意見,是不現實的。應當在尊重司法解釋的基礎之上進行法律解釋,唯此才能真正起到指引司法實踐的作用。基于上述理由,本文認為司法解釋對“逃逸”作出的定義雖名義上不具法律效力,現實中卻具有接近刑法條文的權威性,實際解釋條文時應當將其視為教義性的解釋基礎。
另外,認定“逃逸”為“逃避法律追究”,并不排斥救助義務的存在。解釋“逃逸致人死亡”的規定時依然可以兼顧肇事人救助傷者的義務,盡量實現督促肇事者履行義務、防止危害擴大的立法目的。
3 “逃逸致人死亡”中的“逃逸”
“‘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如前文所述,交通肇事后逃逸由肇事行為和逃逸行為兩個行為構成,而司法解釋進一步闡明了兩個行為之間的關系。首先,肇事者應為“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其次,“被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應當是肇事者的逃逸行為導致的。問題在于,逃避法律追究的行為不可能引起任何人身風險,怎么可能導致被害人死亡?按照這種思路思考下去,自然得出的結論是:既然逃避法律追究無法導致死亡,那么逃逸的含義就不該是逃避追究,而應當是不履行救助義務。但這種思路在不知不覺間已經忽視了形式理性的藩籬,為了追求實質合理性而“深深陷入了法律實質主義的泥坑”,不足以為信。
實際上,“為逃避追究而逃跑”的定義和“致人死亡”的規定之間不是非矛盾不可的。如果逆過來看,可能的解釋路徑會更清晰地顯示出來:“逃逸致人死亡”逆過來,就是“如果行為人沒有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被害人就會得到救助而不會死亡。”可見逃逸致死的因果聯系不應是“逃逸”導致死亡,而應當是“逃逸”導致“不救助”,“不救助”繼而導致死亡。由于逃逸致人死亡的肇事人對死亡結果罪過形態必須是過失,可以進一步將其細分為“過于自信的逃逸致死”和“疏忽大意的逃逸致死”。
就肇事人因疏忽大意而沒有注意到被害人面臨死亡風險的情況而言,逃逸致人死亡的問題可以轉化成“為逃避追究而未能認識到其救助義務,沒有發現被害人面臨死亡風險”的問題——因為刑法當然地期待并預測認識到救助義務的肇事人會履行其作為義務,所以肇事人未認識到救助義務可以視為致本應獲救的被害人死亡的根源。疏忽大意的肇事人構成逃逸致人死亡的方式也就可以概述為“因為逃跑而沒能意識到救助義務”。在肇事人不逃跑就能意識到自己的救助義務的情況下,肇事人逃跑了,因而未能意識到自己的救助義務,被害人因缺乏救助而死亡,此時肇事人構成逃逸致人死亡。逃逸者構成這種逃逸致人死亡的可能性是比較大的:比如,肇事者在冬天夜間醉酒駕駛,將行人撞成重傷,以為人已撞死,遂未停車查看而立即逃離現場。如果肇事人未逃逸,社會一般人的做法應當是及時停車察看并報警,被害人死亡的結局本可避免。而肇事人為了逃逸而放棄了與逃逸沖突的“本可救回被害人”的選擇,因此構成“逃逸致人死亡”。被害人死亡的結果是肇事人逃避法律追究的逃跑行為導致的。
對于過于自信的肇事人而言,達成逃逸致死的條件十分苛刻。因為肇事人此時對于被害人的死亡風險已有認識,只是自信被害人不會死亡。此時肇事人的逃逸行為和報警救援在客觀上并不矛盾,可以同時存在,所以被害人得不到救助死亡的結果很難與逃逸行為建立聯系,而只能定性為單獨的過失致人死亡。雖然理論上肇事人依然可以因“害怕被追究,所以沒有報警”而構成逃逸致死,但是這種心理狀態是絕難證明的。可以說在種種前提限制下,過于自信下的逃逸致死是幾乎被“虛置”的。當然,也有逃逸行為與救助行為直接沖突,肇事人過于自信被害人不會死亡而逃逸的情形,但這種形式的交通事故太過罕見,條件之苛刻只能在理論中實現,所以并沒有多少討論價值。
4 入罪型逃逸中的“逃逸”
入罪型逃逸,即根據司法解釋規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傷且負事故主要責任,肇事人逃逸的,構成交通肇事的基本罪。入罪規定本身并無太大爭議,然而主要的問題在于:如果肇事人的逃逸造成了被害人死亡,能不能構成逃逸致人死亡?本文認為,入罪型逃逸致人死亡不能構成逃逸致死的加重情節,有以下兩方面的原因:
第一,法律和司法解釋的規定排斥了入罪型逃逸中加重情節的成立。《司法解釋》第三條規定構成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的情景限于“具有本解釋第二條第一款規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項規定的情形之一”,而“為逃避法律追究逃離事故現場的”被規定在了第二條第六款,入罪型逃逸被司法解釋的規定明確排除在外。同時,如上文所述,刑法第133 條對交通肇事罪的規定具有遞進性:“構成交通肇事-交通肇事后逃逸-因逃逸致人死亡”,第一檔肇事罪與逃逸行為結合構成第二檔肇事罪,第二檔與導致的死亡結果結合構成第三檔肇事罪。三檔肇事罪層層累進,構成后一檔肇事罪必須以前一檔的成立為基礎。司法解釋排除了入罪逃逸后第二檔交通肇事成立的可能,自然也就使得第三檔的“逃逸致人死亡”不可能成立。
第二,入罪型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可以用過失致人死亡來評價。特殊的過失致人死亡根據法條的特殊規定與交通肇事罪結合為逃逸致人死亡,而一般的過失致人死亡就不需要納入到交通肇事罪中考慮,可以單獨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并與交通肇事罪基本罪數罪并罰,量刑幅度在3 年以上有期徒刑和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間。考慮到肇事行為本身較輕,遠未達到交通肇事的入罪標準,數罪并罰后的量刑幅度較輕是可以理解的。同樣的思路也可以用來回答對“肇事致人輕傷”情況的憂慮:這種觀點認為,如果逃逸致死以構成前層次的交通肇事罪為基礎,會使得“肇事致人輕傷后,被害人被后車撞死”時,只能以交通肇事的基礎刑處罰肇事人。這種擔憂是沒必要的,因為肇事人引起事故致人輕傷的行為,本身就可以作為先行行為,給予肇事人以救助被害人的義務。肇事人逃跑導致被害人被后車碾壓而死,被害人的死亡不是交通肇事導致的,而是交通肇事產生風險后,肇事人的不作為導致的。將死亡結果歸因于肇事人的不作為,理應直接構成故意殺人罪或過失致人死亡罪,而不會構成任何形態的交通肇事罪。解釋者需要謹記,交通肇事罪只是在特殊情況下適用的,維護公共安全的諸多法條之一。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個包羅萬象、解釋一切的罪名。遇到交通肇事規定可能語義之外的行為,就應該放棄交通肇事罪、而用其他適宜的罪名涵蓋。失去這個觀念,就會不自知地陷入“交通肇事萬能”的圈套,無限地擴大化、實質化法條的含義,試圖將一切涉及交通事故的行為都納入到交通肇事罪的范圍之內。萬能論不僅損害罪刑法定原則,更會引起司法實踐中的困惑與混亂,遺害于司法法治、公正司法,損害法律的莊嚴與正義,必須為法律解釋者所警惕。
注釋
(1)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
(2)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