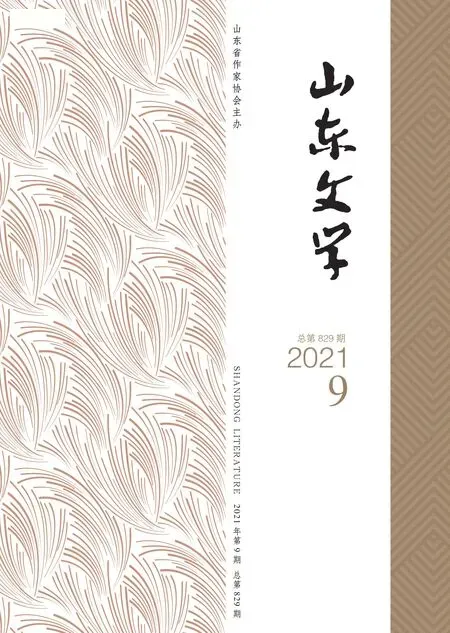那時情誼
深 海
1
因為出生在一月的緣故,在嚴格規定年滿七周歲才能入學的上世紀七十年代,我直到一九七五年秋七歲半才上小學一年級。
那時真是艱苦。小學一年級只有兩個班,可兩個班都沒有教室,桌子板凳更是沒有。我們只能自帶小板凳在學校的小操場上課,因為操場邊有個小樹林,黑板可以掛在樹上。而我們呢,每個同學都買了一塊書包大小的小黑板,老師在大黑板上寫字,我們把小黑板放在自己的腿上練習——小黑板就是我們的桌子,我們的腿,就是桌子腿。天公不作美的時候,我們就只能留在家里。
我被班主任姜雪老師指定為班長,還作為新生代表在開學典禮上發了言。雖然我對于在那么多人面前用蹩腳的普通話念老師寫的發言稿毫不發憷,可對于當班長這件事,內心深處還是有些反抗的——那更像是我媽的好友姜雪老師,幫著我媽戴在我頭上的緊箍。
讓我第一次對自己是一個班長感到自豪的,是張海峰。
小學一年級,我們上課都是有一天沒一天的。一年級結束,我這個班長連班上大部分同學的名字都還沒記住。幸運的是,到了二年級,我們終于坐進了教室,更幸運的是,姜雪老師因為業務突出,被調去帶五年級畢業班了!
我們的班主任換了位姓王的男老師,他帶的是語文課。據說他高中都沒有讀過,而且形容粗放,說話聲音沙啞,總是用力地吼,我們都有些怕他,更不喜歡他。有一次上語文課,他帶領我們讀課文,讀到“不能自已”這句,他讀的是“不能自己”。我也不知道哪兒來的勇氣,舉手站起來糾正他,說老師讀錯了,是“不能自已”,不是“不能自己”(如果是姜雪老師讀錯了,我是斷然不敢這樣放肆的。當然,姜雪老師也不會犯這樣的低級錯誤)。王老師堅持說他沒錯,我堅持說他錯了,正相持不下呢,班上的其他五個班干部都站起來支持我,說王老師讀錯了。王老師幾乎是齜牙咧嘴地看著我們,伸出右手指指點點著,怒吼,你們!想干什么?想造反?他把我們趕出了教室,讓我們拿著小板凳到教室外面去聽課。這時候,坐在第一排的一個面容清秀俊朗的小個子男生也拿著小板凳站了起來,問,老師,我也覺得你讀錯了,我是不是也要出去?王老師大吼一聲,出去!他又問全班同學,你們還有誰跟鐘曉敏、張海峰他們一樣?也給我滾出去。
班上鴉雀無聲。
那個眉清目秀的小個子男生就是張海峰。我以前沒怎么注意他,他個子小,上課坐第一排,排隊站第一個,不愛講話,上課幾乎從不舉手發言,可是那天,他竟然搬起小板凳跟我們一起坐到了教室外面。
我們七個人乖乖地、卻一臉不服氣地坐在教室門口,跟著教室里面的同學一起大聲地誦讀課文。過了一會兒,王老師大概意識到讓我們幾個人這樣坐在外面讀書目標太大,他走到門口說,你們幾個,拿著小板凳,到我辦公室去,安靜點,我下了課再來收拾你們。
我們幾個一點也不反抗,提著小板凳,自覺地排著隊,去了教師們集中辦公的大辦公室,在他的辦公桌旁邊安靜地坐著。也是巧,校長進來了。大辦公室本來空無一人,所有的老師都去上課了,校長大概剛剛巡視了一遍校園回來,他的辦公室在大辦公室的一個角落里。他走進來,看到我們,吃驚地問,鐘曉敏,你們幾個不上課坐在這里干什么?
我站起來,理直氣壯地把經過講給他聽。其他人也跟著嘰嘰喳喳地補充。校長抬起右手,用力地往下一劃拉,嚴肅地說,不像話!我們嚇了一跳,以為是批評我們。他連忙摸摸我的頭,說,走,跟我回教室去上課。
我們又自覺地排成一隊,跟在校長后面。穿過小操場,走到教室門口,我們停住了腳步。王老師見校長領著我們走過來,連忙從講臺下來。校長看都不看他,對我們說,都進去上課。他把王老師叫到門口,盡管壓低了聲音,我們還是聽到了,他說,你今天在學生們面前丟了兩回人!讀錯了字,丟人;讀錯了還不認錯,更丟人。回去立刻向他們道歉,否則你這個老師不要干了,你還是回去跟你爹榨油去吧(后來我才知道,王老師家是開油坊的)。
王老師雖然一百個不情愿,可他還是道歉了。
2
從那時起,張海峰就成了我最好的伙伴之一。下課了,我喜歡叫上他跟我們一起玩;放學了,我領隊,他站第一個,我喜歡走在他身邊。他幾乎比我矮一個頭,我感覺自己多了個小弟弟,見他背著書包、小黑板、小算盤很吃力的樣子,我總想幫他背,可他每次都拒絕。
他不讓我幫他,卻從不拒絕二木,甚至,主動要二木幫他拿東西。
我七歲半上學已經算晚的了,二木九歲才上學,二年級時他已經十歲了,他的大名我忘了,只記得大家都叫他的外號,二木(發音為平聲)。他在家排行老二,高,胖,木訥寡言,學習總是在全班倒數,作業不能按時交,考試永遠不及格。我這個班長,自覺有責任幫助他,自習課的時候我總是坐到他身邊想輔導他寫作業。可是,一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加減法運算,我講得口干舌燥了他還是聽不懂不會算。我急了,吼他,拿老師給我的教鞭敲桌子。二木瑟縮著,躲著我,臉上卻還在對我笑。他的眼睛很大,大而清澈,充滿膽怯卻又信任地看著我。成年之后,在時間和空間上都遠離童年的某些瞬間,我還時常會想起他的眼睛,特別是看到動物的眼睛,那樣單純的干凈的眼睛時,我都會想起二木的眼睛。
二木沒有朋友。下課了,他很少出教室,張海峰是他唯一的玩伴。有時候,張海峰被我們拉出去玩,二木就一個人孤零零地坐在座位上,一天又一天,他的小學生活似乎就要永遠這樣過下去了。
一九七六年深秋,一個周末的下午,學校搞大掃除。掃除完了,同學們先放學回家,我們幾個班干部留下來等老師來檢查,我叫張海峰也留下,張海峰則把二木也留下了。我們七八個人一邊收拾清潔工具,一邊說笑打鬧。二木面帶微笑,安靜地,慢慢騰騰地,配合著張海峰把清潔工具一件件擺放到教室最后面的角落里。等老師檢查完,在教室門口貼上了紅色的“最清潔”的紙條,我們心滿意足地鎖好門,準備回家。張海峰忽然說,班長,我們一起送二木回家吧。為什么?他自己不會回家嗎?他家在哪兒?
張海峰拉拉我的手,說,走吧,你去了就知道了。
天色不早了,有幾個住得遠又不同路的同學怕回家太晚會挨罵,先走了,我跟張海峰還有兩個女同學一起,迎著晚霞,陪二木往他家走。
二木穿一件已經洗得發白的深灰色舊棉襖,棉褲更舊,膝蓋那里不僅補著大補丁,兩條褲腿早已彎曲變形無法復原了。最可憐是,棉襖棉褲里都是空的,也就是里面沒穿秋衣秋褲,也沒穿襪子,一雙快要破洞的單布鞋,布鞋和棉褲腳之間露出臟兮兮的腳脖子,還沒入冬,那里已經開始皸裂了。
可是那天,二木的臉笑得像一朵花。
二木的家有點遠。我們從學校出發,經過公社大院的院墻,轉彎,經過公社的大門口,經過面粉廠前的大路,經過機械廠門口的大路,經過供銷社,經過人民醫院……穿過整個鎮子,我們又穿過了一個村莊,走過一片荒涼的玉米地,在玉米地的盡頭,一所孤零零的破舊的土坯房前,張海峰伸手一指說,二木,你到家了。二木看著他,慢慢地眨了眨眼睛,笑,不說話。我卻被眼前的情景驚呆了。
我從沒有見過人住在這樣破舊不堪的地方。它應該只在我們小學課文或憶苦思甜會上對舊社會的控訴里出現過。
推開木門,吱呀作響。屋里漆黑一片。從右側的更加漆黑的深處傳來一聲孱弱的問候,二子?是二子回來了嗎?二木嗯了一聲。放下書包,也不管我們,走到門外去,在一棵不知名的植物上摘了兩片葉子,用手擦擦,又走進里屋。這時候,我們已經適應了屋里的暗,里屋北邊高處有一個用舊報紙糊住的小窗,微光從那里透進來,我看到床上坐著一位白發蒼蒼的老奶奶,她雙眼直視著我們的方向,卻一點反應也沒有。
張海峰走過去,跳到床上,抓住老奶奶的手說,奶奶,我們班長,還有學習委員、文藝委員跟我一起陪二木回來的。
老奶奶拍拍張海峰的手說,是小峰啊?你看這個二子,知道奶奶看不見也不跟我說一聲。老奶奶說話時伴著呼呼的響聲,就像有個風箱在她的喉嚨里。她說著,伸出一只手在空氣里摸,問,哪個是班長?哪個是學習委員?哪個是文藝委員?
我們三個女生往前站了站,站到老奶奶的手能夠到的地方。她握握我們的胳膊,猶豫著想抬手摸我們的臉,卻只放在肩頭摸了摸,說,你們都是班干部,要多幫助我們家二子,他是難產,生得艱難,時間太長,腦子悶壞了,生他的時候他媽沒了,他從小就木,可是心眼兒好,你們不嫌棄他,愿意跟他玩,奶奶每天都會求菩薩保佑你們。
我們說話的時候,二木一直站在旁邊。奶奶叫他,二木,天黑了吧?你點燈了沒?二木說不用,我看得見。
奶奶的眼睛怎么了?旁邊的女生問。
奶奶說,長翳子,好多年了,現在完全看不見了,沒錢治,小峰他媽帶醫生來給我看過幾回,說要做手術。我老了,不想在自己身上動刀子,就這樣吧……
二木不知道什么時候從我們身邊走開又回來的,奶奶話音未落,他忽然從破棉襖的口袋里掏出一把紅棗來,遞到我們面前。
奶奶似乎感應到了他的這個動作,問,二子,你拿東西給同學吃啊?是什么?干凈不干凈?洗了沒?
二木說,是棗子。干凈。
奶奶笑起來,說,你們吃啊,這是我們自家樹上長的。
張海峰拿了一顆喂到奶奶嘴邊說,奶奶你也吃。
奶奶伸手接過棗子,說,小峰,天黑了嗎?你們快回吧,遠,回去晚了不好。又對二木說,把棗子給他們帶上!你送他們,送到鎮上你再回來。
二木不說話,轉身往外走。
我們在鎮子邊上跟二木揮手告別時,空中的晚霞已經散盡,鎮上有些人家已經亮起了燈火。
那天回到家我一句話也不想說。吃過飯,哥哥在飯桌上寫作業,我就坐在他對面,呆呆地看著他寫字,腦子里想的都還是二木家的情形。
回家的路上聽張海峰說,二木的父親是獨子,老奶奶一個人帶大的,可是,二木的媽懷他的時候他爹就死了,二木出生的時候他媽又死了。二木的哥哥比他大六歲,沒上過學……
那時候,我腦海里應該還沒有艱難、悲慘這樣的詞匯,只知道“窮”和“苦”。這兩個字,是人生還只有八歲的我,所能體會的人世間最可怕最沉重的字,它們突然活生生地擺在我面前,不是課文,也不是講述,而是具體的,非常具體,它們在日落時分,從荒涼的地上升起來,一下子就從眼睛里一直堵到了我的心里。
在燈下補衣服的媽媽,一邊干活一邊沒好氣地說,你們兩個人的腳都長了牙齒吧?雙雙襪子都破洞。
我哥抬頭看著她笑一下,低頭繼續寫作業。
我卻面無表情。
媽媽問,小敏不舒服嗎?怎么一晚上都不講話?
我問,媽,什么是長翳子?
我媽也被問住了,說,什么翳子?
我說,我們班有個同學的奶奶眼睛里長翳子,看不見了。
媽媽看著我,問,你今天去同學家了?
我點頭。她說,我也不知道。時間不早了,天冷,趕緊洗洗睡覺吧。
我躺在溫暖的被窩里,想著二木家也有這樣的被窩嗎?二木這會兒在干什么?是不是躺在他奶奶身邊了……
我忽然大聲喊,媽,媽媽。我媽嚇了一跳,扔下手里的活計跑過來,打開我小隔間的電燈問,怎么啦怎么啦?我問,媽媽,哥哥的秋衣秋褲有沒有多的?舊的也行。我媽問我干什么。我說我想送給同學穿,他沒有爸爸媽媽,奶奶眼睛看不見,他也沒有衣服穿……我說著,忽然就哭了起來。
3
第二天早上起來,吃早飯的時候,媽媽問,你那個同學個子有多高?胖不胖?
我仔細想想,二木雖然才十歲,可他的個子幾乎跟我十三歲的哥哥一樣高,而且比我哥哥胖(后來才知道,他那是虛胖,近乎腫)。
我媽媽說,那你哥哥的衣服他恐怕穿不了,這樣,我把你爸爸的舊衣服找幾件出來改改給他穿。
從那天起,課間或課外活動的時候,我們都會把二木拉出去一起玩。他其實也沒有玩,他不喜歡動,我們玩往返跑,他就給我們當柱子;我們玩老鷹抓小雞,他就當老母雞;我們玩丟沙包,他就站在中間伸開雙臂給我們當網子。
幾天后,我悄悄把媽媽改好的一套抓絨的衛生衣褲塞進他的書包,俯在他耳邊說,這些要穿在棉襖棉褲里面。我還曾經斗爭過,要不要跟王老師說說二木家的事情,發動班上的同學去二木家學雷鋒。斗爭的結果是算了,王老師不喜歡我,他肯定不會支持我的想法。
沒有特殊情況,放學的時候我和張海峰都會跟二木一起走,把他送到鎮子的邊上我們再各回各家。有一次,張海峰帶我們去了他自己家,我才知道他家住在鎮上的老房子里,是他媽媽家的祖產,灰磚黑瓦,兩扇開的大木門,進門是個兩米見方的小天井,天井對面是廚房,右邊是兩間小屋,第一間是他媽媽的臥室,第二間是海峰的房間,沒有客廳。天井的地面是用灰磚鋪的,從大門到廚房、從廚房到房間的部分磨損嚴重,少有人走的地方長滿了青苔。天井靠外墻的角落里,壘了一個小花壇,一棵枝繁葉茂的灌木驕傲地站在上面,這讓我甚是驚奇——入冬,我家鄉的絕大部分植物都會落葉飄零。張海峰說那是梔子花,夏天的時候才會開,白花,很香。還說,班長,明年夏天我每天給你帶一朵。我笑而不語,心里美滋滋的。
我在他媽媽床頭朱紅色的五屜柜上看到一張四人合影,才知道他還有個姐姐,他爸原來是我們公社醫院的醫生,犯錯誤被革命以后,他爸媽離婚了,姐姐跟他爸爸回了浙江老家,他跟著媽媽。他媽媽是公社醫院的助產護士,二木就是他媽媽接生的。照片上的張海峰還不到兩歲,坐在她媽媽懷里。她媽媽真漂亮,漂亮得讓我很期待見到她。
轉眼就放了寒假。我跟張海峰商量好,每天到二木家去跟他一起寫寒假作業,不然的話,他又會跟從前一樣,每次假期的作業都寫不完。其實,那時候作業很少,我們只用了一個星期就把作業都寫完了,包括二木的作業。當然,有些是我們幫他做的。到了臘月二十三過小年后,我媽不準我再往外跑了,說,你野夠了沒?天天往外跑不著家,你跟哥哥一起,在家搞大掃除,爸爸過兩天就回來了。
正月十五之后,新學期開學,我們的班主任竟然還是王老師。
過年的時候,我許的新年愿望就是換個班主任,只要不是王老師,誰都行,姜雪老師也行。從那時我就知道了,向莫名其妙的將來許愿沒用,不靈。
點名時,沒見到二木。張海峰告訴我,老奶奶死了,二木過幾天才能來,說是要守完頭七。
開學三天后才見到二木,他胳膊上戴著黑袖箍,黑袖箍上用石灰點了個白點,不知道什么意思,代表白花?他低垂著頭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我們叫他出去玩,怎么叫他都不理。我們就圍在他身邊,有一搭沒一搭地找他話說。二木始終沒有抬起頭。
從那天起,二木看見我再也沒笑過。他漸漸地跟我們都疏遠了,除了張海峰,他不跟任何人走。
一個月后,沒有被我的愿望趕走的王老師,忽然宣布了一個好消息,同學們,明天,我們的新課桌椅就來了——我們二年級時雖然有了教室,可是課桌就是地上打三個圓木樁子,上面釘一塊木板,板凳都是我們自己帶的。
那天中午放學我們就把小板凳帶回了家。吃過飯,我們早早就跑到學校,發現教室里的舊桌子已經被拆掉,地面上圓木挖走留下的坑還沒有填,我們就主動到學校外面的莊稼地里去挖土,有的用手捧,有的用書包裝,還有的把鞋子脫下來裝。我們熱火朝天地把坑填滿,踩實,興奮得臉發紅,像喝了甜酒。
我們剛剛填好坑,幾輛軍用卡車開到了學校。校長帶著老師們全都出來迎接。
不是只有我們年級換新課桌椅,整個小學部從一年級到五年級全都換了。新課桌不僅是嶄新的,而且每人獨立使用,還帶翻蓋,還刷了深黃色的油漆,椅子還有靠背。同學們爭先恐后地把課桌椅往自己的教室里搬,故意把蓋子打開,蓋上,打開,蓋上,弄得啪啪響。那天下午,學校熱鬧得像過年像慶祝重大勝利一樣。
所有的課桌椅全都擺放好之后,王老師叫我們各自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我們全都坐下了,二木一個人低著頭站在他的位置上,那里空蕩蕩的。
他的課桌椅呢?
王老師趕緊跑去問校長。回來說,三年級來了個轉校學生,計劃里是沒有他的,可人家把課桌椅搬走了,也不好再搬回來。
王老師沖我吼,鐘曉敏,你這個班長怎么當的?搬的時候怎么不數一下?你不識數啊?
全班同學都看著我。
我站起來,臉憋得通紅,心跳得快要爆掉了,卻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王老師說,你怎么不說話?你不是很會講的嗎?聽說你一年級就代表新生對全校師生講話,你講啊?現在怎么不講了?
我無言以對,心里其實已經開始自責了——我們高興得忘記了二木?這么開心的時刻,我們忘記了二木……我們竟然忘記了二木……
我……我,把我的課桌給二木……
什么?那你呢?你天天站著上課?
這時候張海峰站了起來,說,王老師,把我的給二木,我坐第一排,我可以自己帶板凳來。
張海峰,又是你!王老師說,你這么維護鐘曉敏,她是你親戚?還是……
這時候,班上好幾個同學都像張海峰一樣站起來說,老師,把我的桌椅給二木!
王老師看到同學們這樣互助互愛,不僅不表揚,還豎起了眉毛,瞪起了眼睛。他剛想吼,二木突然哭了起來……
二木仰著頭,張大嘴巴,發出單調的啊聲。
全班同學,包括王老師在內,全都呆住了。
二木旁若無人地啊著,抬起右手,擦擦眼淚,忽然喊了一聲,奶奶……
張海峰幾乎是驚喜地叫了一聲,二木,你終于哭了!他扭身跑到二木身邊,緊緊地抱住他。我也跑過去,學習委員、文藝委員也都跑過去,我們圍住他,卻不知道該怎么安慰他,只會用手在他背上拍拍這里,拍拍那里。有幾個情感豐富的女孩子,竟然跟著他哭起來。
4
老奶奶走了已經有一個多月了,二木才發出第一聲哭喊。
是沒有新課桌椅讓他感覺到委屈?還是看到我們要把自己的課桌椅讓給他感到了安慰呢?我至今也不清楚他為什么恰恰在那個時候哭了起來。可是,他的哭不知為何竟瓦解了王老師的憤怒。
王老師的臉色緩和了很多,說,好了好了,二木你別哭了,老師去想辦法,一定給你弄套新課桌椅。鐘曉敏,現在離放學還有一會兒,你領著大家讀讀課文,放學的鈴聲響了我要是還沒有回來,你就帶大家排隊,放學。
我點點頭,第一次對王老師的命令執行得心悅誠服。
第二天,王老師果然給二木弄來了新的課桌椅。后來才知道,那套新的課桌椅竟然是他跟每個班的老師商量后“借來的”。怎么借的呢?誰班上有不來上課的學生,就把課桌椅借來用一天半天的。這多麻煩啦?不知道王老師是怎么說服別人的。他把這個搬課桌椅的任務交給了我們幾個班干部,我們欣然應允,大聲保證,絕對辦到。
從那天起,小學部的教室走廊上,每天都會出現我們抬桌椅的身影。我們抬得很歡快。
漸漸地,隨著春天的到來,二木的臉上又開始有了笑意。
經過這件事之后,我不再像過去那樣討厭王老師了。他卻還是像過去一樣對我橫眉豎眼,可我總是對他笑,無論他怎么大聲吼,我都對他笑,對他說,是,王老師!好的,王老師!四月的時候,王老師對我的態度也和藹起來,甚至,他在班上也不像過去那樣愛發脾氣了。
可是四月末,突然張海峰連著幾天沒來上課。我們問王老師,他說張海峰請了病假。有天放學后,我跟學習委員拉著二木去張海峰家找他,大門上卻掛著鎖。鄰居說,峰娃兒病得很重,到縣醫院去住院了。
誰也不會想到,張海峰死了,毫無征兆的,他就那么死了。
張海峰缺課的第十五天(整整十五天,我每天都數著),下午,還沒到放學時間,王老師突然把我叫了出去,他叫我把書包拿上,跟他一起去辦個事兒。我當時還不知道是什么事兒。
王老師跟一個我不認識的女老師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著。他們走得很快,我要時不時地小跑幾步才能跟上。女老師一邊走一邊唉聲嘆氣地連說了好幾個可憐可惜。她說,你說這周護士到底是啥命呀?男的不爭氣,被革掉公職,遣回原籍改造,她這些年一個人帶著兒子才開始過得舒心一點,這兒子又……王老師問,我還不是很了解情況,怎么突然就這么兇狠了(王老師的原話)?女老師說,一開始是發高燒,張海峰他媽以為也就是春天感冒嘛,喉嚨發炎,就在公社醫院打了三天吊針,可是高燒不退,腮幫子也腫起來了,醫生趕緊叫轉院到縣里去治,還是晚了,說是急性腮腺炎,有了并發癥,一入院就下了病危通知……王老師說,他媽還不要瘋了?
我跟在后面,漸漸地有點魂不守舍。他們在說什么?張海峰怎么了?腮腺炎是什么?什么叫并發癥?什么叫“還是晚了”?
王老師突然對我喊,鐘曉敏,你走快點,要不就趕不上了。
趕上什么?我邊跑邊問。
王老師說,張海峰不好了,剛從縣醫院回來,你代表全班同學,去跟他告個別。
……
我雖然跟著他們緊趕慢趕,可是整個人已經蒙掉了。
5
張海峰家的大門虛掩著,女老師喊了聲周護士,也不等回應,推門而入。
沒人回應。
我們站在天井里,張海峰的媽媽從右邊第一個門里走了出來。
這里我來過一次,知道那是海峰媽媽的臥室。可是,這就是我期待見到的那個照片上的美人嗎?她臉色發青,頭發凌亂,雙目赤紅,上下眼泡浮腫得厲害,整個人輕飄飄的,似乎隨時都會倒在地上。
女老師趕緊上前一步扶住她,從口袋里掏出一個牛皮紙信封塞到她的上衣口袋說,這是我們學校的一點心意,你拿著,別推。快,讓我們進去看看孩子。
海峰媽媽虛弱地點著頭,轉身帶我們進屋。
屋子里沒有開燈,屋頂玻璃瓦透進的光正好照在床頭,海峰的臉就在那微光里,在白色的枕頭和白色的被子之間,一張蒼白消瘦的小臉,若不是他濃黑的頭發在那里,若不是定睛去看,你不會以為那里還趟著一個人。
他閉著眼睛,雙頰凹陷——不是說他腮幫子腫了嗎?
屋子里有一瞬間死寂般安靜。
女老師突然問,孩子這不是還有呼吸嗎?怎么回來了?為什么不治了?
海峰媽媽說,醫生早就說不行了,治不了……他一直撐著,就是要回家,天天還在想著,要上學……
我先是眼淚涌了出來,繼而哭出了聲。
王老師忙把我往前推了推,對海峰媽媽說,這是海峰的班長,代表同學們,來看他。
海峰媽媽說,謝謝王老師,你想得這么周到。又轉向我問,你是鐘曉敏吧?他每天都在念叨你,還有二木……二木沒來?
我走到床邊,又往前站了站,站到床頭。看著海峰那張蒼白可怕的臉,只會哭,什么也說不出來。
女老師說,小敏,你叫他,看他能不能聽到?
我還是哭,說不出話來。
海峰的眼睛卻慢慢地睜開了,睜開了一條縫。他的視線游移了一下,看到了他媽媽。海峰媽媽立刻撲過去,雙手捧著他的臉叫,我的兒啊,你已經昏睡了一整天了,你想喝水嗎?你想要什么?老師和同學來看你了……
他的視線移過來,看到了我,嘴唇動了動,沒有聲音,可我看出來,他在叫我,不是叫我的名字,而是叫班長,他似乎從沒有直呼過我的名字。
我也叫他,張海峰!
不知道是光線變化,還是淚眼婆娑造成的錯覺,我看到他的嘴角倏忽閃過一絲笑意。
他的嘴唇又動了動,這次他是在問二木。我忙說,明天,明天我就帶二木來看你。
海峰的眼睛閉上了,可是他的嘴唇又動了動。他媽媽把耳朵湊到他的唇邊問,兒啊,你在說什么?再說一遍,媽媽沒有聽清……
我忙說,阿姨,他在說書包,書包。
海峰媽媽哦了一聲,轉身跌跌撞撞地跑到隔壁小房間去,取來了海峰的書包,整整齊齊地放在海峰的頭邊,對著他的耳朵說,兒啊,書包就在這。說著,她把海峰的手從被窩里拿出來,讓他摸了摸書包。海峰長出一口氣,又變得異常安靜。
我們默默地在海峰的床邊站著,不知道過去多久,玻璃瓦上的光漸漸暗得已經看不清海峰的臉。
海峰媽媽叫我們回吧,說他這是又開始昏睡了,不知道能不能熬過今天。
我們站在天井里告別,女老師拉著海峰媽媽的手問,海峰他爸爸不回來嗎?海峰媽媽說,好多年都不聯系了,都不知道他在哪兒。
女老師忙安慰說,您要堅強啊!海峰是個好孩子,他這么想回家,想上學,說不定,回來了會出現奇跡……
兩個女人流著眼淚互相擁抱了一下。
王老師走過去握了握海峰媽媽的手,說,有什么事就叫我們,等他好一點兒了,我們來接他去上課,哪怕回教室去坐坐……
王老師的聲音哽咽了。那是我第一次見到王老師流淚,也是唯一的一次。
轉身出門的時候,我看見了院子一角的那棵梔子花,蓬勃油亮的葉子里,似乎已經冒出了幾個胖嘟嘟的嬰兒手指般的綠色小花苞……
我忽然很想跑回去跟他說,海峰,夏天快到了,別忘了你說過的話,每天都給我帶一朵梔子花……
那天夜里,張海峰走了。他終于還是沒有見到二木。
張海峰的后事如何辦的,王老師他們有沒有參與,我毫不知情。他甚至都沒有跟我們多提,只說過,張海峰同學不能再來上學了,他的課桌椅就給二木用吧,鐘曉敏,你們以后不用再到其他班去借課桌椅了。
可是二木不肯用海峰的課桌椅,他寧愿站著上課也不用海峰的課桌椅,總是問,海峰呢?
沒有人回答他的問題。
直到六月的某天,班上一個特別調皮的男生沖他喊,傻瓜二木,張海峰再也不會來學校了,他死了。二木直愣愣地看著那個男生,突然沖上去就對著那個男生的頭打了兩拳。
那兩拳打得太重,一拳打破了那個男生的鼻子,一拳打破了那個男生的眼角。
家長找到學校來了。
二木的哥哥被叫到了學校,當面給人家賠禮道歉,可是,醫藥費他沒錢賠。聽說最后是學校承擔了那個孩子的醫藥費。
二木從那之后就再也沒有來過學校。后來,聽說二木已經不在我們鎮上了,他哥哥剛滿十八歲就去幾十里外的一個村子給人家當了上門女婿,帶著二木一起去的。
差不多一年的時間,我再也沒有去過海峰家所在的巷子,一次也沒有。直到三年級下學期,珠算老師帶我們到街上的商店里去上實踐課,就是帶著算盤和小板凳,到供銷社和各個雜貨店去,請售貨員當面給我們出題,讓我們非常直觀地理解了珠算與日常生活的聯系。海峰家的旁邊就有一家雜貨店。在那家雜貨店門口,我一道題也沒有算對。
直到現在,每年夏天我都會想,海峰家的梔子花還在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