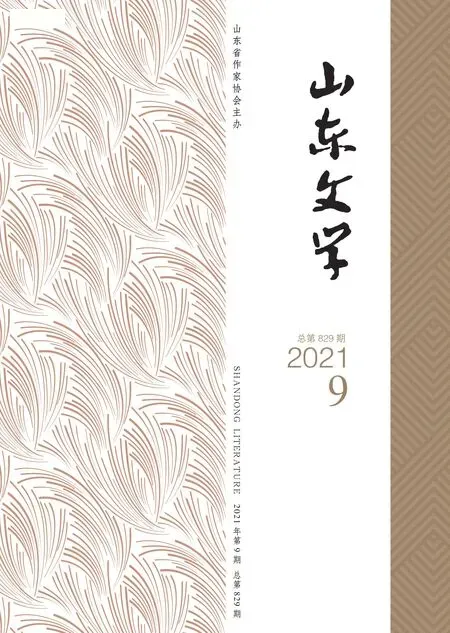提拉米蘇
徐廣慧
王捧玉和孟麗真正下手把房子買到手已經是一年后了,那個時候,房價已經漲到了一萬多一平。
這次,他們看上套一二樓躍層的大房子,算上地下室,面積296平。地下室贈送,整套房子總價210萬。他們貸了80萬房貸,又用上一套房作抵押貸了60萬,湊了湊手頭現金,還差40多萬。他們就再一次厚著臉皮,去親戚朋友那里借了一圈。
周圍的親戚朋友,大部分也都貸款買了房,幾乎很少有人能拿出閑錢來借給他。首付實在湊不夠,買房子的事就暫時擱置了下來。但是他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覺,連做夢都是棚戶區改造政策落地了,那些拆遷戶扛著一大捆現金在售樓部搶房。
以前凡是他看過的房,無論是市中心的,還是郊區的,無論是大的,還是小的,無論是戶型好的,還是戶型差的,統統都像是坐上了火箭,價格一路飆升。單位的小張,在郊區買了一套130多平的房子,一個月的時間賺了40多萬,好家伙,搗鼓房子,一個月掙的錢頂他十年的工資了。他惶恐不安,晝夜難眠,最后總結出一條真理:“買,就是對的。無論在哪里買,只要買了,就是賺了。”這個真理,叫他變得愈加痛苦。他無心再去上班,就請了假,躺在家里撥拉手機。他在手機上了解到南方的一批炒房客已經云游到北方來了,正要掃蕩三四線城市,看到這里,他的頭都大了。他覺得盤子里的肉,馬上就要被別人夾走了。他再也無法忍受自己的懦弱,就咬著牙對孟麗說:“這個房子我要定了,今天就去交定金!”
孟麗說:“這可不是小事,我算了算,要是買下這個房子,咱們除了要欠下四十多萬的外債,還要每月還八千塊的房貸,我覺得壓力實在太大了。你仔細想想,咱們看房都看了一年了,一直沒買,其實根本原因是每一次都買不起。工資沒漲,房價漲了這么多,以前每次都買不起,你覺得這次能買得起嗎?”
好不容易燃起的希望之火,就這么被妻子嘩地潑了一盆冷水,他有些惱火。
“你看看周圍的同事也好,同學也好,掙的錢不比咱多,卻都有二套房了,有的都有三四套了,還在買。咱上次在售樓部門口見的那個肖主任不是嗎?都已經有四套房了,還在看房——房價漲得這么快,要是現在不買,以后就更買不起了。”
擁有兩套房子的愿望像是一只野獸,沖撞著他們的心,使他們再也無法安靜下來。孟麗也請了假,兩個人關住門,在家里想了整整一天,最后騎著他們的那輛破摩托車去了售樓部。交完定金,售樓小姐把他們狠狠地贊美了一番,說他們有眼光,有生活品位,一看就是有能力、生活講究的人。售樓小姐強調說,他們買的上官府邸,是邢州市的高檔小區,在這里買房的,不是當官的,就是大老板。
交定金贈送了一袋小米,售樓小姐提著小米,把他們送到售樓部門口。
“是開車來的吧?”售樓小姐微笑著問。
“啊,是是……”他的臉刷地紅了,心咚咚地跳個不止。
“謝謝您,趕緊留步吧!不用再送了!”他從售樓小姐手里強行奪過那袋米,皮笑肉不笑地說。
售樓小姐嘴上說著“好的好的”,卻還是跟到了院子里。他們不愿意讓售樓小姐看見他們的摩托,就提著小米出了大門,等售樓小姐進了售樓部,才又折返回去。
房子已經定下了,就繼續借錢。拿出電話本,一個一個地琢磨,把老師同學、親戚朋友的電話都打了一遍,最后還是不夠,他們打算向自己的父母張口。
買第一套房時,他們沒有給父母張口。父母雙方都是農民,都已經七十多歲了,手里攢個錢也都是早年從地里刨出來的,從牙縫里擠出來的。他們覺得,父母把自己養大,供自己上大學不容易,現在自己能掙錢了,不給父母錢也就算了,絕不能向父母借錢。在他們看來,不向父母借錢,這是一個人做人的底線。說個不好聽的,借了父母的錢,一旦父母有個三長兩短,突然沒有了,他們卻還欠著父母的錢沒還上,那不是造孽嗎?現在,他們不得不突破這個底線了。
他們回到來福村,由孟麗出面,把買房的事說給了母親。按說買房是好事,母親卻沒有表現出驚喜,也沒有做出任何評價。在飯桌上,王捧玉幾次想給母親開口,嘴上卻像是抹了漿糊,怎么都開不開。母親的臉黑著,似乎已經看出他們有話說,卻硬是不問他們有什么事。母親后來出門了,下午回來母親的臉還是黑著,不見有什么喜模樣。
到了晚上,孟麗實在忍不住了。孟麗說:“娘,俺有個事想給您商量商量……”
父親坐在椅子上,母親坐在床沿上,她一開口,兩個人就都垂下了頭,目光像是潑在地上的水,在磚縫里渙散地流淌。
“我知道你說什么,你想借錢……”
沒等孟麗說完,母親就截斷了她。
孟麗嚇了一跳,從床沿上跳下來,不知所措地掃了母親一眼。
母親的臉黑乎乎的,陰沉沉的,縱橫交錯的皺紋里透著一絲絲涼氣。是啊,這是她的婆婆,不是她的親娘,她怎么忘了呢,一種隔離感油然而生。
“娘,定金都已經交了,現在急著交首付,錢還差一些……”
她說話有些結巴,那聲“娘”喊得一點兒都不利落,倉皇中抓起桌子上的茶壺,給母親倒了一杯水。母親接過她遞來的水,又重新放回到桌子上,直截了當地說:“你們姊妹幾個都買樓,都給我借錢,我的意思是,我能借給他們也不能借給你們……”
孟麗愣了一下,嗓子里帶了哭腔:“娘,他們也給您借錢了……”
母親說:“捧金和捧銀的地都包給別人了,都要在城里買樓,都給我借錢了……我的意思是,他們都是老農民……你們都念過書,再怎么也比他們賣力氣掙錢容易……”
孟麗的鼻子一酸,眼眶一下子紅了。她捂著臉跑出里間屋,蹲在院子里的老棗樹下身子抖了半天。王捧玉知道自己在家說話的分量要重一些,就回到屋里,對母親說:“娘,沒多有少,您給少拿一點兒也行,您知道我們的條件,您什么時候用,您一句話,我立馬給您送來。”
一向在家里當一把手的母親臉色比剛才更黑了,她瞟了一眼蜷縮在椅子上的父親,用極低的聲音說:“這事我不管,你問問你爹吧……”
王捧玉心里絕望極了,但還是把期待的目光轉向了父親。不知從什么時候起,父親就變得不愛說話了。遇到家里討論什么大事,他的頭總是耷拉著。這次也一樣,父親的腦袋,像是被人砍了一刀的茄子,無力地垂在自己的胸前。父親是老了,已經七十八了,但是他耳不聾,眼不花,聽不到她們剛才說的話嗎?聽到了卻裝作沒聽到,就那么一動不動,像是已經死了一樣。一生善良慈愛的他,到老了卻像變了個人。這個老實巴交的莊稼漢正在用沉默表明他的態度——從他們那里借錢,完全沒有可能。
回去的路上,孟麗的眼淚就像是開閘的水庫,一瀉千里——她靠在客車的窗子上,捂著臉,任那洶涌的淚水默默地奔騰。沒多久,她的臉就變得又腫又漲,紅彤彤的,胸前的衣服被淹成了一片湖泊。
王捧玉他們在一個鎮子上下了車,又倒車去了孟麗家。孟麗的娘從一個大木頭箱子里拿出一個煙盒,煙盒里放著七八張存單,有兩千的、五千的,也有一萬兩萬三萬五萬的。孟麗的娘不識字,孟麗爹活著時,經濟大權都在孟麗爹手里,孟麗娘就算是花一分錢都得伸手向孟麗爹要。現在孟麗爹死了,孟麗娘就自然而然地掌握了經濟大權。孟麗娘把那些存單從煙盒里倒到床上,說,拿吧,我也不認得字,你們愿意拿多少就拿多少。孟麗克制著內心的激動和喜悅,從里面挑了一張五萬的,又把剩下的存單疊好,重新放進煙盒里,交給了娘。
房子買到了手,光裝修就花了四十多萬。王捧玉和孟玉搬進了新房子。296平,上下三層,雖然算不上別墅,確實已經是別墅的規模了。最下面的一層地下室,成了王捧玉的活動場所,他把里面分成幾個區域,一個區域擺上了茶桌茶具,一個區域擺了一個大案子,又買了一塊毛氈子鋪上,又買了筆墨紙硯。從上大學的時候起,他就喜歡書法,現在,他終于有了一個自己的工作室,可以在這里練習書法了。
對于王捧玉來說,邢州就是一個謎。早在縣里的中學教書的時候,王捧玉就無數次幻想著能夠在邢州擁有一個家。這個家,房子必須要大,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應該有一個自己獨立的房間。而他自己,也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小天地。除此之外,他希望自己的這個家要有院子,院子里要種著樹。他妻子孟麗的愿望則是養一只貓。她幻想著有一天穿著真絲睡袍,抱著貓,坐在院子里的秋千上悠閑地看小說,或者聽音樂,或者發呆。
王捧玉愛他的妻子,他們是大學時的同班同學,從她嫁給他的那一刻起,他就發誓要叫妻子過上幸福的生活。妻子跟他一樣,也是老師,也是教語文的。這叫他感到苦悶。他雖然身為教師,卻看不起教師這個職業。他覺得當了教師,就是當了一輩子的學生。天天被關在學校,做題,講題,跟孩子們在課堂上斗氣。最讓他心煩意亂的還是他的工資,雖然教師的工資參照公務員工資發放,還比公務員高出百分之十,但他還是覺得不夠花。他出去買東西,為了一根蔥或者一雙運動鞋給人家討價還價,人家瞥一眼他那蒼白的臉、干癟的嘴唇和渙散的眼神,一臉冷漠說,你是當老師的吧?
他有些惱火,又不敢表露出來,哼哼唧唧地說:“呃……不……我……不是老師……”
老板是個女的,胖胖的,穿著一件黑色的像睡袍一樣的超長版大秋衣。她那秋衣質量不怎么樣,領口有一塊兒鵝黃色的不知什么東西的東西,下擺接口處耷拉著一團像蜘蛛一樣的線蛋蛋,但是她說起話來,卻自信得很。她把鞋從他的手里奪過去,重新擺放到貨架上,用她那鼓出眼眶的眼珠子又把他上上下下掃描了一番,以一種不容置疑的口氣說:“不是嗎?我覺得你就是當老師的!”
她干嘛用那樣的口氣,她一個賣鞋的,怎么一下子就把他給看穿了呢,他臉上一陣發燙,心里隱隱疼了一下。人家說他是當老師的,這對他來說,無疑是在說他是個小偷。為了不暴露身份,他不得不努力使自己鎮定下來。
“你……你……為什么覺得我是老師?”
他往前走了幾步,伸出爬滿青筋的手,再次把那雙帶著他體溫的運動鞋拿起來,放到眼前,左看右看,研究了一番。女老板白了他一眼,伸出手在空中一抓,想把鞋從他的手上搶回去,他一機靈,把兩只鞋都穿到了腳上,在屋地上煞有介事地來回走起來。
“哼,這年代,凡是講價的都是老師。”
女老板鼻子聳了聳,搬了把凳子,重重地坐下去,眼睛望著門外。
他有些尷尬,有些難受,也有些驚訝,要是一個人這樣說也就算了,很長一段時間,他已經不止一次聽到賣東西的說這樣的話了。越是這樣,他越想把自己跟老師撇清。為了證明自己不是老師,也為了給女老板一個無形的回擊,他最終以50元的原價買回來了那雙運動鞋。
他穿著那雙鞋去了邢州,參加了大學同學的聚會。他在一間豪華的房間里見到了他的同學們,和他們一起度過了美好的一天。也是在這一天,他發現,他的同學參加工作后都不穿運動鞋了,他們穿的都是锃亮锃亮的皮鞋。這天的聚會除了他妻子,其他同學全都到了。他對他們說,孟麗教高三,請不下假來。同學們不信,說他王捧玉是金屋藏嬌,不舍得叫孟麗露面。其實呢,王捧玉只是心疼那二百元的聚餐費而已。一人二百,兩個人一下子就是四百。經過商量,他們決定出一個代表參加這次聚會。他的那些同學中,凡是當老師的,都四平八穩,唯唯諾諾,那幾個從教師行業跳槽出來的,則說話響亮,走路帶風。
吃飯時,他心神不寧,看老二的眼神有些恍惚。他想起來上大學的時候,有一次班里進行一場關于人生價值的演講,老二當時演講的題目是什么他忘了,他只記得當時老二說了一句“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他就噌地站起來,沖著站在講臺上的老二氣哼哼地喊道:“你怎么說出這樣的話?作為當代大學生,我們不應該一心‘向錢看’,而是應該‘向前看’,樹立起為人民服務的遠大理想和目標。”
當年的自己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啊!看看眼前的花花世界,他開始反思自己,他覺得他內心深處的自卑,不僅僅來自于他是當老師的,更主要的,是他和這個社會脫節了。
“啊,如果我能成為他們該多好啊!如果我也能手腕上戴上名表,在邢州擁有一套像他們那樣的大房子該多好啊!嗯,能過上像他們那樣的生活,那才叫成功呢!”在跟同學們的推杯換盞中,他在心底發出一次又一次的感嘆。
在這一天,他做出一個決定,扔掉縣城里的教師工作,投奔他的同學,到邢州的一家方便面廠去打工。他的那位同學姓秦,叫秦勇。秦勇從一畢業就進了那家廠子,一個月三四千,頂他三個月的工資。他的妻子開始時堅決反對,后來禁不住他一再慫恿也就同意了,跟他一起到了邢州。
那個廠子只要男的,他就讓妻子去飯店打工,一邊干一邊尋找其他賺錢的機會。學校那邊的工資雖然停了,他們的編制學校卻一直給他們保留著,這是秦勇給他們出的主意。秦勇說,工資你們別要了,學校愿意怎么處置就怎么處置,只要給你們保留公職就行。這個社會一會兒一變,得給自己留條后路。一旦這邊不行了,你們就再回去。王捧玉就找到校長,出了點兒血,雙方一拍即合。
他們在秦勇家借住了一段時間,后來經過千挑萬選,終于在城中村租到一處每月只需一百多元的房子。那是個四合院,北屋東屋西屋都住著人,他們住的房子在南邊,房子雖然朝陰,卻是最大最新的一間,房租也比其他的租戶便宜。那幾家住的大部分都是生意人,北屋一共五間,西邊的兩間住著一家賣酥魚的,東邊的三間住著一家賣早餐的。賣酥魚的和賣早餐的每天早上三四點鐘就起床了,東屋賣菜的也是四五點鐘就去菜市批菜,西屋住著一對老夫婦都是清潔工,兩個人像太陽和月亮,不分晝夜,交替著出工。
他們一到這個院子,就得到了大家的熱情歡迎,這不僅僅因為他們腳上穿的都是皮鞋,更重要的是他們身上的衣服都很干凈。他們待人接物也跟一般人不一樣,說話不會用大嗓門,上完廁所也會隨手把門關上。
賣酥魚的老頭帶著兩個孫子,大的上六年級,小的上三年級。上六年級的那個孩子偶爾過來問問題,孟麗都會耐心地講解。等那孩子一走,孟麗就會捂著胸脯咳嗽半天。原來,那孩子得過肺結核,孟麗怕他傳染了自己。
因為有文化,孟麗很快升為了店長,當了店長,工資就跟她當老師時持平了。她當然不能滿足,這么拋家撇業到城市里來闖蕩,不就是為了能多掙些錢,讓生活再上點檔次嗎?孟麗的想法和王捧玉一樣,一天過不上別人過的那種高大上的日子,一天就不能安心。她后來應聘到一所學校當了代課老師,一邊四處去給人家做家教,一個月下來,竟能掙到三千多了。王捧玉在方便面廠工作了幾年后,方便面廠改制,變成了公司,他升為了部門經理。
到邢州后的第八年,他們貸款24萬,又從親戚朋友那里借了幾萬,加上自己的一點兒積蓄,湊了40多萬,在邢州最大的公園達活泉公園旁邊買了一套面積90平的單元房。在這所房子里,他們生下他們的兒子——王別墅。自從有了王別墅,家庭的工作重點就從買房過渡到了教育孩子的問題上。一晃就到了孩子上幼兒園的時間了,他們這時已經還完了外債,每月兩千多元的房貸也只剩下八個月就還完了。一切按部就班,在邢州有家有房的日子終于開始了,王捧玉和孟麗,也過上了他們想要的、城市人的幸福生活。
再一次同學聚會的時候,王捧玉不僅帶了孟麗,還帶了自己的兒子王別墅。這時他才發現,自己又落伍了。同學們的孩子都已經上初中了,他的孩子才上學前班。同學們都已經開始買第三套房了,他還在圍著第一套房轉圈。
回到家,他把家里的錢劃拉了一下,發現手頭竟然有20萬元的存款了。秦勇這時已經到房地產公司上班了。他打電話咨詢了一下秦勇,秦勇說,現在樓市一天一個價,你要買就抓緊買吧,不買以后就更買不起了。第二天,他騎著摩托轉了幾家樓盤,在售樓部碰到好幾個熟人,這才發現,原來買樓的人,比菜市場買菜的人都多。好家伙,真的是一天一個價,他頭一天去還六千一平,一星期后再去就七千二了,又過了一段時間竟然變成了八千一平了。他和孟麗商量,這次再買,一定要買個大點兒的房子。他們現在的房子只有兩室,他們倆一個臥室,王別墅一個臥室,家里連個書房都沒有,更別說來個親戚什么的了。
孟麗養了一只貓,貓的名字叫王別美,小名美美。王別墅這時已經七歲了,該上一年級了,為了接送孩子方便,王捧玉花五千元錢從熟人手里買了一輛紅星。雖然再有兩年就要報廢了,但是汽車保養得比較好。汽車是藍色的,王捧玉不是太喜歡,但是有車開總比沒車開強。
住進這個小區他才發現,小區里停的車,不是寶馬就是奔馳,要不就是奧迪、雷克薩斯,他那輛紅星像是個藍色的幽靈,在小區里進進出出,特別引人注意。王別墅卻異常地興奮,每次從車上下來都會很有儀式感地在車門上摸幾下。王捧玉怕王別墅的指甲把車劃壞了,每次王別墅一下車,就趕緊抓住他的手。
這天,家里迎來一位客人,這位客人是王捧玉的高中同學,這位高中同學在縣里的銀行上班。同學帶來一個不好的消息,說他們的工資停發了,叫他們趕緊回縣里看看。他們回到縣里,到教育局一問,原來縣里清理吃空餉的,把他們的公職給開除了。他們找到校長,問校長為什么沒有及時通知他們,校長支支吾吾,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他們呼天搶地,去縣里托人打聽了一圈,又去省里,錢花了不少,卻都打了水漂。公職沒有找回來,孟麗心情低落,埋怨當初王捧玉不該鼓動她丟下公職出去干。老師的工資現在也漲了,雖然他們現在的工資比當老師要多一些,但畢竟沒有保障。最主要的,他們連養老保險都沒有,將來要是哪一天突然不能干了,就連個退休金也摸不著了。
王捧玉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說到底,這一步走的還是對的。你看看,咱們現在在市里頭都有兩套房產了,我算了算,咱們的固定資產加起來有五百萬了,將來房價要是再翻一番,咱們可就是千萬富翁了。雖然咱們手里沒什么錢,但是我保證,咱們絕對是同學中房子最大的,固定資產最多的。
孟麗的眼圈紅了,孟麗說,有什么用呀?那套小的租出去了,那點兒房租遠遠不夠還房貸的。這套大的,一年光物業費、暖氣費就一萬多。跟在外面租房住也差不多了,要是再征收房產稅,真的就徹底完了。王捧玉把孟麗摟進懷里,用手輕輕撫摸著她那花白的頭發,溫柔地說,咱們抓緊掙錢,緊巴幾年也就挺過去了。孟麗說,是,一挺挺到老了,房貸也還完了,頭發也徹底白了。我覺得現在這個大房子就像是潘多拉的魔盒,打開就再也合不上了。王捧玉說,當初可是你哭著叫著要買房的,如果一天不買,你的心就一天安生不下來。孟麗說,我那時候瘋了,你也瘋了。真的,咱們中間要是有一個人能理智點,也不至于走到今天這一步。王捧玉說,今天這一步怎么了,這不正是我們想要的嗎?——手里有房,心里不慌。房子這么大的物件,住一套,存一套,你真的不覺得在同學和朋友面前倍有面子嗎?沒有壓力,就沒有動力。咱現在不能想別的,每天閉眼睡覺,睜眼掙錢就完了。
孟麗嘆了口氣說:“唉,你真的沒有關心樓市的變化嗎?你上網搜搜,網上說那些房地產大佬都開始停止拿地了,中介也開始紛紛倒閉。我認識一個干中介的,我聽到她打電話給另一個干中介的人說,他們中介,已經三個月沒有交易一套房了。現在我們已經成了高位接盤俠,如果房地產泡沫破滅,我們的下場真的不堪設想。”
“樓市要崩盤?不可能!樓市二十年沒跌,怎么可能咱一買它就跌了?”
“媽媽,房地產泡沫是什么?”坐在汽車后座的王別墅聽著大人的談話,身子變得一點點兒僵硬起來。他趴在車窗上,看看一排排高聳入云的高樓,心里開始突突地跳起來。莫非那些高樓像他用積木搭起的房子,用手指頭一點,就會轟然倒塌?
“停車!停車!”
一顆淚珠順著他的眼角流下來,他不安地伸出一只手,拽了拽坐在副駕駛上的媽媽。媽媽沒有理會他,他又拽了拽爸爸,爸爸也沒有理會他。
“可是,網上鋪天蓋地地這么說,我心里真是慌得不行!你想過嗎,要是樓市崩盤會怎么樣?——首付沒了,房子可能也要被銀行收走……”
“哎呀,真是杞人憂天!你想那么多干什么,房子買了就買了,要真是樓盤崩了,我們就當做生意做賠了不行嗎?”
“可是……我真不想給你說實話,你不知道我有多累,我現在白天做一份工作,晚上和周末又要去上家教,回到家還得管孩子,每天忙得像陀螺,這樣的日子什么時候才是個頭——唉,我……我真是覺得……活著一點兒意思也沒有了……”
王捧玉說,叫俺娘來吧,幫著照看孩子。王捧玉說的娘指的是孟麗的婆婆。孟麗以前跟婆婆的關系跟親娘和親閨女的關系一樣,自從上次借錢的事發生后,孟麗有一年多沒有回過來福村了。王捧玉也只是在一次出差的時候,順便往家里拐了一趟。見孟麗不說話,王捧玉就改口說,叫咱媽來吧,反正她一個人在家也沒事,叫咱媽過來幫著做個飯,再接送一下別墅上下學,這樣,我也能再出去找一份活干了。王捧玉說的媽,是孟麗的母親。孟麗說,我媽都那么大歲數了……王捧玉說,咱們還干呢,又不是什么活都叫咱媽干了。再說啦,咱媽一個人在家多沒意思啊,她那么待見別墅,你給老人家說說,她一準愿意。
孟麗的母親很快就來了。王捧玉和孟麗把二樓空著的房間打掃出來一間,從舊貨市場買來一張可以折疊的鋼絲床,又買來一把靠背被卸掉了的實木椅子放在床邊當桌子,叫母親住了進去。這個老太太一來就看出了門道。她每天把自己的頭梳得光溜溜的,衣服也穿得整整齊齊,打掃衛生,接孩子,做飯,里里外外,一切活全都包了。還有一件事是,自從老太太來了后,家里就不用買菜了,省下了一大筆開支。每天天黑了后她就拿著一個蛇皮袋子去菜市場,把那些商販扔的爛菜撿來,在地下室把能吃的菜葉一根根挑出來。有時候菜多得吃不了她還會給鄰居們送一些。那些菜都是老太太擇干凈洗干凈的,鄰居們都沒有發現他們吃的菜是撿來的。
對門的男主人是市里的一個什么干部,女主人在電力部門上班。女主人姓黃,王捧玉和孟麗都喊她黃姐。這天,老太太去給黃姐送菜,黃姐指著窗外正準備上班走的王捧玉說,這是你兒子?老太太說,不是兒子,是女婿。黃姐說,在哪兒上班啊?老太太說,縣里。黃姐說,看那派頭就不一般,是縣長?老太太一時沒反應過來,含含糊糊地回答:“嗯,是……是……是吧……”
從那以后,黃姐見了王捧玉就喊他王縣長,王捧玉認為她是在開玩笑,哈哈一笑,也沒有去理會,慢慢地,周圍的鄰居就都叫他王縣長了。不知是因為他們的車太破,還是因為他們穿得太不講究。以前,小區的小孩兒都不愿意跟王別墅玩,自從王捧玉成了王縣長,王別墅的朋友漸漸多起來。那些孩子過生日,也會邀請王別墅過去。
孟麗的母親也變得格外地受人尊重。有幾個老太太,沒事就到他們家的院子里來坐著,陪孟麗的母親聊天。王捧玉能看出來,從來到他們這里后,孟麗的母親比以前白了,胖了,臉也舒展了。為了進一步提高一家人的幸福指數,王捧玉給一家酒廠達成協議,他每次搞朗誦活動都掛上那家酒廠的名字,作為交換,他們給他提供一輛豪車,他有重要活動需要出席的時候,就讓他們給提供的車送去。如果時間允許,王捧玉就找各種理由,讓司機把車開到小區里晃一圈。
黃姐是個優雅的女子,每天出門前都會把自己好好打扮一番。她身上噴著濃烈的香水,所到之處,空氣都變成了香的。這天,黃姐敲開了他們家的門,加上孟麗的微信,問孟麗都用什么化妝品。孟麗從沒有用過化妝品,她抹臉用的還是幾塊錢一盒的一抹靚。黃姐就拿出幾盒化妝品,說女人怎么怎么要善待自己,這些化妝品怎么怎么好。她把化妝品倒出半瓶,“啪啪”地拍到孟麗的手上、臉上,讓她現場體驗,又問孟麗要不要拿幾盒。孟麗見她已經把化妝品打開了,又一下子用去那么多,只好遲疑不決地說:“那要不我就把打開的這一瓶要了吧,不然你就不好賣了……”
黃姐說:“你微信給我轉賬就行。”
孟麗問多少錢,黃姐說,600元。孟麗的頭一陣暈眩,胸口尖疼,拿手機的手一個勁兒地哆嗦。轉賬成功。黃姐站起身,拍拍屁股,扭頭走了。她呆坐在被黃姐的體味和唾沫星子攪拌過的黏稠的空氣里,胃里一陣翻江倒海。防盜門一關,她的眼淚嘩地流了下來。從那以后,她變得沉默寡言,多少天不愿意出門。學校打來電話叫她去上班,她說她病了,到底什么病呢,不知道,就是吃不下去飯,睡不著覺,遇到一點兒小事就發脾氣。
黃姐在朋友圈每天發賣化妝品的圖片,要不就發視頻。視頻里配著搖滾音樂,黃姐把自己的一張臉對著鏡頭,把化妝品一層層撲上去,然后拿手掌啪嘰啪嘰地拍,一邊拍一邊嗲聲嗲氣地說:“本小姐今天為什么這么靚麗,就是因為用了多美奇”,然后撮起紅嘴唇,對著鏡頭啵地親一下。
孟麗說:“我真是煩死她了,天天在朋友圈賣自己的那張臉。也真是奇了怪了,她男人當著那么大的官,她的工資又那么高,難道他們家也缺錢嗎?還有那些當老師的同事,一個個不是在朋友圈賣襪子,就是賣腳氣膏,要不就是賣文胸,還有的老師,上課不好好教學生,在家里開輔導班,叫學生交了錢在家里上——你說現在這個社會怎么了?”
王捧玉說:“你不是也帶著家教嗎?干嘛管人家?”
孟麗說:“那不一樣。一,我不是正式老師;二,我沒有從自己的學生中招生。”
越是煩什么,越是來什么。這天,王別墅的班主任給孟麗打來微信電話,繞來繞去,原來是向孟麗推銷衛生巾。孟麗一氣之下,把王別墅的班主任拉進了黑名單。
這還了得,這不是給孩子種蒺藜嗎?
王捧玉隱隱感到不安,帶著孟麗去了醫院,醫生說她是植物性神經紊亂,給她開了一些藥,叫她在家休息一段時間。
陪孟麗看完病,王捧玉回到公司,得到一個非常不好的消息,公司倒閉了,被一個臺灣的商人接手,原來的職工全部回家待命。也就是說,孟麗沒工作了,王捧玉也沒工作了,他們家每月8000多元的房貸一下子沒有了著落。
王捧玉不敢把這件事告訴孟麗,就每天繼續按時按點地出去。他因為普通話好,早年上大學時,在廣播站當過播音員,就一邊在公司上班,一邊成立了一個朗誦協會,他是會長。沒班上了,他就把精力全放在了朗誦協會上。他絞盡腦汁,選項目,定主題,組織人馬,然后仰仗著他的高顏值和三寸不爛之舌去政府部門或者大公司拉贊助,朗誦活動搞得如火如荼,他這個王會長很快成了邢州市的名人。雖然有時得不到現金回報,對方也會給一些名煙名酒作為補償,他就把那些名煙名酒拿到回收煙酒的地方賣掉,一點點地積攢起來,去湊還房貸的錢。這樣捉襟見肘的日子一晃過去兩個月,到第三個月,有個朋友打來電話,說自己最近做生意賠了錢,又不小心從房頂上掉了下來,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月。掛了電話,他深深地嘆了口氣,那口氣,像是一塊大石頭,咚地砸到了地上。孟麗的母親輕輕地走路,輕輕地做飯打掃房間,盡量不讓自己發出一絲聲音。到最后,她還是憋不住,追到地下室,輕聲問借了人家多少,他說,不多,也就三萬。孟麗的母親就把藏在枕頭底下的煙盒拿出來,連同身份證,偷偷給了王捧玉。
“看看還該誰的,能還幾家還幾家吧。”孟麗的母親說。
王捧玉紅著臉,眼眶里濕漉漉的。他張著嘴,想說什么,最終沒有說出口。他在心里反復比對,撿最近催得緊的幾家還了還。還完才發現,當月的房貸還沒地方弄呢。還款的日期一天天逼近,沒辦法,他只好去了原來住過的四合院。那些鄰居們倒是很慷慨,連個借條都沒打,這個一千,那個兩千,一次就給他湊了五千多。就是這樣,最終還是沒能湊夠。
他不得不考慮賣房的問題,孟麗當然同意賣房,她認為都是因為房子她才變成了現在人不人、鬼不鬼的樣子。這個時候他們才知道,從他們買下那個大房子后,房價真的跌了。他們上網搜索,又跑到中介到處打聽,發現讓人恐怖的事不是房價下跌,而是樓市橫盤了。什么叫橫盤,就是樓市變成了死水,沒人進行交易了。那些買房的人,仿佛一夜間從人間蒸發。他們在達活泉旁邊的那棟90平的房子標價115萬,掛了半個月沒人問,降到70萬還是無人問津。
又一次同學聚會如期而至,這一次,王捧玉不想去,孟麗也不想去,可是班長一遍一遍地打電話,叫他們必須過去。咸菜漲價了,雞蛋漲價了,豬肉漲價了,連同學聚會的份子錢都由每人200元漲成了每人300元,那還了得,兩個人一下子就是600元,那可是他們家半個月的生活費呀!最后,王捧玉想出一個辦法,他問好了聚會的地點,估摸著同學們快要吃完飯的時候再過去,那樣,他既見了同學,又省得掏聚餐費了。孟麗一聽他這樣說,嚶嚶地哭了起來。王捧玉說,哭什么呀,一會兒你也去吧。孟麗說不去,我頭疼。
路上,王捧玉一邊開車一邊琢磨見到同學們后該如何解釋他遲到的原因,他想了兩三種理由,到了后,竟然一條都沒有用上。他進門的時候,同學們正圍在桌子上,齊刷刷地低著頭看手機。沒有人關心進來的是誰,也沒有人關心他為什么遲到了。他看了看班長的手機屏幕,問他看什么,他說,正在搶購日本的馬桶蓋。王捧玉說,搶購日本的馬桶蓋干什么?班長笑了笑,詭秘地說:“老王,連日本的馬桶蓋都不知道,看來你真是奧特了!”
孟麗的情緒時好時壞,在家里歇了幾個月后,就又去上班了,課余時間,偶爾帶一兩個家教。這天吃過早飯后,王捧玉在院子里跟孟麗商量種樹的事。王捧玉說,種一棵石榴樹。孟麗說嫁接一棵月季。王別墅跑過來,說種提拉米蘇。
王捧玉說:“提拉米蘇是什么?”
王別墅咽了口唾沫說:“京京家有提拉米蘇。”
王別墅要拉著王捧玉去京京家,王捧玉不去,王別墅就拽著姥姥去了,沒一會兒又跑了回來。王捧玉急著出門,被王別墅攔在了洗手間門口。王別墅說,爸爸,我要提拉米蘇。王捧玉覺得,什么都可以湊合,就是兒子的吃的用的不能湊合,他們大人穿的衣服都是一百多塊錢的,甚至幾十塊錢的,兒子的衣服哪一件都得二三百、四五百,全是名牌。遇到好看的,就一下子給兒子買兩件。吃的東西也是,兒子要是要雪糕,要一個,他就給他買兩個,一個吃,一個拿著看。現在兒子要買提拉米蘇,盡管他不知道提拉米蘇是什么,他還是決定滿足兒子的愿望。他抓著兒子的小手說:“兒子,叫爸爸進去一下,爸爸一會兒去上班,回來的時候給你買提拉米蘇。”
王別墅挓挲著兩只胳膊,像個鴨子一樣,堵在洗手間門口,仰著脖子,大聲喊道:“我現在就要提拉米蘇!”
王捧玉今天要去主持一場市政府主辦的大型詩歌朗誦活動,眼看時間就要到了,卻還沒有出門,他心里有些焦慮,推開王別墅就往里走。王別墅被擠了個趔趄,伸手去抓王捧玉的挎帶背心,沒抓住,一下子摔倒在地上。從洗手間出來,王捧玉想給王別墅道個歉,卻發現王別墅不見了。他去樓上拿他的白襯衣,找了一圈沒找著,跑到地下室,見襯衣被扔在了練書法的案子上,墨水瓶橫在襯衣上,散發著一陣陣惡臭的墨汁從瓶子里咕嘟咕嘟往外流,把他的白襯衣染成了一片黑色的海。
怎么辦?這可是他唯一一件能見人的衣裳。他跺著腳,把襯衣從案子上扯下來,扔到地上,然后像瘋了一樣沖向二樓。他在衣柜里扒拉了將近半個小時,終于找到一件白背心。他把白背心抓起來,套到身上,把領帶胡亂系到脖子上,以百米沖刺的速度,沖出他的大房子。
那件背心是售樓部搞活動時人家給的,背上寫著幾個紅色的大字:剁手黨PK囤貨黨。
大字下面是一個人拿著一把菜刀砍自己胳膊的漫畫。漫畫的周圍,橫七豎八,寫滿了這樣一些大小不一的字:
“買,不要猶豫!”
“不買,后悔一輩子!”
“喜歡就買,錢是個屁!”
“有錢就買,沒錢借錢買!”
“錯過好機會,價格翻幾倍!”
“買買買,不買弄死你!”
“買他媽的!不買還是人?!”
王捧玉走后,王別墅跳著高對姥姥說:“姥姥,買買買,不買弄死你!”
這時候孟麗進來了,孟麗揪住他的耳朵,把他拖到地下室,拿起掃帚疙瘩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頓,一邊揍一邊說:“我叫你買買買,我叫你買買買……揍死你你就不買買買了……”
孟麗打完王別墅,又抱著他哭了一會兒,一邊哭一邊說:“王別墅,你今天可是把你爸爸害慘了,你爸爸穿著那樣的背心,怎么上臺給人家主持啊?”
提到王捧玉,王別墅又想起了提拉米蘇,王別墅說:“媽媽,我要吃提拉米蘇!”
“小兔崽子,家里有房貸,你還吃什么提拉米蘇啊?!”
孟麗從沙發上蹦起來,抄起桌子上的水杯,向王別墅扔去。
王別墅的姥姥撲過去,一把抱住王別墅,低聲說:“我的兒哎,我的兒哎,你沒事吧,你沒事吧,都是姥姥不好,姥姥不該帶別墅去京京家……”
王別墅的姥姥把王別墅領到臥室,把他抱到床上,安慰他說,你在這兒躺著別動,姥姥去給你弄提拉米蘇。王別墅點點頭,躺在床上數數,數到一百,就悄悄起來了。客廳里彌漫著一陣帶著苦澀的焦煳味,王別墅順著煳味找到廚房。王別墅的姥姥端著一個大大的鋁盆正往平底鍋里倒面糊,見王別墅來了,趕緊從灶臺上的筐子里拿起一個熱氣騰騰的面餅子遞給王別墅。
“姥姥給你做的提拉米蘇,快看看好吃不好吃……”
“不!我不要!這不是提拉米蘇!這是燒餅!”
王別墅大吼一聲,伸手把面餅子打到了地上,然后哭著跑走了。
王別墅的姥姥把餅子從地上撿起來,用手擦了擦,攆上王別墅,輕聲細氣地說:“兒哎,趕緊吃吧!上面黑的是巧克力,你嘗嘗,看看是不是跟提拉米蘇一樣……”
“不是!提拉米蘇不是這樣子的!姥姥,你真笨!你沒見過人家京京家的提拉米蘇嗎?”王別墅仰著脖子,嚎啕大哭。
孟麗瞪了王別墅一眼,提著一兜子書,急呼呼出去了。這天是周末,她要去給一個初三的女孩上課。
孟麗走了后,王別墅見姥姥立在陽臺上的水池子旁邊拿著爸爸的襯衣一邊洗一邊唱歌,就從廚房拿了一把水果刀悄悄溜了出去,他沿著甬路走了一圈,用刀把小區里的車一個不落地劃了一遍。
已經是深秋,樹上寬大的梧桐葉,一半碧綠,一半金黃,從空中墜落下來,掉到地上,發出“當”地一聲脆響。王別墅把刀扔進花池,繞過小區中央的假山,去西區找京京了。京京和幾個小朋友在涼亭前的空地上玩遙控飛機,見王別墅來了,有人提議要玩捉迷藏,玩到一半,王別墅突然停下來不跑了,王別墅問京京:“京京,你知道房貸是什么嗎?”
京京說:“房貸就是買房錢不夠,借銀行的錢買,再每月去還。”
王別墅說:“那房地產泡沫是什么?”
京京愣了一下,說:“哎呀,你怎么這么煩,問這么多干什么?”
王別墅說:“京京,那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崩盤?”
京京說:“王別墅,快跑吧,該抓你了!”
王別墅站著不動,一個胖胖的男孩走過來,指著王別墅的鼻子說:“王別墅,你到底還想不想玩,你看看你的眉頭,你怎么跟一個小老頭一樣?”
王別墅蹲在地上哭了起來。京京拍了拍王別墅的肩膀,說,別墅,你怎么了,你是不是想吃提拉米蘇?王別墅搖搖頭。京京說,別墅,你是不是想玩飛機?王別墅還是搖頭。京京嘆了口氣說,別墅,你到底怎么了?你為什么哭呀?王別墅不說話,哭得比剛才更狠了。
迷藏捉不成了,京京又把自己的遙控飛機弄到了天上。飛機在半空中盤旋著,發出一陣陣刺耳的嗚嗚聲。
“快看!流浪貓!”不知誰沖著花園里的灌木叢喊了一聲。
“美美,是美美!別墅,快看,是你們家美美!”另一個小伙伴叫道。
王別墅依然沒有動。小伙伴們一哄而散,有的回家了,有的去追王別墅家的貓。
天一天比一天黑得早,一眨眼的功夫,夜幕就又來臨了。霓虹燈漸次亮起來,把夜晚的高樓涂抹得像個小丑,小汽車一輛挨一輛,碾軋著暴曬了一天的柏油馬路,發出呼嚕呼嚕的吼聲。孟麗坐在沙發上,抱著已經睡熟了的王別墅,盯著防盜門一動不動。屋外,不時傳來一陣陣急促的腳步聲和咚咚咚的敲門聲……
樓前的甬路上黑魆魆的,路燈不知什么時候滅了。王捧玉在門前挖的土坑,正在等待著一棵不知叫什么名字的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