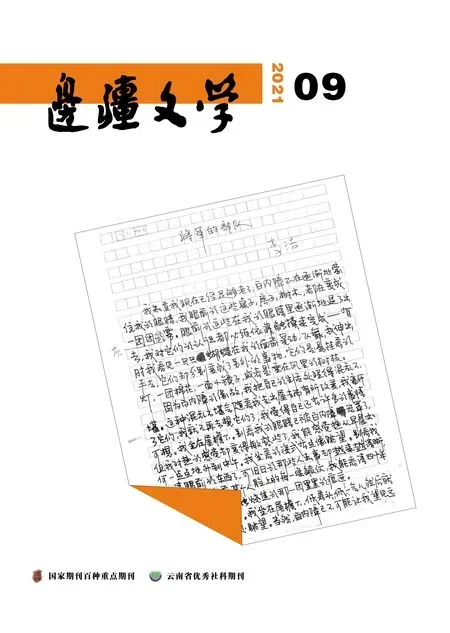百年黨史上云南的三大文化名人 散文
曉雪(白族)
學習百年黨史,我常常想起云南的三大文化名人:狂飆詩人柯仲平、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艾思奇和人民音樂家聶耳。
一
柯仲平(1902—1964)是我國新文學史上一位成就卓著、影響廣泛的杰出詩人。他對中國新詩的民族化、群眾化,對中國文藝的大眾化作出過開創性的重要貢獻,他在延安的一系列文藝活動得到毛澤東主席的親切關懷、熱情鼓勵和高度評價。他崇高的品德、豪放的性格和爽朗的笑聲,他烈火般熊熊燃燒、瀑布般飛騰直瀉、大河般洶涌澎湃的激情和洪鐘驚雷般震天動地、撼人心魄的詩歌朗誦,他數十年如一日為黨為人民的忘我工作、藝術活動和所取得的豐碩成果,不僅給一代人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而且也值得后輩后人永遠懷念和崇敬。
他出生于云南省廣南縣,在家鄉讀完高小后考上云南省立第一中學。在校時曾擔任學生自治會會長,并組織參與了游行、示威、登臺演講、砸日本洋行等愛國學生的活動,17 歲時就在學校創作并登臺演出了話劇《勞工神圣》,18 歲發表第一首短詩《白馬與寶劍》,并與一批思想進步的同學秘密成立了大同社,學習北京、上海傳來的進步書刊。1924年,考入國立北平政法大學法律系,同年10月24日,寫成了他的第一部長篇抒情詩《海夜歌聲》,這一年,他22 歲。1925年,他認識了魯迅先生,就常拿著詩稿到魯迅家請教。據《魯迅日記》載,從1925年6月5日到1926年2月23日,半年多的時間,他與魯迅交往,就達八次之多。常常是交談幾句之后,柯仲平就拿出詩稿,嗓門又高又亮地大聲朗誦起來,有時站到凳子上去朗誦,使魯迅母親周老太太擔心“這個頭發都吊在臉上的人”“怕要同大先生打起來”。朗誦完后,他跳下凳子,走到魯迅跟前,恭敬地彎著腰:“先生,請指教。”每次聽柯仲平“大聲吶喊”之后,魯迅都提意見,鼓勵他,還把他《偉大是“能死”》等詩發表在自己主編的刊物《語絲》和《莽原》上。
1928年冬,柯仲平以大革命時代為背景,創作了反映工農武裝斗爭的詩劇《風火山》,喊出了“被壓迫的工農兵聯合起來”“建立世界勞動政權”的呼聲,詩劇出版三個月后就被查禁。1930年3月,經潘漢年 、陳為人介紹,柯仲平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黨的《紅旗報》記者,后來又擔任上海工人糾察隊總部和上海總工會糾察部秘書。由于他的詩歌、劇本和論文“宣傳赤化”,他在1926年8月、1929年冬天和1930年12月曾三次被捕,在監獄里經受了嚴刑拷打,他始終堅貞不屈,還高聲朗誦自己的詩《走上斷頭臺》:“我是一個共產黨員!”“上刀山,下火海,也永遠是一個共產黨員!”被組織和朋友們又一次千方百計營救出來后,他于1935年夏天到日本留學,在東京一家私人汽車學校學習,準備將來開坦克殺敵。在日本學習期間,他還同徐克、劉御等云南籍留日學生組織成立了“理踐社”,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柯仲平8月便秘密回到武漢,在董必武同志領導下從事抗日救亡活動。由于國民黨特務的追捕,柯仲平于1937年11月來到延安。
到了延安,柯仲平如魚得水,有了大展宏圖的機會。在毛澤東主席的親切關懷和大力支持下,他出任陜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副主任(主任是吳玉章),一方面很快成立了“戰歌社”,自任社長,與詩人田間、林山、邵子南、高敏夫、史輪等共同發起延安街頭詩運動,發表《街頭詩運動宣言》,大力推動邊區的詩歌創作大眾化,另一方面積極籌備并很快組建了陜甘寧邊區民眾劇團,自任團長,請馬健翎、張季純任劇務主任,請劉白羽、柳青、方紀、草明等擔任教員,迅速組織創作和演出工農兵群眾喜聞樂見的戲劇作品。他本人,既寫短小的抒情詩、街頭詩,還寫長篇敘事詩,僅在1938年,4月份推出一部長篇敘事詩《邊區自衛軍》,12月又完成了第二部長篇敘事詩《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前者被譽為“是陜甘寧邊區最早出現的用詩的語言歌頌工農的長篇佳作”,后者則是“中國現代詩歌史上第一部用長詩來表現工人斗爭生活的作品”。兩部長詩都用樸素、清新、平易、親切的語言來抒寫工農兵在抗日戰爭中的感人故事和英雄形象,為群眾所喜聞樂見。
1938年夏天,一個星期六的晚上,邊區印刷廠舉辦周末文藝晚會,柯仲平最后一個登臺朗誦他的新作《邊區自衛軍》。他聲若洪鐘,熱情奔放,博得一陣陣熱烈的掌聲。毛主席也坐在觀眾席上,聽得很認真,同觀眾一起給他鼓掌。朗誦了一半,他感到時間太晚,便彎腰問前排的毛主席:“主席,我看算了,時間不早了。”主席回頭看看后面還坐滿了聽眾,便把手一揮說:“朗誦下去!”朗誦完后,毛主席緊緊握住他的手說:“很好!抗戰的,民族的,大眾的,民歌風的。怎么樣?稿子讓我拿回去看看,可以嗎?”柯仲平激動得心都快跳出來了:“當然可以,只是改得太亂,不好看。要么我重抄一遍再送來。”毛主席說:“不必了,先睹為快。”第二天,毛主席就派人把稿子送回來,只改了一個字,并在上面批了“此詩很好,趕快發表。毛澤東”幾個大字。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周刊第41、42 兩期,破例連載了兩千多行的長篇敘事詩《邊區自衛軍》。1940年,柯仲平的《邊區自衛軍》和《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第一章)》由重慶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
老詩人肖三說:“延安詩歌運動最初和最有力的發起人要算柯仲平同志,他是朗誦詩放頭炮的吶喊人。”柯仲平不但在詩歌創作、詩歌朗誦、詩歌普及和詩歌活動的組織方面在延安做了大量工作,起著引領帶頭的作用,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創辦和領導的邊區民眾劇團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堅持創作和演出戲曲現代戲,在抗戰八年中走遍邊區190 多個市鎮鄉村,演出達1475 場,觀眾達260 余萬人次,在中國戲曲發展史上寫下了燦爛的篇章。毛主席曾專門把他和馬健翎等人請到棗園一敘,贊揚他們的創作和演出“堅持文藝和群眾相結合,既是大眾性的,又是藝術性的,體現了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是大眾化的道路。”稱他們是“邊區文藝的先驅,走到哪里就將抗日的種子播到哪里。”林默涵在《柯仲平與民眾劇團》(見1992年11月7日《文藝報》)中說,毛主席在發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前,“找來了許多位作家交談,征求大家的意見,可見毛主席的思想、觀點,是從群眾中來的。經過綜合、提煉、形成科學的理論,反過來又到群眾中去,指導群眾的革命實踐。這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過程。柯仲平同志和民眾劇團的藝術實踐,也對毛主席的文藝思想和理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素材。”
1949年7月,在全國第一次文代會上,柯仲平當選為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即后來的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當時只有兩位副主席,另一位是丁玲。新中國成立后,他又先后任西北文教委員會副主任、西北文聯主席、西北藝術學院院長、中國作協西安分會主席等職,在做好組織領導工作的同時,還寫了許多好詩,出版了《從延安到北京》等多部詩集。1962年12月,他花多年心血創作的歌頌陜北根據地和劉志丹的一部長詩卻被康生之流誣陷為“反黨長詩”,受到錯誤批判。1964年10月20日,柯仲平在一次會議的發言中不幸倒下去世。
1979年9月20日,陜西省委在西安舉行柯仲平骨灰安放儀式,為他平反昭雪,恢復名譽,對他的一生給予高度評價。1985年元月五日,中國作協在北京召開“紀念著名詩人柯仲平逝世二十周年座談會”,習仲勛、賀敬之、張光年等出席。習仲勛在講話中號召大家“要向柯仲平同志學習”,說他是“一個把一生獻給中國革命事業的著名詩人,是一輩子和人民血肉相連、與人民休戚與共的文藝戰士。”柯老的愛人王琳在臺上朗讀了因病未能出席的王震同志的一封信,說“柯仲平同志是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是一位革命的大詩人,人民的大詩人”。
二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10年2月3日生于云南西部高黎貢山下騰沖縣和順鄉水碓村。他的父親李曰垓1903年畢業于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是一個有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的有為青年,在仰光由黃興介紹加入同盟會,積極投身于推翻滿清的革命斗爭,參加了昆明的“重九”起義,任護國第一軍秘書長,起義勝利后任云南都督府軍政部次長。他學貫中西,見多識廣,寫文章才思敏捷、文采飛揚,被章太炎稱為“滇中一支筆”。艾思奇從小受到父親的影響,臥室里掛著父親寫的“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的條幅,幼年讀私塾時就能背誦先秦諸子的許多文章。11 歲后進入公立國民小學讀四年級,除課堂學習外,還在晚間、假日和課余時間向家庭教師學英語、向父親學古文,并與父親聊天,少年的心靈里開始有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憂患意識。父親對孩子們的教育很開明也很科學,強調學習的自覺性。他多次說過:“學業的上進,單靠課堂講授是不行的,要養成博覽群書的習慣,要靠自己發奮努力,多讀多想,才能成為有學問、有能力、有創造精神的人才。”
1923年,因父親受到唐繼堯的排擠,全家被迫移居香港,艾思奇考入教會學校嶺南分校讀書。學校的主課是《圣經》、國文和英文。艾思奇的國文和英文在全班數一數二,只是對《圣經》不感興趣,有時甚至同講授《圣經》的校長發生爭論。有一次,當校長講到《圣經》里的“箴言”:“當人打你的右臉時,你應該再讓他打你的左臉”,艾思奇立即站起來憤慨地說:“我堅決反對《圣經》中的這些話!我們不是奴隸,挨了打,就應該勇敢地反抗還擊,我們不能這樣忍受屈辱。我們中國之所以貧弱,就是因為受了帝國主義的欺凌和封建勢力的壓迫而不敢反抗的結果!”不容置疑的《圣經》居然受到一個十三歲少年的挑戰和褻瀆,氣得校長大怒:“這是對上帝的冒犯,主將降罪于你!”說完就拍著桌子宣布下課。
1925年,艾思奇回昆明考入省立第一中學讀插班二年級。省立一中是云南學生運動的策源地之一,1919年就成立了學生自治會,并創辦了宣傳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刊物《滇潮》,后來又成立了共青團云南特別支部。艾思奇積極參加學校的反帝愛國斗爭,成為學生運動的骨干和學生會文藝部的負責人,并擔任《滇潮》的編委,經常在《滇潮》發表反帝反封建的短論和雜文。他還擔任省一中義務夜校的訓導主任兼教員,利用課余時間搞義務教育,學生大多是工人、學徒和貧苦人家的失學子弟。
艾思奇的社會活動引起當局的注意,把他列入“學生領袖”的抓捕名單。他得知消息后,裝扮成一位英國牧師的家庭教師,于1926年隨同牧師持化名護照離開云南,到蘇州找到父親。1927年春天,他東渡日本求學。在東京,中共東京特別支部領導下的社會科學研究會負責人、他的云南同鄉張天放、寸樹聲介紹他加入了社會主義學習小組。為了更好地閱讀、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他在日本期間整天閉門不出,先是苦攻日語,后是學習德語,僅用了一年時間,就能閱讀日譯本的馬克思著作和德國古典哲學,也能通讀德文版的馬克思主義經典原著。
1928年春,因在日本生活艱苦,勞累過度,他患了胃病,回昆明養病兩年。這兩年時間,他邊養病,邊比較系統地閱讀從日本帶回來的英、日、德幾種文字版本的馬列著作,積極參加黨的外圍組織的活動,還以 “店小二”“三本森”等筆名,發表了許多雜文、短論、譯文,針砭時弊,鼓吹革命,宣傳新思想、新哲學、新文化,在讀者中很有影響。
1930年初,艾思奇再度來到日本,考入福崗高等工業學校采礦系。他一方面刻苦學習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研究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同時更加深入地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當時中共東京支部每周在神田組織一次中國青年會的學習會,他每次都從遙遠的福崗趕去參加,從不缺席。經過多年的學習與思考,艾思奇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逐漸堅定,他說:“我總想從哲學中找出一種對宇宙和人生的科學真理,但總覺得說不清楚,很玄妙。最終讀到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才豁然開朗,才找到了對宇宙和社會的發生、發展的一個比較明確的認識和合理解釋。”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九一八”事變發生,艾思奇和一批愛國的留日學生表示強烈抗議,憤然棄學回國。1932年初,他先在上海一家日本研究所靠翻譯謀生,后又到泉漳中學任理化教員。在學校教書期間,他參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積極從事革命宣傳活動,并開始以“思奇”“李東明”等筆名在《中華月報》上發表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文章。1933年6月,他第一次以艾思奇的筆名在《正路》雜志創刊號上發表了長篇哲學論文《抽象作用與辯證法》,不久又發表了《二十二年來之中國哲學思潮》,兩篇文章都思想敏銳、見解獨到、文采飛揚,顯示出扎實的哲學功底和出眾的文字表達能力,在哲學界引起注意。
1934年6月,艾思奇到李公樸先生任館長的“《申報》流通圖書館指導部”,負責做“讀書問答”的工作。11月,“讀書問答”欄目從《申報》獨立出來,正式改成《讀書生活》半月刊,半月刊中的《哲學講話》和《科學講話》兩個欄目的組稿、審稿和定稿主要由艾思奇承擔。艾思奇早有打破哲學的神秘感,把哲學從哲學家的書齋和大學講臺上解放出來,使馬克思主義哲學變成人民大眾手中的銳利武器的想法,便自己帶頭寫《哲學講話》,第一篇的題目就叫《哲學并不神秘》。他用平易親切的談話形式,通俗易懂的群眾語言,大家熟悉的生動故事,來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連續在《讀書生活》半月刊發表了二十四篇,1935年11月結集出版,書名就叫《哲學講話》,先出了兩版,大受讀者歡迎,很快賣光。國民黨宣傳機構下令禁止印刷發行。后來改名為《大眾哲學》繼續出版,1936年不到五個月就出了四版,到1948年全國一共出了三十二版。早在1935年,李公樸先生就說過:“這一本通俗的哲學著作,我敢說可以普遍的做我們全國大眾讀者的指南針,拿它去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
1935年10月,艾思奇由周揚、周立波作介紹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除了編著、翻譯外,還積極從事新文化運動。他與老舍、鄭振鐸、李公樸、郁達夫等聯合署名發表了《我們對文化運動的意見》。1936年,他發起并組織成立了秘密的新哲學研究會。他還先后出版了《新哲學論集》《思想方法論》《如何研究哲學》《哲學與生活》等著作,并有一批科學小品發表。1937年,他參加了上海著作人協會,與郭沫若、茅盾、朱自清、郁達夫等署名發表了《中國文藝宣言》。
1937年9月,周揚、艾思奇、李初梨、何干之等一批上海的文化人來到延安,受到熱烈歡迎。土墻上貼出了“歡迎青年哲學家艾思奇到延安來”的標語。他們到達的當天晚上,毛澤東主席就來看望,還給每個人斟茶、遞煙。見到艾思奇,毛主席很高興地說:“噢!搞《大眾哲學》的艾思奇來了!你好啊,艾思奇同志,你的《大眾哲學》我讀過幾遍了,最近還有什么新的著作嗎?”艾思奇說:“半年前出了一本《哲學與生活》。”毛主席謙虛地說:“能否借我拜讀呀?讀完一定完璧歸艾!”
不久,毛主席讀了《哲學與生活》后,還給艾思奇同志寫了一封信:“思奇同志:你的《哲學與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書,我讀了得益很多,抄錄了一些,送請一看是否有抄錯的。其中有一個問題略有疑點(不是基本的不同),請你再考慮一下,詳情當面告訴。今日何時有暇,我來看你。毛澤東”
毛主席那么忙,怎能讓他來看望呢?艾思奇主動聯系,一天晚飯后到毛主席住的窯洞去拜望。45 歲的領袖同27 歲的青年哲學家朋友式的親切交談,談中國,談世界,談哲學,談抗日戰爭,一直談到深夜。毛主席對哲學的濃厚興趣和廣博知識,特別是他談每一個問題都善于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實際情況結合起來的思想方法和獨到見解,給艾思奇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到延安后,艾思奇先后擔任抗日軍政大學和陜北公學的主任教員、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主任、中宣部哲學小組的指導員、中宣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秘書長、綜合性理論刊物《中國文化》主編、《解放日報》副刊部主任等。他主編的《中國文化》在1940年的創刊號上就以頭版頭條的顯著位置,發表了毛主席的光輝著作《新民主主義論》。他按毛主席指示主編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思想方法論》是延安整風運動的必讀文件之一。他編寫的哲學基本教材在《中國文化》上連載。在延安時期,他在做好繁忙的行政組織工作、教好哲學課的同時,還寫了大量繼續研究哲學、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文章,出版了《科學歷史觀教程》《論中國的特殊性及其他》等著作,翻譯了《海涅詩選》,為在延安掀起學習哲學、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熱潮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作為一位有廣泛影響的哲學家,在新中國成立后,艾思奇主要還是從事哲學的教學和研究。五十年代初,他應邀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舉辦《社會發展史講座》,出版了專著《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發表了一批有現實針對性的理論文章,如《評關于社會發展史問題的若干非歷史觀點》《學習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毛澤東同志發展了真理論》《進一步學習和掌握無產階級世界觀》《反對唯心論》等等。他統籌主編的《自然辯證法提綱》是我國第一部比較系統完整的自然辯證法著作。他寫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是我國第一本較為系統地論述馬克主義哲學基本原理的教科書。特別難得的是,在許多人都頭腦發熱的“大躍進”年代,他能冷靜地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大膽地先在《中州評論》上發表《破除迷信·立科學·無往不勝》的文章,指出“破除迷信一定要立科學”,“沖天的干勁一定要與實事求是的精神結合起來”;接著又在1959年初的《紅旗》上發表《無限和有限的辯證法》,強調指出:“群眾力量的發揮總有一定的最大限度,而不是無窮無盡的。”“既要深信人民群眾力量的無窮無盡,又要注意到人民群眾力量的有窮有盡方面……”。表現出他作為一個真正馬克主義者的堅定立場和卓越膽識。
1959年底,艾思奇被任命為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1966年3月22日,艾思奇在北京病故,終年56 歲。他的遺體告別儀式,莊嚴而隆重,靈堂前放著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悼念他的四個大花圈,朱德委員長還親筆寫了一條橫幅:
艾思奇同志永垂不朽!
三
聶耳(1912—1935),原名聶守信,號子義(又作紫藝)。父親聶鴻儀是個中醫,他四歲那年就病逝了。母親彭寂寬,是一個勤勞賢惠而又愛講民間故事、會唱許多民歌的傣族婦女。聶耳從小受到母親的啟蒙,喜歡聽民歌,愛聽滇劇清唱,愛看花燈表演,還常常到郊外去聽農民“對歌”。他的記憶力特別好,白天聽了別人唱的調子,晚上能原原本本唱給家人聽,十歲時他已學會了吹笛子、拉二胡、彈三弦,成為小學校“學生音樂團”的主要骨干,除演奏樂器外,他還擔任指揮。
1927年秋,聶耳考入全省唯一的公費學校省立第一師范高級部外文組,除搞好課堂學習外,他對音樂、戲劇、文學、美術、體育都有興趣,成為學校業余文藝活動的積極分子。當時云南已成立了中共云南省特委和共青團省委,省師是黨團組織秘密活動的重要據點。聶耳開始讀到一些進步書刊和馬列主義的著作。1928年秋,聶耳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聶耳積極參加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各種活動,被列入軍警到處抓捕的黑名單。得知消息后,聶耳便先離開學校躲起來,于1930年7月頂替他三哥到上海“云豐申莊”當伙計。
在云豐申莊不到一年時間,他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在做好分內工作的同時,堅持學英文、日文、練習口琴、二胡和小提琴。1931年4月,他考入明月歌劇社當樂隊練習生,經過半年多的刻苦練習,他小提琴演奏技巧迅速提高,很快成為樂隊的主要小提琴手。他參加歌劇社的各種演出,受到歡迎。但1931年7月12日離開家鄉到上海剛滿一年的時候,他卻在日記中反省自己:“在這一年中,我的生活雖有小小的變遷,但仍不如我計劃中的一年應有的進步。”他感到自己只忙于練小提琴,提高業務水平,而沒有投身到抗日救亡的火熱斗爭中去。他開始思考“怎樣去做革命音樂”的問題。1932年4月,他認識了比他多大十四歲的詩人、戲劇家田漢,兩人看法一致,交談甚歡,成為知己朋友。不久,他在《電影藝術》上發表《中國歌舞短論》,批評明月歌劇社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仍然為歌舞而歌舞,演出香艷肉感的節目,提出音樂舞蹈應當為人民大眾服務。他說:“你要向那群眾深入,在這里面,你將有新鮮的材料,創造出新鮮的藝術。喂!努力!那條才是時代的大路。”
這年8月,聶耳主動退出明月歌劇社,來到北平。在這里,他結識了于伶、宋之的等左翼文化戰士,加入北平劇聯,參與左翼戲劇音樂的創作演出活動,由田漢介紹,接觸了黨組織,還多次深入到貧民區天橋等地,“鉆入了一個低級的社會”,收集北方民族民間音樂素材,體驗城市貧民的生活。11月,聶耳重返上海,進入聯華影業公司,從此,主要從事群眾歌曲和電影音樂的創作,進入了他音樂生涯的新階段。
1933年初,聶耳在田漢家中認識了夏衍。2月發起成立中國電影文化協會,夏衍、聶耳分任協會文學部、組織部秘書。不久,經過組織考察,由田漢、趙銘彝作介紹人,聶耳加入中國共產黨,在聯華一廠的一個攝影棚內秘密舉行了莊嚴的入黨宣誓儀式,監誓人就是夏衍。
1933年夏,聶耳為上海聯華影業公司拍攝的電影《母性之光》創作了他的第一首電影插曲《開礦歌》,從此就一發不可收拾。他的創作靈感如泉涌、如井噴,從寫《開礦歌》到在日本遇難這兩年的時間里,他成功地創作了四十多首廣受歡迎、充滿激情、反映時代精神和人民心聲的優秀歌曲,從《開礦歌》《賣報歌》、為話劇《饑餓線》寫的《饑寒交迫之歌》,到為田漢的歌劇《揚子江暴風雨》創作的《碼頭工人歌》《打磚歌》《打樁歌》《苦力歌》,從黨直接領導下的電通影片公司拍攝的第一部電影《桃花劫》的主題歌《畢業歌》到為電影《大路》創作的《大路歌》和《開路先鋒》,從為電影《新女性》創作的《新女性》組歌到他改編灌制成唱片的民間器樂曲《金蛇狂舞》《翠湖春曉》《山國情侶》等等,都很快傳遍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受到廣大群眾的喜愛和歡迎。在1934年底寫的述評《一年來之中國音樂》中,聶耳除繼續對脫離群眾的音樂痛加聲討外,還充分肯定了左翼電影音樂自《漁光曲》以來新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說:“尤以《大路歌》《開路先鋒歌》的剛健新穎、雄烈悲壯為難得,這些膾炙人口的歌曲,應該是一九三四年中國音樂不可多得的出產”。
聶耳在群眾中的影響,引起了反動當局的注意和仇恨,準備逮捕他。黨組織為了保護他,并考慮他渴望得到進一步深造的要求,決定讓他取道日本,去蘇聯或歐洲其他國家學習。1935年2月,田漢在被捕前匆匆寫下電影《風云兒女》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聶耳看了歌詞,立即“掄”下了作曲的任務。他從夏衍處拿到電影劇本和最后改定的歌詞后,連續幾天反復推敲、修改、試唱,幾乎廢寢忘食,夜以繼日,一會兒在桌上打拍子,一會兒在鋼琴上彈奏,一會兒在樓板上不停地走動,一會兒又高聲地唱起來。他還同導演許幸之反復商量,征求意見。許幸之聽了初稿后問他:“你是不是受到《國際歌》和《馬賽曲》的影響?”他自信地回答:“是受到一些影響,但要爭取比《國際歌》更明快,比《馬賽曲》更激昂。”最后,《義勇軍進行曲》的曲譜是聶耳1935年4月18日帶到日本后,又改了幾遍才從東京寄回上海的。5月9日,任光組織盛家倫、司徒慧敏、鄭君里、袁牧之、金山、顧夢鶴、施超等七人,第一次在百代公司錄音棚內錄下了這首今天已舉世聞名的《義勇軍進行曲》。《義勇軍進行曲》唱出了中華兒女萬眾一心、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心聲,唱出了中國抗日救亡的時代最強音,唱出了中華民族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會昂首挺胸、奮勇前進的偉大民族精神。
聶耳寄走了《義勇軍進行曲》的最后修改稿后,開始了對日本音樂的觀摩、考察和研究。6月2日,他在東京中華青年會舉行的第五次藝術聚餐會上作了題為《最近中國音樂界的總檢討》的報告,還演唱了他創作的《大路歌》《開路先鋒》《義勇軍進行曲》等歌曲,受到大家的熱烈歡迎。7月17日,他與友人去藤澤市鵠沼海濱游泳,竟被無情的海浪奪去了年輕的生命。那時,他才23 歲。他的骨灰和遺物,由他的好友張天虛、鄭子平送回上海,后來安葬在風景如畫的昆明西山,可以遙望五百里滇池。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在原地重建了聶耳墓。郭沫若題寫碑文,稱他為“中國革命之號角,人民解放之鼙鼓”,稱他譜寫的《義勇軍進行曲》(我國現在的國歌):“聞其聲者,莫不油然而興愛國之思,壯然而宏志士之氣,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