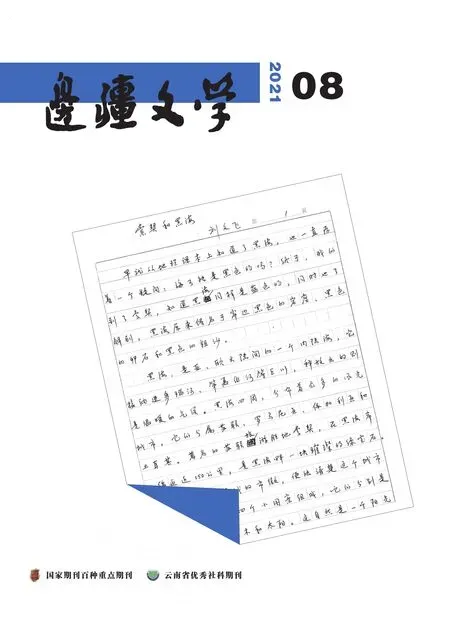繆祥濤的詩
繆祥濤
故鄉
帶一罐井水、一只碗
做一個背井離鄉的人
夜晚,把一個喝井水長大的人
倒出來。一低頭就看見碗里的月亮
直徑,比老家的小十五厘米
茶歌
那是早晨,我和茶
倚在出租屋的茶案上,相依為命
像奔波者遇上流浪漢
靜靜地等待識別、注入、接納
某一刻,茶會陷入短暫的遲疑
它不知道一把壺的胸懷,能不能
容下一片葉子風曬的遭遇
清明前,它離開母樹
剛經歷過揉曬、焙炒、擠壓
在沒有遇見容器之前,孤獨在寂靜中
沉默,隱忍
它偏愛熾熱,將清冽冽的水煮沸
像煮沸我搓揉過的心靈
我迎面撞見,自身的枯萎、退讓、無助
跟著沸騰一點點交出內心的苦澀
痙攣的葉脈里,藏著小小的春天
撞上拉姆拉措——致徒步人寧紅瑛
水往低處流,你偏要向高處走
柔軟不是宿命。在拉姆拉措神山的身體里
能夠找到天空
——邊遠、荒蕪、貧瘠,開始敗露
——被俗世拋棄的云朵,有超出我們千尺的冷暖
——拉姆拉措湖的內心也是積雪。
你聽見雪融化的聲音,給了你
冰裂疼痛的知覺,也給你遼闊和胸襟。
——潔白覆蓋靈魂時,有多于我們萬米的陡峭
在拉姆拉措湖漂洗隔世的經卷,
朝圣者的足跡,也是慈悲的梵文
還要給你歲月的慷慨,給你勇氣
讓安寧轉過身來,再走回去
沿著兩倍長的蜿蜒,向泥土匍匐
在理塘
不是所有的水都喜歡急流
姊妹湖化身為天使的眼淚,為水草靜默
水草為牛羊靜默,牛羊為土地靜默
磕長頭的人們匍匐在大地之上
向蔚藍俯首,稱臣
風怎么吹都是順從
不是所有的山都喜歡高高在上
在理塘,我把自己摁進水里,摁進
天空和浮云
格桑花開成一生中最美的自己
星辰在湖中飲水,準備著另一場春天
一片素不相識的流云
在扎嘎神山背面,傾聽理塘寺的佛音
第一次離天這么近,借風的尺度
丈量白鶴的翅翼,夕陽一樣遼闊
在理塘,圣潔的事物
先于人類學會了放棄語言
無字經
你見過無字經書嗎?
我見過。逢年過節
她擺出兩把空椅子,兩副空碗筷
燒三炷香,三張錢紙
行三跪九叩之禮
拜請天地諸神駕臨,就輕言細語念起來
她念到:菩薩保佑,丈夫
就往碗里夾一個荷包蛋
她念到:阿彌陀佛,兒子
就往碗里拈一只雞腿
她念到那些冥冥中注定的人和事
總是用筷子敲一下碗口
多少年了!我一字不識的母親
一直緊握一雙木質的命
敲打著瓷質的木魚
喜鵲之變奏
許多鳥鳴都有吉祥的玄音
喜鵲更勝一籌,音符里藏著卦象
嘰為乾,喳為坤
聞聲而至的游子對著曠野卜算
或客至,或書信。把家安在樹的頂端
遙遙有期,大吉
繁花落盡,喜鵲并不知道
我們所稱之為命運的聲音
在一千公里之外飄零、仰望
從遠處看,往近處飛
更適合一片落葉傾聽
鳥窩,線團一樣捂在誰的懷里
羽毛動了凡心,禿枝就有了溫度
在高高的樹頂,家
高懸于人間
在醫院
“呼就是呼,吸就是吸,憋著氣別動。”
——在醫院,醫囑如同佛旨
需赤身裸體,完全暴露出真實的樣子
醫生如是說:“少抽煙,尼古丁和焦油,
是催命的鬼,取出太難。”
這讓我感到毛孔粗大,緊張、沉默
第一次脫離汗水、淚水和血肉
與寄養在自己體內的賤骨頭相遇。
醫生如是說:“CT 室的射線比陽光更為有力
可以洞穿一個人的肉身,亦可佐證
靈魂犯下的罪惡。”
通透啊!在沒有確診之前我一直擔心
帶著太多生活的油膩混跡在健康的人群
孤獨和恐懼,會不會發霉?
醫生如是說:“在這塵世偷食惡果的人,
久了,還會生出狼心和狗肺。”
我忽然覺得,來到這人世
像是等一場原諒,或者救贖
披著煙熏火燎的袈裟
——掩凡胎,如裹尸
八月豆——致我親愛的妻子
八月的藤蔓已經褪色。她的青春
還清晰可見。盤錯于人世紛亂的枝叢
要讓我遇見:真葉露心,抽蔓,旋蔓,開花結莢
風里來,雨里去,纏綿也曾被捆綁
但是不怕,柔軟的命更具堅韌的品格
在高高的枝頭,找尋熱烈的出口
以她應有的和想要的方式
——孕育,垂愛,牽掛。
風吹過的時候,搖動著另一種驚心的可能
那是一個人滿懷恭敬的心事
她欲撕裂自己,擠干畢生的水分
她腹中的籽粒就要分娩
當年,妻子就是這樣剖開自己
抱出體內的豆子
先生:L 大爹
在老家鄉下,先生的職業
就是扎堆亡靈:裝殮,堂祭,超度,誦經
一輩子焚香,擊罄,叩拜,凈身
食別人家的齋飯,供別人家的神靈
L 大爹是佼佼者,更善于供奉心中的菩薩
七老八十,依然堅持為成了家的兒女們
積陰功,化福德。堅持在死人面前
替活人求福佑,訴衷腸,敲自己的木魚
說到傷心處,就在陰魂面前,替活人叫苦
流淚。說不下去,就咳兩聲
咳是他轉換悲痛的方法。那一瞬
仿佛跪在靈棚里的孝眷都是他的兒女
而他心知肚明,他們一心想要
活成在世的菩薩。他們并不愿意給生活下跪
是的,生死和垂暮離兒女太過遙遠
當年我走的時候,他的咳嗽聲比磬還沉
回來時,已置身堂屋供桌上的相框里
他身邊有尊菩薩,燭燈,香爐和天地諸神
多年來,只有大媽端著清水
擦洗他玻璃的肉身
這個唯一懂他的女人,秉承了信仰
閑著沒事就孤獨的伏于供案
——誦讀,發呆,對話,打盹
她睡著的時候,仿佛也已不在人世
那一刻,她也成了供桌上的擺設
在諸神面前,和他一起蒙受著灰塵
孤獨小院
你住進去,灰色的面容
她不會拒絕你
——久違的老人。在枯萎的季節
牽掛:遠行的蓬勃
我喜歡這種渴望的狀態
守望的衰老性和植物的盛開性,形成懷抱
——那些父親種下的花草
會和母親抱著取暖
海棠、芍藥、牡丹、茶花、杜鵑和迎春花
包圍了熱鬧——他們是約好的
而這僅僅是
一個漸次老去的看花人對于盛開的誤判
事實上,我們只是在花間取樂
搜尋奔波的舊翅膀
火葬
我愿意接受火的審判
一看見墳頭草,我就擔心
那些埋不掉的罪惡會重新發芽
我柔軟的一生,未必
配得上一塊石碑的硬度
燒了吧!一副沒有貢獻的軀殼
怎好占用國家土地
連同塵世這張二皮臉化成灰
撒掉,正好符合我的一生
只是不要撒在水里,在人海
我已漂泊得太久。撒到山中去
做草木的骨骼,一個五行木旺的人
生來,就欠人間一片森林
月如霜
中秋又占領了人間。黑白分明起來
我送走過的親人,在月亮內部
起伏
第一個是父親。二十二年前(冬月)
夜半風雪定,堆成他的晚期。
月色在他瞳孔里散開,他顫叨著:
“雪白,月亮白,白蛋白……白,
白,注射多了,人就沒用了。”
四年前是大哥。9.18,月光
撞上恥辱的日子,體溫在我懷里一寸寸
冷卻,來不及呢出半句話的熱量。
我第一次替他說出遺言:
“臉色蒼白,唾沫黏白,海洛因……死白,
白,吸多了,人就報廢了。”
孩子們圍著我的母親,要月餅
要天上白嫩嫩的圓圈。他們并不知道
餅一樣的奶奶早已中了白色的圈套
一生面對著太多無法填寫的空白
手里捧著心一樣的餅,餅一樣的月
掰不開的苦難,是她窮盡一生
對月光的熱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