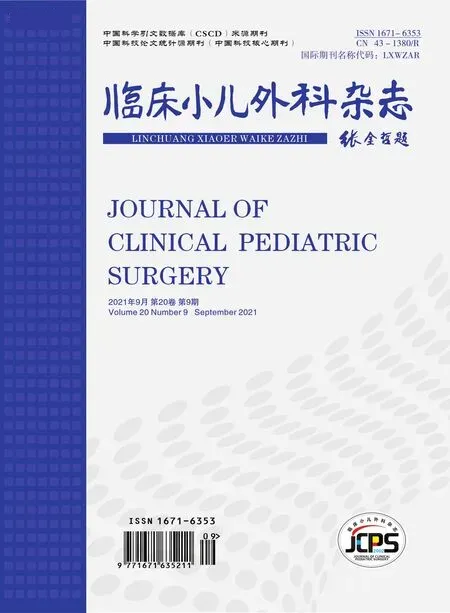Taylor空間支架在兒童下肢畸形矯正中的應用
王士奇 王一臣 應 灝 焦 勤 王 隼 馬琪超 趙利華
兒童復雜下肢畸形包括神經源性畸形和外傷性/感染性后遺畸形,一直以來是兒童骨科醫師面臨的挑戰。這些下肢畸形常同時存在短縮、內外翻、內外旋、屈曲或過伸等畸形,不僅影響肢體外觀和患者步態,也常因下肢負重關節軟骨的加速退變而誘發下肢早發性骨關節病及繼發性脊柱側彎。
傳統的肢體畸形矯正包括即時矯正(acute correction)和逐漸矯正(gradual correction)兩種策略[1,2]。當肢體不等長或軟組織條件差時,截骨內固定即時矯治方案受到限制,即時矯治方案也容易導致韌帶松弛、殘余畸形或繼發畸形等并發癥[2]。逐漸矯正策略根據Ilizarov的張力-應力法則,應用Ilizarov支架等外固定裝置緩慢逐漸牽拉,刺激截骨端新骨生成,從而達到畸形矯正的目的。近幾十年來,外固定已經成為矯治股骨、脛骨或足踝畸形的標準治療方案。在伴或不伴肢體不等長的嚴重復雜畸形矯治中,由于對骨和軟組織逐漸牽引原理和機制的認識不斷加深,外固定矯治肢體畸形的并發癥發生率明顯降低,患者肢體功能也得到明顯改善[3]。雖然經典的Ilizarov環形支架畸形矯治療效顯著,但多平面復合畸形矯治后的殘余畸形仍然是普遍存在的問題,由于Ilizarov支架常需調整外固定架的構型才能矯治這些殘余畸形,因此該調整過程繁瑣、技術復雜、學習曲線長[4]。
Taylor空間支架(Taylor spatial frame,TSF)是一款結合電腦軟件的先進環形外固定支架,支架的安裝以及逐漸矯治的原則與Ilizarov支架一致[2,5-7]。該支架由2個環和6根可伸縮連接桿組成,在基于網絡軟件生成的電子處方引導下(殘余畸形或階段性矯治結束后很容易根據該軟件生成新的處方),只需要調節桿的長度即可改變2個環的相對空間構象,從而同時矯治不同平面的成角、短縮或旋轉畸形,使多平面、復雜畸形的矯治簡單化。近年來,TSF支架在國內的應用逐漸增多,目前更多應用于成人四肢畸形的矯治,在兒童矯形外科領域應用尚少,近期有國外學者將TSF支架應用到兒童Blount病及馬德隆畸形的矯正中,取得了滿意的療效[5-9]。本文將對TSF矯治的系列兒童下肢畸形病例療效進行回顧性分析。
材料與方法
2016年12月至2018年12月上海市兒童醫院采用TSF矯治兒童下肢畸形5例,女4例,男1例;年齡4~15歲,平均8.2歲。
術前評估:術前詳細詢問病史和查體,常規攝雙下肢全長站立前后位X線片、患肢全長站立位側位X線片以及膝關節側位或踝關節側位或足正側位X線片,通過量化患肢的機械軸偏移、關節方向角以及肢體長度等資料評估肢體骨性畸形的位置、嚴重程度、單處或多處畸形,找到畸形的頂點(CORA點)并做畸形分析、制定矯治方案。常規測量以下數值:①雙下肢股骨和脛骨長度以及雙下肢整體長度差異(包括足、踝、脛骨、股骨及骨盆綜合長度);②機械軸偏移距離(mechanical axis deviation,MAD)和方向,理想MAD值為0 mm(±3 mm);③股骨近端外側機械角(mechanical lateral proximal femoral angle,mLPFA),正常85°~95°,平均90°;④股骨遠端外側機械角(mechanical lateral distal femoral angle,mLDFA),正常85°~90°,平均87°;⑤脛骨近端內側機械角(mechanical medial proximal tibial angle,mMPTA),正常85°~90°,平均87°;⑥脛骨遠端外側機械角(mechanical lateral distal tibial angle,mLDTA),正常86°~92°,平均89°;⑦股骨遠端后側角(posterior diatal femoral angle,PDFA),正常79°~87°,平均83°;⑧脛骨近端后側角(posterior proximal tibial angle,PPTA),正常77°~84°,平均81°;⑨脛骨遠端前側角(anterior diatal tibial angle,ADTA),正常78°~82°,平均80°。
術前根據以上X線片測量和查體確定6個畸形參數:①畸形在冠狀面的內翻、外翻成角度數;②畸形在冠狀面內側或外側位移距離(單位:mm);③畸形在矢狀面的前弓或后弓畸形成角度數;④畸形在矢狀面上向前后向后的位移距離(單位:mm);⑤畸形在軸向的內旋或外旋畸形度數;⑥畸形在軸向短縮或延長的距離(單位:mm)。同時,查體明確大腿、小腿旋轉畸形及其角度,髖關節、膝關節及踝關節的活動度、肌力、肌張力。
5例患者病情分別如下:病例1為女性,11歲,無明確誘因,隨著生長發育逐漸出現左側特發性膝外翻及左股骨30 mm短縮畸形,曾行骨骺阻滯等3次手術矯治畸形,無顯著療效;病例2為女性,13歲,因脊髓脊膜膨出逐漸出現雙側重度神經源性馬蹄內翻足畸形,曾行跟腱延長、軟組織松解、關節融合等手術后,仍存在雙足嚴重馬蹄內翻樣畸形;病例3為女性,11歲,3歲時摔傷后逐漸出現左側膝內翻合并膝關節過伸、左側脛骨內旋及左股骨10 mm短縮和左脛骨25 mm短縮畸形,曾行骨骺阻滯及截骨術,畸形無改善;病例4為男性,15歲,患者7歲時因車禍傷至左踝關節外翻、左脛骨近端內翻、左脛骨近端前弓、左脛骨遠端后弓及左脛骨35 mm短縮畸形,曾行截骨矯治及關節融合術仍存在畸形;病例5為女性,4歲,出生后發現左股骨遠端骨髓炎后逐漸出現左股骨外翻及左股骨50 mm短縮畸形,曾行骨骺阻滯及截骨矯治無顯著療效。5例患者術前畸形情況見表1。

表1 5例患者術前畸形情況分析Table 1 Analysis of preoperative deformities in 5 cases
手術及術后處理:①病例1存在左側股骨外翻、前弓及3.0 cm短縮畸形:近、遠端環均為2/3環,遠端環為參考環,用1枚2.0 mm克氏針及2枚4.5 mm半釘安裝固定參考環后拍片獲得安裝參數,包括正位、側位和軸位X線片上參考環中心距原點的距離和方向以及參考環的內旋/外旋角度;安裝6根連接桿(記錄連接桿類型和長度)后安裝固定近端環;最后采用小切口經皮鉆孔股骨遠端截骨,截骨完成后,用外固定支架固定患肢在術前畸形的位置上。②病例2為脊髓脊膜膨出后遺雙側重度神經源性馬蹄內翻足畸形:采用TSF足踝畸形6×6 Butt矯正模式進行支架安裝,參考環為遠端足環,截骨部位為中足。③病例3為創傷后左股骨外翻、1 cm短縮和脛骨內翻、后弓和2.5 cm短縮畸形:先行左腓骨中段截骨及脛腓骨遠端空心螺釘固定,分別于股骨遠端(遠端環為參考環)及脛骨近端(近端全環為參考環)安裝TSF支架各1套,分別于股骨遠端及脛骨近端截骨。④病例4為創傷后左側踝關節外翻及左下肢3.5 cm短縮畸形:先行腓骨中段截骨,再于脛骨近端及遠端各安裝一套TSF環,中間全環為共用移動環,近、遠端環為參考環,分別于脛骨近端及脛骨遠端截骨。⑤病例5為骨髓炎后遺左股骨外翻及左下肢5.0 cm短縮畸形:于股骨遠端安裝TSF支架,參考環為遠端環,股骨遠端截骨。
術后第3天患者開始下地活動,逐漸增加患肢髖、膝和踝關節的主動和被動功能鍛煉,以盡可能維持和增加其活動度。術后1周內,每2天消毒并更換覆蓋針道及截骨處傷口的敷料。手術后1周去除無菌敷料,并告知患者家屬進行針道碘伏涂擦消毒和針道護理方法。
術后醫生根據患者畸形的參數和支架安裝參數,通過TSF生產公司特有的網絡軟件生成畸形矯治電子處方。術后1周,醫生教患者家屬根據電子處方調節6根可伸縮連接桿的長度,6根連接桿每天同一時間1次性完成調整。畸形矯治過程中,每周攝雙下肢全長前后位或足踝正側位X線片檢查畸形矯正效果。根據電子處方調節完成后,如尚存殘余畸形,根據攝片測得的殘余畸形參數再次輸入軟件并生成二次矯治處方,直到畸形完全矯正。截骨處新骨礦化成熟后去除外固定架。
結 果
共5例病例6個下肢節段(3例股骨,2例脛骨,1例足)接受治療。1例男性患者接受了脛骨2個水平的TSF矯治(2套TSF3環,中間環為共用移動環,兩端為參考環),1例女性患者接受了股骨和脛骨各1套TSF矯治不同節段的畸形,1例采用6×6 Butt模式矯治足踝部畸形。患者均在術后7~10 d根據電子處方開始調節支架,經過35~42 d的調節,2例患者的畸形部位經過1次處方得到完全矯正,肢體的外觀恢復正常且雙下肢等長,X線片顯示患肢的機械軸偏移量(MAD)和關節方向角(mLDFA、mMPTA、mLDTA、PDFA或PPTA)恢復至正常范圍,肢體的成角、旋轉和短縮畸形得到矯正;2例因殘存畸形或過度矯治經過2~6 d的調整后畸形得到矯正;1例神經源性馬蹄內翻足畸形患者經過多次處方調整后仍殘留部分畸形:內收10°(術前40°),旋后15°(術前60°),內翻10°(術前40°),該例患者畸形不能完全矯正,考慮與術中中足截骨不徹底、畸形嚴重等因素相關,同時本例患者術后存在第3跖趾關節脫位。所有患者截骨處新骨生成和礦化良好,術后1.5~6個月去除外固定架(圖1,圖2)。4例關節活動正常或接近正常,能參加學校常規的體育活動,活動后無關節疼痛和不適,生活自理;神經源性馬蹄內翻足畸形患者術后能依靠右足獨立行走,生活自理;由于左側足仍存在嚴重馬蹄內翻足畸形,不能參與體育活動。
外固定架去除后患者步態逐漸恢復正常,隨訪6~29個月,畸形無復發。患者及家屬均對治療效果表示滿意。術后馬蹄內翻足畸形患者發生針道切割和感染,經敏感抗生素及局部換藥治療后感染治愈,無需拔除克氏針、橄欖針或半釘以控制和治療感染;其余患者無針道感染。5例均無重要血管神經損傷、骨不連、繼發馬蹄足畸形、關節僵硬及取出外固定后骨折等并發癥發生。
討 論
TSF支架目前更多應用于成人四肢畸形的矯治,由于兒童處于骨骼發育階段,骨骺尚未閉合,因此在兒童中使用時更需謹慎。本組5例中,4例手術時患者年齡接近發育結束年齡(骨齡片提示骨骺閉合或接近閉合),1例5歲患者接受畸形截骨矯治術失敗后病變累及80%以上骨骺,最終考慮TSF支架矯治方案。5例接受過多次手術均失敗,術前評估TSF支架矯治方案對患者骨骺影響較小,且畸形復雜,因此我們選擇TSF外固定支架對患者進行下肢畸形矯正。我們的研究顯示,TSF外固定支架能夠同時、精準矯治多平面的兒童復雜下肢畸形(特發性、外傷性、感染性以及神經源性)。本組5例患者中,4例短縮畸形合并其它畸形,3例同時存在冠狀面(內/外翻)和矢狀面(前/后弓)畸形,2例同時存在冠狀面(內/外翻)、矢狀面和旋轉畸形。3例冠狀面、矢狀面、旋轉和短縮畸形得到完全矯治;1例在最近一次隨訪中發現其左下肢機械軸出現6 mm的內側偏移,但是該患者術前存在的股骨遠端mLDFA和PDFA及脛骨近端的mMPTA和PPTA均矯治至正常范圍,需要密切隨訪其機械軸的轉歸。Tetsworth等[10]應用Ilizarov支架矯治28例復雜下肢畸形,他們發現約21%的患者殘存10 mm以上MAD偏移,14例股骨遠端畸形病例中有8例(57%)股骨關節角恢復至正常范圍的3°以內,22例脛骨近端畸形病例中有17例(77%)脛骨近端關節角恢復至正常范圍的3°以內。我們的5例關節方向角均恢復至正常范圍。
一、TSF可同時矯治多平面畸形,精準度更高
Manner等[4]開展了一項經典研究,他們通過評估278例采用TSF或Ilizarov環形支架(IRF)治療的病例是否能達到預期畸形矯治的目標來對比研究TSF和IRF的精準度,他們發現應用IRF矯治的79例病例中有44例(55.7%)無殘余畸形,應用TSF矯治的129例病例中有117例(90.7%)無殘余畸形,提示TSF的畸形矯治精準度高于IRF;隨著需要矯治的軸向和維度(內翻、外翻、前弓或后弓)增加,殘余畸形的發生率也增加。Manner等研究提示,TSF在矯治多平面畸形時較IRF有明顯優勢,精準度更高。本研究中的病例均存在多維畸形,上述畸形均同時得到矯正。理論上,由于環的大小和伸縮桿長度的限制,畸形的矯正范圍有限,我們的病例中,角度畸形最多矯治了30°的冠狀面畸形,馬蹄內翻足畸形患者矯治結束后仍殘留內翻、內收和旋后畸形,也可能與該矯治方案的局限相關[11]。
二、TSF操作簡單,術后并發癥少
有研究提示TSF支架的安裝和畸形的調整較Ilizarov外固定架更簡單、并發癥更少,且病患的舒適度更好[12-15]。我們在治療過程中發現,不同顏色標記的6根可伸縮桿以及簡單的電子處方明顯提高了患者及家屬調整支架的依從性和可操縱性,顯著降低了調桿過程的復雜程度;同時保證了畸形矯治的精準度。Feldmann等[16]報道了18例脛骨畸形愈合和骨不連病例經過TSF支架矯治的療效,患者平均年齡為29.6歲(10~64歲),TSF矯治的同時進行了骨移植、皮瓣轉移或移植、感染后擴創/清創術等,TSF矯治后最終殘余畸形為1.8°(0~3.6°)。Rozbruch等[17]分析了102例脛骨畸形病例TSF逐漸牽拉矯治的療效,提出TSF能夠精準、逐漸矯正所有脛骨畸形,并發癥少,患者依從性及滿意度高,尤其適用于伴感染、肢體不等長、軟組織覆蓋條件差的病例。我們在5例患者矯治過程中發現,行股骨遠端截骨畸形矯治和延長時,截骨處新生骨量和截骨部位的愈合速度快于脛骨近端及遠端的速度,與文獻報道結果一致,亦與Ilizarov支架畸形矯治時截骨部位愈合速度存在相似的規律[18]。本研究的病例包括特發性、外傷性、神經源性及感染性病例,所有病例均存在多維、多軸面畸形,經過TSF牽拉矯治后,均獲得滿意療效,1例最后一次隨訪時發現6 mm機械軸內移,需要進一步隨訪并關注其轉歸情況;1例馬蹄內翻足畸形患者的殘余畸形可能與我們對該類畸形的治療經驗不足、畸形嚴重并經歷多次手術矯治后骨及軟組織條件差等因素相關。針道感染、外固定架取出后再骨折、關節僵硬、外固定架取出后新生骨畸形或彎曲等都是TSF或IRF等外固定架畸形矯治中常見的并發癥,截止最后一次隨訪,本組報道的患者均無明顯并發癥發生,患者患肢關節活動范圍恢復至術前活動范圍的98%以上[15,19,20]。本組5例盡管病種不同,但是均根據畸形測量參數進行畸形矯治,從目前已有數據、治療經過和療效看,只要畸形參數測量準確,并針對畸形參數根據TSF外架安裝和調整畸形處方進行矯治,即可達到滿意療效,這也是Taylor支架的使用對醫師的外固定支架臨床經驗要求較低、學習曲線較短的獨特優勢之處。
目前,TSF支架在兒童肢體畸形矯治中的應用逐漸增加,本研究納入的病例數較少,存在一定局限性,需要不斷豐富該方法的使用經驗。我們的病例治療過程和療效提示,Taylor空間支架在矯正兒童多維度、多軸面復雜畸形上療效確切,術后功能及外觀恢復良好,精確度及可重復性高,是矯治兒童下肢畸形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