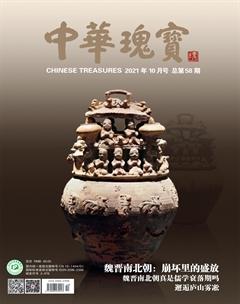談?wù)勎簳x南北朝的駢文



在駢文走過的漫長歷史中,魏晉南北朝三百多年是最為重要的時(shí)期。魏晉南北朝的駢文,可謂名家輩出,佳作如林。無論是寫景狀物、緣情抒懷,還是論事說理,都出之以駢文。
什么是駢文?駢是成雙作對之意,一篇文章之中,有較多的對偶句子,即稱之為駢文。
駢文之歷史
駢文的形成,是一個(gè)從量變到質(zhì)變的過程。早在先秦時(shí)代,詩歌文章里便有對偶。經(jīng)由兩漢,對偶成分漸多。到了東漢末,尤其是建安時(shí)期,駢偶已常見于不少作者的筆底,也日趨工整。試看蔡邕《郭有道碑序》“若乃砥節(jié)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干事,隱括足以矯時(shí)。……于時(shí)纓緌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翔區(qū)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云云,已經(jīng)是典型的駢文語感:對偶工整,句子較短,以四字、六字為多。多用四字、六字,形成一種既整齊又有變化的節(jié)奏,后世駢文往往如此。
到了西晉陸機(jī),可以說典型的駢文已經(jīng)成熟。這不僅因?yàn)樗淖髌否壟汲煞侄喽ふ捎谒\(yùn)用這種文體得心應(yīng)手。錢鍾書先生曾說:“漢魏文章,漸趨偶儷,然時(shí)有單行參乎其間。蔡邕體最純粹,而庸暗無光氣,平板不流動,又多引成語,鮮使典實(shí)。及陸機(jī)為之,搜對索偶,竟體完善,使典引經(jīng),莫不工妙,馳騁往來,色鮮詞暢,調(diào)諧音協(xié)……儷之體,于機(jī)而大成矣!”(《上家大人論駢文流變書》)此后至于南朝,駢儷作風(fēng)成為文壇主流。
齊梁時(shí)在聲律理論的影響之下,在搜對索偶時(shí)更加注意音聲的和諧,同時(shí)在用典、辭藻方面也越發(fā)講究,南朝末期的徐陵、庾信乃是這一時(shí)期的代表作家。駢文至此已達(dá)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余風(fēng)一直及于唐代。整個(gè)唐代,駢文都還是占主導(dǎo)地位,雖有中唐韓愈、柳宗元等人有意識地反對駢體,以“古文”相號召,但彼眾我寡,未能動俗。直到宋代歐陽修、王安石和三蘇(蘇洵、蘇軾、蘇轍)等,方才逐漸改變駢文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的局面。但是駢文并未絕跡,而且在一些應(yīng)用文體中,還是必須使用駢文的。此后駢文日漸陵夷,到了清代,有人不滿于“古文”在一些作者筆下變得熟濫庸弱,于是又提倡和創(chuàng)作駢文。
在駢文走過的漫長歷史中,魏晉南北朝三百多年當(dāng)然是最為重要的時(shí)期。在當(dāng)時(shí)人們的意識里,并不存在駢文與非駢文的對立,也不曾專門用一個(gè)名詞去稱呼所謂駢文。他們認(rèn)為運(yùn)用偶對乃天經(jīng)地義,向來就有,至于對偶成分的由少到多、由粗率到工整,那只是一個(gè)自然而然的發(fā)展過程罷了,就像各種事物由簡單到復(fù)雜,由質(zhì)樸到華麗,“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一樣。唐宋“古文”有意識地反對駢文,避免偶對,打破整齊的句式,然后人們才鮮明地感到二者的區(qū)別。不過當(dāng)時(shí)也并未使用“駢文”一詞。宋代稱那些“駢四儷六”的應(yīng)用文字為“四六文”。直到清代,方才使用“駢體”“駢文”這樣的名詞,沿用至今。
總之,所謂駢文,是從修辭角度著眼的一種文章分類名稱,與散行相對。駢文與非駢文之間也沒有截然劃分的界限。大體說來,駢文給人最鮮明的印象是在對偶以及句式節(jié)奏方面。
魏晉南北朝的駢文,可謂名家輩出,佳作如林。無論是寫景狀物、緣情抒懷,還是論事說理,都出之以駢文。下面略舉數(shù)例。
寫景狀物
南朝自謝靈運(yùn)創(chuàng)作山水詩,蔚然成風(fēng),也影響到駢文。吳均的《與朱元思書》:“風(fēng)煙俱凈,天山共色。……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岸高山,皆生寒樹,負(fù)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囀不窮,猿則百叫無絕。”真所謂洗凈俗埃,而生氣盎然。
鮑照則是另一幅筆墨。其《登大雷岸與妹書》描繪廬山“積云霞,雕錦縟。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彩,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里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yōu)轺焐保瑢㈥柟庀碌臒熢谱兓脤懙帽M態(tài)極妍,猶如一幅金綠山水,使人感受到作者的浪漫氣質(zhì)。南朝作者普遍具有強(qiáng)烈的山水自然意識,常常隨手點(diǎn)染,即成雋語。蕭綱送別友人,一開頭就說:“零雨送秋,輕寒迎節(jié)。江楓曉落,林葉初黃。”(《與蕭臨川書》)丘遲勸降叛將,欲動其鄉(xiāng)關(guān)之思:“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與陳伯之書》)都是寥寥數(shù)筆,而境界全出。
齊梁詠物詩發(fā)達(dá),駢文刻畫事物亦屬屢見。劉孝標(biāo)《送橘啟》:“采之風(fēng)味照座,劈之香霧噀人”,“脈不粘膚,食不留滓”,一字一句,精確不移。庾信《謝滕王賚馬啟》:“柳谷未開,翻逢紫燕;陵源猶遠(yuǎn),忽見桃花。”雖跡近游戲,卻也見其巧思,映帶成趣。宮體詩興,刻畫女性美麗與男女情事,影響亦及于駢文。何遜《為衡山侯與婦書》:“雖帳前微笑,涉想猶存;而幄里余香,從風(fēng)且歇。”伏知道《為王寬與婦義安主書》:“九重千日,詎想倡家;單枕一宵,便如蕩子。”寫夫妻離別,何等風(fēng)懷繾綣。
緣情抒懷
駢文之抒發(fā)情懷,這里舉徐陵、庾信為例。徐陵出使,適值侯景之亂,家國淪喪,憂心如焚,卻被北齊拘留,屢請歸而不獲,于是作書與齊尚書仆射楊愔,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其言云:“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自東南丑虜(指侯景),抄販饑民,臺署郎官,俱餒墻壁。況吾生離死別,多歷暄寒,孀室嬰兒,何可言念!……歲月如流,平生有幾?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yáng)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不自知其為生,不自知其為死也。”可謂字字血淚。
庾信經(jīng)歷與徐陵有相似之處。他奉梁元帝蕭繹之命出使西魏,而正值此時(shí),西魏攻破江陵,元帝被害。從此庾信留滯敵國,雖位望通顯,然而常有鄉(xiāng)關(guān)之思,亦不能不心懷愧恧。其心情之沉痛與復(fù)雜,當(dāng)有過于徐陵。乃作《哀江南賦》,也是文學(xué)史上有名的大篇。其序云:“傅夑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燕歌》遠(yuǎn)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日暮途遠(yuǎn),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fēng)蕭瑟。”泣血椎心,蒼涼無際。用典雖繁而得當(dāng),古典、今典融匯無間,大大加強(qiáng)了表現(xiàn)力。
論事說理
駢文束縛較多,似乎不適宜說理,其實(shí)不然。六朝作者擅長于此者甚多,陸機(jī)便是其中佼佼者,他的《辯亡論》《五等論》《演連珠》《豪士賦序》等都是論政的名作。它們未必具有多么深刻、獨(dú)創(chuàng)的政治見解,但從寫作藝術(shù)而言,在駢文史上具有頗高的地位。與陸機(jī)的詩賦一樣,這些論文力求說得盡,說得透,曲折達(dá)意。《豪士賦序》幾乎全篇偶句,但絕無堆砌之病,讀來但覺充實(shí)緊湊,音情頓挫,開合回旋而又氣勢貫通。《演連珠》意象豐富而新鮮,多以四字、六字相間隔,已是后世駢文的典型句式。
陸機(jī)之外,說理的名篇眾伙。僅《文選》所錄“史論”“論”便有七卷二十余篇之多,其中不乏膾炙人口者。還有不以“論”名而實(shí)際是論事說理的。如上面說到的徐陵《與齊尚書仆射楊遵彥書》,不但對于對方所持借口予以駁斥,更設(shè)想其不肯放歸的種種可能的緣故,一一解釋,非常周全詳密,不留一點(diǎn)罅隙,使對方無從辯駁。洋洋數(shù)千言,意緒紛繁,而出言必當(dāng)。“吾無從以躡屩,彼何路而齊鑣?……豈盧龍之徑,于彼新開;銅駝之街,于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于五丁;我路為難,如登于九折?”一連串的反問,犀利憤慨,全以對偶出之。其對偶以相反的兩面構(gòu)成,即劉勰所謂“理殊趣合”,“反對為優(yōu)”。“且夫?qū)m闈秘事,并若云霄;英俊訏謨,寧非帷幄。……朝廷之士,猶難參預(yù);羈旅之人,何階耳目?”這是說自己根本不可能知曉齊之機(jī)密,也運(yùn)用了反對。總之駢儷之體,在高手那里不會成為說理論事的束縛,而是可以曲折盡意,如心之使手。
當(dāng)然還必須提到劉勰的《文心雕龍》。全書五十篇,凡有關(guān)詩文寫作的種種,幾乎無所不談,用思精深而葩藻紛披,不但是文論史上的杰作,也是駢文史上的奇觀。嗣后初唐劉知幾的《史通》可與并肩,但既是論議史學(xué),故藻麗不比《文心雕龍》,也是言各有當(dāng)吧。
當(dāng)然,駢文并非萬能。描寫、抒情、議論皆可勝任愉快,唯有述事紀(jì)實(shí)一項(xiàng),駢文只能做概括性的、粗枝大葉的敘述,若要詳盡記錄各項(xiàng)細(xì)節(jié),實(shí)非其所能。其他且不論,即人名、地名、官職、制度、人物對話等,就難以如實(shí)納入簡短而整齊的句式之中。因此即使駢文鼎盛時(shí)期,史書仍不能不是散行文字。只有其中的序、論,可供作者在表現(xiàn)史識的同時(shí),運(yùn)用駢體,逞其翰藻。《文選》不錄史書中的紀(jì)傳篇章,卻選入班固、干寶、范曄、沈約的史論,其緣由就在于此。
今人覺得駢文難懂,原因之一是駢文作者,尤其是六朝作者,往往大量用典,即征引古書中的事實(shí)和語句。用典可以做到言簡意賅,含蘊(yùn)豐富,使文章耐人尋味,還可以讓文章顯得典雅內(nèi)斂。但若過于繁密生僻,便會造成閱讀困難。駢文文句齊整短促,不可能照引原書,而須加以剪截改造,若處理失當(dāng),就又添一重障礙。但是,駢文流行的時(shí)代漫長,從文學(xué)欣賞的角度說,其中精品甚多;從歷史研究的角度說,其中有重要的資料。因此,今天的讀者,若對于古代文史有興趣,是很應(yīng)該下一點(diǎn)功夫,擴(kuò)大眼界,讀一些駢文作品的,這也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楊明,復(fù)旦大學(xué)中國語言文學(xué)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