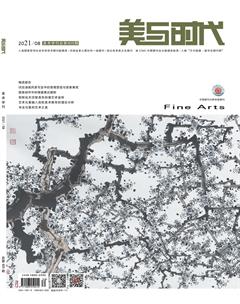余任天山水畫中的藝術情感
李向陽
摘 要:從余任天山水畫四個風格時期入手,分析其理智情感、道德情感和藝術情感。藝術情感是一種審美情感,主要指向于美;而理智情感和道德情感則分別指向于真和善。隨著藝術水平的提高、時代環境的變化、人生閱歷的增加,余任天山水畫中的理智情感、道德情感和藝術情感此消彼長,最終藝術情感占據了主要地位,作品藝術感染力得到增強。余任天晚年的藝術反映的是心靈的境界,投射了其藝術情感,一片山水就是一片心靈的境界,藝術本身就是人生之顯現,藝術作品體現的是審美境界,也是人生境界。
關鍵詞:余任天;山水畫;風格;藝術情感
余任天(1908—1984年),字天廬,浙江諸暨人,著名金石書畫篆刻家。曾任浙江省美協理事、浙江省文聯委員、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館員、杭州市政協委員、杭州市美協副主席、西泠印社社員、逸仙書畫社社長等。書法以隸、草見長,筆力蒼勁;國畫人物、山水、花鳥兼擅,而尤以山水見重于世;篆刻清剛、拙樸,自具一格;作詩不刻意求工,自舒性靈。著名書法家沙孟海譽之為“四絕壓群倫”的藝術家。
情感是藝術創作的一個原發性的觸點,“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白居易《與元九書》)可以說,藝術創作是以藝術家的審美情感為中心所展開的精神創造活動。美國哲學家、美學家蘇珊·朗格甚至認為:“所謂藝術品,說到底也就是情感的表現。”一個優秀的藝術家,總是善于把原始自然情感,通過內覺體驗轉化為藝術情感,并將之形式化,用自己獨特的藝術語言表現出來。原始自然的情感,人皆有之。但原始情感的喚起并不等于藝術情感的生成,只有轉換為藝術情感,并將之形式化(對象化),再通過藝術家獨特的、個性化的藝術語言創作出藝術作品,才能打動觀者之心,引起其情感的共鳴,進而體悟藝術作品的審美境界和藝術家的人生境界。這樣一個由“情”到“境”的創作、審美生成機制,復雜,隱秘甚至帶點神秘色彩。而這里的“情”也是經過藝術家沉思、醞釀、體悟(即再度體驗)得到了藝術升華,并使藝術家與欣賞者的心靈都處于享受狀態中的情感,這才是藝術情感。
在藝術作品中,不僅有藝術情感,還存在理智情感和道德情感。藝術情感是一種審美情感,主要指向于美;而理智情感和道德情感則分別指向于真和善。當然,藝術情感中也要真和善,但如果把真和善抬到優先的地位,那么由此產生的情感,就不是藝術情感,而是理智情感和道德情感了。
綜觀余任天一生的山水畫創作。依照畫風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研習傳統期(早年至1955年)、畫風初成期(1956年—1965年)、畫風突變期(1966年—1976年)、畫風成熟期(1977—1984年)。下面結合余任天四個時期的畫風來談談其山水畫中的藝術情感。
一、研習傳統期(早年至1955年)
余任天這一時期的作品,從現存的來看,整體風格面貌受馬遠、夏圭、八大山人、石濤、“四王”的影響較大,還處于臨摹、研習傳統階段。這些作品藝術情感相對較弱,而理智情感相對較強。究其原因,主要是從臨摹的范本到臨作,畫面上呈現的是間接的藝術情感,從某種程度上說,已屬于理智情感的范疇,并非余任天直接“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結果。毋庸諱言,就像大多數畫家一樣,在藝術生涯的初期,余任天還未形成自己的繪畫語言,也就是還處于對傳統筆墨的研習、摸索期,對藝術情感的轉換、升華缺乏有效的手段。這一時期他所創作的作品感染力較弱,很少有能打動欣賞者心靈、引起情感共鳴的佳作,對意境的傳達并不盡如人意。當然,在學習傳統的過程中,由于自身耿直、真率的氣質、性情所致,余任天繪畫形式語言中透露出多方折用筆、重骨氣剛健的意味,并不完全因襲前人之法。而浙東山水的陶養,使余任天對“師自然”的畫理也多有參悟,作品頗得自然之助,畫面構圖饒有山林野趣。
二、畫風初成期(1956年—1965年)
1956年,余任天參加浙江省文聯美術組,其身份便成了帶有官方性質的專業畫家。這意味著余任天的藝術從書齋(私人空間)走向展廳(公共空間),由自娛(審美功能為主)轉向娛眾(教育、宣傳功能強化)。從1956到1965年的十年間,余任天山水畫的題材、構圖、筆墨語言、審美取向都發生了極大的轉變,并初步形成個人比較成熟的畫風。在此期間,作為官方專業畫家,余任天多次參加了文聯、美協等組織的寫生活動,曾赴紹興、四明山、桐廬富春江、雁蕩山、新安江水電站等地寫生并收集創作素材。這一時期,他還創作了一批主題性作品,多次參加慶祝建國、建軍、建黨等主題的全國及省級展覽。1962年,他為北京人民大會堂浙江廳作巨幅山水畫《富春江嚴陵瀨釣臺》,與潘天壽所作《映日荷花別樣紅》相對懸掛。可以說,這一時期是余任天山水畫創作的第一個高峰期。政治待遇提高,生活條件改善,多次寫生采風,同道互相交流,極大地激發了余任天的創作熱情,使其開闊了視野,拓寬了題材,豐富了筆墨,初步形成個人比較成熟的畫風,聲譽鵲起。
這一時期余任天山水畫中的情感豐富飽滿,甚至激蕩。藝術情感、道德情感得到提升,互有交替,但畫面上道德情感的成分相對較強,而理智情感在這一時期,則經歷了一個從強到弱的變化過程。直接面對自然真山真水寫生,進而組織創作,表現現實生活,為工農兵服務,這對余任天是一個嶄新的挑戰。當時,山水畫創作中,傳統文人優游林下的閑情逸致已消失無蹤,畫面場景化、生活化的痕跡較重,傳統筆墨語言在表現場景、描繪新生事物時,也顯得有些捉襟見肘,畫作中藝術審美情感的成分被減弱,理智情感被努力強化,而道德情感的表達顯而易見地變成了中心思想,有些畫甚至已有些政治口號圖解的味道。難能可貴的是,余任天在這種時代氛圍中,仍不乏藝術審美情感為主,將道德情感、理智情感減弱并巧妙地通過藝術處理轉化為藝術情感,創作出了一批筆墨語言與意境傳達結合較好的佳作。
三、畫風突變期(1966年—1976年)
1966年,余任天的藝術進入了畫風突變期。畫風改變,對于余任天這樣一個已經形成自己日趨成熟的風格的年近花甲的畫家,是無奈的選擇。延續以前的畫風已不可能,而如何變是一個問題。經過探索,余任天找到了一條適合于當時境況的新路子——“草書入畫”。這是合乎情理的發展:一方面,繪畫是造型藝術,即使是傳統中國畫也講究“寫形傳神”。如他自己所說:“作畫追求形質,隨形質而下筆用墨。”而因視力關系,再延續1966年以前畫風去寫形、構圖已不可能,對“形”“質”的弱化,已成必然。脫略形跡、以意為之,成為其自然而然的選擇。而這也是中國山水畫的高層次的追求,即所謂“得意忘形”“境生象外”。另一方面,書法各種書體中草書的筆筆相連、筆筆相生,因筆生勢、氣隨勢轉的特性最強。草書筆與筆的連貫性,使得余任天能借助于“手”而不是“眼睛”來完成對繪畫的最低限度的“形”的要求,哪怕是被弱化的“意象化的形”。“草書入畫”便成了一個順理成章的選擇:既解決了一個近盲畫家“如何畫”的難題,同時也是余任天率真、不事雕琢的性情的自然流露。
“以書入畫”是中國傳統繪畫理論中“書畫同源”的題中之意,“草書入畫”亦代不乏人。明代陳白陽、徐青藤以草書畫花鳥,清代黃癭瓢以草書畫人物,但以草書畫山水且有成就者不多,余任天是其中的佼佼者。“草書入畫”牽涉書法藝術語言向繪畫藝術語言的轉化,這一高難度動作的完成,無疑得益于余任天書畫兼擅的優勢及對書畫兩種藝術本體語言的深層次理解。
四、畫風成熟期(1977—1984年)
“畫什么”這是一種選擇,一種基于審美取向、審美思想的選擇,一種涉及繪畫中情感表現的選擇。余任天晚年,政治環境趨向寬松,社會地位日漸提高,生活安定從容。山水還是這片山水,但,心境變了。藝術審美情感重新在畫中居于主體,基于政治性因素的道德情感和追求表面物象、形質的理智情感明顯被減少與弱化,余任天的山水畫重新回歸藝術的本體,使得筆墨本身的美感被凸顯,重新回到“澄懷觀道”“神與物游”的自舒性靈。年過花甲的“盲畫家”詩心大發,創作了大量的詩意畫,如《寫杜少陵詩意》《寫賈島詩意》《寫元遺山詩意》等等。這以后,余任天的山水畫開始“山色模糊”“墨華蕩漾”“筆墨荒疏”“意在鴻蒙”,“老來筆墨全無法,半似草書半是詩”“新詩對畫成”“春風似我閑”。
在中國古代的文藝理論中,“意境”和“境界”是兩個經常出現的概念。它們被用來描繪和形容藝術創造的美學追求,用來評價藝術作品所具有的審美品質,喻指藝術作品所敞開的精神世界和生命意趣。有時兩者可以等同,但顯然它們又不完全一致。宗白華認為:“以宇宙人生的具體為對象,賞玩它的色相、秩序、節奏、和諧,借以窺見自我的最深心靈的反映;化實景而為虛境,創形象以為象征,使人類最高的心靈具體化、肉身化,這就是‘藝術境界。藝術境界主于美。”這里的“藝術境界”也就是“意境”。而境界是一個人的生命整體風貌,在其人生態度、人生取向等方面體現出來。審美活動與人生最是相關,人格境界與審美境界密不可分。余任天晚年的藝術反映的是心靈的境界,投射了其藝術情感,一片山水就是一片心靈的境界,藝術本身就是人生之顯現,藝術作品體現的是審美境界(即意境),也是人生境界。
參考文獻:
[1]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第二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朗格.藝術問題[M].滕守堯,譯.南京:南京出版社.2005.
[3]余勝,余成.藝術大師之路:余任天[M].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5.
[4]宗白華.意境[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作者單位:
浙江美術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