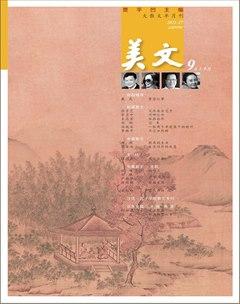文藝
胡松濤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報告中講到了延安文藝界的巨大變化:從“很多文化人總是和工農兵搞不到一起”“躲飛機也不走一條路”“老百姓見了他們是敬鬼神而遠之”,到“現在在一起扭秧歌了”“打成一片”了。一派喜悅之情。
經過《講話》指引和整風鍛煉的文藝隊伍服從、服務于革命,成為一支“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隊伍。
中共手里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拿槍桿子的隊伍,一支是以筆墨為刀槍的文藝隊伍。國民黨的蔣介石建立起一支“黨軍”——還不那么具有戰斗力;蔣介石從來沒有掌握文藝隊伍,正如陳荒煤1946年6月《關于文藝工作若干問題的商榷》中所說:“國民黨反動派也有文藝……它只是服務于少數統治者的,與人民無關,所以力量不大,成不了什么軍。”蔣介石與毛澤東的較量,從一開始就輸掉一大半。
毛澤東武功文治,文武并重,一手排兵布陣,一手錦繡文章。高度重視文藝“軍隊”,發揮革命文藝的作用,是毛澤東的一大文化創新,是中國共產黨文化的高明之處。“很少有政治家、領導人像革命的政治家、革命政權的領導人這樣重視思想、理論、意識形態直到文學藝術唱歌演戲的。”曾任共和國文化部長的王蒙如是說。
見證延安文藝革命的蕭軍說:“子孫們向我們發問,日本鬼子是怎樣被打敗的?中華民族怎么艱難地從屈辱中跋涉過來?我們可以毫無愧色地告訴他們:請讀一讀延安文藝!”
毛澤東籌備文藝座談會
“戲劇系裝瘋賣傻,音樂系呼爹喊媽,美術系不知畫啥,文學系寫的啥,一滿解不下。”老百姓編了這個順口溜諷刺魯迅藝術學員的“洋包子”。“一滿解不下”是陜北話,意思是不知道說的啥,一點都聽不懂。文藝作品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打轉轉,不為群眾所待見,魯藝是一個縮影。
“延安文藝界表面上似乎是天下太平的,但彼此在背地里,朋友間,卻常常像村姑似的互相誹謗,互相攻擊;各自為是,刻骨相輕。顯然的,這里存在著許多待解決的問題,如對文學理論的見解、作品的看法,以及作家之間正常的關系,等等。”《解放日報》1942年3月12日上發表奚如的《一點意見》中指出了延安文藝界的問題。
1942年春天,《解放日報》發表了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節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 尊重作家》,羅烽的《還是雜文時代》等,還有“輕騎兵”墻報上發表的一些文章,聲音有些異樣。
知識分子如何同新的生活、同工農兵打成一片?知識分子如何成為革命知識分子?這引起毛澤東的思考。他對詩人蕭三說:“如果瞿秋白還在,由他領導文藝工作就好了。”
“邊區的經濟問題我們整頓得差不多了,現在可以騰出手來解決文藝問題了。”毛澤東對劉白羽說。畢竟,“任何階級都要用這樣的一批文化人來做事情,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都是一樣,要有為他們使用的知識分子。”毛澤東目光如炬,深謀遠慮,他開始為新的政權培育文化人了。
“毛主席請你去。”西北局宣傳部部長李卓然好不容易找到延安青年藝術劇院院長塞克,他對塞克說。塞克手里不停地揮舞著拐杖,說:“不去。”“為什么?”塞克把披肩的長發往后一甩說:“有拿槍站崗的地方我不去。”
在延安文藝整風前夕,毛澤東要做些調查研究,聽聽文人們在想些什么,關注些什么,他就想到了著名的塞克。塞克原名陳秉鈞,曾用名陳凝秋,“塞克”是“布爾塞維克”之縮寫。他創作有《流民三千萬》《鐵流》等抗日劇目,是抗戰文藝的開山之作。塞克1938年到延安,他和冼星海、蕭軍、馬達被稱為延安文化界“四大怪”。他的“怪”在于留一頭延安革命女性都很少見的長發,經常叼個大煙斗,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副名士派頭。
李卓然請不動塞克,只好如實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笑起來:“好,塞克來的時候,一路撤崗!”毛主席的這個決定遭到衛士們的反對。毛澤東給警衛人員做工作說:“我的朋友來看我,你們不能擋駕。這位朋友脾氣可大啦,你一擋駕他就回去了,那你們可吃罪不起呀!”
毛澤東給足塞克面子,撤掉了崗哨。那天,毛澤東與塞克談古論今,談了四五個小時,吃飯的時候特意燉了只雞招待他。塞克回來對人說,主席掰了一只雞腿給他吃。在延安吃一只雞腿是很驕傲的事情,況且是毛澤東掰給他吃的。
毛澤東找了幾十位文藝界人士談話談心,調查和交流文藝問題。邊區有三大文藝組織,一個是魯迅藝術學院,人稱“魯藝派”,代表人物是周揚;一個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簡稱“文抗派”,就是以丁玲為首,包括蕭軍、舒群、艾青、羅烽等;還有一個是邊區文協,著名詩人柯仲平是主任。毛澤東個別談話、集體談話,還讓一些同志幫助搜集材料,提供有關文藝的意見。
4月27日,一張張粉紅色的請柬從昆侖收發室發出。“昆侖”是中共中央辦公廳收發室的代稱。請柬64開大小,豎排,油印,封面上寫著“謹希蒞會”,打開請柬,是毛澤東與凱豐聯署的請柬:“為著交換對于目前文藝運動各方面問題的意見起見,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時半在楊家嶺辦公廳樓下會議室內開座談會,敬希屆時出席為盼。”
這個請柬很快送達到一百多位作家和藝術家手里。
第一次座談會·引言
延安的五月,山野間盛開著大片藍色的馬蘭花,還夾雜著黃色的野薔薇、白色的杜梨花、淺粉色的杏花,那火紅的山丹丹奪人耳目,老遠就把人的目光拉了過去。
5月2日是個艷陽天。毛澤東來到楊家嶺中央辦公廳的辦公樓——俗稱“飛機樓”。走進會場,舉目一看,濟濟一堂,延安文化界的著名人物幾乎都到了。他與大家一一握手寒暄。
中宣部代部長凱豐主持會議,他說:“座談會現在開始,首先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毛主席給大家講話。”
毛澤東用他那特有的柔綿細長、抑揚頓挫的湖南腔,開宗明義地說道:“同志們!今天邀集大家來開座談會,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換意見,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系,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借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接著,毛澤東風趣地說:“我們有兩支隊伍,一支是朱(德)總司令的,一支是魯(迅)總司令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毛澤東站著講話,與會者注意到,他褪色的灰布褲子的兩個膝關節處,補了兩方塊顏色鮮明的藍色補丁,單薄的棉襖肘彎處也露出白色的棉絮。毛澤東侃侃而談,講了文藝家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作品服務的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并且現身說法:
在這里,我可以說一說我自己感情變化的經驗。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干凈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臟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干凈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為是臟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凈了,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毛澤東從自我的心理轉變入手,使用“衣服”“牛糞”等形象化的“符號”,用文學化的表達方法開始了自己的講話。
毛澤東講話中間,遠處隱隱傳來隆隆的炮聲。有人給毛澤東傳來小紙條,上面寫著:聽到炮聲,會議是否暫停?毛澤東說:“大家不要擔心,炮聲離我們還遠著呢。前方有聯防軍在保護著我們,所以呀,我奉勸大家兩點,一是母雞不要殺了,留著下蛋;二是娃娃不要送給老鄉,還是自己撫養好。如果前方抵抗不住,我還可以帶你們鉆山溝嘛。”大家笑起來。前一陣子傳說胡宗南的軍隊要進攻延安,有人趕緊把家里養的母雞殺掉吃了,有的為了轉移方便,聯系老鄉準備把孩子送出去。
毛澤東講話之后,大家自由發言。毛澤東提議說:“蕭軍同志,你來談一談嘛。”丁玲坐在毛澤東身邊,她捅了捅蕭軍說:“蕭軍是學炮兵的,你先打頭炮吧。”
蕭軍是個爽快率真之人,又不在黨,他站起來毫不客氣地說:“……紅蓮、白藕、綠葉是一家;儒家、道家、釋家也是一家;黨內人士、非黨人士、進步人士是一家;政治、軍事、文藝也是一家。雖說是一家,但他們的輩分是平等的,誰也不能領導誰。……我們革命,就要像魯迅先生一樣,將舊世界砸得粉碎,絕不寫歌功頌德的文章。像今天這樣的會,我就可以寫出十萬字來。我非常欣賞羅曼·羅蘭的新英雄主義。我要做中國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蕭軍的發言有些跑題走調。毛澤東兩耳低垂,微笑著做記錄。他看見蕭軍把一缸子水喝完了,馬上讓人去外邊給他打水,蕭軍也不客氣,潤潤嗓子接著講。蕭軍發言的題目是《對當前文藝諸問題的我見》。蕭軍是魯迅的弟子,以《八月的鄉村》聞名,他與毛澤東交往頗密,是毛澤東的座上客。他文氣逼人,桀驁不馴,發言中多有鋒芒畢露之處。他說:“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獨立的,魯迅在廣州就不受哪一個黨哪一個組織的指揮。”
“我要發言!”蕭軍的話音剛落,坐在蕭軍旁邊的胡喬木大叫一聲站了起來。胡喬木是毛澤東的秘書。他反駁蕭軍說:“文藝界需要組織,魯迅當時沒受到組織的領導是不足,不是他的光榮。歸根到底,是黨要不要領導文藝,能不能領導文藝的問題。”
蕭軍毫不示弱,馬上回擊胡喬木。接下來的發言中,有人同意蕭軍的意見,有人不同意蕭軍的意見。毛澤東一直微笑地聽著。何其芳、李伯釗、徐特立、李又然、杜矢甲、艾青等各抒己見,暢談對當前文藝的看法,其中不乏一些“過激”言辭。
毛澤東是一個優秀的傾聽者,他不時微笑,時而抬頭注視發言者,更多的時候埋頭做記錄。這天會議的最后,毛澤東說:“同志們有什么意見,下次會議大家可以說,還可以寫信給我。”毛澤東總是有他的原則與立場的。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叫胡喬木到他家里吃飯,他對胡喬木說:“祝賀開展了斗爭。”
第二次座談會·傾聽
5月16日,延安文藝座談會舉行第二次會議。
晴天白日,延水湯湯。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自始至終參加會議。毛澤東邊聽邊拿著鉛筆做筆記,偶爾插言,沒有正式講話。
丁玲為自己發表《三八節有感》作了檢討性的發言。她說,自己雖然參加革命時間不短了,可從世界觀上看,還應該脫胎換骨地改造。
“民眾劇團”的負責人柯仲平是延安的知名人物。他長方臉,留一大把胡子——其實他才40歲,毛澤東稱之為“美髯公”。他站起來發言,介紹“民眾劇團”堅持走通俗化道路,在邊區巡回演出大受歡迎的情形。他說:“這兩年在演大戲的過程中,好些人把給老百姓看的小戲給忘了,我們民眾劇團就是演《小放牛》。你們瞧不起《小放牛》嗎?老百姓卻很喜歡。劇團離開村莊時,群眾都戀戀不舍地把我們送得好遠,并送給我們很多慰問品。你們要在哪些地方找到我們劇團?怎么找呢?你們只要順著雞蛋殼、花生殼、水果皮、紅棗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我們……”
大家笑起來。毛澤東高興地說:“你們吃了群眾慰問的雞蛋,就要更好地為群眾服務,要拿出更好的節目來為群眾演出,不要驕傲自滿。你們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沒有雞蛋吃了。”
接下來是歐陽山尊發言。他前兩天給毛澤東寫過一封信,信中說:前方非常需要文藝工作者,希望延安的專家、藝術家、文學家能夠到前方,為部隊、為老百姓服務。毛澤東馬上給他回信說“他的意見是對的”。受到毛澤東回信的鼓舞,歐陽山尊站起來發言。他說:“戰士和老百姓對于文藝工作者的要求是很多的,他們要你唱歌,要你演戲,要你畫漫畫,要你寫文章,并且還要求你教會他們干這些。不能說你是一個作家就拒絕給他們唱歌,也不能說你是演員就不給他們布置‘救亡室(即俱樂部)。他們需要什么你就應該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毫無保留地獻出來。……初看起來似乎你付出去的很多,但事實上,你從他們身上收到的、學習到的東西更多。”
蕭軍仍是焦點人物。談到作家立場和暴露與歌頌等問題,蕭軍認為,“在光明里反倒常常看不到光明”。吳黎平和艾思奇當場與他爭論起來。
毛澤東兩耳低垂,微笑傾聽。
胡喬木上次會議上的表現得到毛澤東的表揚,他越戰越勇,再一次站起來反駁蕭軍:“我們黨提出整風是因為我們堅信自己的事業的正確性,所以才能夠進行這種嚴格認真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我們這么做并不是從現在提出整風才開始,而是從建黨的那一天起就這樣做的。我們歡迎各種善意的批評,但也不懼怕任何惡意的中傷和歪曲。”
中宣部工作的吳亮平也駁斥蕭軍的觀點。魯藝戲劇系主任張庚說:“我不贊成主席的有些意見,提高是非常必要的,我們的共產黨的文化運動搞了那么多年,難道不是提高嗎?我主張普及與提高來個分工,像文工團、演出隊,去做普及工作;像魯藝這樣的學府,能不能主要去做提高的工作呢?”
中央研究院文藝室主任歐陽山站起來發言,他從“什么是文學藝術”的定義講起,拉開架勢講起了文學基本知識。大家都有些忍耐不住了。蕭軍憤怒地說:“發言人要尊重規定時間、聽者的精力;不要到這里來講起碼的文學課、背書,引證名人警句。要抓住題目做文章。”
新四軍文藝干部吳奚如發言說:“搞文學的都要有個立場,現在不是抗日嗎?能不能提出黨員和非黨員作家都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而中共黨員不必要時刻都將自己的無產階級立場和黨的立場掛在門面上,這樣會不會更有利于統一戰線?我們最大的敵人是日本侵略者,我們革命文學的立場應當是一切有利于抗日,國共摩擦,同室操戈,只能是讓親者痛,仇者快。”
吳奚如剛從“皖南事變”中突圍,回到延安。朱總司令聽了他的話,站起來直接批評說:“吳奚如,你是人民軍隊的一名老戰士,居然講出這樣的話來,你完全喪失了無產階級的立場!”
囂囂然,紛紛然。這一天的座談會,論點龐雜,氣氛活潑,爭論聲不斷,笑聲掌聲不斷。
第三次座談會·結論
5月23日,第三次會議,也是座談會的最后一次大會。
座談會馬上就要開始,“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匆匆趕來,大家連忙給他讓座。徐老嘴里說著“別別”,一屁股坐在一米多高的窗臺上,然后從兜子里掏出一個本子,又拿出一支鉛筆,在舌頭上蘸濕筆尖,埋頭記錄起來……
何其芳、蕭三發言之后,蕭軍又一次發言,胡喬木又一次站起來批駁蕭軍的觀點。毛澤東微笑傾聽。艾青發言,陳云發言……因為發言的人多,毛澤東的講話推遲到晚飯之后。
延安的日頭下山早,攝影師吳印咸有些著急。會場小,與會人員多,室內光線不好,這么重要的會議,不留下影像紀錄將非常遺憾。他看到禮堂外有一塊很大的空地,就向毛主席提出到禮堂外拍攝照片的要求。毛澤東建議:拍一張集體合影。
太陽快落山了,天上散布著幾朵彩云。走到禮堂門口,毛澤東自己先坐下來,大家很快圍上來站好坐定。正要拍攝時,丁玲走過來,毛主席說:“丁玲同志你過來了,你離我坐得近一點,不然的話,你明年又要寫《三八節有感》了,又要發牢騷了。”在大家的笑聲里,丁玲坐在毛澤東的右邊。吳印咸正要拍攝,一條小狗闖進鏡頭。毛澤東說:“康生,管好你的狗。”康生是社會部部長,社會部的任務是反特務、抓“走狗”。大家笑著把小狗轟了出去。吳印咸正按快門,劉白羽的大塊頭把馬扎坐塌了,弄出來的動靜很大,毛澤東跟大家一樣,聽見動靜都轉過頭去看。吳印咸只好重拍一張。一幅珍貴的歷史照片誕生了。
拍照之后,毛澤東請朱德總司令講話。朱德針對前兩次會上出現的一些思想觀點和情緒,不點名地批評說:“大會第一天有人發言,他不但要做中國第一作家,而且要做全世界第一作家。又說魯迅一直是革命的,并沒有什么轉變。還說,我從來不寫歌功頌德的文章。以我看,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農兵。中國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封,都要由工農兵批準。”
第二次會議時,蕭軍和歐陽山、何其芳、周揚等就魯迅所走的道路是“轉變”還是“發展”問題,發生爭論。蕭軍認為魯迅是“發展”而不是“轉變”。朱德在講話中毫不含糊地說:“不要怕說轉變思想立場,豈但要轉變,而且是投降。我是一個從舊軍人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產黨的。我認為共產黨好,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我到上海找黨,沒有解決參加黨的問題,后來到法國,才入了黨。我投降無產階級,并不是想來當總司令。后來打仗多了,為無產階級做事久了,大家看我干得還可以,才推我當總司令。……共產黨、八路軍有功有德,為什么不該歌、不該頌呢?”朱老總的發言深入淺出、生動有力,受到藝術家們的歡迎。
晚飯時分,暮色蒼茫。毛澤東坐在窯洞前的石桌旁修改他的講話提綱。
西北高原的夜空,星光燦爛。一些沒有受邀參加座談會的人聽說毛澤東晚上要講話,也來到楊家嶺旁聽。由于參會人員增加,會議改在中央辦公廳小樓外的院子里開。工作人員用三根木棍架起支架,懸掛起汽燈。畫家羅工柳坐在毛澤東講話的小桌子邊,他聽到毛澤東拿著提綱時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哎呀,這個文章難做啊。”
汽燈放出銀白色的光,一群小蟲子圍繞燈光飛舞。毛澤東站起來,手拿一疊毛筆書寫的提綱,用他那柔綿細長的湖南腔抑揚頓挫地講話:“同志們,座談會開了三次,開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添幾把交椅,請你們來坐。我對文藝是小學生,是門外漢,向同志們學習了很多。前兩次是我出題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題目,要我做文章。我就答一下,看能不能及格?我答卷的題目就叫‘結論。朱總司令講得很好,他已經做了結論。中央的意見是一致的,有些問題我再講一點……”
毛澤東態度謙和,侃侃而談,給人的感覺是很風趣,既不指名道姓地批評誰,也不糾纏于任何具體事件,而是圍繞文藝問題,著重于從理論上加以闡明。他具體講了“文藝是為什么人的”“如何去服務”“文藝界統一戰線”“文藝批評”和作風等五個方面的問題。
蕭軍在當天的日記中評價說:“夜間毛澤東做結論……這是一個值得喜歡的結論。”
《講話》別裁
毛澤東的《講話》,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既是政治家講文藝,又是文藝家講政治,政治觀中有文藝觀,文藝觀中帶政治觀,正可謂金甌一片,革命文化卓然呈現。文學事關“亡黨亡國”——這話別的政治家沒說過,文藝家更沒想到,只有毛澤東把文學提高到事關興亡的高度。《講話》規定了文藝標準,傳達了毛澤東把“筆桿子”與“槍桿子”相結合的奇妙思路,奠定了革命文化秩序。《講話》是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的重要范文,它構成中國共產黨文化最具特色之一部分。
毛澤東對他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十分在意。講完之后,仍在不停地修改,直到一年后的1943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七周年紀念日,才在《解放日報》全文發表。
——體與用。《講話》之“體”,是列寧1905年寫作的《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毛澤東讓博古把這篇文章重新翻譯出來,刊發在5月14日《解放日報》上。在這篇文章中,列寧提出“黨的文學”的概念,指出“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毛澤東《講話》中關于文學的階級論、文學為政治服務、文學的黨性原則等關鍵性立論,基本上源自列寧的《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同時,《講話》創新了列寧的文藝觀,把列寧的原則具體化了,具有強烈的本土化取向。《講話》中提出許多具體做法,屬于“用”的層面。
——經與權。郭沫若評價《講話》“有經有權”。這話傳到毛澤東耳朵里,他覺得找到了知音,高興地說:“這道理是對的。” “經”是必須堅守的道理,“權”是權宜之計;“經”是法門,“權”是方便法門。《講話》中哪些是“經”?哪些是權宜之策?“文藝為工農兵服務”,這是毛澤東《講話》提出和回答的問題,是《講話》的核心觀點,屬于“經”的部分。胡喬木說:“《講話》主要有這樣兩個基本點:一是文藝與生活的關系,二是文藝與人民的關系,在這兩個基本點上,《講話》的原則是不可動搖的。” 這應該屬于“經”的部分。毛澤東在“普及與提高”中強調普及,褒“下里巴人”而貶“陽春白雪”,屬于“權”的部分。畢竟群眾文藝是整個文藝中比較粗糙的部分,不屬于精華部分,但在炮火連天、風緊云急的形勢下,在以農民為主的欣賞群體的環境中,遷就民眾的趣味以求普及,使得文藝發揮“群”的作用,文藝才能“有用”。這不是挫高就低,不是對藝術美的反動和否定,是時勢使然。按照毛澤東《講話》指引而創作的《白毛女》,從鄉民之口,經文人之手,成為舞臺上的經典,經歷的是由土到洋、由俗到雅的提高過程。《講話》中的一些觀點不是從文藝審美出發,而是從當時的軍事、政治斗爭要求出發來講的,這都屬于“權”的內容。
——政治性與藝術性。毛澤東強調政治標準優先。“任何階級社會中的任何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政治”這個概念,其含義伸縮性很大,既可以理解為某一歷史階段的戰略任務,也可以是某個階段具體的政治任務。毛澤東強調文藝為政治服務,主要是為工農兵服務。毛澤東說:“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
——文藝與黨的文藝。毛澤東期望黨與文藝之間的關系達到一種新的可能性。他說:“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如同列寧所說,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把文藝當作革命的一部分,強調文藝的政治功能,實現黨對文學、文藝的領導,強調這是“文學的黨性原則”。“黨的文藝”的提出,終結了中國兩千多年來行政權力與文化權力相分離的傳統。
——文藝家藝術家與文藝工作者。《講話》一上來就把“文藝”稱為“文藝工作”,把藝術家、文藝家、作家等稱為“文藝工作者”。這是一種位置的調整。文藝工作者必須調整角色,放下架子,做好“孺子牛”,當好革命的“齒輪與螺絲釘”。參加文藝座談會的林默涵體會說:“藝術家要打碎‘藝術高于一切的觀點,到實際工作中去,并且是以一個工作者的身份真正參加實際工作。”
——歌頌與暴露。《講話》中“引言”部分和“結論”部分都講到了歌頌與暴露的問題,這是文學的一個基本問題,也是革命文藝隊伍中產生爭論的問題。毛澤東在《講話》中說:“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必須歌頌之,這就是革命文藝家的基本任務。”“歌頌呢,還是暴露呢?這就是態度問題。”“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還有毛澤東對民間文藝、民族形式的倡導,強調本土意識,將民族形式引入文化領域……
延安文藝座談后之后,“工農兵”“ 大眾化”“孺子牛”“螺絲釘”“牛糞”“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并沒有完全入黨”……這些剛剛誕生的新詞跟新句子,猛烈地撞擊著每一個文藝工作者的靈魂。作家嚴文井參加了文藝座談后,說:“我覺得原來那一套不行了,得跟著毛主席走。”延安文藝即將脫胎換骨,詩人興會更無前……
革命新歌劇《白毛女》
《白毛女》的故事,是魯藝人從流傳在晉察冀邊區一帶“白毛仙姑”的民間故事傳說中“化”來的。最早的傳說是:在一個山洞里,住著一個渾身長滿白毛的仙姑,法力無邊,懲惡揚善,主宰人間禍福。
晉察冀邊區河北西北部也流傳著“白毛仙姑”的故事:某山村經常出現一個夜間顯身的一身白的仙姑,村民白天供在廟里的供品,到了晚上就會被她取走。區干部聽說了這個奇聞,決定會會這位“仙姑”,于是悄悄地帶了幾個民兵藏在山廟周圍。夜半之后,一個白影閃身進廟。區干部喝問,白影子轉身向他撲來,區干部開槍,那個白影子負傷逃跑。區干部帶著民兵尾隨追至一個山洞,發現那個白影子蜷身護著一個孩子。在干部的喝問下,一頭白發的“仙姑”失聲痛哭,講述了自己的身世。她17歲時,父親被逼債而死,她以身抵債到了債主家,被強奸懷孕,債主不想娶她,還圖謀加害。她逃進山里,靠吃廟中的供品維生和養活孩子。區干部和民兵把母女從山洞里解救出來,讓她重新過上“人”的生活。
蕭軍1943年6月12日在一個故事會上聽到過類似故事,簡要記在當天的日記中:“白毛婦人,是一個被逐的懷孕妾,藏于草內,每夜以取廟里供品為生,后借自己是菩薩,被一偵察兵識破……”
最初,作家邵子南想用這個故事寫一劇本,主題是發動群眾,破除迷信。他將這個打算告訴周揚,周揚一聽,來了興趣,他感到僅僅以破除迷信為主題太低了。幾經提煉,最后確定這個劇本應當表現兩個不同社會的對照,揭示出“舊社會把人逼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鮮明時代主題。邵子南寫了幾場腳本,因為不好,就退出了創作。后來委派王濱組織《白毛女》的集體創作。在創作中,王濱是主講者,他的主意很多,每場戲都是他構思,搭出架子,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往里面加戲。從文學系借來的20來歲的尖子學生賀敬之先是筆錄,然后根據大家的意見進行再創作。寫到最后一場斗爭會時,賀敬之說他這方面沒有生活經驗,于是推薦丁一(丁毅)來寫斗爭會的歌詞。劇組采取“流水作業”的形式,一邊寫劇本,一邊由張魯、瞿維、馬可、向隅等人譜曲,一邊由王大化導演排練。
民族新歌劇《白毛女》經過反復修改,反復排練,作為向七大的獻禮作品,1945年6月在黨校禮堂給中央領導和七大代表正式演出。
《白毛女》引起了轟動。這部新歌劇通過對民間傳說的一番“改造”,對迷信中神鬼的一番“重塑”,對人物故事的一番“革命化”,直抵革命經典。從秧歌運動、《白毛女》開始,文藝工作者逐漸嫻習文藝武器的理論與實踐。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風,新的文化,似繁花笑滿春山……紀念碑一般的作品誕生了。
延安文藝座談會還“催熟”了一種新的文藝創作方式:集體創作。
文學創作通常是一種個體化的行為,革命者把它“集體化”“革命化”了。中央黨校編排的《逼上梁山》、平劇研究院編排的《三打祝家莊》、魯藝編排的歌劇《白毛女》,還有深受群眾喜愛的秧歌劇《兄妹開荒》等都是采取領導、內行和群眾三結合的辦法編演出來的,領導出題目,群眾出生活,專家出技巧。集體創作的關鍵,在于眾人參與,集中大家的智慧,各顯身手;在于在思想的碰撞中產生火花和靈感。這是一種革命思維和新的世界觀在文藝創作上的投射。這是一種與個人創作不同的全新的文藝生產方式。
新傳統:工農兵文藝
革命文藝的大門打開了。毛澤東伸手一指,指向工農兵。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
文藝,曾經為宗教服務、為宮廷服務、為士大夫服務、為有錢人服務、為自己服務、為藝術而藝術。毛澤東鮮明地提出“為工農兵服務”。對于大多數從事文藝的人來說,“工農兵”是很抽象的,毛澤東就這么鮮明地把具體的“工農兵”推到大家面前。
《八路軍大合唱》的詞作者公木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后說:“經過座談會,‘工農兵頓然成了一個熟語,‘兵字綴于‘工農后面,構成一個復合詞,這是以往所不曾聽見過的。”
呼喚“韓荊州”的詩人艾青,在文藝座談會后說:“我第一次聽到了為工農兵的論點。”
美術家王朝聞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他說:“我在上海畫畫的時候,只曉得為革命,不曉得為工農兵,我是想一個空頭的革命,不曉得具體的工農兵,從這一點上,我的腦子打開了。”
參加文藝座談會和“棗園之宴”的作家舒群說:“在文藝座談會以后,我們才認識到另一個道理,到底什么叫作‘面向工農兵。”“當我們從‘亭子間來到工農兵群眾中間,面臨新的人物新的事件的時候,真好像從另一個星球掉在地球上來似的。”
以《兄妹開荒》《擁軍花鼓》聞名的李波說:“‘面向工農兵這個口號,當時在我們腦子里特別新鮮,我們把這幾個字寫在自己的筆記本上,作為座右銘。”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文藝工作者的心里逐漸地、真正地有了工農兵的地位。工農兵的形象成為小說、舞臺、詩歌、繪畫中的主角——一改從前文藝作品中多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花花草草的傳統局面。民歌、秧歌、剪紙等向來都是野蠻生長,自生自滅,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間藝術前所未有地上升到國家藝術的高度。中國歷史上許多從來不入詩入歌入畫、不能上舞臺的人和事,被文藝家納入視野,寫進作品。前人裝不進去的東西,被新時代裝進去了。
中華文化在歷史中沉淀出來的傳統是儒釋道,共產黨和毛澤東創造了一個新傳統:工農兵。
(作者有刪節。注釋略。)
(責任編輯:孫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