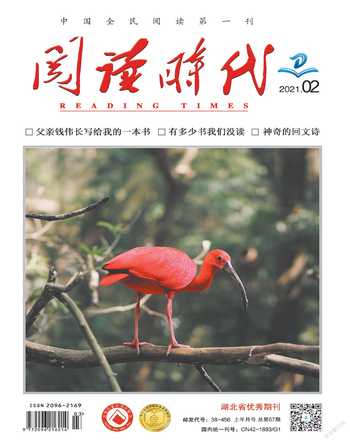燈籠、鑼、煙花:一位中國文人的春節記憶
林語堂

中國陰歷新年,是中國人一年中最大的佳節,其他節日,似乎均少節期的意味。五日內全國均穿好的衣服,停止營業,閑逛,打鑼,放鞭炮,拜客,看戲。那是個黃道吉日,每人都盼望有一個更好更榮華富貴的新年,每人都樂于增多一歲,而且還準備了許多吉利話向他鄰居祝賀。
不能在元旦責罵女傭,最奇怪的是,中國勞苦女人也清閑了,嚼著瓜子,不洗衣,不燒飯,甚至拿一把菜刀都不肯。這種懶惰的辯論是元旦切肉就會切掉運氣,洗什么東西就會洗掉運氣,把水倒掉就會倒掉運氣。紅色春聯貼滿在每家門上,寫著:好運、快樂、和平、富貴、青春。因為這是個大地回春,生命、發達、富貴復歸的節日。
街頭屋前,到處是爆竹聲,充塞著硫磺味。父親失了他們的威嚴,祖父更比以前和藹,孩子們吹口笛,戴假面具,玩泥娃娃。鄉下姑娘穿紅戴綠,跑三四里路到鄰村去看草臺戲。村上的紈绔少年,恣意地賣弄他們的風情。那天是女人的解放日,洗衣燒飯的苦工解放日,有人餓了,就煎年糕來吃,或用現成的材料下一碗面,或到廚房里偷兩塊冷雞肉。
頑固的陰歷新年
中國政府早已正式廢除陰歷新年,但陰歷新年依然故我,不曾被廢除掉。
我是個極端摩登的人。沒有人可以說我守舊。我不懂遵守舊歷,而且還喜歡倡行十三個月的年歷,每月只有四個星期或二十八天。換句話說,我的觀點很科學化,很邏輯化。就是這點科學的驕傲,使我在過新年時大失所望。每人都假裝著慶祝,一點沒有真感情。
我并不要舊歷新年,但舊歷新年自己來了。那天是陽歷二月四號。
科學的理智教我不要遵守舊歷,我也答應照辦。舊歷新年來到的聲音在一月初已經聽到了,有一天我早餐吃的是臘八粥,使我立刻記起那是陰歷十二月初八。一星期后,我的傭人來借額外的月薪,那是他舊歷除夕所應得的。他下午息工出去的時候,還給我看他送給妻子的一包新衣料。二月一號、二號,我得送小費給郵差、運貨車夫、書店信差等等。我常覺得有什么東西快來了。
到二月三號,我還對自己說:“我不過舊歷新年。”那天早晨,我太太要我換襯衣,“為什么?”
“周媽今天洗你的襯衣。明天不洗,后天不洗,大后天也不洗。”要近乎人情,我當然不能拒絕。
這是我屈服的開始。早餐后,我家人要到銀行去,因為雖然政府命令廢除舊歷新年,銀行在年底照樣有一種微小的提款恐慌。“語堂”,我的太太說,“我們要叫部汽車。你也可以順便去理一理頭發。”理發我可不在意,汽車倒是個很大的誘惑。我素來不喜歡在銀行進進出出,但我喜歡乘汽車。我想沾光到城隍廟去一趟,看看我可以給孩子們買些什么。我想這時總有燈籠可買,我要讓我最小的孩子看看走馬燈是什么樣的。
其實我不該到城隍廟去的。在這個時候一去,你知道,當然會有什么結果。在歸途中帶了一大堆東西,走馬燈,兔子燈,幾包中國的玩具,還有幾枝梅花。回到家里,同鄉送來了一盆家鄉著名的水仙花,我記得兒時新年,水仙盛開,發著幽香。兒時情景不自禁地出現在我眼前。我一聞到水仙的芬芳,就聯想到春聯、年夜飯、鞭炮、紅蠟燭、福建橘子、清晨拜年,還有我那件一年只能穿一次的黑緞袍。
沒有蘿卜粿
中飯時,由水仙的芳香,想到吾鄉的“蘿卜粿”(蘿卜做的年糕)。
“今年沒人送‘蘿卜粿’來。”我慨嘆地說。
“因為廈門沒人來,不然他們一定會帶來。”我太太說。
“武昌路廣東店不是有嗎?我記得曾經買過,我想我仍然能找到那家店。”
“不見得吧?”太太挑釁的說。“當然,我能夠。”我回駁她。下午三時,我已手里提一簍兩磅半的年糕從北四川路乘公共汽車回來。
五時炒年糕吃,滿房是水仙的芳香,我很激烈地感到我像一個罪人。“我不準備過新年,”我下了決心說,“晚上我要出去看電影。”
“你怎么能?”我太太說。“我們已經請了X君今晚來家里吃飯。”那真糟透了。
五時半,最小的女兒穿了一身新做的紅衣服。
“誰給她穿的新衣服?”我責問,心旌顯得有點動搖,但還能堅持。
“黃媽穿的。”那是回答。六時發現蠟燭臺上點起一對大紅蠟燭,燭光閃閃,似在嘲笑我的科學理智。那時我的科學理智已很模糊,微弱,虛空了。
“誰點的蠟燭?”我又挑戰。“周媽點的。”“是誰買的?”我質問。“還不是早上你自己買的嗎!”“真有這回事嗎?”那不是我的科學意識,一定是另外一個意識。
我想有點可笑,但記起我早晨做的事,那也就不覺得什么了。一時鞭炮聲音四起,一陣陣的乒乓聲,像向我的意識深處進攻。
我不能不抵抗,掏出一塊洋錢給我的仆人說:
“阿秦,你拿一塊錢去買幾門天地炮,幾串鞭炮。越大越響越好。”
在一片乒乓聲中,我坐下來吃年夜飯,我不自覺地感覺到很愉快。
責編:何建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