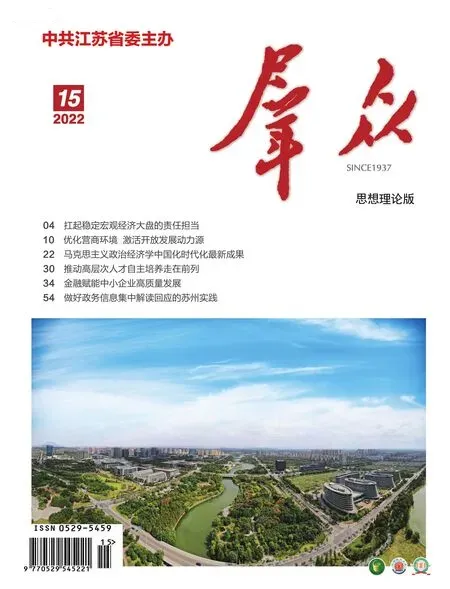紅色題材戲曲的創作探索
6月29日上午,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七一勛章”頒授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瞿秋白烈士的女兒、賡續紅色基因的革命先烈后代、百歲高齡的瞿獨伊榮獲“七一勛章”。6月29日晚,首部以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和宣傳家,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瞿秋白的革命事跡為題材創作的現代昆劇《瞿秋白》在紫金大戲院成功首演。該劇以瞿秋白被捕及犧牲為切入點,聚焦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個月,展現其舍生取義的人生歷程,同時深刻剖析其內心世界,追溯他信仰之源流與畢生之堅守。本刊記者特采訪昆劇《瞿秋白》的編劇羅周,請她談談紅色題材戲曲的創作感想。
記者:之前您創作的作品涉及京劇、昆劇、揚劇等眾多劇種,題材也多以帝王將相傳統戲為主,近年來,您接連推出幾部紅色題材作品,京劇《蓄須記》、昆曲《瞿秋白》等。在現代紅色題材作品創作方面,您認為最難的突破點是什么?
羅周:無論古裝戲還是現代戲,關鍵在于你是否把握住了戲曲內在的規律性。對現代戲曲創作而言,更大的難度是表演藝術。表演需要創造與現代生活相關的、新的程式,既能讓當代人接受,同時又是戲曲性的。用哪些新程式去延展、突出、放大、定格情感呢?這不是一兩個動作的問題,而關乎一整個藝術體系。從這一點上說,現代戲曲表演藝術之難度,在我看來,實在遠遠大于劇本寫作。
記者:傳統戲以歌舞演故事,現代紅色題材戲曲創作方面,您更加注重表現的是哪些元素?
羅周:戲劇是寫人的藝術,而人性是貫通的,古今中外文藝作品書寫與表達的技巧技法,也都有相互借鑒之處。
傳統戲以情節取勝,故事跌宕起伏,用歌舞抒發內心情緒,并且,“抒情性”越來越顯現其魅力。我近年來創作昆曲比較多些,其中一個原因是,昆曲“抒情性”較之其他劇種更為顯著。相對其他劇種而言,昆曲經常以濃墨重彩的曲唱,表現人物情感之跌宕、心靈之起伏、個性之張合。我在昆曲現代戲創作方面,也繼承了劇種這一特征,不單以講故事為目的,而是以展示人物豐富復雜、獨特細膩的情感個性為追求。這恰恰是戲曲立足當代舞臺、最有別于其他藝術樣式的特性與所長。“講故事”不是為了故事本身,是以故事為載體,展現獨特的人物,展現人物豐富的情感世界。
在表達方式方面,現代戲的寫法要注重與當代人的表達方式相近。我寫“抗疫”題材昆曲《眷江城》,對每一句念白、唱詞都反復斟酌,以保證這是當代人的表達方式。不過,又要保證其文學性,保證念白可以上韻,這就不能純是“大白話”,個中尺度非常微妙,需要不斷地領會。
記者:紅色題材的藝術創作最難的地方在于如何把握史實與創作之間的關系。一旦處理不好,容易變成戲說。在處理真實和虛構之間的關系方面,您在創作中是如何把握的?
羅周:紅色題材作品是現代戲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因為人物大多史有其人,故而在創作時,要特別注意把握好“史實”與“創作”的關系。我經常以寫論文般嚴謹的態度來閱讀史料并從中發掘戲劇性之所在。
要準確判斷哪些史實、包括史料中的細節,可以入戲。有些史料雖然能增加我們的知識面,但難以進入戲劇;有些本身就具有非常強烈的戲劇性,甚至連最高明的編劇都編不出來。甄別、判斷、選擇,是極為關鍵的一步。《瞿秋白》中《取義》一折,幾乎所有的細節都是真實的:瞿秋白被一百多士兵押往刑場,去而復返,集唐詩以志昨夜之夢,八角亭飲酒照相,因為看到一個盲人乞丐而短暫停步,在青松挺立之處言道“此地甚好”,從容就義……這些真實,具有任何虛構都無法企及的力量。所以我想,處理史實與虛構的關系,絕不是簡單地分出占比,而要嚴謹地斟酌發現,面對每一塊不同的史料,進行詳盡、獨到、一戲一格的衡量與思考。
記者:今年是建黨100周年,涌現了不少紅色題材戲曲作品,有的勝在故事,有的勝在以情動人,有的勝在人物鮮明,您創作紅色題材作品時,最想突出哪個方面?
羅周:我導師章培恒先生曾說,能感動人的文字就是文學。戲劇和其他的藝術一樣,追求的都是感人的力量。戲劇之所以能感動人,激蕩受眾內心、產生共情共鳴,還得靠塑造人物來實現。我筆下充溢著的,是對真善美之向往、追求,而很少寫那些窮兇極惡之徒。我總懷著虔誠、敬重又分外親近之心,希望能寫出人性中最高貴、最優美、最從容、最堅韌處,比如陸靜華、比如瞿秋白,從他們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人類之美好、人類之偉大,人類永不放棄的自我成長、自我完善。
記者:我認真觀看了昆劇《瞿秋白》,為他的情懷、氣度打動。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戲劇結構,設置非常精致。請問您是如何設置戲劇結構的?
羅周:《瞿秋白》每場都設置了“晝”和“夜”,剖四折為八小塊戲。“晝”寫的是瞿秋白在獄中和國民黨進行斗爭的這一條線索,可對于塑造瞿秋白其人,想體現其豐富的內心世界,僅有這一條線索是不夠的,所以我又寫了“夜”,通過他與親情、友情、愛情之訣別,將人物寫得更豐盈、飽滿。寫親情,是因為母親之死對瞿秋白產生了極大的震撼,也是促使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最強烈的情感原動力,他意識到母親之死不是一個人的悲劇,而是整個社會的悲劇。在第二個夜晚中的魯迅先生,是瞿秋白的摯友。他倆的友誼是獨特的、真摯的,是心靈乃至生命的托付。兩人心中都燃燒著改變世界的熱情,是基于這一共性,建立起的知己之交。寫愛情,描寫了瞿秋白與妻子分別時的依依不舍和眷戀,他們深知,每一次別離可能都是生離死別,他們將個人的愛戀與對國家、對民族的愛糅到了一起,全力以赴地深愛著。所有這些都指向了一個更加血肉豐滿的瞿秋白。
記者:在處理昆劇《瞿秋白》的高潮部分時,瞿秋白赴死時的從容與淡定,更能讓人感受到主人公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請您談談當時您創作的時候是如何構思這個高潮的?
羅周:秋白之死,完全是歷史之真實,幾乎沒有任何虛構的成分。首先要詳盡閱讀材料并有效掂量,看它能否承載、完成、綻放高潮部分所需的戲劇力度,可以的話,就用戲劇技巧將之酣暢淋漓地表現、書寫出來;如果覺得戲劇性不足,那就在尊重歷史的前提下,順著史實指引之方向,謹慎而熱烈地,在史書的縫隙中,發掘更多可能性。
記者:創作現代題材的昆曲,從《當年梅郎》到《眷江城》,再到《瞿秋白》,遇到的最大挑戰是什么?主創們是如何克服的?
羅周:劇本創作方面,一個難點是語言。既不是古典的,又不是純粹的口語,它得能用韻白念。其分寸尺度一定要牢牢地把握住。而更大的挑戰在于表演。念白、曲唱、配樂……方方面面,都有待嘗試、實踐、開拓。比如念白之節奏。傳統戲之念白有既定節奏,這是昆曲程式之一,現代戲卻不能過于拖腔拖調。每個現代戲,都要根據人物、時代進行念白節奏、念法等方面的校準調整。曲唱也一樣。昆曲是曲牌體,所謂曲牌格律不僅是文字上的,也是音樂上的。傳統曲牌節奏相對緩慢,若原樣照搬到現代戲上,常有拖沓冗長之感。作曲就必須在原旋律、節奏上進行再創造。至于配樂,在昆曲舞臺上,演員念白時,希望能控制情緒音樂的音量。因為昆曲念白本身是具有音樂性的、是能充分展現情緒的,配樂太響,容易擾亂甚至淹沒念白之聲,就使觀眾失去了很大一塊審美、欣賞的藝術體驗。
責任編輯:陳偉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