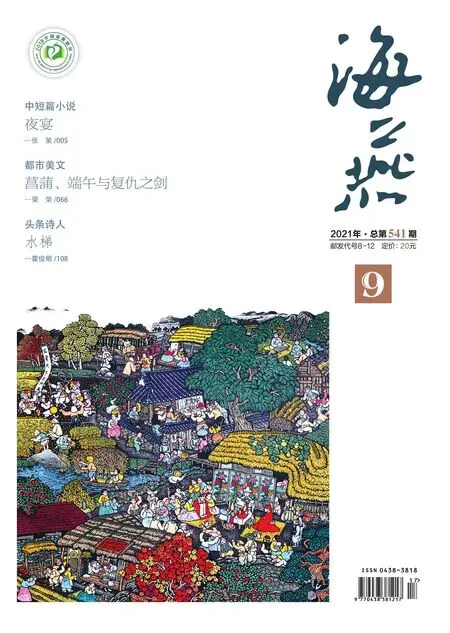莊源往事
文 程亞星
偶然看到安徽省攝影家協會副主席、黃山市攝影家協會主席潘成拍攝的一張照片,那是我家鄉歙縣相對比較偏僻貧困的莊源村村頭的一棟跨路的舊房子,曾是莊源學校的一部分。
簡陋的小學校
莊源學校很難界定是小學還是中學,因為它有小學,同時還有一個附屬初中,學校沒有規整的校舍,大致分四個部分,照片上這座破舊的小樓里有兩個班;一個破舊的倉庫里面有幾個班;小河邊上還有一個三面有墻一面空的小房子,我不確定之前是一座廟還是一座小戲臺,這里面有一個班,一小段角鋼掛在房子的一角,是打鈴用的;還有兩間平房算是條件最好的了,初二、初三的學生才能坐里面上課。我父親程邦平曾在這所學校待過五六年,我哥哥程兵小學五年級以及初中三年都是跟隨我父親在莊源村度過的。
我父親擔任班主任,同時帶語文、物理兩門課。當時鄉村學校師資力量都很緊缺,極少有高學歷的科班出身的老師,父親算是文理比較均衡的,所以帶了語文和物理這兩門跨度很大的課程,有人戲說我父親是文理通吃的老師。
據說現在莊源村已經有了一座條件相當不錯的學校。
滾落的山核桃
我母親在距離莊源4公里的朱村供銷社工作,因為業務出色,基本上每年都被評為縣里甚至是徽州地區的先進個人,都要到縣城或屯溪去參加先進個人表彰會,而開會的時間大多是我春季開學的頭一個星期,于是我便向老師請上一個星期假,跟隨我父親在莊源待一個星期。莊源民風淳樸,村民們非常友好,每年去莊源的那一個星期,我都非常快樂。

插圖:王譯霆
我父親的宿舍很小,一張小小的床,父親和我哥哥兩個人睡,我去的時候是沒地方睡的,只能跟他們學校里一位姓汪的中年女教師插鋪,一個十來歲的小女孩和一個四五十歲的女教師插鋪那是相當拘束的。有一次讓我印象深刻,那是一個極其寒冷的夜晚,倒春寒比冬天還冷,我們把脫下的棉衣壓在被子上,穿著毛衣毛褲睡,仍然覺得好冷。汪老師也覺得冷,但已沒有多余的被條了,她就起來用一張塑料布在被條外面裹了一層,于是我睡在床上每動一次,塑料布就會窸窸窣窣地響。睡著睡著還是覺得冷,汪老師又起來,把一個斗笠壓在床上,說多壓一點東西總會暖和一點。于是我更加不敢動了,怕斗笠會被我翻動的時候顛下床來。但一個小孩子在沒有入睡的時候是很難保持安靜的,我不自覺地、又很拘謹地動來動去,于是就聽到塑料布加斗笠窸窸窣窣不停地響。不一會兒,只聽見有東西滾落床下,在地板上滴滴哆哆地滾出很遠,聲音清脆而持續,汪老師豎起耳朵聽,并且自言自語地說:這是什么聲音?我心里清楚但沒好意思說,這是我外衣口袋里裝著的三顆山核桃,白天沒舍得吃,這一下滾到地下去了,不知道還能否找到。第二天早上,汪老師仍然帶著狐疑地問,昨天晚上不知道什么東西掉下床了,滴滴哆哆地響。我也幫著她在四處找,目的是想找回那三顆山核桃,可是竟然一顆也沒有找到,沒準是滾床底下去了,也沒準是給老鼠當宵夜了。只是后來想起這事覺得有點過意不去,應該跟汪老師說清楚的。
蘿卜燉肉吃反了
那時候的小山村是買不到葷菜的,因為農村里沒有買葷菜的習俗和需要,父親在朱村過完周末返回莊源時,有時候母親就會割上半斤肉,買點豆腐干給他們帶上。
那一次半斤肉用來燉蘿卜了。而那天村里面有一位老鄉,見到我父親時很熱情,邀請我父親到他家去吃晚飯,說是來了一個親戚也認識我父親的。當時被人邀請去吃飯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不好意思再帶孩子的,更何況是兩個孩子,三張嘴去不像話。于是我和我哥哥只能留在宿舍里面自己弄晚飯吃。炭爐砂鍋,蘿卜燉肉,越燉越香,哥哥很孝順,跟我說:“我們晚上只能吃蘿卜,肉我們一人吃一塊,剩下的留給父親。”我當時聞到燉得那么香的肉口水直掉,但哥哥的話在理,我們也只能就著蘿卜和湯下飯。父親回來以后看著砂鍋里剩下的肉,說:“你們干嗎不吃肉啊?長身體的時候,我牙齒不好,正想吃點蘿卜喝點湯呢。”我當時一聽心里就生我哥哥的氣:“都是你,不讓我們吃肉,你看,你看,吃反了吧,本來我們把肉吃掉,把蘿卜和湯留給父親多好。”哎,那么小的孩子,哪里真聽得懂大人的話呢。
汪志平的故事
那一年的中考,是莊源小學附屬初中班教學史上的巔峰,一個小小的鄉村初中班,有4位學生超過了初中中專的分數線,其中2位讀了中專,還有2位學生因為年齡不到不能上中專,去讀了高中,當時那兩個讀高中的學生非常羨慕那兩個讀中專的同學,說一只飯碗到手了,我哥哥就是其中的“一只飯碗”。而兩年后,這兩位讀高中的同學分別考上了很好的大學,一位考上了醫學院,另一位考上了清華大學,這是莊源歷史上首位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位考取清華大學的學生,當然也是我父親這一輩子帶的學生當中唯一一個考上清華大學的學生,他的名字叫汪志平。
我對汪志平印象比較深,因為他是我父親的學生,也是我哥哥的同班同學,父親和哥哥常常在談話中提到他。印象中這是一個安靜的、好學的、能吃苦的學生。他的家境不好,母親身體差,父親身材瘦小,做農活不占優勢,靠為村子里的代銷店挑一些零散貨物,掙幾個腳錢來養活家庭。為了供汪志平上清華大學,他的一個弟弟一個妹妹輟學在家務農。
父親說的一件小事我至今印象深刻,說有一年大年三十,汪志平問他母親:“明天過年會給我吃雞蛋嗎?”母親說:“會的。”他說:“給我吃幾個呢?”母親說:“可以吃兩個。”汪志平說:“那你少放兩個雞蛋,給我一毛四分錢吧,我想買兩本練習本。”這個小故事讓我們全家都非常感動,覺得應該多幫幫這個苦孩子。
莊源村有個鄉村小水電,每天晚上只能發電兩小時,停電了晚自習也就下課了,我哥哥就邀請汪志平到我父親的宿舍里,兩人共用一盞煤油燈再學習一個小時回家。我母親也總是把一些可用的紙留下來訂成小本子讓我哥捎給汪志平,本意是讓他用來打草稿的,但據說他總是用來記學習筆記。
知識改變命運,汪志平后來成了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他家的經濟條件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我的救命恩人
那年我上小學三年級,扁桃體發炎引發肺炎,朱村雖然有醫院,但醫療條件是有限的,開了點消炎藥,吃了幾天,卻越來越厲害,高燒燒了三四天,人燒得迷迷糊糊的,嘴上都起了泡。母親沒有經驗,總覺得扁桃體發炎不是什么大病,想等周末我父親從莊源回來了,再看看怎么處理。
那天,我母親在供銷社棉布柜臺上賣布,來買布的正好是莊源村的一個年輕婦女,一邊買布一邊和我母親聊天,我母親就說到我生病的事,說發燒都好幾天了,吃了藥也不見好,明天星期六他爸爸就要回來了,到時候再看看怎么處理。結果這位年輕的小嫂子回莊源村,在村口正好遇上我父親送放學的學生出村口,遇上后就聊了幾句,她說:“程老師,你這是要回朱村吧?”我父親說:“今天不去,明天星期六再回去。”這位小嫂子說:“聽你老婆講你女兒生病了,高燒燒了好幾天,說等你明天回去以后再看看怎么搞。”
我父親當時就預感到情況不太好,立即跟校長請了假,交代了我哥哥自己解決晚飯,立馬就趕回朱村。到了朱村天已擦黑,我父親上樓看我,我已經燒得迷迷糊糊了,父親當場決定連夜送縣醫院,于是從隔壁鄰居那里借了一個小搖床,先是我父親和我姐姐抬了一段路,然后讓我姐回去了,接著就是我父親和我母親兩個人抬著我。
我母親個子小,又沒干過重活,盡管父親已經把搖床盡量往自己這邊拉過來,母親還是抬不動。中途歇肩的時候,母親看到我小小的身軀躺在小搖床里,昏沉沉地睡,臨走時放在我頭邊的一個麻餅一口都沒動,就嚇得眼淚出來了,說麻餅都不吃了,怕是真不好了。說完這話,不知哪兒來的勁,抬上我,幾里地不歇,一口氣就到了縣醫院。
到醫院已經是晚上8點多了,又累又餓,我父母準備到我母親的好朋友、在醫院工作的章蝶娜阿姨家先吃點飯再去醫院,娜姨一看我的狀態,說先別吃飯了,趕快先去看病。一到醫院,醫生讓馬上住院,在住院部樓梯口的走廊加了一張床。剛安頓好,娜姨正準備讓我父母輪流到她家去吃點飯,我這邊突然就發生危險了,眼睛往上翻白眼,昏厥過去,渾身抽搐,沒了知覺,立即展開搶救。當時醫生懷疑可能是腦膜炎,用很粗的針管插進我的脊柱里面抽脊髓出來化驗,母親一看那種場景,慌了神,一屁股癱坐在樓梯上開始哭,不斷地拉著醫生問要不要緊?還有用嗎?還有沒有救?父親強作冷靜,把我母親穩住,配合醫生一起展開搶救。
我清醒過來的時候已經是快天亮了,父母把昨天搶救的過程跟我說,他們說的所有細節我一點印象也沒有,好像是在說一個和我無關的故事。醫生說再晚點送來怕是不行了,細想想,這時間就是那個小嫂子幫我爭取的呀。
生命中常遇貴人,這位小嫂子就是其中一個。后來聽說她有一次跟丈夫吵架,想不開,上吊尋短見,結果繩子是爛的,不牢,又摔下來了,腦袋磕在水缸上腫一個大包,大哭一場事情也就過去了。我想這是好人有好報,老天護佑她吧。只可惜我至今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