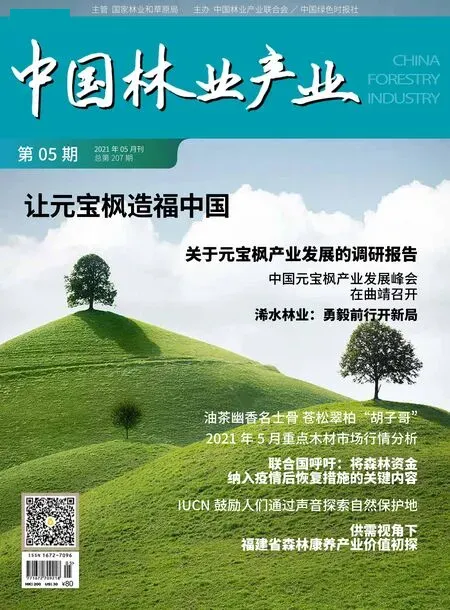榴花開處照宮闈
文 那 海
一
是五月了。熙和門外的石榴花開了。
猶如那些不經意的少年時光,無意去吸引什么,卻讓人直抵明澈而熱烈之境。
榴花開的時候,走在紫禁城,有種莫名的歡愉。
這是在白天和黑暗之間感受到的毫無倦意的歡愉,也是宋人詠榴花詩句“枝枝葉葉綠暗,層層密密紅滋”的沉靜與暗涌。
生有熱烈,藏與俗常。
在黃瓦紅墻間,在繁密的綠意中,榴花星星點點,絢爛而不聲張。
我猜想唐人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稱“近代之畫,煥爛而求備”,他當時或許正對著一樹盛開的榴花。
在五代南唐畫家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中,見到了石榴的那抹紅。
這是一個穿著綠衫紅裙,坐著吹笛的女子。
她出現(xiàn)在這幅連環(huán)長卷的場景之中。長卷的迷人之處便是它常以極強的敘事性,在縱橫綿延的時間與空間中,尋找最恰當?shù)那楦泻穸取?/p>
韓熙載為避南唐后主李煜猜疑,以聲色為韜晦之所,在家中開宴行樂。李煜聞其荒縱,欲知情狀,“乃命閎中夜至其第竊窺之,目識心記,圖繪以上之,本欲借圖畫來規(guī)勸他,豈料熙載視之安然。”
畫中的這個女子,身著的紅裙,色調鮮妍明媚,如同開了一朵榴花,無法不讓人將視線落于其中。
想必這就是讓多少人拜倒的“石榴裙”。
原本屏氣斂息的模樣,一切繽紛奢華有著浮夸與無奈之味,或許盡皆消失,或許將陷入一團混亂。
這一抹石榴紅,讓人遁入若有所思的嫵媚中。
一幅畫在視覺上與我們日常的思慮極其妥帖,在這幅色彩的盛宴中,人物以石青、朱砂、緋紅、石綠等色為主,室內陳設大抵以深棕、黑灰等凝重之色,濃麗沉著,色墨相映。
當我們可以在一幅畫里承載更多的情緒,無疑也是一個孤獨的人可以在這里度過等候多時的時光。
夜宴難盡歡。
唐寅的《臨韓熙載夜宴圖》,筆墨濃重,亦為傳世之作。
唐寅還有一幅《韓熙載夜宴圖》軸,則是將“觀舞”中舞姬王屋山舞“綠腰”的一個情節(jié)加以補充,場景設在夏日的庭院,成為再創(chuàng)造的故事人物畫。
蔥蘢的園苑,石榴花開得正盛。蓮花池,桌上的一瓶榴花,點綴著新綠密葉。
如唐寅致友人信札所云:“丈夫潦倒江山花竹之間,亦自有風韻。”
倘若將場景放在秋日,多了幾分蕭瑟。夏日剛剛好。
縱然“北方誰唱延年曲,猶有傾城獨立人”,亦是紅塵俗世的憶舊。
在夏日,總有一份和煦的東西,如這榴花,使得這份悠然沁入的明麗而又極度深味的色澤,喚起人們對靜穆的觀照與飛躍的生命的覺知,還能怎樣呢?
于是,人們酌滿斑駁中夾雜著青翠的時光的酒杯。
二
那日匆忙路過,看到細雨中宮墻邊的那兩三枝石榴,正如火如荼地開花。
這樣的時節(jié),月季花也開得正盛,斷虹橋、左翼門、慈寧宮,總有花兒艷非尋常。
御花園的山梅花,色白如雪,初夏的風拂過,滿是淡雅的花香。
山梅花又稱“太平花”,承蒙宋仁宗賜名“太平瑞圣花”,花開千百苞,卻有分寸,并萃一簇,舒展又節(jié)制,據(jù)說是慈禧太后的鐘愛之花。
紫禁城中的石榴,大都是經歷一定年代的。你看它熱烈,你看它靜寂,沒有看穿世事,哪來這般云淡風輕冷冷清清地嬌艷如火。
這番的心性鮮活,風風火火,榴花開欲燃,突然,它就柔情起來。
說起來,讓花朵都有意義是件無趣的事,就如每樣事物都有其局限,包括柔情蜜意。
但榴花開的時候,心性怎能凝滯。這么熱烈的生命,一種以最豐富的激情做出的證言,是某種靈性與深度的東西。一切藝術皆可當作某種證據(jù)。
惲南田癡迷于宋人石榴圖,曾見宋人所畫石榴,渲染數(shù)十遍,至無筆可尋,無色可擬,幾乎神韻俱妙,心識之已久,始終不得法。
一日在白云精舍,剛好友人攜一顆成熟的石榴,碩大豐麗,霜皮剝裂,正書家所謂壁折路。由此大悟,“因以宋人設色法圖之”。
在文本上看到惲南田作的《安石榴圖》題跋與末跋,“余凡寫榴十數(shù)本,唯此為得勢。攬之磊然,流珠欲滴;緗膚赤犀,晶彩陸離”。猶是進入詩與人生合一的浪漫的美學命題,將人置入醉境。
惲南田自小遭遇家國之變,后與父親削發(fā)為僧,于靈隱寺苦度光陰。
他的《古木寒鴉圖》蕭瑟與哀婉,瑟瑟西風,寒鴉尋找歸處,透著凄惶而又無可住的茫然。這是在南田繪畫中很少見到的情緒。
或許是那一刻,黃昏古木,寒鴉無處棲息,觸動了他內心深處的凄涼悱惻。
當世界從豐盛回到簡單,不可把握的命運追逐著每一個人。
無疑,這當中,糾纏、矛盾、激切、疏遠,一切的情緒,都只是在萬化之中。
世人身上總是無可避免地遭受一些為人所無法擺脫的生命的內容,命運、衰老、死亡,讓人迷惘的同時,藝術總是在尋找一種永遠必定要回來的情緒。
我對經歷最冷、最硬的情緒的人,依然去表達個體生命擺脫一切苦難的重負,他的心緒以及作品與大自然共頻,有著莫名顫動的統(tǒng)一感的人,總是充滿敬意!
就如此時,看到南田的石榴圖,瞬間忘記他一生的顛沛流離,只有這份清凈寬和的心緒,無邊際地蔓延。
三
曾在云南瀾滄江邊的小村落,看到滿枝白花的樹,待到走近,才發(fā)現(xiàn)是白色重瓣石榴,與紅色石榴完全不同,簡直難以置信。也曾被杉洋古鎮(zhèn)的粉石榴花驚艷到。
生命中有些事,沉重、委婉都不可說。
古物中的石榴,卻讓人有話想說。
石榴作為一種典型的陶瓷裝飾紋樣,曾以石榴紋抽象圖案的形式出現(xiàn)在唐三彩陶器上。
作為喜慶吉祥圖案,明代的石榴逐漸采取折枝花卉的形式與其他花果一起出現(xiàn)在瓷器的紋飾中。
到了清代,在青花、粉彩瓷瓶上,常常可以看見石榴紋飾。
相較于明代器物色釉的濃厚深穆,瓷器上的石榴紋飾用筆粗疏而古氣橫溢,康熙朝的石榴紋大抵行其縝密,于工致之中而寓其高古,雍正時期則是逸麗而秀倩,乾隆時期于繁密富麗之極而時露清氣,“百花不落地”便是其中一種。
我們感受器物,牡丹絢爛,榴花火紅,玉蘭芬芳,見其光輝里有歡喜,便覺盛世升平,萬花呈瑞,世道與人事皆是寬心與明朗,便有一種從心而發(fā)的寬慰了。
故宮博物院藏有一個“大明永樂年制”六字款的剔紅石榴花圓盤。盤面滿雕石榴花,茂密的枝葉,花朵或開放,或含苞。
這是黃金時代的作品,是被光撫摸過的時刻鍛造的漆器。結構、材質已經無與倫比,渾然天成。
器物制作到了明代,已經進入游刃有余的時期。
一切都已更加開闊,可堂皇,可奢華,可簡純,又有樸素的念力,將一切控制得合理,極致。
與宋代定窯的白釉盤面上呈浮雕形的印花石榴紋不同的是,明代的剔紅石榴花圓盤,以溫和的、謙遜的特性,讓我們進入難以想象的真實之中。
乾隆朝有粉彩百花不落地石榴尊,仿石榴形,侈口分五瓣為蒂,通體榴花、牡丹、玉蘭、茶花、月季等繁密細致,各盡其妍,卻又粉潤清新,覆蓋全器。
這是粉彩器之珍貴雋品,專供宮中賞花,歷為藏家所珍。
榴花種種,澄明,濃烈,讓人“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酣暢而通透。這樣的器物,總是佳偶天成的。
各色花朵將整個畫面填滿,又不露出瓷底,燒制工序之繁縟,也絕非數(shù)人之力可成,故稱彩瓷翹首。
此時瓷器上的線條、層次、顏色,都是一場奇異的相逢,又是預謀已久的布局。
如果說永劫、矛盾、苦惱、極樂,都是萬物之源,那么生命力一定是充滿激情的實在,它的存在勢必使感性個體深摯、堅強。充實、宏大的生命力,早已幻化在器物之中。
有一日見清道光天藍釉石榴尊,形如石榴,通體瑩潤,合“雨過天青”之意。瓷上刻折枝梔子花兩株,清新怡人,生趣盎然。
這番的雅致與圓潤吉祥,讓人剔除凡俗種種,而這美意的表達,總能把自身中蟄伏的生命和緩起來。
四
不知宋人是如何數(shù)十遍渲染石榴的顏色。
我一直以為“石榴紅”是用石榴染成。
直至后來看到一個科普文,說古代染紅色的染色劑,主要是赭石、茜草、紅藍花、蘇木、紫鉚蟲膠等。
周代開始用茜草染紅色,它的根含有茜素,人們以明礬為媒染劑可染出紅色。
但茜草不是正紅而是暗土紅色,后世逐漸發(fā)明了紅花染色技術,才得到了鮮艷的正紅色。
石榴皮的主要染料成分是鞣花酸類物質,可直接染色,也可以加媒染劑做媒介染色。
用石榴皮,還可染成一種素雅的淺黃色,稱為“緗色”。宋詩“緗裙羅襪桃花岸,薄衫輕扇杏花樓”,著緗色裙子的女子,該是多么美妙。
《雪宦繡譜》將“緗”分老緗、墨緗、銀緗,此色有深淺之分。《清稗類鈔·服飾》中記載“香色,國初為皇太子朝衣服飾,皆用香色,例禁庶人服用。”此處的“香色”應為“緗色”。
單純用石榴皮,還可染成“秋香色”。
《清史輿服志》中,皇帝“禮服用黃色秋香色”。
秋色加上香氣,便是這秋香色吧。
而這香氣,是怎樣絲絲縷縷沁入心中,又是怎樣不可言喻的微妙之香,只能想象了。
這些純粹的、溫和的色調,有著石榴的色澤與溫度,尤其在陽光下,透著無窮色。
清宮舊藏有一款《月白緞織彩百花飛蝶袷袍》,領口系黃條,上墨書:“月白緞百花妝袷襯衣一件,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收”,是乾隆時期后妃的閑暇所穿服飾。
月白色妝花緞面,有折枝花卉及蟲蝶紋樣,以紅、綠、黃、絳、藍、會、黑、白等十余種色線織制,花卉有石榴花、牡丹、水仙、牡丹等,蟲蝶有螳螂、蟈蟈、蜻蜓和蝴蝶。猶如把整個春天都穿在身上。
不知乾隆時哪個后妃曾經穿過。
或許,與那些皓腕上戴著珈藍香鐲子,雙鬢淺戴金海棠珠花步搖、鑲寶石蝶戲雙花鎏金銀簪的妃子相比,穿過這件衣裳的后妃,縱然沒有佩玉鳴鑾,卻旖旎曼妙,溫文流美。
在《紅樓夢》金陵十二釵正冊中,賈元春的判詞為:“二十年來辨是非,榴花開處照宮闈。三春爭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夢歸。”
從女史到鳳藻宮尚書,直至賢德妃,元春在宮中生活了二十多年,她似榴花榮耀一時,卻又歷盡多少孤寂與榮辱。
不知為何,總讓我想到加繆筆下的那些花兒:
“我還住在阿爾及爾的時候,冬天里總是引頸期盼,因為我知道在一夕之間,在二月某個寒冽而純凈的夜里,路上的杏樹將全部覆蓋白色的花朵。接著我會滿心驚奇地看著這片脆弱的白雪在雨水和海風中抵抗。然后,年復一年,這些花兒從不放棄,恰如其分,為了結出果實。”
關于她們,廢名說:
“不管天下幾大的雨,裝不滿一朵花。”
春深閉戶可染衣。用草木染出的這些織物,又是繞過多少時序輪回、風霜雨露,才能穿到你的身上。
五
石榴,稱為丹若、金罌,又一種味最甜者,名天漿。
說起來,石榴就是普通的植物,卻被世人所喜。當它從遙遠的西域安石國被張騫帶回,它便有了另一個名稱,為“安石榴”。
似乎這個“安”字,亦是讓人心更為安妥。
晉人潘岳在《安石榴賦》中寫道:“榴者,天下之奇樹,九州之名果……繽紛磊落,垂光耀質,滋味浸液,馨香流溢。”這也是石榴的魅惑之處了。
在清代陳淏子《花鏡》卷四花果類考中見到石榴:“唯山種者實大而甘,千房同膜,千子如一。花有數(shù)色,千葉大紅,千葉白,或黃或粉紅,又有并蒂花者。南中一種四季花者,春開夏實之后,深秋忽又大放。花與子并生枝頭,碩果罅裂,而其傍紅英燦爛,并花折插瓶中,豈非清供乎?”
能把石榴的科普文寫成文采飛揚的文字,如同一篇華美的賦,讓人讀了后實在忍不住,也想種上一棵石榴樹。
看張恨水寫過五月的北京小院,石榴花開著火星樣的紅點,夾竹桃開著粉紅的桃花瓣、在上下皆綠的環(huán)境中,這就是五月的小院,幾點紅色,嬌艷絕倫。
人們總愿賦予植物一些情感內涵與意象。千房同膜,多子多福。
宋人用石榴果裂開內部的種子數(shù)量來占卜預知科考上榜的人數(shù),“榴石登科”便是寓意金榜題名。
石榴也因其好寓意與好兆頭,使得我們常在古畫上遇見它。
清代宮廷有逢節(jié)必畫的傳統(tǒng),宮中檔案說《午瑞圖》“端陽節(jié)備用”。端午有“端五”之稱。清顧祿記《清嘉錄》:瓶供蜀葵、石榴、蒲蓬等物,婦女簪艾葉、榴花,號為“端五景”。
在清代郎世寧的《午瑞圖》中,見到榴花。它與菖蒲葉子、艾草、蜀葵花一起插在一個青灰色的瓷瓶里,托盤里盛有李果,邊上還散著幾個角黍。
據(jù)清廷內務府造辦處的檔案記載:“四月二十九日,西洋人郎世寧畫得《午瑞圖》絹畫一張……端陽節(jié)備用。”
郎世寧此幅看上去有點像西方靜物畫的作品,作于雍正十年(1732年)。
郎世寧并不是一個繪畫上讓人覺得功德圓滿的畫家,《午瑞圖》卻滿是祥瑞雅致。似乎一個刻板的人,突然有了人情,讓人心契。
榴花在明隆慶陸治的筆下,則有另一份“妍麗”。
《畫榴花小景圖》軸,點以朱砂的榴花,水墨和花青染成的菖蒲,以墨寫百合,只覺畫面清新古雅,時序分明,畫上自題“隆慶庚午(1570年)天中節(jié),包山陸治寫”。天中節(jié)即是端午節(jié)了。
端午臨近,翻開古畫讀之,總覺置身那個香氣馥郁的五月,被榴花所包圍,大雨傾襲而至。
還是徐渭的《榴實圖》,縈繞不絕。一枝倒掛的石榴,畫中題:“山深熟石榴,向日笑開口,深山少人收,顆顆明珠走。”卻并不蒼涼。
就如某一日醒來,滿眼晨光,飽滿而又清透,以為人生還可以很長,最愛的人就在身邊,萬物和從前一樣,人生才剛剛開始。
六月的一天,從大暴雨的杭州出發(fā),開車近300公里,到了那個開滿榴花的小院,只為喝到一杯“荒野古樹茶”。
如今記起就是那個茶氣醇厚的夜晚,與老古樹茶的幾分沉穆,以及世事回味時,總有的那份甘甜。
榴花也就是如此吧。
生有熱烈,藏與俗常。
這是我鐘愛它的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