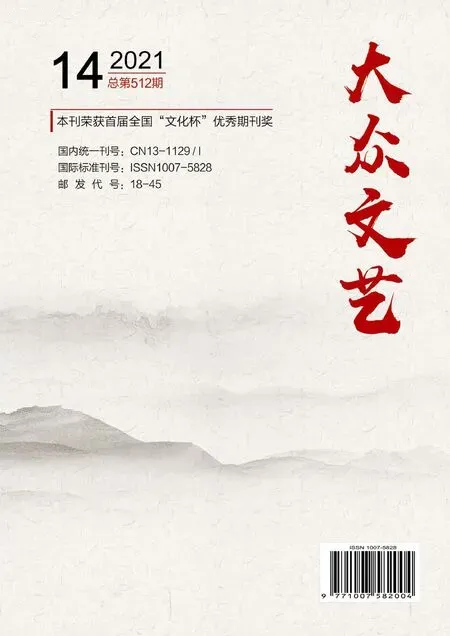笛福小說《摩爾?弗蘭德斯》的真實與偽裝*
萬 鋒
(貴州師范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貴州貴陽 550000)
丹尼爾?笛福的小說《摩爾?弗蘭德斯》講述了同名女主人公跌宕起伏的一生。她在監(jiān)獄里出生,隨著吉卜賽人流浪過,做過女仆,結(jié)過幾次婚,也做過妓女和小偷,最終因偷竊罪被判流放,卻因母親留下的遺產(chǎn)在殖民地過上富足的生活并虔誠地懺悔過去的罪惡。在她送走無力撫養(yǎng)的孩子時,對幫助她的老保姆說,希望能夠在不讓孩子知道她是誰的情況下時不時見到孩子,老保姆告訴她“你不可能同時既隱藏又現(xiàn)身。”在此種情況下,摩爾的確不可能既能現(xiàn)身見到孩子又隱瞞身份,但在整本小說中,她卻是不斷游走在隱藏和現(xiàn)身之間,用敘述的語言、身體的符號、衣著的偽裝來構(gòu)建身份,調(diào)和講述真實歷史與隱藏真實身份之間的矛盾。
一、語言層面的真與謊
在小說的前言中,敘述者聲稱自己即將講述的是“個人歷史”,只是因為諸多原因無法透露真實姓名,因此以她為人所知的“摩爾?弗蘭德斯”作為代號,除了被編輯隱去粗俗不宜閱讀的文辭外,所講之事均出自其真實回憶。聲稱自己為“歷史”而非“故事”或“小說”是十八世紀小說的慣常做法,亨利?菲爾丁的《湯姆?瓊斯的歷史》更是直接將“歷史”放在了正式題名中。這種對于“歷史”的執(zhí)著源自這類作品的特殊處境,在小說剛興起的十八世紀,虛構(gòu)故事被認為是不入流甚至有害的,所以作者們紛紛為作品冠上“歷史”的頭銜,并在其中充分加入道德說教成分,使其具有真實性和教育意義,更為讀者和評論家所接受。摩爾的故事即是這種偽裝成真實的虛構(gòu)。
摩爾很早就明白了語言的欺騙性,也學(xué)會了利用語言符號來構(gòu)建的僅停留在能指層面的真實去達到自己的目的。語言符號是她慣常利用來隱藏和偽裝的手段,如艾倫?波拉克指出,摩爾在利用語言和社會文化符號進行假面武裝上天賦異稟。但這種能力并非天賦,而是摩爾通過慘痛經(jīng)歷習(xí)得的。
小時候,摩爾對語言符號的指涉關(guān)系處于簡單直接的層面,認為能指和所指之間就是純粹的一一對應(yīng)關(guān)系,因此會被她服侍的人家的大少爺以謊言欺騙。大少爺口中的“愛”和承諾最后都沒有兌現(xiàn),而是停留在能指層面。年少無知的摩爾經(jīng)歷了那次心痛之后,不僅不再相信男人和愛情,也不再相信語言的可靠性,她明白了語言是可以創(chuàng)造出子虛烏有的所謂“事實”并用來欺騙他人為自己服務(wù)的。于是那之后的她學(xué)會了用編造的故事為女性朋友重新贏得情人青睞;也學(xué)會了用詩句和謊言構(gòu)建自己“貴婦”的身份來吸引男子;在一次行竊中,她還未開始行動就被錯誤地當作小偷抓住了,摩爾當即編造出一個寡婦身份,說了許多翔實卻無法證實的細節(jié),讓符號為自己編織了一個正當合法的身份,順利逃脫。
可以說,語言在摩爾眼中逐漸成了武器和偽裝的手段。然而摩爾對這種語言武器的使用并非不受拘束,據(jù)她宣稱,她對于謊言是持否定態(tài)度的,認為人不應(yīng)該說謊和欺騙,但她實際的做法又明顯違背這一態(tài)度。一方面,她在成功利用語言達到目的之后表現(xiàn)出來的是沾沾自喜的心情;另一方面,她反對說謊并非因為道德原因,而是不愿意面對謊言被戳穿帶來的后果。在散布謊言將自己偽裝成貴婦之后,她對著即將成為第三任丈夫的男子“假裝”不承認自己的富有,而男子卻認為她是故意試探自己的真心,所以明確表示不在乎她的錢財多少。于是,摩爾似乎獲得了內(nèi)心的平靜、坦然接受他的追求,她自我思忖:“如果有一天他發(fā)現(xiàn)上當受騙了,只能說是被騙了,不能說是被我騙了。”似乎這樣她就獲得了良心上的安寧。
除了通過語言符號創(chuàng)造“事實”和身份以往,摩爾還善于利用身體上的符號,讓它們參與到表意和身份建構(gòu)中,為她謀取利益。
二、身體符號的真與偽
與對語言符號的認知和使用類似,摩爾對于身體上可展示的符號也經(jīng)歷了一個從簡單信任到有意識利用的過程,這類身體上可感知的非語言符號與語言類似,也承擔(dān)了指涉功能、參與了意義表達和生成。這類身體符號主要以表達情緒和情感為主,其中,摩爾較多筆墨描摹的是她流淚的場景。眼淚作為直觀可見的情緒表達,有時能夠達到比語言更有說服力的效果。
初入社會時的摩爾在情緒的表達上是自然流露的,當時的眼淚傳遞的是真實的情緒,無論是對大少爺講述自己的擔(dān)憂,還是對女主人袒露心扉,流下的都是真誠的眼淚。眼淚是摩爾為數(shù)不多的真實。盡管遇到了背叛和欺騙,遭到了貧窮的威脅,經(jīng)歷過身處孤立無援的境地,她在面對每一個原本只是想要利用的男性時,內(nèi)心依然會有感情,依然會為他們落淚,尤其是與叫杰米的那任丈夫分開后,她的悲傷無法抑制,不停落淚;在她灌醉路上遇到的紳士還偷走了他的財物后,看著他熟睡的樣子,摩爾心中想到一個體面的紳士竟然會因為喝酒的緣故就落到如此地步,非常惋惜,以至于流下眼淚;在獄中遇見了同為階下囚的丈夫,摩爾更是淚如雨下;而在流放到殖民地與兒子重逢之后,她再次流下了欣慰和感動的淚水。可以說,自始至終,摩爾的眼淚中都保存著一份純真。
盡管摩爾大多數(shù)情況下的流淚是真誠而自然的,有時她也會有意識利用眼淚,正如她自己所說,眼淚是“女人的修辭”。在偷竊被抓住時、被帶到監(jiān)獄時,以及勸說丈夫時,摩爾都會有意識地掉下淚來,這些情況下的眼淚,就如同她編造的故事一樣,是空洞的外部符號,并不與內(nèi)心的情感或情緒有對應(yīng)指涉關(guān)系,只是一種“修辭”,一種達到目的的手段。
伊恩?瓦特認為英國小說自笛福起表現(xiàn)出對空間的現(xiàn)實主義呈現(xiàn),辛西婭?沃爾在回溯英國小說對細節(jié)描寫的發(fā)展史時也曾指出,笛福小說較以往的敘事文學(xué),在空間的呈現(xiàn)上更加細致和具體,細讀小說不難發(fā)現(xiàn)很多對于空間物質(zhì)性細節(jié)的描述,同時,笛福對于人物身體的物質(zhì)性細節(jié)也描繪得較為詳盡,摩爾就時常利用撲過去、靠在柜臺、輕挨著門等動作和姿勢將物質(zhì)性的身體符號與空間細節(jié)相結(jié)合,再配合以流淚、編造的故事等等符號的手段,讓在場的人完完全全相信她。摩爾正是利用了身體符號,創(chuàng)造出極具真實感的謊言,為自己服務(wù)。
三、衣著的“得體”與偽裝
摩爾淪為小偷后開始了更大規(guī)模的斂財,在行竊的過程中,她常常喬裝打扮,有時是扮成采買的仆人,有時是獨居的寡婦,有時又是穿著光鮮還帶著手表的貴婦人。這些服飾的主要用途在于為她建立一種身份,讓她能安全混入人群,并為自己的在場提供合理證據(jù)。衣著與語言、身體表征一樣,是摩爾建構(gòu)身份的手段。
摩爾的一生和衣物、服飾關(guān)系緊密,不僅她的名字弗蘭德斯與進口布料有關(guān),她第一次有安定下來的居所和微薄的收入即是通過幫大戶人家做針線活,可以說,織物從一開始就將摩爾編織到了社會經(jīng)濟活動的大網(wǎng)中,從編織縫補開始,摩爾進入了她充滿罪惡的一生。幾乎每次出門行竊,摩爾都認真裝扮,這樣即使被懷疑,也可以通過衣著洗脫嫌疑。在她偷盜生涯的很長一段時間中,給她提供住處和指導(dǎo)的老婦人堅持要她女扮男裝去行動,跨性別的喬裝讓摩爾心中十分不舒服,因為她感到另一種性別的衣著違背了自己的“本性”(nature)。但在實際操作中,摩爾卻從未露出馬腳,連與她配合行動、睡一張床的合作伙伴都沒有發(fā)現(xiàn)她真實的性別。女扮男裝最后也救了她,讓她在差點被抓住時逃回家中迅速換裝逃過一劫。
在這次異裝經(jīng)歷中,摩爾原先擔(dān)憂自己的內(nèi)在本性會與外在衣著相悖,從而暴露真實身份。但事實上,本性并非內(nèi)在固有的,而是由外部符號構(gòu)建的,當她通過衣著展露的是另一種性別外在時,構(gòu)建的也就是與另一種性別相對應(yīng)的“本性”。摩爾自己所認為的“真實”是被外部的偽裝所消解的,外部偽裝構(gòu)建了另一種具有欺騙性但更具實際用途的虛假的真實。
朱迪斯?巴特勒在談道性別身份時曾指出,性別身份其實是一種操演性的身份建構(gòu),外部的身體特征并不是內(nèi)在身份的表達,內(nèi)在身份是由外部特征,包括姿勢、衣著構(gòu)造出來的,主體通過不斷重復(fù)與文化期望相吻合的外部性別特征,獲取了自身能被社會解讀和認可的身份。摩爾的女扮男裝正是一種自我賦能式的性別操演,將自己從并不存在的“真實本性”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成為自由建構(gòu)外在身份、擁有行動自由的主體。摩爾每一次“得體”的裝扮和女扮男裝的行為,都讓她暫時獲得了對自己有用和有利的身份。
摩爾充滿罪行的一生,游走在真實和偽裝之間,利用語言、身體、衣著三重符號系統(tǒng)編造對她有利且具真實效果的諸多謊言。在整本小說的敘述過程中,摩爾數(shù)次說她真誠懺悔過去的罪惡,直到小說結(jié)尾依然是聲稱自己在懺悔中度過余生。但在敘述中摩爾對自己常常是持肯定態(tài)度的。她的懺悔如同她編造的那些故事一樣只停留在語言能指符號的層面。但當我們批判摩爾的罪行時,又不得不思考逼迫她一步步滑向犯罪深淵的根源。十八世紀的英國,留給貧苦出身的女性的出路并不多。與其說笛福暗暗贊賞摩爾,不如說笛福通過描述困境中依然努力生活并利用一切可利用條件去獲得經(jīng)濟獨立的女性,是在批判那個催生出這類人生的社會。從這個意義上,整本小說其實可看作穿著得體道德教化外衣的批判現(xiàn)實的“身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