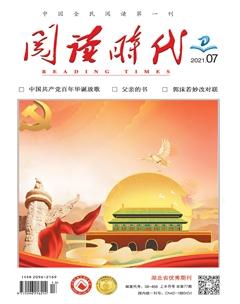書籍的誕生:有典有冊(cè)
尚瑩瑩
我們每天都要看的書,最開始的樣子就是簡(jiǎn)牘。不過簡(jiǎn)和牘是兩種東西。“簡(jiǎn)”字從竹,是把竹子削成平平的一小片豎條,從上到下直直的,只能寫一行字;牘,是寫了字的木片,版面比較大,經(jīng)常用作公文處理。現(xiàn)在“簡(jiǎn)牘”合在一起已經(jīng)成為一個(gè)名詞。不過在紙出現(xiàn)前的約2000年的時(shí)間里,書寫上一直以竹簡(jiǎn)為主。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我國(guó)文獻(xiàn)記載和考古發(fā)現(xiàn)均可以說明。
不像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那樣一鳴驚人,古人用簡(jiǎn)牘來記事作文是我們一直都知道的事情,而且可能遠(yuǎn)早于甲骨記事。《尚書·周書·金縢》寫周公為武王祈福——“史乃冊(cè)祝”,《尚書·周書·多士》“惟殷先人,有冊(cè)有典,殷革夏命”,《詩經(jīng)·小雅·出車》寫因有緊急的軍書來到,戰(zhàn)士不能回家,“豈不懷歸,畏此簡(jiǎn)書”。這些記載說明商周時(shí)期乃至更早,文字的主要載體介質(zhì)就是竹簡(jiǎn)。
幾個(gè)最主要描寫書籍的字都和竹簡(jiǎn)有關(guān)系。
冊(cè),最早見于甲骨卜辭。字?jǐn)?shù)比較多時(shí),一根竹簡(jiǎn)寫不下,就寫在多枚竹簡(jiǎn)上。將這些單枚簡(jiǎn)按照上下文順序依次擺好,用皮繩兩道編好。孔子讀書勤奮,幾次翻爛了編連《周易》的皮繩,“韋編三絕”就是這么來的。
篇,是比冊(cè)更大一點(diǎn)兒的計(jì)量單位,有很長(zhǎng)的文字內(nèi)容在一起完整地成為一個(gè)單位。通常一“篇”中可能有很多“冊(cè)”。班固著錄最早的系統(tǒng)性書目《漢書·藝文志》,就大量采用篇來做書籍描述單位,因?yàn)闁|漢時(shí)能搜集來的書籍大部分都是簡(jiǎn)書。
典,雙手捧冊(cè)為典。許慎在《說文解字》里講典,說它從冊(cè)從大,是重要的書,所以用來稱呼“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這些上古最重要的書。我們今天看到“典”,仍然有一種威嚴(yán)古雅的觀感。
比如“史”字。《說文》謂:“史,記事者也。從右持中。”說寫史要有公正立場(chǎng),不偏不倚,正是史家之傳統(tǒng),2000年來無人疑問,直到清末吳大澂據(jù)金文字形提出“從右執(zhí)簡(jiǎn)冊(cè)說”。他說:“史,記事者,像手執(zhí)簡(jiǎn)形。”古人寫簡(jiǎn),不像我們今天這樣伏案寫作,而是一手持簡(jiǎn),一手秉筆,懸空而書。吳大澂的新論正好也符合簡(jiǎn)書規(guī)制。如果真如此,人類萌發(fā)歷史概念的那一刻,或許就受到了簡(jiǎn)冊(cè)書籍的啟發(fā)。
此外,還有比簡(jiǎn)更短一些用于占卜的“簽”,大臣上朝時(shí)舉的“笏”板,算數(shù)時(shí)用的“籌”,都是因?yàn)橹窈?jiǎn)的關(guān)系而造出來的字。
我們?cè)賮碚f一說“牘”。它是采用一塊平整的木板,在上面寫字或者畫上需要的地圖和紋飾樣子。因?yàn)槌叽绫容^大,所以用起來比較自由,不像簡(jiǎn)只能寫字。王充在《論衡》里寫的“斷木為槧,?之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就是制作木牘底板的過程。寫了字的木板叫做牘,還沒寫字的叫做槧。古人寫起文章來用字雖然少,可是意思一點(diǎn)兒也不馬虎。
說到牘,好像一般都附庸在簡(jiǎn)的后面,原因可能有兩個(gè)。一是簡(jiǎn)出現(xiàn)和使用的時(shí)間要遠(yuǎn)早于牘。從文獻(xiàn)和相關(guān)出土文物看,竹簡(jiǎn)大約從上古時(shí)代一直用到公元5世紀(jì)初,而木牘從秦漢時(shí)才出現(xiàn)。二是在使用數(shù)量上,牘也遠(yuǎn)不如竹簡(jiǎn)。木牘一般單片使用,也有數(shù)片編連成“札”的,但不普遍。牘主要用于政府公文性質(zhì)和書信函柬,長(zhǎng)篇著述一般還是使用簡(jiǎn)。劉禹錫《陋室銘》名句“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正是以案牘代指公務(wù)文件。今天我們也用尺牘代指書信,“尺牘書疏,千里面目”,就算遠(yuǎn)隔千里,收到故人來信,見字如面也備感親切。
責(zé)編:何建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