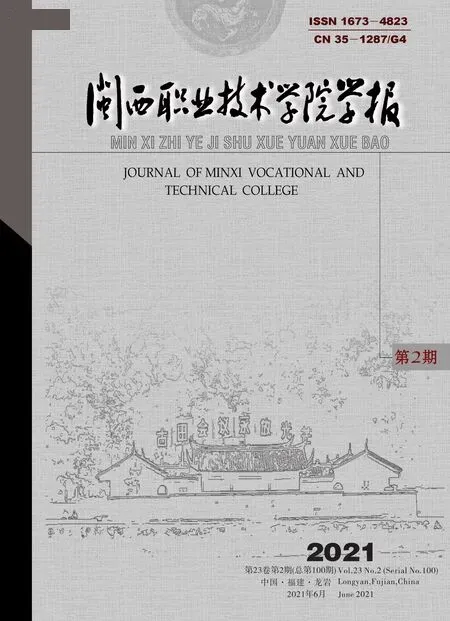漢語二語課堂互動中糾錯反饋及其有效性研究
徐順錦
(上海大學 文學院, 上海 200444)
糾錯反饋是語言課堂互動中十分重要的一個環節。很多實證研究都表明,糾錯反饋對學習者二語的習得有積極的作用。在過去的三十年,國外許多研究者對二語課堂中糾錯反饋的使用情況進行了大量的觀察與研究。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Lyster 和Ranta對加拿大法語沉浸式課堂的觀察和分析,根據“課堂糾錯分析模型” 將糾錯反饋分為了六種: 明確糾正(explicit correction)、 重述 (recast)、 元語言線索(meta-linguistic clue)、重復(repetition)、誘導(elicitation)和澄清請求(clarification request)[1]。之后,Lyster又把元語言線索、重復、誘導和澄清請求這四種統稱為“提示”(prompt),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形式協商”(negotiation of form)[2]。 Lyster 和 Ranta 的研究和發現為后來的二語課堂糾錯反饋研究提供了借鑒模式。 因而,在對外漢語學界,張歡、祖曉梅、鮑蕊等人的研究基本上沿用了Lyster 和Ranta 的理論框架和分類模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3-5]。不過從已有的研究來看, 有關漢語二語課堂的糾錯反饋研究主要集中在初級漢語課堂或口語課堂等單一水平或課型上, 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 基于此, 本文借鑒了Lyster 的“三分法”,將糾錯反饋策略分為明確糾正、重述和形式協商,并以“課堂互動”作為研究的出發點,拋開語言課型的限制,希望能夠較為全面地分析比較現階段不同水平的漢語二語課堂互動中教師糾錯反饋的使用情況, 并對以下兩個問題進行討論回答。 一是在漢語二語課堂互動中教師糾錯反饋使用情況是怎樣的,反饋率是多少,各個策略的占比又分別是多少, 與學習者的語言水平和錯誤類型是否有對應關系;二是哪種糾錯反饋策略更有效,更能引起學習者的理解回應,修正率更高。
一、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
筆者選擇了華東師范大學漢語強化項目寒假班的12 位漢語教師的24 節課(共18 小時)作為調查分析的對象。 這些漢語教師都具有較為豐富的教學經驗(3 年以上),在期末評估中也頗受好評。 被觀察的班級共有6 個,包括初級、中級和高級三個水平,主要有綜合課和口語課兩種基礎課型。 學習者來自不同的國家,以韓國、日本、美國為主,還有部分來自泰國、印度尼西亞、新西蘭、新加坡等國家。他們參加華東師范大學的寒假短期項目,為期三周。學習者們的學習態度都很積極,平時的學習時間也相差無幾,可以在較大程度上排除個人因素對研究結果的影響。而且教師、學習者和課程的構成與中國國內漢語教學的現狀基本相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研究方法和步驟
本研究采用的是非參與性課堂觀察的方法。 研究者隨堂聽課,用錄音筆錄音,并做筆記,但不參與課堂教學環節, 對觀察課堂中的變量也沒有進行任何的控制和引導。而且為了保證語料的真實性,課堂觀察前并未告訴教師所要觀察的內容, 也沒有和該教師討論過與糾錯反饋相關的問題。 在集中觀察之后,筆者對12 位教師的課堂錄音進行了文字轉寫。
在轉寫過程中, 因為研究對象是課堂互動過程中的糾錯反饋, 所以轉寫的內容主要包括學習者的語言錯誤、 教師的糾錯反饋和學習者的回應這三部分,至于教師的領讀、學習者讀課文和交際活動并不包括其中。每位學習者的語言錯誤、教師的糾錯反饋和學習者的回應都可構成一個“片段”。隨后對該“片段”進行標注。 按照語言錯誤的類型,分別標注為語音錯誤、詞匯錯誤和語法錯誤。其中語音錯誤包括發音及聲調的錯誤,如“* 我家有四(shí)口人”;詞匯錯誤包括實詞和虛詞的誤用和漏用, 如 “*我家有四人”“*韓國歲”;語法錯誤則包括句子成分、句式、助詞等的誤用和漏用,如“*很高興我的生日晚會”“*我在飯店工作服務員”。 同樣的,教師的糾錯反饋也按照反饋的類型進行標注,分別為明確糾正、重述和形式協商。而關于學習者的理解回應,我們認為以下兩種情況可以看作學習者沒有理解回應: 一是教師在糾錯反饋后馬上繼續話題,或進入下一個話題,沒有給學習者回應的機會;二是在教師反饋后,學習者繼續話題,或者低頭做自己的事情,說明反饋沒有引起學習者的注意。其他的情況,如學習者在教師反饋后馬上重復或在教師的引導下自己說出正確的句子等都可以看作是理解回應。因此,分別標記為理解回應和未理解回應。而理解回應的結果也有兩個,以學習者是否輸出正確的目的語形式為判斷標準, 分別標注為修正(repair)和有待修正(need-repair)。
在對轉寫資料進行標注之后, 筆者對糾錯反饋的使用率、 分布情況和學習者的理解回應進行數據統計和分析。最后,筆者還請其他研究者對本研究糾錯反饋策略的分類和數據統計進行核查, 以確保分類和數據的準確性。
二、調查數據分析
在所觀察的24 節課中,學習者共出現了353 次錯誤。教師對這353 次錯誤進行了263 次糾錯反饋,平均糾錯反饋率是74.5%。
首先,從糾錯反饋的類型來看(見表1),在所提供的263 次糾錯反饋中,其中重述占162 次,形式協商占85 次,明確糾正只有16 次。重述占糾錯反饋總數的61.6%,是使用率最高的反饋策略。而明確糾正的使用率最少, 表明漢語教師在課堂上很少使用這一種直接的糾錯反饋方式。

表1 漢語教師糾錯反饋策略使用情況
如果按照學習者的語言水平做進一步的分類(見表2), 筆者發現三個水平組明確糾正占比率的差別不大, 中級水平組和高級水平組之間的差別也不大,存在較大差距的是初級水平組和中、高級水平組之間重述的占比率。 初級水平組的漢語教師明顯比中、高級水平組的教師更依賴重述這一反饋策略,占比率高達70.9%。 在中、高級水平組中,形式協商這一反饋策略的占比率也有所增加,分別為39.8%和36.3%,明顯高于初級水平組的23.3%。 此外,教師的糾錯反饋率隨著學習者語言水平的提高也有明顯的下降趨勢, 從初級水平組的88.0%到高級水平組的64.2%。

表2 不同水平組糾錯反饋策略的分布情況
其次,從語言錯誤類型來看(見表3),在所有的糾錯反饋中, 語音錯誤是學習者發生率最高的 (占36.3%),接著是語法錯誤(占34.3%)。 但語音錯誤的反饋率卻是最低的,只有54.7%;反饋率最高的是詞匯錯誤,高達87.5%。兩者之間差異顯著。語法錯誤的反饋數量最多,占全部反饋總數的38.8%。
依據教師在面對不同錯誤類型時所具體使用的的糾錯反饋策略做進一步的分析(見表4),發現教師在處理語音錯誤時基本上只用重述這一反饋策略,占比高達94.2 %;在處理語法錯誤和詞匯錯誤時,也是以重述為主,分別占該錯誤類型的49.5%和50.0%, 不過形式協商的占比較之語音錯誤有顯著提升,分別為42.8%和43.1%。
當筆者再按照學習者的語言水平對表3 和表4做進一步的描述分析時(見表5),發現在語音錯誤上,無論是初級、中級或高級,在糾錯反饋策略的選擇上并無差別,重述是他們的第一選擇,只會隨著學習者語言水平的提高而減少在語音錯誤上的反饋,從初級水平的83.1 %的反饋率減少到高級水平的14.8%; 詞匯錯誤的反饋率則一直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重述也始終是詞匯錯誤的主要反饋手段;對語法錯誤的反饋則具有一個起伏的過程, 初級水平的時候以重述為主,占比為50.0%,在中級水平的時候,形式協商的占比一度超過了重述,為52.5%,但到了高級水平時, 又重新變成以重述為主, 占比達60.7%,比初級水平重述的占比還高,而且反饋率也大幅度降低,為65.1%。

表3 語言錯誤類型與教師糾錯反饋的分布情況

表4 語言錯誤類型與糾錯反饋策略的分布情況

表5 不同水平組語言錯誤類型與糾錯反饋策略分布情況
最后,從學習者的理解回應及修正來看,在提供的語料中,學習者理解回應的“片段”總數為161 個,占所有糾錯反饋的61.2%。 其中,學習者修正的“片段”為119 個,占所有糾錯反饋的45.2%。 與國內外同類研究相比,這樣的比例并不高。 此外,重述是引起理解回應率最低的反饋策略,只有55.6 %。而形式協商是三種反饋策略中最高的, 理解回應率占69.4%,修正率占44.7%,另有待修正、需要教師進行二次糾錯的占24.7%。另外,還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使用率最低的明確糾正, 無論是理解回應率還是修正率都相當高。
三、相關問題的討論
(一)漢語二語課堂互動中教師糾錯反饋情況
首先, 在糾錯反饋率上,12 位教師對學習者的錯誤都比較敏感,平均反饋率達到了74.4%,明顯高于Lyster 和Ranta 以西方語言為研究對象61%的平均反饋率。再結合國內的同類研究,調查分析發現漢語二語課堂中教師的反饋率普遍高于西方的語言課堂, 這一方面反映了漢語二語課堂以語法形式為中心的教學特點, 另一方面也提醒我們的漢語教師需要更加關注課堂中糾錯反饋的問題。
其次,在糾錯反饋策略的選擇上,在教師所用的三種糾錯反饋策略中,重述所占的比例是最高的,高達61.6 %; 明確糾正所占的比例是最低的, 只有6.1 %。其中,教師提供正確的目的語形式的反饋(重述和明確糾正)合計67.7%,不提供正確的目的語形式引導學習者進行自我糾正的形式協商所占比例僅為32.3%,前者是后者的兩倍有余。許多國外的研究表明,重述是交際性語言課堂最常用的反饋策略,具有糾錯時提供正確的目的語形式、 不會打斷言語交際和課堂節奏、不會損害學習者學習積極性等優點。結合本次研究和國內同類研究的結果發現, 重述也是漢語課堂最常用的反饋策略。這表明,漢語二語課堂雖然是以語法形式為中心, 但是同樣十分重視語言的交際功能,對學習者的情感反應也非常關注。
(二)不同水平組之間漢語教師糾錯反饋情況
從表2 可以看出,在糾錯反饋率上,不同水平組之間差異很顯著。其中,初級水平組的反饋率是最高的,為88.0%。 之后隨著學習者語言水平的提高,反饋率有所下降。 Chaudorn 曾指出,越強調語法,糾錯的頻率就會越高[6]。 在漢語教學中,初級水平的教學主要以句型講解和操練為主, 所以糾錯反饋率會比較高。 中級和高級水平組會慢慢多出一些諸如角色扮演、討論等更強調交際性的練習,學習者語言的輸出變得更自由也更復雜, 教師為了保證話題的完整性,往往會有意忽略掉一些錯誤,導致整體的反饋率下降。由此可見,漢語教師在對初級水平的學習者進行教學時, 需要加倍關注課堂上自身的糾錯行為和反饋策略。另外,調查分析還發現初級水平的學習者因學習內容有限,語言錯誤比較集中,也比較容易預判。 這便要求初級班的漢語教師應該熟悉學習者常見的一些語言錯誤,并提前想好相應的糾錯策略,使學習者的語言錯誤可以得到更有效的處理, 促進學習者漢語的習得。
在糾錯反饋策略的選擇上, 對于初級水平的學習者,教師多采用重述這一糾錯策略;對于中、高級水平的學習者,教師使用形式協商的頻率明顯增多。產生這種變化的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兩點:一是初級水平組的學習者語言能力還比較低, 在教師用形式協商進行引導時并不能很好地理解和配合,而中、 高級水平組的學習者隨著語言能力的提高可以更好地回應教師的引導, 同教師進行一定的協商互動,然后自我糾正;二是初級水平的學習者語音錯誤比較多,而語音錯誤多采用重述策略進行反饋,而隨著學習者語言水平提高,語音錯誤逐漸減少,教師對語音錯誤的容忍度也在提升, 形式協商的使用率便相應地提高。
此外,通過課堂觀察發現,就漢語教師糾錯反饋時的課堂氛圍而言,中級水平組的氛圍會比較好。教師會盡可能地運用多種反饋策略, 引導學習者進行自我糾正,說出正確的句子。 在整個互動過程中,學習者既意識到自身的語言錯誤, 又有正確的目的語形式的輸出,且很少會有情感上的挫敗感。在初級水平組這種友好的協商互動則相對少見。 重述策略的大量使用,使整個糾錯過程變得模式化、機械化。 很多學習者并沒有意識到語言錯誤所在, 只是機械性地重復教師的話語。而在高級水平組,因為學習者語言水平的提高,出現的語言錯誤也變得復雜起來,特別是近義詞辨析類的錯誤, 有時候教師很難馬上進行回答和有效的引導, 此時重述策略便又成了一個很好的選擇。 這也反過來要求漢語教師需要時時刻刻記得提高自身的專業素養和知識儲備。
(三)面對不同語言錯誤類型時漢語教師糾錯反饋情況
如表3、表4、表5 所示,在糾錯反饋率上,不同語言錯誤類型之間也存在著顯著差異。 學習者發生的錯誤最多的是語音錯誤, 但語音錯誤的反饋率卻是最低的,僅為54.7%。而且按照學習者的水平分組發現,大部分的語音糾錯集中在初級水平組,中、高級水平組的語音糾錯反饋率相當低。 而詞匯錯誤的反饋率是最高的, 在詞匯錯誤中有87.5%的錯誤得到了反饋。另外,語法錯誤的反饋數量是最多的。 這種現象說明, 漢語課堂較之西方以交際為中心的語言課堂而言,與語言流利度相比,漢語教師更加重視學習者語言的準確度。
在糾錯反饋策略的選擇上, 語音錯誤多采用重述策略, 占比高達94.2 %。 這一結果大大超過了Lyster 研究中64%的占比率。由此可以看出,漢語教師在語音糾錯上手段比較缺乏,極為依賴重述策略。當然,出現這種結果,一是語音的學習和準確性確實依賴于對母語者的模仿, 教師使用重述策略進行語音糾錯其實并不存在理論上的問題; 二是對于教師而言, 重述也確實是最為簡單而且被證實有效的糾錯方法。 但是,從課堂觀察中發現,重述反饋的糾音效果確實不太理想,特別是對于學習者的那些已經開始僵化的語音錯誤, 比如泰國學生經常產生偏誤的“zh”“ch”“sh”和“j”“q”這些音,達不到糾錯的目的。
詞匯錯誤和語法錯誤的反饋情況差不多, 雖然重述策略的使用率還是高于形式協商, 但相較于語音錯誤,形式協商的使用率已有顯著的提升。 不過,在Lyster 研究中, 詞匯錯誤反饋的主要策略是形式協商,使用率為55%,高于重述的38%[2]。 洪蕓在以漢語二語課堂作為調查對象的研究中也得出相似的結論,詞匯錯誤多采用協商類糾錯方式[7]。 對于詞匯反饋為什么要較少采用重述策略,Lyster 給出的解釋是,如果使用重述,學習者可能誤認為教師只是提供了另一種說法,而沒有意識到自身的錯誤,達不到糾錯的效果[2]。 結合課堂觀察,筆者認為Lyster 的這一解釋是成立的,面對詞匯錯誤時,特別是中、高級水平學習者的詞匯錯誤, 重述策略比較容易引起學習者的誤解。 而我們的觀察結果也反映出在詞匯錯誤的糾錯上, 漢語教師并沒有充分考慮到語言錯誤類型的特性, 存在著糾錯過于隨意和糾錯手段單一的問題。
在語法錯誤的反饋中, 重述仍然是最主要的策略,這與Lyster 的研究結果一致。 在漢語課堂中,語法錯誤的反饋數是最高的, 且語法錯誤的類型和成因最為復雜, 因此對語法錯誤采用什么反饋策略便受到教師的糾錯理念、專業知識、教學技巧以及學習者語言水平等因素的制約。如表5 所示,初級水平組的教師多采用單一的重述策略, 這是因為初級水平組學習者的語言水平不能很好配合教師的引導。 當學習者具備了一定的語言知識以后,如中級水平組,便可以使用形式協商對其進行引導和自我糾正,因此形式協商的使用率在此時高于重述。 不過到了高級,學習者的語法錯誤變得更加復雜和難以解釋,重述就又成了教師使用最多的反饋策略。
(四)糾錯反饋策略的理解回應和修正率情況
理解回應指的是學習者緊跟在教師的反饋之后的話語, 可以看作是學習者正確理解教師的糾錯意圖之后的回應, 也是測量糾錯反饋有效性的一個重要的依據。在三種糾錯反饋策略中,明確糾正的理解回應率是最高的,而且修正率也是最高的。 不過,很多漢語教師考慮到學習者的情感因素認為明確糾正太過于直接,可能損害學習者學習語言的積極性,所以在課堂上避免使用明確糾正。那么,在漢語二語課堂中,是否應該使用明確糾正,其實在Ellis 和Sheen的研究中曾提到過直接糾錯和間接糾錯都有助于二語的習得。直接糾錯一般來說比間接糾錯更為有效,因其具有凸顯性的特點, 學習者可以明確知道自己錯了,然后錯在哪里[8]。在本研究中,如果就以學習者的理解回應和修正作為判斷標準的話, 明確糾正這一典型的直接糾錯也確實要優于重述這一典型的間接糾錯。 當然,由于研究中明確糾正的樣本量較少,雖然調查分析中不能直接得出此類結論, 但是對于明確糾正不能一味地持否定態度。況且在祖曉梅、馬嘉儷、符琦、夏遠飛等關于學習者對糾錯反饋態度的問卷調查中顯示, 絕大多數學習者并不討厭明確糾正這一反饋策略, 反倒希望教師能夠明確指出他們語言中的錯誤[9-11]。 因此,調查中需要重新審視明確糾正的糾錯效果。
相比于明確糾正, 使用率最高的重述引起的理解回應率卻是最低的,僅為55.6%,也就意味著有近一半的重述反饋是未被理解回應的。 而在Lyster 和Ranta 的研究中,重述的理解回應率甚至只有31%。在國內同類實驗中, 引起理解回應率最低的反饋方式也是重述。 這也驗證了前面提到的重述策略可能引起學習者的混淆, 容易使學習者無法確定教師糾錯的目的,從而無法給出回應。 相比之下,形式協商的理解回應率明顯高于重述。 這是因為重述是教師單方面的行為, 而形式協商則更強調師生雙方的互動,教師將問題又重新反饋給學習者,這就要求學習者必須給出回應。
數據中還顯示, 形式協商的有修正率要高于重述。 這里需要注意的是重述的修正同形式協商的修正有很大的不同。重述反饋的修正,學習者很大程度上只是簡單地重復教師提供的正確的目的語形式。而形式協商的修正,更傾向于學習者的自我糾正,學習者需要對句子進行深度加工, 找出自己的中介語與目的語之間的差距, 然后還有一個再次輸出的過程。正因為如此,形式協商有待修正的比率會高于重述。而明確糾正和重述一樣,都是教師提供正確的目的語形式,沒有給學習者進行自我修正的機會。由此我們認為, 形式協商引起的學習者理解回應及修正的效果從整體上來講是要優于提供了正確的目的語形式的重述和明確糾正的。
四、結語
通過以上對漢語二語課堂互動中教師糾錯反饋使用情況,及其與學習者語言水平、語言錯誤類型和理解回應之間的關系的分析和討論, 筆者得出了以下幾點結論。
(一)在漢語二語課堂中,教師對學習者的語言錯誤比較敏感,尤其是對于初級水平的學習者,教師的糾錯反饋率是最高的, 之后隨著學習者語言水平的提高,反饋率明顯下降。
(二)在明確糾正、重述和形式協商三種反饋策略中,重述的使用率是最高的,特別是對于初級水平的學習者。 對于中、高級水平的學習者,教師使用形式協商比例顯著提高,但重述還是首要選擇。
(三)漢語教師面對不同的語言錯誤類型時,語音錯誤基本上只用重述策略進行糾錯, 效果并不理想。在詞匯和語法錯誤上,形式協商的使用率有明顯的提升,不過重述依舊是首要選擇。
(四)形式協商的理解回應率和整體的修正效果要優于重述和明確糾正。 因為后兩種方式都是教師提供正確的目的語形式, 沒有給學習者自我修正的機會。
此外, 筆者還發現漢語二語課堂互動中的糾錯反饋現階段存在著過于依賴重述策略、 教師糾錯過于隨意和單一、 缺乏相應理論的指導這些問題。 因此,在漢語二語教學過程中,漢語教師需要更加關注自身在課堂互動中的糾錯反饋,多使用形式協商,積極引導學習者進行自我修正。 特別是對初級水平的學習者,教師應減少對重述策略的過度依賴,鼓勵學習者對反饋作出積極的回應。而在語音錯誤方面,漢語教師應嘗試其他的糾錯策略, 從發音部位和原理上對語音錯誤進行解釋和糾正, 而不是一味地重復和機械式地模仿。另外,漢語教師還應積極主動地去了解一些糾錯反饋的相關理論知識和最新的研究成果,用來指導自己在課堂上的糾錯行為,提高課堂糾錯的有效性,使學生的語言錯誤得到更好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