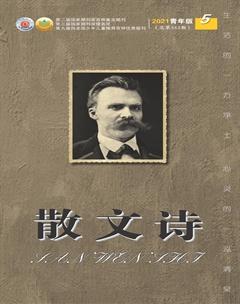桂冠七詩葉
陳黎譯

主持人:姚 風
主持人語:臺灣優秀的詩人和翻譯家陳黎先生從花蓮為我們送來一組異常精彩的譯詩,作者都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獲獎者,大家對這些名字應該不會感到陌生。智利女詩人密絲特拉兒在愛的絕望中把心跳嫁接給杏樹,孤絕地讓生命繼續生長;慣于旋轉意象萬花筒的聶魯達顯得克制內斂,一縷芳香穿越記憶,空靈得彌久不散;米沃什寫的也是記憶,記憶中的“相逢”引起的卻是詩人對生命的消逝的感嘆和驚奇;相比之下,布羅茨基卻跋涉于離別的苦痛中,他的愛情充滿流亡的悲苦;希尼是幸福的,他沿著紐扣跑進蜜月,卻沒有說為什么一個回望就將萬劫不復;特朗斯特羅姆慣用冷峻的詞語,卻難得地寫到了笑臉和快樂,而辛波斯卡再一次露出她那譏諷的微笑,溫和中蘊含著對世事的洞明。
194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密絲特拉兒(Gabriela Mistral,1889-1957,智利)
為杏樹修枝
我用一只純潔無瑕的手
為伸向天際的纖細杏樹修枝,
感覺我親愛的臉頰觸到了
充滿渴望的輕飛的面容。
仿佛創作著一首
嘔心瀝血的真實的詩,
我敞開心胸,接收
春天豐沛澎湃的血液。
我的胸膛把我的心跳傳給杏樹,
樹干在隱秘的木髓里聽到了,
我的心仿佛一支深入的鑿子。
所有愛我的人都已離我而去,
在一棵杏樹里維持生命
是我的心對世界唯一的貢獻。
197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聶魯達(Pablo Neruda,1904-
1973,智利)
香 襲
紫丁香的
芬芳……
我遙遠童年明澈的黃昏,
如平靜的水流般流動著。
而后一條手帕在遠處顫抖。
絲綢的天空下閃爍的星星。
再無其他。漫長的流浪中疲憊
的腳
以及一種痛感,一種咬住不放、
不斷加劇的痛感。
……在遠處,鐘聲,歌聲,悲
傷,渴望,
眼瞳如此柔美的少女們。
紫丁香的
芬芳……
198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米沃什(Czeslaw Milosz,1911-
2004,美國)
相 逢
黎明時我們乘著馬車穿過冰封
的田野。
一只紅翅膀在黑暗中升起。
而突然一只野兔從路上跑過。
我們中有一人用手指著它。
那已經很久了。今天他們都已
不在世間,
那只野兔,或者那指手的人。
噢,親愛的,它們何在,它們
去向何方,
那手的一閃,那行動的飛馳,
那卵石的沙沙聲。
我詢問,并非出自悲傷,而是
感到驚奇。
198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美國)
愛
今夜我兩度醒來,
走向窗口。街燈是
夢中囈語的片斷,
像刪節號一般,無頭無尾,
不曾帶給我慰藉或歡愉。
我夢見了你,懷著孩子。而今,
在相隔兩地,在相隔、
受罪這么多年之后,我的雙手,
歡喜地輕拍著你的腹部。
卻發覺它們摸弄著的只是我自
己的褲子,
以及電燈開關。緩步走向窗口,
我明白你并不在我的身邊,你
孤守在
遠方。在黑暗中,在夢里,你
耐心地
等候著我歸返的時刻,
一點也不責備這不合情理的
斷絕。因為在那被光打醒的
持續的黑暗里,
我們曾結婚,結合,扮演
雙背的野獸——孩子們
可以為我們的赤裸見證。
在未來的某一夜,你將再度
走向我,如今已疲憊而瘦削,
我將看見尚未命名的我的
兒子或女兒——這回我將
不再急著找電燈開關,不再
移動我的手。因為我無權
置你于那寂寥的陰影之域,
讓你守候在時日的欄柵前,
從有我的現實變成無依無靠
——再也觸不到我。
199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希尼(Seamus Heaney,1939-
2013,愛爾蘭)
地下鐵
我們在那有著圓頂的隧道里奔
跑,
穿著蜜月外套的你飛速向前,
而我,于是像敏捷的神急急
追趕你,在你變成一根蘆葦或
一抹緋紅潑染的新品種白花之
前。
你的外套狂野地拍動,紐扣
一顆接一顆彈脫,掉落在
地鐵和艾伯特廳之間的路上。
度蜜月,月光下秘會,沒趕上
音樂會,
我們的回聲消逝于那回廊,現
在
我仿佛韓賽爾踩著月下的石子
循原路折返,我撿起一顆顆紐
扣
來到通風佳、燈火明的車站。
列車離站后,潮濕的鐵軌
裸露、緊繃如我,全心注意
你跟隨在后的腳步,一旦回望
就萬劫不復。
199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辛波斯卡(Wislawa Szymborska,1923-2012,波蘭)
離 婚
對孩子而言:第一個世界末日。
對貓而言:新的男主人。
對狗而言:新的女主人。
對家具而言:樓梯,砰砰聲,
卡車與運送。
對墻壁而言:畫作取下后留下
的方塊。
對樓下鄰居而言:稍解生之無
聊的新話題。
對車而言:如果有兩部就好了。
對小說、詩集而言——可以,
你要的都拿走。
百科全書和影音器材的情況就
比較糟了,
還有那本《正確拼寫指南》,里
頭
大概對兩個名字的用法略有指
點——
依然用“和”連接呢
還是用句點分開。
201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特朗斯特羅姆(Tomas Transtromer,1931-2015,瑞典)
C大調
他在幽會之后下樓走到街上,
此時空中白雪紛飛。
在他們互相依偎之時,
冬天已然來臨。
夜晚白光閃耀。
他的步伐輕快愉悅。
整座城都是下坡路。
身旁滿是笑意——
豎起的衣領的后面是一張張笑
臉。
自由自在!
所有的問號開始歌贊上帝的存
在。
他如是想著。
音樂突然響起,
在飛舞的雪中
邁開大步。
一切都朝C音前進。
一個指向C音的顫抖的羅盤。
超脫痛苦的一個小時。
輕輕松松!
一張張笑臉在豎起的衣領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