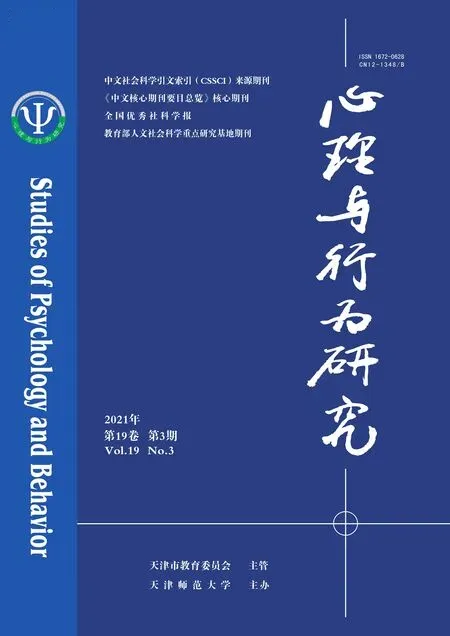家庭親密度對高中生心理健康的影響:有調節的中介模型*
魏靈真 劉衍玲 劉傳星 林 杰 王 旭
(1 西南大學心理學部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重慶 400715)
(2 四川省教育科學研究院德育與心理健康教育研究所,成都 610225)
1 引言
2016年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等22部委聯合發布的《關于加強心理健康服務的指導意見》指出,心理健康是影響當今社會發展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鼓勵社會各界加強與心理健康相關的科學研究。研究顯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呈下降趨勢(辛自強, 張梅, 2009),且高中生的心理健康問題尤為突出(辛自強, 池麗萍, 2020)。高中生常見的心理問題為焦慮、抑郁、孤獨、自卑等,會導致學生學業成績下降、人際交往受挫(Maurizi, Grogan-Kaylor, Granillo, & Delva, 2013),甚至出現自殺行為(陳偉, 程誠, 楊麗, 劉新春, 劉海玲, 2016)。鑒于高中生日益嚴重的心理問題,探索高中生心理健康的影響因素至關重要。
生態系統理論(Bronfenbrenner, 2005)認為,人的心理發展是環境因素與個體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在環境因素上,家庭是直接影響青少年心理發展的微系統之一,相對于其他家庭變量(如家庭教養方式、親子溝通等),家庭親密度更能夠衡量家庭的整體氛圍,是反映積極家庭氛圍及家庭成員之間親近關系的綜合指標(劉世宏, 李丹,劉曉潔, 陳欣銀, 2014)。此外,中學生所接觸的環境并不僅限于家庭,學校中的教師和同伴也在其心理發展中占有重要地位(Hernandez, 2000; Torres &Hernandez, 2009),并且主要體現在社會支持上。而社會支持同樣是心理健康的重要預測變量之一,對促進個體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作用(Cohen &Wills, 1985)。在個體因素上,生命意義感是人生的重要體驗,探索與尋求生命意義感是人類的基本動機之一,也是影響個體心理健康的關鍵因素(van Tongeren & Green, 2010)。因此,本研究將從環境因素(家庭親密度、社會支持)與個體因素(生命意義感)入手,探討高中生心理健康的影響因素。
家庭親密度(family cohesion)是指個體感受到的與家庭成員的情感聯結程度(劉世宏等,2014)。家庭親密度會影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狀況。研究表明,家庭親密度能夠顯著預測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和適應狀況(李兵寬, 劉啟輝,2012)。家庭親密度較低會導致青少年表現出更多的焦慮(Bernstein & Borchardt, 1996)、抑郁(徐潔, 方曉義, 張錦濤, 林丹華, 孫莉, 2008)、孤獨(任澤鑫, 2020)和適應不良(劉世宏等, 2014)等心理問題。而且,家庭親密度對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問題行為(如吸煙、酗酒、物質濫用等)也起到了關鍵作用(Cumsille & Epstein, 1994)。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1:家庭親密度能夠促進高中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生命意義感(meaning in life)是個體對自己及其存在的本質和對那些自認為重要的事物的感知和覺察(Steger, Frazier, Oishi, & Kaler, 2006)。根據生命意義感的關系性,生命意義感是個體在其主觀世界上所建構的自己與周圍人、事、地、物等的關系,個體的關系結構是生命意義感的重要來源(Heine, Proulx, & Vohs, 2006)。其中,家庭關系是個體最重要的社會關系之一,而家庭親密度則是反映個體家庭關系是否良好的重要指標。實證研究表明,家庭關系是個體生命意義感的重要來源(Lambert et al., 2010),良好的家庭親密度能夠有效預測個體的生命意義感(程建偉, 楊瑞東,郭凱迪, 顏劍雄, 倪士光, 2019; 申琳琳, 張鎮,2020)。此外,生命意義感可以促進個體的心理健康水平(張榮偉, 李丹, 2018)。意義治療理論(維克多·弗蘭克爾, 2010)認為,生命意義的缺失會使個體感到無聊、空虛、厭煩等,并采用其他不良行為進行補償,如酗酒、暴力、違法行為等,而這些補償行為將進一步引發內心的矛盾,導致神經癥,甚至自殺。研究發現,高生命意義感有助于緩解個體的焦慮、抑郁水平(Yek, Olendzki,Kekecs, Patterson, & Elkins, 2017),提升生活滿意度(Steger & Kashdan, 2007)和幸福感(Ho,Cheung, & Cheung, 2010)。已有研究還發現,生命意義感能夠中介家庭親密度與心理健康的積極指標(如主觀幸福感)(申琳琳, 張鎮, 2020)、消極的童年期經歷與心理健康的消極指標(如抑郁)(于洪蘇, 段剛, 張廣清, 萬雪良, 2020)之間的關系。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2:生命意義感在家庭親密度與心理健康之間具有中介作用。
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是個體對他人所給予的關心、幫助和支持的認知與評價(葉俊杰,2005)。根據生命意義感的維持模型(Heine et al.,2006),生命意義感的獲取取決于個體的關系結構,當家庭層面的關系結構受到破壞時,個體會把其他層面的關系轉換過來補償被破壞的關系結構,以幫助自己維持和增強生命意義感。研究顯示,社會支持對個體的生命意義感具有顯著影響(劉亞楠, 張舒, 劉璐怡, 劉慧瀛, 2016)。社會支持水平不同的個體,其生命意義感水平高低存在明顯差異:相比于低社會支持個體,高社會支持個體的生命意義感明顯較高(陳秋婷, 李小青, 2015)。對于社會支持水平高的個體,即使家庭親密度較低,其生命意義感可能也不會降低或仍然能夠保持穩定。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3:社會支持在家庭親密度與生命意義感之間起調節作用。
根據社會支持的緩沖器模型,社會支持能夠通過調節其他因素對心理健康的消極影響,從而提高個體的心理健康水平(Cohen & Wills, 1985)。研究表明,高社會支持能夠顯著減少抑郁、焦慮、孤獨感等心理問題(Davidson & Adams, 2013;Wang, Mann, Lloyd-Evans, Ma, & Johnson, 2018)。而社會支持水平不同的個體,其心理健康水平也大有不同。例如,低社會支持會增加青少年抑郁的風險(Frison & Eggermont, 2015),擁有高質量友誼的青少年會出現更少的焦慮、抑郁等心理問題(Roeser & Eccles, 1998)。前文提到,生命意義感正向預測個體的心理健康水平,可以推測高社會支持個體相比于低社會支持個體的生命意義感更能夠預測其心理健康水平。已有研究證實了社會支持在人格特征與心理健康之間的調節作用(林初銳, 李永鑫, 胡瑜, 2004)。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4:社會支持在生命意義感與心理健康之間起調節作用。
有調節的中介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有調節的中介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采用整群抽樣法,選取四川省兩所高中1097名學生,以班級為單位進行集體施測,剔除無效問卷后回收有效問卷1020份,有效率為92.98%。被試平均年齡為16.22±0.98歲。其中男生429名(42.06%),女生591名(57.94%);高一359名(35.20%),高二306名(30.00%),高三355名(34.80%)。
2.2 研究工具
2.2.1 家庭親密度量表
采用費立鵬等人(1991)修訂的家庭親密度量表,共15題。采用5點計分(1代表“不是”,5代表“總是”),分數越高表明青少年的家庭親密度越高。該量表信效度良好,適用于多數中國家庭(劉世宏等, 2014)。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9。
2.2.2 中學生心理健康量表
采用王極盛、李焰和赫爾實(1997)編制的中學生心理健康量表,共60題,分為強迫癥狀、偏執、敵對、人際關系敏感與緊張、抑郁、焦慮、學習壓力感、適應不良、情緒不穩定、心理不平衡十個維度。采用5點計分(1代表“從無”,5代表“總是”),得分越高表明個體存在較多心理問題,心理健康狀況越差。該量表在中學生群體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石國興, 林乃磊, 2011)。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7。
2.2.3 領悟社會支持量表
采用嚴標賓和鄭雪(2006)修訂的領悟社會支持量表,共12題,分為朋友支持、家人支持和其他支持三個維度。采用7點計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7代表“完全同意”),分數越高表明青少年領悟到的社會支持程度越高。該量表的結構效度良好,χ2/df=4.84,RMSEA=0.08,GFI=0.94,CFI=0.92(葉寶娟等, 2018)。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4。
2.2.4 生命意義感問卷
采用王鑫強等人(2013)修訂的生命意義感問卷,共10題,分為擁有意義感和尋求意義感兩個維度。采用7點計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7代表“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青少年的生命意義感越高。該問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王文超, 伍新春, 田雨馨, 周宵, 2018)。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6。
2.3 統計分析
采用SPSS 20.0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描述統計和相關分析,采用Hayes(2013)開發的PROCESS for SPSS進行有調節的中介效應分析。
3 結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Harman單因素檢驗法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周浩, 龍立榮, 2004)。結果顯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15個,且第一個因子解釋的變異量為29.75%,小于40%的臨界標準,說明本研究中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可能性較小。
3.2 描述統計和相關分析
各變量的描述統計和相關分析見表1。結果發現:家庭親密度與心理健康呈顯著負相關,說明高中生家庭親密度越高,其心理健康問題越少。生命意義感與家庭親密度呈顯著正相關,與心理健康呈顯著負相關;社會支持與家庭親密度以及生命意義感呈顯著正相關,與心理健康呈顯著負相關。由于性別、年齡與本研究的主要變量相關顯著,在后續分析中將其作為控制變量納入分析。

表1 各變量的描述統計和相關分析
3.3 中介效應檢驗
根據溫忠麟、張雷和侯杰泰(2006)的建議,將所有變量標準化,在控制性別、年齡等變量后,檢驗生命意義感在家庭親密度與高中生生命意義感之間的中介作用。結果顯示,家庭親密度顯著正向預測生命意義感(β=0.31,t=10.52,p<0.001),且生命意義感(β=?0.20,t=?7.05,p<0.001)和家庭親密度(β=?0.40,t=?14.05,p<0.001)均可顯著負向預測心理健康。進一步采用偏差校正Bootstrap方法檢驗中介效應的顯著性,結果顯示,中介效應值為?0.06,SE為0.01,95%CI[?0.09, ?0.04],占總效應的13.04%。因此,生命意義感在家庭親密度與高中生心理健康之間的中介效應顯著。
3.4 家庭親密度與高中生心理健康的關系: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
根據溫忠麟和葉寶娟(2014)的建議,將所有變量標準化,考察生命意義感在家庭親密度與心理健康間的中介作用,以及社會支持在前半路徑和后半路徑的調節效應,結果見表2。

表2 有調節的中介效應分析
首先,檢驗家庭親密度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及直接效應是否受社會支持的調節。結果表明,家庭親密度顯著負向預測高中生的心理健康(β=?0.25,t=?7.83,p<0.001),家庭親密度與社會支持的交互項對心理健康的預測作用不顯著(β=?0.03,t=?1.17,p>0.05)。然后,建立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檢驗生命意義感的中介效應是否受社會支持的調節。結果表明:家庭親密度顯著正向預測生命意義感(β=0.14,t=4.06,p<0.001),家庭親密度與社會支持的交互項對生命意義感的預測作用顯著(β=0.11,t=4.37,p<0.001)。生命意義感顯著負向預測心理健康(β=?0.13,t=?4.53,p<0.001),生命意義感與社會支持的交互項顯著負向預測心理健康(β=?0.06,t=?2.44,p<0.05)。模型估計結果驗證了生命意義感在家庭親密度與高中生心理健康之間的中介作用,且這一中介作用的前半路徑和后半路徑均受到社會支持的調節。
為了進一步理解社會支持調節作用的實質,按照平均數上下一個標準差將社會支持進行高低分組并繪制簡單效應分析圖(見圖2、圖3)。結果發現,對于低社會支持的高中生,隨著家庭親密度的增加,其生命意義感無顯著變化(β=0.03,t=0.64,p>0.05);對于高社會支持的高中生,隨著家庭親密度的增加,其生命意義感顯著上升(β=0.26,t=5.78,p<0.001)。也就是說,家庭親密度對生命意義感的影響隨著社會支持的升高而增強,這表明社會支持可以增強家庭親密度對生命意義感的正向預測作用。隨著生命意義感的提升,對于低社會支持的高中生,其心理問題呈顯著下降趨勢(β=?0.09,t=?2.47,p<0.05);對于高社會支持的高中生,隨著生命意義感的提升,其心理問題表現出更強的下降趨勢(β=?0.22,t=?5.87,p<0.001)。也就是說,生命意義感對心理健康的預測作用隨著社會支持的升高而增強。

圖2 社會支持對家庭親密度與生命意義感的調節作用

圖3 社會支持對生命意義感與心理問題的調節作用
4 討論
4.1 家庭親密度與高中生心理健康的關系
本研究發現,家庭親密度顯著負向預測高中生的心理問題,家庭親密度越高,其心理健康狀況越好。這一結果證實了研究假設1,說明家庭親密度對高中生心理發展的重要性,且與以往的研究結果一致(雷榕, 鎖媛, 李彩娜, 2011)。家庭親密度是個體感知到的與家庭成員之間情感聯系的程度,是家庭功能的重要組成部分(李藝敏, 李永鑫, 2018)。與低家庭親密度的個體相比,處于高家庭親密度的個體更傾向于以成熟穩重的方式處理問題,以積極向上的心態面對生活(馬喜亭, 李冉, 鄧麗芳, 2009)。因此,當他們遇到負性生活事件時,能夠更加從容地應對和解決問題,更少出現焦慮、抑郁情緒,從而表現出較高的心理健康水平。
4.2 生命意義感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發現,家庭親密度也可以通過生命意義感間接預測高中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即生命意義感在家庭親密度與心理健康之間起中介作用。這一結果證實了研究假設2,顯示了生命意義感對高中生心理健康的重要作用。高家庭親密度的個體在家庭中與其他家庭成員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能夠從家庭中得到足夠的愛和溫暖,更有歸屬感和安全感,有利于個體積極地探索和尋求生命的意義(馬茜芝, 張志杰, 2020),能夠提升個體對生命意義的感知(Lambert et al., 2013)。同時,生命意義感作為最重要的一種壓力應對資源,能夠緩解壓力對心理健康的消極影響(Halama, 2014),促使個體采取更加積極、更具適應性的應對方式(Aldwin, 2007),提升個體的心理彈性、幫助個體積極適應壓力環境(Fife, 2005; Grotberg, 2003),從而對個體的心理健康起到一定的保護作用。
4.3 社會支持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發現,社會支持在家庭親密度與生命意義感之間的調節作用顯著,證實了研究假設3。隨著個體社會支持水平的提升,家庭親密度對生命意義感的預測作用顯著增強。生命意義感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穩定的關系結構(Heine et al., 2006)。社會提供理論認為,家庭、朋友、教師都是青少年心理發展的重要社會資源,當一種社會關系發展不良時,個體會轉向其他社會關系以補償不良社會關系所帶來的消極影響(Furman & Buhrmester,1985)。對于高社會支持水平的個體,即使家庭親密度較低,其生命意義感也仍然能夠維持。這是因為盡管家庭層面的關系結構不穩定,但是來自朋友、教師等重要他人的社會支持彌補了家庭的缺失,有助于個體形成穩定的關系結構,從而提升了個體的生命意義感。對于高中生而言,隨著社會化的進程,其自主性和獨立性不斷發展,朋友、教師等重要他人對個體的影響逐漸增強(趙金霞, 趙景欣, 王美芳, 2018)。
本研究還發現,社會支持在生命意義感與心理健康之間的調節作用顯著,證實了研究假設4。相對于低社會支持水平高中生,生命意義感對高社會支持水平高中生的心理健康問題的預測作用更顯著,這一結果驗證了社會支持的緩沖器模型。對于高社會支持水平的個體,即使生命意義感較低,也能夠預測更低的心理健康問題,這是因為社會支持不僅能夠給青少年提供更多的社會資源,還能夠給予青少年更多的正性情感能量和有效的應對方式(史滋福, 謝云天, 2019),從而起到緩沖的效果,減少低生命意義感對其心理健康帶來的不利影響。
5 結論
(1)家庭親密度顯著負向預測高中生的心理健康問題;(2)生命意義感在家庭親密度和高中生心理健康之間起中介作用;(3)社會支持調節了生命意義感中介效應的前半路徑和后半路徑。隨著社會支持水平的提升,家庭親密度對生命意義感的正向預測作用、生命意義感對心理健康問題的負向預測作用顯著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