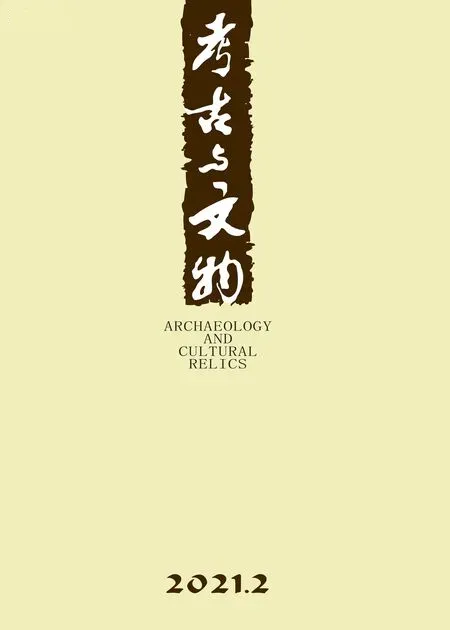半坡和姜寨出土仰韶文化早期尖底瓶的釀酒功能
劉 莉 王佳靜 劉慧芳
(1. 斯坦福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2. 斯坦福大學考古中心;3.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4. 西安半坡博物館)
近年來,考古學家對中原地區3個前仰韶時期遺址(舞陽賈湖、寶雞關桃園和臨潼零口;距今約9000~7000年)出土的小口鼓腹罐[1、2]和4個仰韶中晚期遺址(西安米家崖、高陵楊官寨、藍田新街和澠池丁村;距今約6000~5000年)[3-6]出土的小口尖底瓶進行了殘留物分析。這些研究采用科學方法直接分析陶器內殘留物,通過觀察其中淀粉粒、植硅體和真菌的形態,證明這些器物用于釀造以黍或稻米為主要原料的發酵酒精飲料,釀造方法包括谷芽酒和麹酒。但是這兩組釀酒器的年代并不銜接,有近1000年的缺環,此時正處于仰韶文化早期(距今約7000~6000年),是小口尖底瓶出現的時期。
與仰韶中晚期的大型尖底瓶有所不同,早期的尖底瓶以中小型為主。例如,根據姜寨發掘報告,仰韶早期的27件尖底瓶標本高度大多都在16.8~48厘米范圍之內,只有1件高度為74.4厘米;而2件仰韶晚期標本高度為57和74 厘米[7]。根據對10個仰韶文化遺址(臨潼姜寨、隴縣原子頭、高陵楊官寨、扶風案板、寶雞福臨堡、西安米家崖、秦安大地灣、陜縣廟底溝、洛陽王灣、靈寶西坡)[7-17]中62件尖底瓶高度數據的分析,29件仰韶早期尖底瓶中有26件(90%)高度在16.8~42厘米之間,只有3件(10%)高度在74.4~94.5厘米之間;仰韶中晚期的22件尖底瓶的高度均在39~87.5厘米范圍之內(圖一)。這些數據顯示,從仰韶文化早期至晚期,小口尖底瓶形制趨于向大型發展。雖然我們的前期研究已證實晚期的尖底瓶用于釀酒,但我們尚無法確認早期尖底瓶是否有類似的功能。

圖一 經殘留物分析有釀酒器的遺址分布及尖底瓶高度變化
小口尖底瓶(尤其是中小型)的功能是考古學家們長期爭論的問題,其主要觀點包括:汲水器[7、18]、凈水器[19]、干旱地區祭天祈雨的禮器[20]、盛酒的祭器或禮器[21]、釀酒器[22、23]及儲酒器[24]等。其中汲水器的觀點曾經最為流行,并編進中學教材[20],但是有學者在進行實驗后證明使用尖底瓶汲水并不十分實用[25、26]。
早期尖底瓶的功能分析對重建中國史前時期釀酒技術的起源和發展至關重要。西安半坡和臨潼姜寨是著名的仰韶文化遺址,代表了黃河流域新石器中期以粟作農業為基礎的環壕聚落。兩遺址的陶器組合中都有數量較多的小口尖底瓶。2017年,斯坦福大學考古中心與半坡博物館合作,對從半坡遺址(2件)和姜寨遺址(9件)出土的11件仰韶文化早期不同大小的尖底瓶標本進行了微植物和微生物殘留物的提取和分析,主要目的是檢驗谷物釀酒的證據。這些尖底瓶出土于成人墓葬、房址、灰坑及甕棺葬。出于墓葬的是隨葬品,均為中小型,基本完整;大型器出土于居住區,均破損。1件用于兒童甕棺的尖底瓶應為該器物的二次利用(圖二)。其中半坡尖底瓶標本屬于半坡類型,姜寨標本屬于姜寨I期和II期(半坡類型和史家類型)。對這兩個仰韶典型遺址中出土的尖底瓶殘留物分析有望提供比較全面的功能性資料,同時也可以檢驗在不同的埋藏環境中有機物的保存程度。

圖二 本文分析的半坡和姜寨出土尖底瓶
一、谷物發酵酒釀造過程及其殘留物特征
檢驗尖底瓶是否有釀酒功能,首先要了解發酵酒的釀造過程。谷物釀酒包括兩個過程:第一是糖化,通過淀粉酶的作用將淀粉轉化為糖;第二是發酵,通過酵母的作用將糖轉化為酒精和二氧化碳。利用富含淀粉植物(包括谷物和塊根植物)釀酒的基本方法有三種:(1)谷芽酒,首先將谷物發芽使酶得以活化,然后加熱水糖化,再利用酵母發酵。(2)麹酒,使用谷物制麹,有時加入某些植物莖葉或種子,稱為草麹。例如,江南地區普遍利用蓼草(Polygonum)制作小麹[27],臺灣原住民使用多種植物做麹,其中包括藜屬(Chenopodium)種子[28]。麹中含有多種微生物,包括霉菌、酵母和細菌(其中霉菌可以分泌多種酶),然后將麹拌入蒸熟或煮熟的谷物,糖化和發酵同時進行(并行復式發酵法),可達到更高的酒化度。(3)口嚼酒,首先口嚼谷物或塊根植物,利用人唾液中的酶達到糖化的效果,再利用酵母發酵[28-30]。
古代文獻中也有早期釀酒方法的記述。根據甲骨文的記載,商代至少有酒、醴和鬯三種酒[31]。周代文獻中對這些酒的釀造方法有了進一步說明。《尚書·說命》有“若作酒醴,爾惟麴糵”的記載。糵的意思是發芽谷物。明代宋應星著《天工開物》也說“古來麹造酒,糵造醴”。這些正是我們所說的麹酒和谷芽酒。先秦文獻中多處提到鬯,如《詩經·大雅·江漢》有:“厘爾圭瓚,秬鬯一卣”。毛傳解釋為:“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筑煮合而郁之曰鬯。”鬯為何種香草,自古以來眾說紛紜[32]。但是基本的共識為,鬯是黍加以某些草本植物釀造而成的酒,相當于后代所說的草麹釀酒。口嚼酒不見于先秦古代文獻,但近代民族學研究中多有記述,其中包括見于臺灣原住民的釀酒傳統[33]。
值得注意的是,這三種釀酒方法的主要區別在于糖化過程,而發酵都是利用酵母。小口尖底瓶有3個形制特點適于酵母進行發酵。首先,酵母存在于自然環境中,在合適的溫度、濕度及營養環境中會很快繁殖;但是需要在厭氧的環境中才產生酒精和二氧化碳。因此,用于釀酒的陶器一般為小口,以利于封口,形成厭氧環境[18、34]。小口尖底瓶的口部設計,與釀酒器皿需要封口與提供厭氧環境的要求相符。雖然尖底瓶的小口不便于倒進醪液,但是這一問題完全可以通過漏斗解決。其次,釀酒會產生大量渣滓,如原料中的谷殼、酵母等;小口尖底瓶底部呈錐狀體有利于渣滓的集中和沉淀。此外,由于酵母發酵時釋放二氧化碳并產生熱量,醪液中會出現上下的自然對流(convection currents);熱流從錐狀底部上升到醪液的上部,同時周圍溫度低的液體下降,形成循環運動模式;對流的過程最終使發酵容器內的液體溫度達到均勻,有利于保證酒的質量。液體的高度與自然對流的強度成正比;尖底瓶一般為瘦高型體,高度與直徑的比例基本都大于2:1,該特點可促進自然對流。這種錐狀體的設計也見于現代啤酒廠的筒形錐底發酵罐的形狀,經測試證明是啤酒發酵罐的最佳設計[35-37]。根據釀造發酵過程的原理,對陶器殘留物的特征及其中微植物和微生物的分析可以幫助我們鑒定釀酒使用的原料和釀造方法,列舉如下:
1.淀粉粒和植硅體分析有助于鑒定釀酒原料的種類。由于糖化過程需要在較高溫度下進行(65~70°C),會對淀粉粒造成特定的損傷和糊化特征,因此淀粉粒的損傷形態能夠提供是否經過發酵的信息。根據我們的釀酒實驗及觀察釀造過程中淀粉粒的變化,經過糖化發酵的淀粉粒的損傷特征為:表面有中心凹陷、裂痕及微型凹坑,有些顆粒的中心部分幾乎完全缺失,僅保存邊緣部分并在偏光鏡下顯示雙折射光澤,有些顆粒表面部分缺失、部分層紋暴露、也有些具有膨脹變形的糊化特征 ,消光十字模糊或消失等。這些損傷是淀粉酶分解以及糖化時加熱的綜合作用造成[38]。值得注意的是,器物上的淀粉粒也可能被土壤環境中存在的酶分解而出現損傷,如部分缺失、出現裂痕及微型凹坑等[39]。但是發酵過程形成特有的損傷特征,既有酶的分解,又有加熱造成的糊化特征。特別是那些中心部分缺失但邊緣部分仍存,并有雙折射光澤的糊化淀粉粒、最具代表性。這些發酵所造成的糊化與一般的蒸煮食物所造成的損傷糊化形態也有明顯區別;后者主要表現為淀粉粒比較均勻地向周邊膨脹,而不見中心部分缺失的現象[40、41]。釀酒過程中,在加入作為糖化劑的原料時(發芽谷物或麹),也加入經過蒸煮的谷物[29];因此在醪液中也會存在具有一般蒸煮特征的淀粉粒。
2.如果古代陶器盛裝的是谷芽酒,那么谷物的穎殼有可能保存在器物內壁上;因此可以根據殘留物中穎殼植硅體的存在進行判斷。對穎殼植硅體的種屬鑒定有助于了解釀酒使用的發芽谷物種類。這一方法已經運用在上述多項酒器殘留物的研究中[2、3、6、42、43]。必須指出,根據穎殼在陶器中出現推測釀酒方法有一定局限性。因為如果古人在加工谷物時沒有把谷殼脫凈,這樣也會在釀酒陶器殘留物中發現少量穎殼植硅體。
3.如果陶器盛裝的是麹酒,那么與酒麹有關的霉菌可能會保留在殘留物中。中國傳統釀酒使用的酒麹中的霉菌主要包括曲霉(Aspergillus)、根霉(Rhizopus)、紅曲霉(Monascus purpureus)及毛霉(Mucar)等[44、45]。霉菌的主要組成部分包括菌絲、孢子和孢子囊。霉菌由分枝或不分枝的菌絲構成,交織在一起的菌絲稱菌絲體。菌絲是霉菌營養體的基本單位,由孢子發芽而成。在菌絲的生長過程中,一部分化為孕育菌絲,頂端生出孢子囊,產生孢子。不同霉菌的菌絲、孢子囊和孢子的形態有別[46]。在古代標本中的霉菌如果保存的好,可以根據其形態特征進行初步鑒定。釀酒霉菌的最早證據來自寶雞關桃園遺址前仰韶時期的陶壺上,形態與曲霉和根霉相似[2]。另在澠池丁村仰韶中期尖底瓶的殘留物中發現有曲霉和毛霉[6]。
4.在制麹過程中加入某些野生植物莖葉或種子,是由于植物莖葉上會附著多種霉菌、酵母及細菌,能夠提供制麹過程中所需要的菌群[27、28]。關桃園前仰韶時期的釀酒陶器殘留物中有大量主要來自植物莖葉的棒型植硅體,與霉菌共存,應是利用草麹的結果[2]。因此,殘留物中存在較多莖葉植硅體應為使用草麹的證據。
5.無論哪種釀酒方法都需要酵母菌幫助發酵,因此酵母的存在是釀酒的重要證據。傳統釀酒所利用的酵母有多種,其中最常見的是釀酒酵母(Saccharomyces cerevisiae)。其形狀為圓形和橢圓形,長度大致為5~10微米。鑒定酵母的最好標志是芽殖狀態;芽殖是酵母菌最常見的繁殖方式,表現為細胞表面向外突出,長出芽體,逐漸增大到正常大小時,與母體脫離,成為一獨立細胞[46]。顯示出芽殖狀態的酵母細胞也發現在關桃園和丁村的釀酒陶器殘留物中[2、6]。
6.根據人類學家在非洲埃塞俄比亞的調查,當地民族有利用谷物釀造谷芽酒的傳統。釀酒的陶罐是專門制作并專用于釀酒發酵;每次發酵后剩在陶器中的渣滓要留到下一次釀酒時才洗,而且從來不將發酵罐完全清洗干凈,因為他們認為如果洗干凈會加速酒液對陶罐表面的侵蝕[47]。這種做法實際上會使一些釀酒原料留在器壁上,并滲入器壁內,使微生物(例如酵母)在發酵罐中得以保存。重復使用專用的釀酒容器有利于保存和選擇理想的發酵微生物群,這也是接種發酵的方法之一[48]。接種發酵方法有多種,世界各地的古今釀酒史中普遍存在,許多古代釀酒器壁上常見一層有機殘留物[48、49],應為長期重復使用的結果。因此,為了選擇理想的菌群,有效地進行長時期的接種發酵,釀酒器在使用期間應該不用于其他功能。以此推測,考古遺存中有明顯殘留物的發酵罐很可能是專用的釀酒器。
7.尖底瓶殘留物中是否存在與釀酒發酵有關的微植物和微生物組合是判斷是否為酒器并分析釀酒方法的重要證據。這種特殊組合不存在于土壤中或與酒無關的器物上。因此,根據分析采自土壤或非釀酒陶器上的控制標本,與殘留物標本比較,也可以進一步幫助判斷殘留物是否確實與陶器功能有關。
二、標本采集和分析方法
半坡遺址發掘于1954~1957年[50],姜寨遺址發掘于1972~1979年[7]。兩遺址出土的陶器在發掘之后都已經過清洗,存放在半坡博物館文物庫房中。根據上述釀酒器的特點,我們選擇陶器內壁表面可見黃白色或黃黑色殘留物痕跡的標本進行取樣(圖二,B、C)。殘留物樣品的采集及分析方法的過程為:(1)用干凈牙刷清掃每件器物表面的浮土。(2)對小型陶器殘片使用超聲波清洗儀震蕩6分鐘,對大型陶器使用超聲波牙刷清洗6分鐘,獲得液體殘留物;同時用干凈的刀片在陶器內部表面直接刮取固體殘留物。(3)在實驗室通過EDTA(Na2EDTA·2H2O)清洗法和重液離心法將殘留物進行分離,重液為比重為2.35的多鎢酸鈉(sodium polytungstate)以便同時提取可能存在的多種微植物和微生物遺存(包括淀粉粒、植硅體、真菌等);吸取分離后的殘留物溶液滴在干凈的載玻片上,干燥后滴加50%甘油溶液,加蓋玻片,并用指甲油封片。(4)使用剛果紅(Congo Red, 0.1%, 1mg/ml) 染色法[51]對部分器物的殘留物中一小部分進行測試,以判斷是否存在糊化淀粉粒。(5)微植物和微生物記錄使用蔡司生物顯微鏡(Carl Zeiss Axio Scope A1),配備有微分干涉相差(DIC)及偏振光裝置,并配有數碼相機(AxioCam HRc Rev.3)記錄影像。
我們提取了半坡博物館庫房標本架上的塵土作為控制標本,發現其中有大量纖維和孢粉,但只有極少量淀粉粒,不見糊化特征,與陶器殘留物的組合截然不同(表一~三)。這一分析可以證明陶器內壁附著的殘留物不是環境的污染,而是與器物的原始功能有關。

表一 半坡(BP)和姜寨(JZ)淀粉粒記錄
三、殘留物分析結果
經分析,尖底瓶殘留物中發現有較多淀粉粒、植硅體、霉菌的菌絲、孢子和孢子囊、以及酵母細胞;并有少量棒狀方解石晶體。以下,我們對殘留物結果進行詳細描述。
1.淀粉粒
11件陶器標本的殘留物中共發現328顆淀粉粒,其中242顆(73.8%)可以鑒定為6種類型(圖三)。有86顆(比例26.2%)淀粉粒缺少鑒定特征,歸為無法鑒定類(表一、圖四)。

圖四 半坡-姜寨尖底瓶殘留物中的損傷淀粉粒(每顆淀粉粒顯示DIC和偏振光鏡拍攝的影像)

圖三 半坡-姜寨尖底瓶殘留物中的淀粉粒類型及現代對比標本(每顆淀粉粒顯示DIC和偏振光鏡拍攝的影像)
I型為黍亞科(Panicoideae)(n=72;比例22%;出現率72.7%),粒長7.13~19.05微米,為多邊體或近圓形,臍點居中,多有裂隙。這些特征見于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及薏苡(Coix lacryma-jobi L.)的淀粉粒,往往很難鑒定到更精確的分類[52]。
II型為薏苡(C. lacryma-jobi L.)(n=33; 比例10.1%;出現率36.4%),粒長為8.61~23.03微米。其形態特征可區別于粟黍,但與薏苡相似,如粒型較大、臍點偏心、消光十字臂呈“Z”形曲折狀[52]。
III型 為 小 麥 族 (Triticeae)(n=103; 比 例31.4%;出現率81.8%),粒長4.72~44.96微米,粒型為透鏡體,臍點居中。這些特征與中國北方常見的冰草屬(Agropyron sp.)、披堿草屬(Elymus sp.)和賴草屬(Leymus sp.)的淀粉粒近似[53]。
IV型為栝樓根(Trichosanthes kirilowii)(n=29;比例8.8%;出現率63.6%),粒長10.2~32.79微米,其型態為圓形、鐘形、半圓形等,臍點居中或偏心,消光十字多彎曲。栝樓廣泛分布于中國南北方[54]。
V型為豆類,可能為野豌豆(Vicia sp.)(n=3; 比例0.9%;出現率18.2%)粒長22.57~27.4微米。呈不規則的橢圓形或腎形,消光十字有多個臂,中心呈現大面積黑色區域。秦嶺地區有17種野豌豆,古文獻中的“薇”鑒定為大野豌豆(Vicia gigantea Bunge)[55]。詩經中“小雅·采薇”記述了西周人在渭河流域采集野豌豆的活動。
VI型為芡實(Euryale ferox)(n=2; 比例0.6%; 出現率9.1%),淀粉粒整體為近圓形聚合體(23.28、26.89微米),內部包含許多小形多邊體顆粒(n=22; 2.8~5.41微米)。這些特征與芡實十分接近。在我們的現代對比標本中,芡實淀粉粒往往呈圓形或橢圓形出現(直徑9.51~32.33微米),內含大量小型顆粒(1.71~3.93微米)(圖三,8)。我們僅在BP2標本上發現兩顆芡實淀粉粒聚合體,其中一顆部分缺失(圖三,7)。芡實生在池塘、湖沼中,遍布中國南北各地[56]。
總之,淀粉粒殘留物中包含的植物主要是粟黍、薏苡和小麥族,另外有少量的栝樓根、野豌豆和芡實。這些植物的淀粉粒均見于中國北方新石器時期的磨盤磨棒上以及渭水流域新石器時代的陶器殘留物中。其中最常見的植物包括粟黍、薏苡、小麥族和栝樓根;臨潼零口和寶雞關桃園的新石器早期陶器中有類似野豌豆的淀粉粒,藍田新街的仰韶文化晚期的尖底瓶中發現有芡實[3-5、57]。根據關中地區西安魚化寨和華縣東陽遺址的浮選結果,粟黍是仰韶時期最主要的農作物[58、59]。半坡-姜寨陶器淀粉粒組合反映了渭水流域仰韶文化先民普遍栽培和采集的植物。
另外,大多數淀粉粒都顯示有損傷特征(61.2%),并可以分為未糊化(29.9%)和糊化(31.3%)兩類。前者可以代表淀粉酶分解造成的破壞,后者具有經加熱和發酵造成的糊化特點。另外也有少量糊化淀粉粒顯示為一般蒸煮所致,這類糊化特征在我們的釀酒標本中也很常見(圖四)。綜合來看,淀粉粒的整體特征包含了植物發酵所造成的的各類損傷現象。
2.植硅體
殘留物中共發現852顆植硅體。8件器物中出有來自黍族穎殼的植硅體(n=288; 23.8%),其中大多數只能鑒定為黍族(n=176),其次為黍的η型(n=111),只有1例為粟的Ω型。鑒于絕大多數能夠鑒定到屬的穎殼均來自黍,推測那些定為黍族的穎殼大多數也是黍。啞鈴型、多鈴型和十字型等一些黍亞科中常見的植硅體主要出現于9件器物中(n=61),大部分可能來源于黍;其中一部分十字型植硅體的長或寬超過18微米,不見于粟黍,可能來自薏苡的內稃和外稃。有3例為絞合狀樹枝狀型,可能來源于早熟禾亞科的穎殼;殘留物中有較多的小麥族淀粉粒,因此推測這些穎殼可能來自野生小麥族,但無法準確確定其來源種屬。另外,有一例水稻穎殼的雙峰型。還有較多禾本科中常見的棒型、扇型和帽型,其中包括6例來自蘆葦莖葉的盾型。主要見于真雙子葉植物(eudicots)莖葉的毛細胞出現在10個標本中(n=30)。毛細胞來自于菊科(Asteraceae)、榆科(Ulmaceae)、葫蘆科(Cucurbitaceae)、蕁麻科(Urticaceae)等植物[60],我們目前尚無法提供更準確的鑒定;但殘留物中有屬于葫蘆科的栝樓根淀粉粒,標本中的毛細胞中是否有些來自栝樓,需要將來做進一步分析。總之,殘留物中有大量黍族和少量小麥族及水稻的穎殼植硅體,并與禾本科的多種植物莖葉植硅體共存(表二、圖五)。

表二 半坡-姜寨尖底瓶殘留物中的植硅體記錄

圖五 半坡-姜寨尖底瓶殘留物中的植硅體和棒狀方解石晶體
3.真菌(酵母和霉菌)
殘留物標本中共發現412個真菌個體或組合,包括酵母細胞和霉菌(表三)。

表三 半坡-姜寨尖底瓶殘留物中真菌(酵母和霉菌)記錄
在8件陶器上共發現134個酵母細胞,為圓形和橢圓形,直徑范圍3.19~11.9微米。其中40個顯示出有小突起狀的芽體,是芽殖的初期形態(圖六,1、2)。這些酵母細胞形態與釀酒酵母接近(圖七,8),但我們無法僅僅根據形態鑒定其種屬。

圖六 半坡-姜寨尖底瓶殘留物中酵母細胞和霉菌
除了2件標本外(JZ3,JZ8)其他陶器標本都發現有較多霉菌的組成成分,包括154個菌絲和菌絲體、80個孢子囊和44個孢子。其中有些具有曲霉和根霉的特征。曲霉菌絲有分隔,無假根,分生孢子梗從厚壁而膨大的菌絲細胞生出,分生孢子梗頂端膨大而形成頂囊,頂囊表面產生小梗,從小梗生出分生孢子。根霉菌絲無分隔、有假根、菌絲在與假根相對位置向上生出孢囊梗,頂端形成孢子囊,內生孢囊孢子。孢子囊的囊軸明顯,囊軸基部與柄相連處成囊托。毛霉的外形成毛狀,菌絲無隔,有分枝,囊軸球形,與囊梗不分隔,無囊托。根霉和毛霉形態比較相似,但毛霉無假根(圖七,1~7)[46,61,62]。
在JZ2標本發上發現大量的霉菌(n=137),大多數具有明顯的曲霉特征,其中至少有42個可以分辨出分生孢子梗和圓形的頂囊,以及從頂囊表面生長出的小梗和孢子。同時,JZ2中也有少量根霉或毛霉,顯示為與孢子梗連接的圓形孢子囊,其中還可見的黑褐色的孢囊孢子。在BP1和JZ5中發現有分枝的菌絲,其形態類似根霉從假根相對位置生長出菌絲的狀態(圖六;對照圖七中的相應霉菌形態)。

圖七 現代真菌對比標本
4.棒狀方解石晶體(rod-shaped calcite crystals)
在3個標本中發現有少量棒狀晶體。這些晶體大多表面光滑,以單體出現,多為直棒形,有方鈍形末端。在偏光鏡下可見雙折射光澤(圖五,11、12)。這些特征與棒狀方解石晶體的形態十分吻合。棒狀方解石晶體是真菌菌絲生物礦化的結果,菌絲在分解后將針狀物釋放到周圍環境中[63、64]。棒狀方解石晶體的出現表明殘留物中曾存在真菌,與上述真菌菌絲的鑒定互為佐證。
四、討論:殘留物組合與釀酒和飲酒方法
綜合殘留物中各種微植物和微生物的出現情況,可以觀察到以下現象。
第一,根據淀粉粒和植硅體的類型可以推測,尖底瓶中盛裝的植物種類包括粟黍、薏苡、水稻、野生小麥族、野豌豆、栝樓根及芡實。有明顯糖化和發酵特征的淀粉粒存在說明這些植物是釀酒原料。其中各種谷物淀粉粒在數量和出現率中都占主要地位,而豆類和塊根類較少。姜寨植硅體中有1例水稻穎殼的雙峰型,但淀粉粒中沒有發現水稻。根據我們的釀酒實驗,大米淀粉粒在發酵過程中大部分消失,而且大米淀粉粒顆粒很小,如果不是以群組的狀態出現,不易鑒定,因此可能很難在古代殘留物中發現。另外,在釀酒發酵過程中,大部分淀粉粒由于糖化和糊化而變形,導致無法鑒定。因此,我們不能根據淀粉粒的數量直接計算釀酒原料的比例,但大致可以推測主要的釀酒谷物為粟黍、薏米、小麥族和稻米,并附加野豌豆和塊根植物。
第二,小麥族淀粉粒的出現率較高,見于9件陶器,并在其中3件陶器中(BP2, JZ2, JZ3)與早熟禾亞科穎殼植硅體共存。這些淀粉粒和植硅體可能來自同樣的植物,但目前無法鑒定到種屬。這些殘留物至少說明仰韶時期對野生小麥族植物的利用包括釀酒。
第三,在姜寨的8件標本中發現黍族穎殼植硅體;其中2件標本(JZ3、8)有數量非常高的黍族穎殼(分別為51、110),但基本不見霉菌(圖八)。谷物穎殼和相應的具有發酵特征的淀粉粒同時出現可以作為釀造谷芽酒的指示物,因此這2件尖底瓶中盛裝的可能是以發芽黍為單純發酵劑的谷芽酒。渭河流域釀造谷芽酒的最早證據見于臨潼零口遺址白家期的小口鼓腹罐的殘留物中,其釀酒原料主要為黍和稻米,年代接近距今7800年[2]。零口距離姜寨約19公里,兩遺址中的釀酒原料和方法的類似,可能與其相似的自然環境及同一地區的技術傳承有關。

圖八 根據陶器殘留物中黍族穎殼植硅體、霉菌和棒型植硅體分布推測釀酒方法
第四,利用霉菌制麹釀酒的方法見于2個遺址中,其中9個標本中霉菌的數量在8個個體以上。能夠鑒定的霉菌包括曲霉和根霉。尤其在JZ2標本中發現大量霉菌的片段,如孢囊和菌絲;以曲霉為主,并有少量根霉。利用曲霉和根霉釀酒的最早證據見于寶雞關桃園前仰韶時期的陶器上,是至今所知中國最早的麹酒[2]。另外,澠池丁村仰韶中期尖底瓶殘留物中發現曲霉和毛霉[6]。這3種霉菌都是現代麹中常見的菌種[45]。曲霉和根霉在一個尖底瓶(JZ2)中集中出現說明仰韶早期人們已經有意識地選擇和培養有益的發酵菌群。他們并不明白其中的科學原理,而是經歷了千百年反復嘗試而獲取的實踐經驗。
另外,在半坡—姜寨陶器上發現有較多霉菌的8個標本中,3個不見穎殼植硅體(BP1、2;JZ8),說明是單純使用酒麹釀酒。另外6個標本中發現既有霉菌又有穎殼植硅體(JZ1、2、4~6,9),可能是在同一器物中曾經利用谷物發芽和酒麹兩種方法釀酒。從整體來看,我們觀察到的兩種釀酒方法和器型大小之間沒有直接聯系。例如,可以鑒定為單純使用酒麹的標本(BP1、2;JZ7)和可能使用兩種釀酒方法的標本(JZ1、2、6、9)都來自大小不同的尖底瓶。另外,我們不能肯定那些只有極少量穎殼植硅體的標本(JZ5只有1個黍穎殼植硅體)屬于有意識利用發芽谷物釀酒(圖八)。
第五,每個標本中都發現有棒型植硅體;這類植硅體主要來自禾本科植物莖葉,但是也見于穎殼中。標本中出現棒型植硅體可能反映兩種情況:(1)如果在制麹過程中加入某些植物莖葉作為草麹,那么殘留物中會同時存在霉菌和來自莖葉的棒型植硅體。我們的標本中有4例(BP1、2;JZ2、6)是較多數量的霉菌(n=24~137)和棒型植硅體(n=39~105)共存,其中兩例不見穎殼;這4例標本可能是使用草麹的反映。(2)如果殘留物中不見或極少霉菌,但有較多穎殼和棒型植硅體,那么這些棒型植硅體也許主要來自穎殼。標本中的JZ3、8可能屬于這種情況(圖八)。
第六,根據有些尖底瓶口沿磨損的微痕形態(如垂直向線狀痕),我們曾經推測仰韶人可能使用蘆葦或竹子做的吸管飲酒[65]。在本文所分析的2個姜寨尖底瓶標本中(JZ2、8)發現來自蘆葦莖葉的盾形植硅體(圖五,7),可以作為使用蘆葦吸管飲酒的佐證。
BP1、BP2、JZ7為單純麹酒;JZ3、JZ8為單純谷芽酒;其他可能為兩種方法混合釀造。
第七,仰韶文化早期代表著一個相對平等的農業社會,在所有仰韶遺址的居住區和墓葬中都出土有尖底瓶,該器物的廣泛分布表明酒被人們普遍享用,而不是僅作為少數精英人士的奢侈品。各種大小的尖底瓶可能在不同的社會場合中使用,例如,小型尖底瓶可能適于個人或家庭飲用,而大型尖底瓶可以滿足更多人的需求,如社區宴饗時的群飲。這一推測需要更多的證據來檢驗,但半坡和姜寨的聚落模式可以支持這種假設;兩個遺址均為有壕溝圍繞的村落,少數大型公共建筑被許多中小型的家庭住所圍繞。大型公共建筑與宴飲活動之間的關系也已經通過對河南偃師灰嘴遺址大房子地面中殘留的分析得以確認[66]。此外,尖底瓶的形制趨于向大型發展,這與仰韶大房子的規模從早期(約100平方米)到晚期(約300平方米)增加的總體趨勢一致。這一規律也許意味具有宴飲性質的公共聚會的規模逐漸擴大。這些現象都表明,仰韶文化中的飲酒行為與社會復雜性發展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
最后,器物埋藏學背景的差異似乎影響了殘留物中微生物的保存,特別是淀粉粒的保存。來自墓葬的2個完整小型尖底瓶(JZ2、9)中發現了最多的淀粉粒數量(65和69),JZ2中也保存了最多的霉菌(137)。而來自房址(JZ5)和甕棺(JZ7)的標本保存的淀粉數量最少(各為6)。這些結果表明,為了獲取最好的釀酒證據,除了針對器表有可見殘留物的釀酒器之外,墓葬中完整的隨葬品也是較理想的采樣對象。
五、結論
以上的分析證明,出現于7000年前最早的仰韶文化尖底瓶是一種新型的釀酒容器,其結構設計有利于釀造發酵。酒的原料是當時常見的各種栽培和野生植物,大小不等的尖底瓶可能用于不同的社會場合。綜合半坡和姜寨尖底瓶殘留物中淀粉粒、植硅體、霉菌、酵母細胞和棒狀方解石晶體的組合規律可以看出,黍可能是釀酒的主要原料,加以其他谷物(粟、小麥族、水稻)、豆類和塊根植物(栝樓根、芡實)。釀酒方法基本為谷芽酒和麹酒兩種,使用蘆葦吸管咂酒可能是飲酒方法之一。谷芽酒主要利用黍發芽,制麹的原料包括谷物和禾本科植物莖葉,麹中的霉菌主要有曲霉和根霉,或許也有少量毛霉,酵母的形態接近釀酒酵母。這兩種釀酒方法有時分別使用,有時可能同時使用。這一研究填補了中國新石器時代釀酒歷史上1000年的空白,使我們能夠重建從9000年到5000年前在黃河中游地區持續發展的釀酒技術。在這數千年中,那些有益于釀造發酵酒的真菌在酒器殘留物中持續出現,表明史前時期的先民已經掌握了接種發酵的方法,包括反復使用專用發酵容器(包括尖底瓶)使得所需微生物菌群得以延續。
這項研究的結果不僅為了解中國史前悠久的釀酒技術傳統提供了新資料,而且為深入探索仰韶人與飲酒相關的社會活動開辟了新途徑。未來的研究需要分析在更大的區域和更長的時間段內,釀酒和飲酒行為與社會復雜化之間的關系。
致謝: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孫周勇促進本項目的合作;西安半坡博物館的領導和工作人員大力支持并配合工作;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提供設備和人員支持;河南澠池仰韶酒廠陳蒙恩提供現代真菌標本并協助鑒定真菌;美國斯坦福大學東亞系馮索菲協助提取殘留物標本;本項目由美國斯坦福大學考古中心資助。
[1]McGovern P. E., Zhang J. , Tang J., Zhang Z., Hall G. R. , Moreau R. A. , Nunez A. , Butrym E. D. , Richards. M. R. , Wang C-S. , Cheng G. , Zhao Z., and Wang C.. Fermented beverages of pre- and proto-historic China[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4(51): 17593-8.
[2]Liu Li, Wang Jiajing, Levin Maureece J., Sinnott-Armstrong, Nasa Zhao Hao Zhao Yanan, Shao Jing, Di Nan, and Zhang.Tian’en. The origins of specialized pottery and diverse alcohol fermentation techniques in Early Neolithic China[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9 (26): 12767-12774.
[3]劉莉,王佳靜,趙雅楠,楊利平.仰韶文化的谷芽酒:解密楊官寨遺址的陶器功能[J].農業考古,2017(6):26-32.
[4]劉莉,王佳靜,趙昊,邵晶,邸楠,馮索菲.陜西藍田新街遺址仰韶文化晚期陶器殘留物分析:釀造谷芽酒的新證據[J].農業考古,2018(1):7-15.
[5]王佳靜,劉莉,等.揭示中國5000年前釀造谷芽酒的配方[J].考古與文物,2017(6):45-53.
[6]Liu Li, Li Yongqiang, and Hou Jianxing. Making beer with malted cereals and qu starter in the Neolithic Yangshao culture, China[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2020(29): 102-134.
[7]西安半坡博物館,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潼縣博物館.姜寨—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8]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
[9]寶雞市考古工作隊,陜西省考古研究所.隴縣原子頭[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10] 王煒林,張偉,張鵬程,郭小寧,袁明,馬明志.陜西高陵楊官寨遺址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2011(6):16-32.
[11] 西北大學文博學院考古專業.扶風案板遺址發掘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12] 寶雞市考古工作隊,陜西省考古硏究所.寶雞福臨堡: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13]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米家崖:新石器時代遺址2004~2006年考古發掘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
[14]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灣[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15]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廟底溝與三里橋[M].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16]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洛陽王灣[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17] 魏興濤,李勝利.河南靈寶西坡遺址105號仰韶文化房址[J].文物,2003(8):4-17.
[18]鞏啟明.仰韶文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19] 韓明友.仰韶小口尖底瓶的功能模擬與探釋[J].社會科學戰線,2015(12):107-113.
[20] 王先勝.關于尖底瓶流行半個世紀的錯誤認識[J].社會科學評論,2004(4):5-10.
[21] 蘇秉琦.關于重建中國史前史的思考[J].考古,1991(12):1109-1117.
[22]李仰松.對我國釀酒起源的探討[J].考古,1962(1).
[23]包啟安.中國酒的起源(上)[J].中國釀造,2005(2).
[24] 衛雪,錢耀鵬.陶尖底瓶的功能結構分析[J].考古,2019(11).
[25] 孫霄,趙建剛.半坡類型尖底瓶測試[J].文博,1988(1).
[26] 周衍勛,苗潤才.對西安半坡遺址小口尖底瓶的考察[J].中國科技史,1986(2):48-50,28.
[27] 俞為潔.釀造江南米酒的草麹[J].東方美食(學術版),2003(4):75-80.
[28] 凌純聲.中國酒之起源[C]//民族學研究所集刊.臺北:民族研究所,1958:883-901.
[29] 洪光住.中國釀酒科技發展史[M].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1.
[30]Huang H. T..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 Vol 6[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31] 袁庭棟,溫少峰.殷墟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M].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
[32] 何駑.郁鬯瑣考[C]//考古學研究(十).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244-254.
[33] 凌純聲.中國及東南亞的嚼酒文化[C]//民族學研究所集刊.臺北:民族研究所,1957(4):1-23.
[34]Hornsey, Ian S.. A History of Beer and Brewing[M].Cambridge: The Royal Society of Chemestry, 2003.
[35] 劉瑞賽,安家彥,董文勇,王越.利用計算流體力學技術分析啤酒發酵罐構型對溫度和流動的影響[J].食品與發酵工業,2016(42):52-57.
[36] Briggs, Dennis E., Boulton, Chris A., Brookes, Peter A., and Stevens, Roger. Brewing Science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RC Press, 2004.
[37] Delente, Jacques, Akin, Cavit, Krabbe, Erik, and Lanenburg, Kurt. Fluid Dynamics of Anaerobic Fermentation. biotechnology and Bioengineering, 1969: 631-646.
[38] Wang Jiajing, Liu Li, Georgescu, Andreea Le, Vivienne V., Ota, Madeleine H., Tang Silu, and Vanderbilt, Mahpiya. Identifying ancient beer brewing through starch analysis: A methodology[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17(15): 150-160.
[39] Hutschenreuther, Antje, Watzke, J?rg, Schmidt, Simone, Büdel, Thomas, and Henry, Amanda G.. Archae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Digestion of Starches by Soil Bacteria: Interaction among Starches Leads to Differential Preservatio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2017(15): 95-108.
[40] Henry,AmandaG.,Hudson,HollyF.,andPiperno,DoloresR.,Ch anges in starch grain morphologies from cooking[J].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2009(36):915-922.
[41] 葛威,劉莉,陳星燦,金正耀.食物加工過程中淀粉粒損傷的實驗研究及在考古學中的應用[J].考古,2010(7):77-86.
[42] Wang Jiajing, Liu Li, Ball Terry, Yu Linjie, Li Yuanqing, and Xing Fulai Revealing a 5,000-y-old beer recipe in China[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6(23): 6444-6448.
[43] 同[4]:7-15.
[44] 李兵,張超,王玉霞,王娟,蔡馨,楊茂,邢蓮.白酒大曲功能微生物與酶系研究進展[J].中國釀造,2019(6):7-12.
[45] Jin Guangyun, Zhu Yang, and Xu Yan. Mystery behind Chinese liquor fermentation[J]. Trends in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7(63): 18-28.
[46] 岑沛霖,蔡謹.工業微生物學[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8.
[47] Wayessa, Bula Sirika, Lyons, Diane, and Kooyman, Brian.Ethnoarchaeological Study of Brewing Technology in Wallaga Region of Western Oromia[J]. Ethiopia. Journal of African Archaeology 2015(1): 99-114.
[48] McGovern, Patrick E.. Uncorking the Past: The Quest for Wine, Beer, and Other Alcoholic Beverage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49] Samuel, Delwen Archaeology of ancient Egyptian beer[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Brewing Chemists, 1996(54): 3-11.
[50]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
[51] Lamb, Jenna and Loy, Tom. Seeing red: the use of Congo Red dye to identify cooked and damaged starch grains in archaeological residues[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05(32): 1433-1440.
[52] Liu Li, Ma Sai, and Cui Jianxin. Identification of starch granules using a two-step identification method[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14(52): 421-427.
[53] Yang Xiaoyan and Perry, Linda. Identification of ancient starch grains from the tribe Triticeae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13(40): 3170-3177.
[54] Wu Z. Y., Raven P. H., and Hong D. Y., etc. Flora of China. Vol. 19 : Cucurbitaceae through Valerianaceae, with Annonaceae and Berberidaceae[M]. Beijing and St. Louis:Science Press and 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 Press, 2011.
[55] 中國科學院西北植物研究所.秦嶺植物志:種子植物[M].北京:科學出版社,1981.
[56] Wu Z. Y. and Raven P. H., etc. Flora of China. : Caryophyllaceae through Lardizabalaceae(Vol. 6)[M].Beijing and St. Louis : Science Press and 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 Press,2001.
[57] 劉莉,陳星燦,趙昊.河南孟津寨根、班溝出土裴李崗晚期石磨盤功能分析[J].中原文物,2013(5):76-86.
[58] 趙志軍,仰韶文化時期農耕生產的發展和農業社會的建立--魚化寨遺址浮選結果的分析.江漢考古,2017(6):98-108.
[59] 趙志軍.渭河平原古代農業的發展與變化—華縣東陽遺址出土植物遺存分析[J].華夏考古,2019(5):70-84.
[60] Piperno, Dolores R.. Phytoliths: A Comprehensive Guide for Archaeologists and Paeoecologists[M]. Lanham: Altamira Press, 2006.
[61] St-Germain, Guy and Summerbell, Richard, Identifying Fungi: A Clinical Laboratory Handbood[M].Belmont, CA: Star Publishing Company, 2011.
[62] 何國慶,賈英民,丁立孝.食品微生物學[M].北京:中國農業大學出版社,2017.
[63] Bajnoczi, Bernadett and Kovacs-Kis, Viktoria. Origin of pedogenic needle-fiber calcite revealed by micromorphology and stable isotope composition—a case study of a Quaternary paleosol from Hungary[J]. Chemie der Erde, 2006(66): 203-212.
[64] Verrecchia, Eric. Needle-fiber Calcite: A Critical Review and a Proposed Classification[J]. Journal of Sedimentary Research, 1994. 64A: 650-664.
[65] 劉莉.早期陶器、煮粥、釀酒與社會復雜化的發展[J].中原文物,2017(2):24-34.
[66] 劉莉,王佳靜,陳星燦,李永強,趙昊.仰韶文化大房子與宴飲傳統:河南偃師灰嘴遺址F1地面和陶器殘留物分析[J].中原文物,2018(1):3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