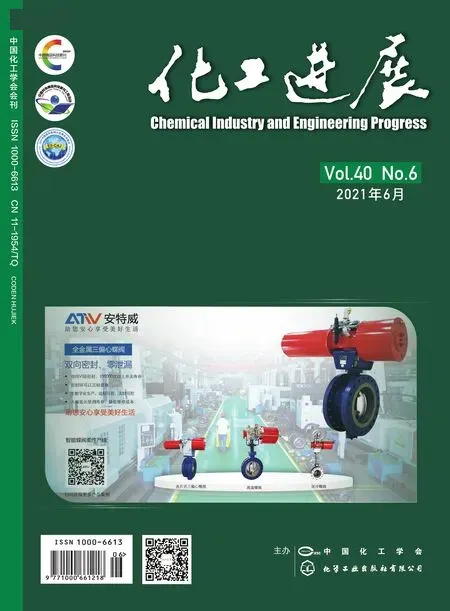環境中短鏈氯化石蠟去除方法的研究進展
韓婉玲,錢勇興,張會寧,陳吉煒,馬建青,張科鋒
(1浙江大學工程師學院,浙江杭州310000;2浙大寧波理工學院土木建筑工程學院,浙江寧波315000;3寧波市城鄉水污染控制技術重點實驗室,浙江寧波315000;4浙江大學寧波研究院,浙江寧波315100;5寧波市河道管理中心,浙江寧波315100)
氯化石蠟(chlorinated paraffins,CPs)是由正烷烴原料自由基直接氯化而成的復雜混合物,CPs也稱多氯代烷烴(polychlorinated alkanes,PCAs),氯化程度通常為30%~70%(質量分數)。根據不同碳鏈長度,CPs可分為短鏈(short-chain chlorinated paraffins,SCCPs,C10~C13)、中 鏈(middle-chain chlorinated paraffins,MCCPs,C14~C17)和 長 鏈(long-chain chlorinated paraffins,LCCPs,C18~C30)[1]。CPs的第一次合成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主要用于制備防腐產品。然而從1930年起,國外開始工業化生產CPs來替代因毒性危害大而被禁用的多氯聯苯,導致其產量日益增加。由于阻燃及電絕緣性良好、揮發性低、價格便宜等優點,CPs一般用作高溫潤滑劑、增塑劑、阻燃劑、黏合劑、油漆、橡膠和密封劑等的添加劑[2]。
2016年全球CPs生產總量已超過100萬噸,而世界范圍內的SCCPs產量則至少為16.5萬噸[3]。中國從1950年開始生產CPs,據中國氯堿網統計,2018年國內CPs總生產能力已達208萬噸,實際產量83.5萬噸[4],其中SCCPs生產和消耗全球均排名第一。隨著我國含CPs產品的大量生產和使用,其不斷在各類環境介質中,如空氣[5]、水[6]、土壤[7]和沉積物[8]以及各種生物[9]等被檢出。在生產CPs的過程中往往會產生具有環境持久性、生物累積潛力和毒性的副產物SCCPs,故SCCPs的污染問題日益引起人們的重視。通過了解SCCPs的來源及遷移路徑,可以有的放矢地控制和減少SCCPs的排放,減輕對環境的污染。現階段關于SCCPs的研究論文數量逐年增加,但對SCCPs去除方面的研究還很有限[1-3]。因此,本文主要通過比較分析SCCPs去除的兩大類方法(物化法和生物法)來闡述現階段關于SCCPs環境去除的研究進展,以期能為SCCPs的環境行為和去除研究提供有價值的信息。
1 SCCPs的環境賦存及危害
較之于MCCPs和LCCPs,SCCPs的物理化學性質最為特殊,環境釋放潛力最大,具有致癌、致畸和致突變的“三致效應”,毒性最高,最終在2017年被列入《關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附件A受控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POPs)清單[10]。而且,SCCPs含量超標也會引起一些危害事件,如備受媒體關注的“毒跑道事件”[11]、“臺灣食品塑化劑事件”[12]以及“酒鬼酒增塑劑超標事件”[13]等。在一些國家,SCCPs已被禁止或限制使用。我國作為《斯德哥爾摩公約》的履約國之一,并且作為CPs等鹵代阻燃劑的生產和使用大國,也正承受減少和去除環境中SCCPs污染的壓力。
SCCPs迄今為止尚未見有天然來源[14],主要來源于人為活動,在生產、儲存、運輸、產品制造以及氯化石蠟使用過程中,通過點源、非點源的排放(包括意外泄漏或沖洗等)進入環境受體[15]。SCCPs雖然大部分能被傳統污水處理廠中的污泥吸附去除,但仍有部分會進入受納水體[16-17],或吸附于懸浮顆粒,或沉入水體底泥[18],或揮發進入大氣,被大氣顆粒物吸附,實現長距離運輸。SCCPs在環境中的遷移轉化途徑具體如圖1所示。SCCPs在室溫下的蒸氣壓較低,極易受到長距離大氣輸送的影響而發生環境擴散[19]。SCCPs在北極和南極的生物群和環境基質中都有檢出,如在北極生物格陵蘭鯊魚、海鳥、鱈魚、白鯨和環斑海豹[20-23]等體內檢測到了SCCPs,其還存在于南極水域的海洋哺乳動物座頭鯨[24]和大氣中[25]等,這些都為SCCPs遠距離傳播提供了相關的證據,表明其對環境構成潛在的生態威脅。

圖1 SCCPs在環境中的遷移轉化途徑
另一方面,SCCPs有著很強的生物富集性以及生物放大性[26]。Li等[27]通過水培暴露體系研究了大豆和南瓜對SCCPs吸收、遷移及生物轉化的影響。大豆根、莖中SCCPs積累量分別為1.98%~54.5%、0.50%~2.54%,南瓜根、莖中SCCPs積累量分別為23.6%~59.9%、0.7%~3.81%,其幼苗能夠吸收、富集和遷移SCCPs。Wang等[28]測定了中國19個省的谷物和豆類樣品,SCCPs濃度分別為343ng/g和328ng/g(濕重),初步風險評估顯示,谷物和豆類中的SCCPs不會對居民構成重大風險。但由于SCCPs是親脂性化合物,能在食物鏈中進行生物積累和生物強化,動物源性食品中的SCCPs可能來自于被污染飼料的生物積累。Dong等[29]在全國采集了16份動物飼料材料樣本,SCCPs的濃度范圍在120~1700ng/g,并在動物源性飼料中檢測到相對高濃度的SCCPs。生產和使用時釋放到環境中的SCCPs可通過生物積累被人類攝入,飲食攝入是人類接觸SCCPs的主要途徑。人類可能通過食用生鮮產品[30]及水產品[31]而攝入高濃度的SCCPs,進而使SCCPs存在于人乳[32]以及人體血漿[33-34]中。此外,SCCPs能危害人體免疫系統和生殖系統[35],同時還會顯著影響人體肝癌HepG2細胞[36-37],這些毒副作用表明SCCPs對人類健康具有很大的潛在威脅。
SCCPs在環境中具有較強的遷移轉化能力,是影響非常廣泛的環境污染物,并對環境安全和人體健康構成嚴重威脅。因此關于如何減少和去除環境中存在的SCCPs理應引起人們的重視,然而迄今為止,比之于SCCPs在環境中的分析檢測研究,針對SCCPs去除的研究報道依然有限,只有零星的信息可供參考。
2 SCCPs的去除方法
2.1 物化法
近年來,SCCPs的去除方法陸續得以報道,主要包括物化法和生物去除法,其中物化法可劃分為一般物化去除法、高級氧化法等,去除機制主要有吸附、氧化還原、化學降解、光降解等。這些技術被認為是去除或礦化SCCPs的有效技術[38]。
2.1.1 一般物化去除法
SCCPs在環境中相對穩定,用合適的吸附劑對其進行吸附去除理論上是一種較好的方法,但尚未發現有此類研究報道。Ding等[39]通過分子動力學和密度泛函理論從理論上證實了單壁碳納米管能對CPs有較好的物理吸附作用。此外,多孔聚合樹脂[40]在吸附二氯甲烷、四氯化碳等揮發性有機污染物方面,有機黏土(有機蒙脫土和有機膨潤土)[41]在吸附去除包括農藥、個人護理用品等有機污染物方面都有較好的效果,但上述吸附劑對SCCPs的吸附研究仍是空白。
在合適的條件下,環境中的SCCPs會進行脫氯。Lahaniatis等[42]發現在氨化二乙醚的溶液中,鈉能使CPs還原脫氯,經過鑒定降解產物是正構烷烴和正構烯烴。Zhang等[43]在用納米零價鐵顆粒還原脫氯去除SCCPs時發現,納米零價鐵對SCCPs的脫氯速率與pH、投加量、溫度以及腐殖酸的投加量有關。適量的腐殖酸投加有助于納米零價鐵還原SCCPs,但當濃度高于15mg/L時,會抑制脫氯速率。Zhang等[44]在紫外光照射條件下發現SCCPs可在2h完全光化學降解,初步提出了SCCPs的詳細光化學降解機理,即SCCPs首先被激發并發生光離子化,釋放的Cl·可以生成·OH,然后·OH通過攫氫反應引發SCCPs降解,生成多個脫氫自由基,通過自由基-自由基反應生成醇類或長鏈中間體。雖然納米零價鐵等物化法去除SCCPs效率高,但成本較高且操作條件復雜,為此需要進一步改進。
2.1.2 高級氧化法
SCCPs因為缺少適當的取代基團吸收>290nm的紫外光,在環境條件下一般不會直接光解,具有優良的熱穩定性和化學穩定性,室溫下在水相中的水解和氧化作用很小,但當水生環境中存在自由基或催化劑時,可以誘導其發生水解或氧化的光解反應,可能會被對流層中的氧化自由基攻擊而發生間接光降解。近年來,光催化、芬頓等高級氧化技術[45-47]在去除環境中難降解有機污染物方面迅速發展起來,能通過直接礦化或氧化提高難降解污染物的可生化性能。為了尋找有效的SCCPs光催化材料,一些學者也進行了探索研究。
Koh等[48]發現紫外燈(中壓汞燈)與過氧化氫(H2O2)的協同作用能有效降解SCCPs,光催化處理5h后,降解率為33%。與不添加H2O2的空白組相比,添加H2O2可以有效提高降解率。同時,高級氧化技術還可用于各種氯代烷烴的降解。其中光催化劑TiO2的水懸浮液[49]可以快速地光降解一種PCAs(1,10-二氯癸烷,D2C10),在300nm紫外線下,D2C10在TiO2懸浮液中的反應機理如下:首先TiO2在紫外線照射下,產生表面·OH,同時吸附D2C10,而后吸附的D2C10被表面·OH氧化。光催化降解相對較快,D2C10在15min的光解過程中降解62%。同時El-Morsi等[50]研究了在芬頓和光芬頓體系下,PCAs組的另一物質1,2,9,10-四氯癸烷(T4C10)在H2O2中的降解效果。T4C10能被H2O2/UV大幅降解,在配備300nm光源強燈的光反應器中照射20min后,可降解60%的T4C10。該反應產生的Cl-化學計量數表明氯代正構烷烴完全脫氯。Friesen等[51]采用H2O2/UV和改進的Fe3+/H2O2/UV光芬頓法,研究了SCCPs的光化學氧化反應,該SCCPs混合物能在0.02mol/LH2O2/UV的酸性條件下被降解,在300nm光源下照射3h后,降解率為80%±4%。
在此基礎上,為了提高可見光的利用率,Chen等[52]合成了一種氧化還原石墨烯(RGO/CoFe2O4/Ag)納米復合材料,可用于可見光下降解SCCPs,并與商用二氧化鈦(P25TiO2)進行了對比。該催化劑在12h內對SCCPs去除率為91.9%,遠遠高于P25TiO2的21.7%。同時,該實驗還研究了連續吸附富集基板后的光催化降解SCCPs的效果,為采用適當設計的復合材料增強SCCPs的降解提供了依據。除此之外,Xiong等[53]通過原位還原法制備了一種Fe2O3@PDA(聚多巴胺)-Ag雜化物,其通過生成·OH自由基的優勢反應,在SCCPs的去除中表現出優異的光催化活性。SCCPs在光催化劑表面存在解吸和吸附行為,在48h內達到吸附平衡。攫氫反應沒有規律可循,但脫氯通常發生在相鄰的氯原子中。而且基于PDA的混合動力技術已在廢水處理中得到有效應用,可為去除SCCPs提供實踐指導。
盡管光催化、芬頓法等高級氧化法可用于SCCPs降解,但往往受到初始污染物濃度、反應條件等因素的限制。而且光腐蝕是光催化的一個典型缺點,半導體光催化劑在光照射下通常不穩定。故探索更加高效環保的SCCPs礦化方法,尋找其他具有成本效益的降解技術極為重要。
2.2 生物去除法
相比于物化法,生物去除法作為最經濟的方法,對污染物進行生物吸附或生物降解,被認為是去除環境中有機污染物最可靠的方法之一,備受研究者青睞。一般分為細菌降解法、細菌吸附法、植物吸收法及其他理論可行法(真菌、藻類及動物)。
2.2.1 細菌降解法
某些微生物可以通過生物降解作用去除環境中的有害污染物,其固有的微生物代謝可作為主要的生物降解機制[54-55]。已有研究證實鹵代化合物可以作為某些特定需氧微生物的碳源和能量來源,故獲取具有降解能力的微生物是微生物治理方法的首要條件。
微生物去除是利用篩選、馴化特定的微生物來降解環境中的有機污染物的方法,同時微生物降解也是有機污染物降解的重要過程之一。CPs是一種耐普通微生物侵襲的化合物,能夠被特定微生物降解去除,降解過程易受氯化度和碳鏈長度的影響,氯化度小于60%的SCCPs很容易被微生物氧化[56]。近年來,細菌降解法在處理SCCPs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前景。Omori等[57]報道了一系列土壤細菌菌株對CPs的共代謝脫氯作用。事實上,大多數接種的細菌都具有降解烴類的能力,但只有特定微生物能降解少量SCCPs。目前能夠降解SCCPs并且可以成功應用的菌株較少,好氧降解菌株有紅球菌、假單胞菌等,但不同的菌株對SCCPs的降解能力有很大差異。為更好地了解其生物去除潛力,一些學者對耐受SCCPs細菌的降解能力進行了深入研究。
Allpress等[58]篩選出了一株革蘭氏陽性菌紅球菌S45-1,該菌株能以SCCPs作為唯一碳源和能源進行代謝降解,這是首次報道微生物利用氯化石蠟作為唯一的碳源和能源。但唯一的缺陷是降解時間長,需要30~100天。除了革蘭氏陽性菌外,革蘭氏陰性菌對SCCPs也有降解作用,如假單胞菌。這些細菌被認為是好氧性的,大量分布于土壤、水體、動物和人體中。Heath等[59]篩選出了一株假單胞菌273,該菌株對氯代烷烴具有較好的脫氯效果,但與Allpress篩選的菌株一樣,該細菌脫氯周期較長,需要20天甚至更長時間。Lu[60]從二沉池中收集的脫水污泥中篩選出了一株假單胞菌N35,該純菌株也能以SCCPs作為碳源和能源,并能有效將其降解,20天內能脫氯57.5%。在污泥中投加該菌能去除73.4%的SCCPs,但降解周期也較長,需要30天。
已有的研究工作表明長鏈烷烴是短鏈氯化石蠟的降解產物[48],在此基礎上有學者對長鏈烷烴降解菌進行研究。有報道稱一種革蘭氏陰性球菌食烷菌2B5能夠在15天內從2g/L原油中降解C13~C30正構及支鏈烷烴[61]。此外,不動桿菌也能夠降解或去除多種有機和無機化合物[62]。Acer等[63]從石油污染土壤中分離出一株長鏈烷烴降解菌,鑒定為不動桿菌BT1A,該菌株在1%原油中培養7天后降解了83%的C11~C34正構烷烴。類似的烷烴降解菌還有不動桿菌DSM17874[64]、兩種放線菌SoB和SoCp[65]、假單胞菌GPo12[66]等。
在人工控制條件的生物反應器中,可以采用適宜的細胞生產各種所需的酶。微生物已進化出許多不同的酶催化機制來去除有機鹵化物,如一些細菌能將有機鹵化物作為碳源、能源或電子受體來使其自身得到增長。細菌裂解碳-鹵素鍵是由多種酶催化的,譬如某些鹵代烷脫鹵酶具有通過碳-鹵素鍵的水解裂解將這些鹵代烴轉化為相應的醇的潛力[67]。烷烴脫鹵酶能對碳-鹵素鍵進行裂解,從而將這些外源性生物轉化為代謝中間體。紅球藻的第二代鹵代烷水解酶Y2[68]利用C14、C16和C18烷烴作為生長底物,在1-氯丁烷的作用下,培養的紅球藻Y2休眠細胞懸浮液能在好氧和厭氧條件下催化脫鹵反應。在C7~C8的1-氯代烷烴和相應的正構烷烴存在下,紅球藻Y2的氧合酶型脫鹵酶活性明顯增強。此外,也有研究者分別從海洋環境和六氯環己烷垃圾場中發現了食堿菌分泌的鹵代烷脫鹵酶HLD[69]以及鞘脂單胞菌株分泌的脫氫鹵素酶LinA2[70],這些酶均在降解各種短鏈鹵代烷烴中起著關鍵作用。但用這些細菌分泌的脫鹵酶或表達這種酶的細菌對SCCPs進行完全的生物去除仍是一個挑戰(因酶對SCCPs的體外轉化緩慢且不完全),且需要提前研究轉化產物的環境和毒理風險[71]。
2.2.2 細菌吸附法
細菌處理污水體系中,細菌在沒有被馴化的情況下對污染物降解效果較差,但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對污染物存在一定的吸附性能。現階段利用細菌吸附去除抗生素等污染物,仍是行之有效的手段(見表1)。
從表1中可以看出,細菌及其聚合體污泥作為吸附劑吸附難降解污染物具有非常好的去除效果,主要通過表面吸附、靜電相互作用以及化學吸附將污染物從液相轉移到固相,用較短的時間就能達到較好的去除效果。因此,SCCPs作為一種難降解有機污染物,對其進行細菌吸附去除也將是一種有效可行的方法,但迄今為止,尚無研究者用耐SCCPs的細菌作為生物吸附劑對SCCPs進行吸附去除。

表1 其他POPs的細菌吸附去除性能
在生物去除過程中,合適的微生物對污染物的生物吸附/降解至關重要。可以推測,在CPs污染地區應用細菌去除的方法將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與市場。但大多數細菌只能利用有限的含氯有機化合物,且降解周期較長,同時由于每種細菌的生理特性和降解機理不同,細菌對降解物質的耐受性和降解程度也不同。因此,為探索更多新的微生物及其在SCCPs降解中的行為,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來了解SCCPs生物降解和生物轉化潛力。
2.2.3 植物吸收法
植物可通過根的被動吸收或主動吸收從土壤或水中吸收污染物,如非離子型污染物,主要是通過化合物在根內外電位梯度驅動,被動吸收進入植物體內,另外植物也可通過葉片吸收大氣中的污染物[77-78]。Li等[27,79-80]選取大豆和南瓜作為模型植物,通過室內水培暴露實驗發現了在植物作用下的SCCPs碳鏈斷裂過程。高氯代的SCCPs同系物在南瓜和大豆幼苗的作用下能夠脫氯為低氯代同系物,并且在分子上發生氯原子重排,在兩者組織中均檢測到脫氯和氯重排產物——子體氯癸烷C10H17Cl5、C10H16Cl6和C10H15Cl7等,同時還發現了碳斷裂產物。相比之下,大豆對親本SCCPs的易位和降解速度快于南瓜,且降解程度大于南瓜,而南瓜對親本SCCPs的累積程度則大于大豆。雖然實際土壤-植物系統與水培暴露系統不同,SCCPs往往吸附在土壤上,生物利用度可能更低,但為環境中SCCPs的植物降解提供了重要信息。
2.2.4 其他去除法
除了已經成功應用的上述物化法及生物法外,其他去除SCCPs的方法(包括真菌、藻類及動物等去除法)在理論上也具有可行性。與細菌降解相比,人們對于真菌降解知之甚少。因微生物降解動力學的研究尚不全面,將真菌應用于SCCPs的去除更具挑戰性。Murphy等[81]對在1-氯十六烷或1-氯十八烷上培養的兩種絲狀真菌(秀麗隱桿線蟲和帶狀青霉菌)和一種酵母(解脂假絲酵母)的脂肪酸組成進行了測定,這些生物能利用氯代烷烴作為唯一的碳源和能源,培養后這些生物中均存在大量的末端氯化脂肪酸。在某些情況下,微生物的脫鹵作用并不總優先于生物利用,而且有報道稱在細菌和真菌中長鏈氯代烷烴直接與氯化脂肪酸結合。此外,白腐菌分泌的胞外酶錳過氧化物酶MnP[82]也能有效降解四溴二苯醚,在培養15天后,降解率高達70%。這表明將真菌應用于去除SCCPs或許在理論上是可行的,但目前還沒有這方面報道,有待驗證。
鑒于在綠潮發生期間,綠潮藻[83]能去除海水中多環芳烴(PAHs),當其初始濃度為5μg/L時能去除91.3%。而且在沿海沉積物中沉積的大量藻類殘余物[84]也能吸附去除PAHs,但由于藻類光能自養的局限性,其降解效率很低,尚未有藻類降解SCCPs的相關報道。藻類是一種很有前途的可再生資源,隨著對環保生物替代能源消耗需求的日益迫切,利用藻類去除SCCPs的潛在技術理應被考慮。
利用動物去除SCCPs的文獻暫無報道,但存在去除其他氯代烷烴的報道。譬如,有研究發現從大藻組織中分離出的一種原生動物(海洋變形蟲)[85-86]能通過氧化脫鹵作用將氯代烷烴生物降解,轉化為相應的脂肪酸。變形蟲TrichosphaeriurnI-7在培養24h內開始吸收并轉化鹵代烷1-氯代十八烷,并將其作為碳源加以利用,培養6天后在培養皿表面未檢測到氯烴。海洋變形蟲攝取并生物降解鹵代烷烴1-氯代十八烷,經氧化脫鹵生成十八酸,十八酸與細胞脂質結合或氧化降解。原生動物在SCCPs去除方面還需進一步研究。
2.3 各去除方法的優缺點比較
不同方法下SCCPs的去除效果存在差異,表2比較了不同方法之間的優缺點及去除SCCPs的影響因素和可能機理。從表2可以看出,不論哪種方法,pH和溫度都是SCCPs去除的主要影響因素。物化法對SCCPs去除效率高,但操作條件復雜、苛刻,同時成本也高;而生物法去除SCCPs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則依賴于生物本身的降解吸附性能,總體而言,生物法處理周期普遍較長,且容易受到外界環境的干擾。

表2 SCCPs(包括氯代烷烴)去除方法的對比
一些典型方法去除SCCPs(包括氯代烷烴)的可能降解途徑如圖2所示。物化法通過氧化脫氯生成烷烴,后通過碳-碳鍵斷裂變成小分子物質;細菌法通過氧化酶氧化脫氯形成烷烴,后氧化形成有機酸等一系列小分子物質;植物吸收法主要通過氯重排、脫氯等反應生成烷烴類物質。這些方法中有些能將氯代污染物完全礦化,有些則不能。每一種去除技術也都有其針對性和局限性,處理SCCPs的物化法成本高,而生物法則是一種簡單、安全、成本效益高的治理污染的技術,通過生物降解能力,把有毒的有機污染物轉化為無害的物質。總體而言,相較于物化法,生物法由于工藝簡單、經濟環保而具有較大的后續發展潛力,但不足之處是降解周期長,后續與物化處理或植物吸收等方法耦合可用于實際工藝開發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圖2 不同方法去除SCCPs(包括氯代烷烴)的降解途徑
3 結語與展望
CPs是一種含有氯化物的有機混合物,也即PCAs,氯化程度在30%~70%之間。在所有CPs組中,SCCPs的環境污染是最受關注的問題,本文主要針對現階段SCCPs的去除方法進行比較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1)迄今為止,SCCPs已經在許多不同的環境中發生遷移,包括土壤、污水污泥和水體、生物和人體,甚至能傳播到極地等偏遠地區。環境風險較大,但現階段關于環境中SCCPs去除方法的研究較少,尚未引起廣泛關注。
(2)現行的SCCPs去除方法主要分為物化法和生物去除法。物化法能將SCCPs部分或完全礦化,但成本高。與物化法相比,生物去除法能通過氧化酶氧化脫氯形成烷烴及酸類物質,是一種相對經濟且清潔的方法。由于微生物分布廣且代謝能力強,利用細菌去除SCCPs的方法可用于各種環境中,應用前景廣闊。
(3)細菌吸附和降解是一種經濟的污染物去除技術,其中細菌降解是當前去除環境中SCCPs較為有效的方法。以往對SCCPs細菌降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好氧生物降解方面,但缺氧或厭氧環境下卻鮮有報道,同時未發現利用細菌吸附去除SCCPs的研究。
雖然上述提到的去除方法實現了SCCPs的減量化,但是一些方法由于成本高或降解時間長而阻礙了技術的應用,目前的研究只針對有限的幾種SCCPs進行去除,而且大多停留在實驗室階段,因而,如何獲得對SCCPs有高效去除效能的新方法和技術仍需不斷探索和研究。今后關于SCCPs去除方面仍需開展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1)針對細菌降解去除周期長的缺陷,可通過與其他方法進行耦合,譬如可與物化處理或植物吸收等方法聯用,以提高降解率。同時,對于物化和生物降解后的產物需要進行毒性試驗研究,以避免降解產物對環境產生二次污染。
(2)針對長鏈烷烴降解菌株對大分子的SCCPs降解能力差甚至不能降解的缺陷,可通過生物共代謝強化或改良菌株來構建出對SCCPs具有高效降解性能的菌株,但對于改良菌株特別是基因工程菌株對環境產生的影響也需要進行后續試驗評價。同時需研究處于低氧或厭氧環境下細菌對SCCPs的去除,以期完善不同環境下細菌與SCCPs的相互作用機制。
(3)基于生物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新分離物的不斷探索,古生菌或極端微生物日益引起研究者的重視。因此,未來的研究可著重于識別和評價這些古生菌或極端微生物對難降解有機污染物的去除效率,進而獲得具有高效去除SCCPs的微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