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的反思:從“歷史的終結”到“民主的崩壞”
弗朗西斯·福山 潘競男/編譯
編者按:本文作者弗朗西斯·福山是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曾師從塞繆爾·亨廷頓。福山在其代表作《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中認為,冷戰結束意味著自由民主的勝利,人類的制度演進史將走向終結。多年來,他一直在修正自己的觀點。
面對美國日漸失靈的政治機制,2014年我在《外交》上撰文,對植根于美國的政治衰退深表遺憾。我當時寫道:“知識僵化和權力固化共同阻礙著制度改革,同時誰都無法保證,在不沖擊政治秩序的前提下能改善現狀。”

弗朗西斯·福山
隨后幾年里,伯尼·桑德斯和唐納德·特朗普在政壇崛起,似乎預示著某種政治沖擊。2016年總統大選期間,在重新思忖政治衰退時,我驚喜地注意到“兩邊的選民都奮起抵制他們眼中腐敗的‘建制派,轉而投向激進的‘局外人,希冀得到政治清明 ”。不過,我也發出提醒,“民粹主義兜售的‘靈丹妙藥幾乎毫無用處,一旦采納,不僅會阻礙經濟增長、加劇社會矛盾,更有可能讓情況變得更糟而非更好。”
事實上,美國人還是接受了這些“靈丹妙藥”——至少有足夠多的美國人接受,否則特朗普就不可能入主白宮。不過,形勢卻變得越來越糟。政治惡化以驚人的速度持續著,規模之大讓世人難以預料,最終導致1月6日暴徒沖擊國會山——這可是美國總統鼓動的暴動。
與此同時,這場危機的深層因素并無改變。執掌美國政府的依舊是強大的精英群體,他們為了自身利益不惜歪解政策,結果便是政權合法性大大降低。這些問題以出乎意料的方式發展變化。兩種新現象讓形勢更加糟糕:新通信技術令協商民主的公共基礎不復存在,紅藍兩大陣營的政策分歧已上升為文化認同上的分歧。
無法調和的分歧
不同陣營厭惡的對象截然不同。左翼人士認為,精英群體無疑是大企業和資本利益集團,如石油公司、華爾街銀行、對沖基金富豪和共和黨的超級捐贈人——他們的說客和金錢致力于保護他們的特殊利益,使其免受任何形式的“民主清算”。但在右翼人士看來,天生邪惡的精英群體是那些與美國保守派的傳統價值觀或基督教價值觀相左的人群。這些人以“喚醒”世俗意識為己任,是主流媒體、高校、大公司、好萊塢的超級經紀人。即使在觀點看似重合的議題上,如對科技巨頭權力擴張的不斷擔憂,雙方的顧慮也各不相同。藍色陣營指控推特和臉書推廣陰謀論和特朗普主義,而紅色陣營則認為這些公司的問題在于他們對保守主義精神的偏見。
體制的僵化已變得越來越明顯,但體制也有其優點。憲政中的分權制衡機制一直在奏效:盡管特朗普不遺余力地試圖削弱制度基礎,但法院、官僚機構和地方官員卻令他無法踐行最壞的舉措。最明顯的例子莫過于特朗普試圖推翻2020年總統大選的結果,但以失敗告終。司法系統——通常就是特朗普任命的大法官——拒絕了特朗普方面提交法庭的數十起無意義的訴訟。共和黨官員如布拉德·拉芬斯珀和其他負責監督佐治亞州選舉的人,英勇地站出來反對總統,拒絕總統在該州非法扭轉他的歷史性失敗。
不過,這些制衡特朗普的機制反過來也會令自我革新大打折扣。得益于選舉人團制度和參議員的產生機制,共和黨即便在聯邦和州一級的選舉中贏得的大眾選票較少,也能在參議院享有絕對優勢。取消選舉人團制度是不可能的,因為通過和批準相關法案的門檻非常高。雖然民主黨在參議院以微弱優勢令共和黨在內閣任命等普通議題上失去了否決權,但在更大議題上——如哥倫比亞特區的州地位或新的《投票權法案》——他們勢必遭遇共和黨的掣肘。即使是推動野心相對較小的議案如新的經濟刺激計劃,拜登也需要運氣和技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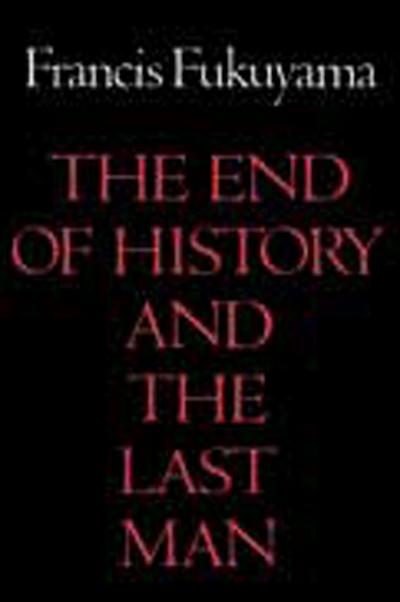
上世紀90年代,福山在其著作《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中表示,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制可能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和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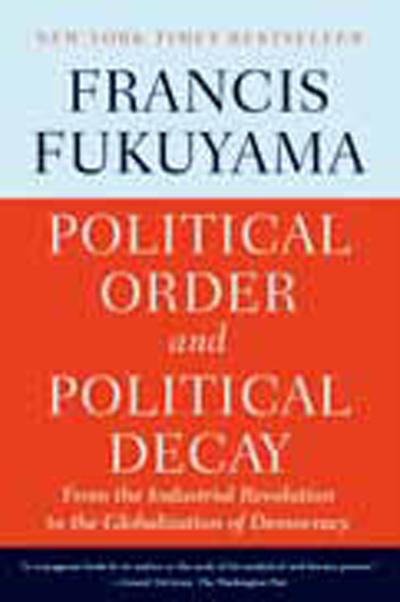
2014年,福山在《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中修正自己的觀點,認為除了法治和民主,國家治理能力同樣重要。多數觀點認為,中國崛起和中東混亂導致福山必須修正觀點。
從政黨到邪教
正如我在2016年的文章中指出的,美國制度失靈的首要問題是制衡機制同政治極化相互交織,黨派斗爭僵持不下、持續不斷。政治極化愈演愈烈,科技是驅動因素之一。新技術削弱了主流媒體和政府機構等正式組織塑造民意的能力。最新的昆尼皮亞克民調發現,如今有77%的共和黨人相信2020年總統大選存在重大舞弊。數千萬人投票支持特朗普,不是因為他們不喜歡民主理念,恰恰相反,他們覺得,這才是捍衛民主,防止“偷走大選”的民主黨上臺。
解決技術引發的問題會是未來一段時期的一項重大挑戰。暴徒襲擊國會山后,推特和臉書關閉了特朗普的賬號,這個決定合情合理。但從長遠來看,私營公司自行作出對公眾影響重大的決定是不合法的。當然,先前坐視這些平臺發展壯大到如此地步,本身就是政府的失誤。
另一個問題也加深了政治極化——政策爭論升級為身份之爭。上世紀90年代出現政治極化時,雙方爭論的焦點往往是稅率、醫保、墮胎、槍支、海外使用武力等問題。這些問題現在并沒有消失,但爭論的焦點被特定群體的身份問題取而代之,種族、族群、性別和其他社會標志都是身份的界定標準。
政黨被政治“部落”取代。“部落政治”在共和黨中最為明顯。特朗普輕輕松松地就讓共和黨及其選民拋棄了他們原有的核心價值,如信仰自由貿易、支持全球民主和反對獨裁。當他越來越神經質和專注自我后,共和黨就越來越個性化。在特朗普執政期間,你的共和黨成分取決于你對他本人的忠誠度。如果你跟他的言行有絲毫偏差,那你就出局了。共和黨在2020年全國代表大會上沒有推出任何新的黨綱,而是直截了當地申明,他們會支持特朗普想要的一切。為什么佩戴口罩和嚴肅對待新冠疫情這種小事也能引發激烈的黨派紛爭?原因就在此。

2016年特朗普勝選,福山在《金融時報》發文指出,整個人類世界已經進入“民粹式民族主義”時代。
2016年后,地理環境和人口因素讓社會分裂愈演愈烈,成為以上問題發酵的土壤。正如政治學家喬納森·羅登所展示的,支持或反對特朗普的最大關聯性因素是人口密度。美國社會被分割成截然不同的兩種價值體系:藍色陣營的城市、近郊和紅色陣營的鄉村、遠郊。但結構性因素不能完全解釋目前的形勢。美國國家公共電臺和益普索在去年秋天進行的一項民調發現,近1/4的共和黨人相信“匿名者Q”陰謀論的核心主張。共和黨不再是基于相同理念和政策的政黨,更像是一種邪教組織。
“部落政治”也存在于左翼群體中,但形式上沒有那么突出。身份政治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左翼社會運動的產物。基于身份的社會動員,起初是為了對抗因種族、族群、性別或性取向而形成的社會歧視。但如今對一些左翼人士來說,社會動員就是為了獲得群體認同,得到社會對群體差異的正面肯定。
分裂之家
拜登上臺,誰也不知道美國將走向何處。最大的不確定性是共和黨內部會發生什么。國會山的暴力風暴是特朗普及其追隨者的嚴重越權,一些共和黨人終于走上了與他公開決裂的道路。幾年前,共和黨不僅贏得總統大選,還控制了參眾兩院,而現在這些優勢全然不再。特朗普的個人崇拜已經主宰了共和黨,以致訴諸暴力也沒能讓追隨者離開。可以想見,為了適應失去權力的現實和擴大黨內聯盟以贏得日后的大選,先前的主流共和黨人會穩健地重塑權威。再或者,特朗普可以把自己打造成甘于為國家犧牲一切的烈士,從而保持他的黨內權力。最極端的是,特朗普及其鐵桿追隨者可能會變身為地下恐怖分子,用暴力反擊他們心中非法的拜登政府。

2020年, 福山接受《觀點》采訪,承認新自由主義已經死亡,政府力量必須加強。
事態如何演化對未來幾年的全球民主將產生重大影響。就像上世紀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一樣,我們不僅要拋棄特朗普主義,還要徹底取消其存在的合法性。為國家建章立制的社會精英們必須重拾勇氣,重塑道德權威。他們能否迎難而上不僅決定著美國制度的命運——更重要的是,還將影響美國人民的命運。
[編譯自美國《外交》]
編輯:要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