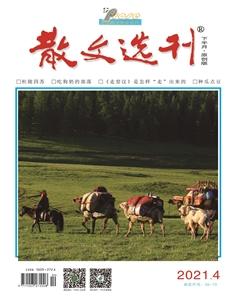一碗天羅子
吳有君

直白地說吧,天羅子就是一道菜,“今天沒菜吃,打碗天羅子”這句話,村民一天到晚都吊在嘴上。有時,自己身上的“軍用書包”還沒摘下,就會接到母親的指令:“打天羅子去!”“打”,就是“摘”,到天羅地里小心地采摘。天羅是何物?其實就是全身是寶的絲瓜呀。
那時,是生產隊的年月。老家叫汪家園,既可愛,又可怕,一千多畝的泥沙地,有相當的肥力,自然就成為城里的“菜園地”。要命的是整個行政村(過去叫大隊),正好長在信江和豐溪河的間距里,完全是被北面的江、南面的河裹挾而來。難熬的是清明前后,見識一下村民的口頭禪“四月的洪水四月的菜”,說的是洪災和菜荒結伴而來,上半年的藤蔓蔬菜剛剛下地,自然就沒有下飯菜,好在有天羅子的接濟。打天羅子,就是從坐果期即4 月底的菜荒時開始的。
很有意思,天羅開花是雌雄同株,兩者都長在一個花序上,形成總狀花序。雌花是帶著“小孩”來的,細長的花柄前方都長有一條小絲瓜,這是正品果實。雄花不長瓜只長“子”,所謂“子”就是有十余個類似小螺絲造型的青壯花骨朵,簇擁在雄花的背下方,看上去,有點兒母雞抱小雞的滑稽。這種“花骨朵”,就是造福村民的伴生品“天羅子”。
打天羅子時,即使生產隊長看到了,也是不打橫杠,最多笑瞇瞇地提醒不要傷及帶果實的雌花。實際上,打掉天羅子,對天羅的生長是有益處的,疏掉了大量的雄花,更多的營養就奔向雌花。左鄰右舍、男女小孩兒,一般都在中午時分在天羅地照面。有的花骨朵到了傍晚就要開花。花打回家也是可以吃的,但糊塌塌不爽口。所以,大家趁中午以前就下手,便于打上青蔥狀態、吃起來非常清脆的“小蕾子”。中午雖然悶熱,還常常要忍受“蜘蛛網”罩到臉上發生的奇癢,但胃口的滿足壓倒了一切。
說來也奇怪,在我們這地方,老天十分地通人性,夏秋時分,動不動把臺風和陣雨送上門。穿行在密扎的天羅地,孩子們總是無意識地聚到一起,一邊拎著笆簍或端著洋瓷臉盆摘下心愛的天羅子,一邊放縱孩子喜歡玩耍沖雨的天分,任由身上單衣單褲濕透。家家吃,人人要,飯桌上,隔餐也不隔日。村莊十來個生產隊都喜歡多栽多種。我家所在的第十隊一種就是幾十畝,面積大于其他品種。后來看懂了,如果種少了,村民就打不上,乃至打不夠。不能指責菜農有私心,那是為了過日子被逼出來的“小算盤”。
母親在當時,做飯做菜是天生的廚娘。煤火炒出來的天羅子,即使不像現在這樣奢侈的有啤酒、料酒、碎肉幫襯,照樣好看又好吃。藍邊大碗里,青灰色的天羅子,搭配上斜切的紅椒絲,剁的白蒜泥,還有升騰的乳白色熱氣,看一眼,夾進嘴巴,品出了剛剛好的干濕度。清香味中有點兒甜,脆爽之中帶點兒苦,飽滿的口感,牽引著不停的筷子。我的舅舅和叫我舅舅的外孫,這兩代人雖然算不上酒鬼,但貪杯是事實。他們三天兩頭自帶廉價的“廣豐高粱”和“信州春”來,正是沖著媽媽手下一碗爽歪歪的下酒菜——“ 爆炒天羅子”。
歲月在翻書,老家也揭開了精彩的一頁。三座穿村而過的超美景觀大橋,帶活了老家。聲聲急的棚戶區改造,跨越了“一江一河”,四季常青的蔬菜現在不種了,好在天羅子沒有消失,反而越吃越香。周邊縣(市)的菜農、菜販摸透了上饒市區和郊區的人們對天羅子的偏好,到很遠的鄉村收購。如今,在老家新建起來的菜市場、鄰近的墟市,還有城區的農貿市場,都有天羅子的青影。不同的是,老家人現在想吃不是去打,而是去買。12 元一斤,隨便下單。如果不想自己燒制,就下館子,25 元上下就可以點上一盤。
盡管搬離老家20 年,但天羅子仍然活躍在餐桌,每每吃起,感念深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