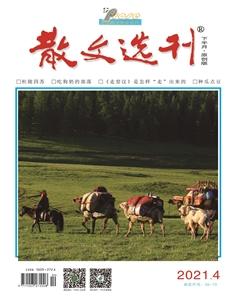父親打我
康涇
小時候很皮,大錯不犯,小錯不斷,老師經常到家里“告狀”。每次老師家訪走后,我就免不了挨父親的尺子。父親不善言辭,所以教育我的方式就是抽尺子。尺子是現成的,就是母親做裁縫用的直尺,是父親自己動手做的,竹條磨得光光的,上面的刻度也是父親一刀一刀刻上去的。小時候家里的玩具都是父親手工做的,連這把“戒尺”也不例外。
父親打我是有講究的。在父親看來,錯誤嚴重的,抽四五下,最多六下;程度輕一點兒的,抽兩三下。有時候他心血來潮,先征求我意見抽幾下。我不知道父親葫蘆里賣的什么藥,只好按照犯錯誤的嚴重程度,約莫著說個數兒,父親基本上就依我的要求抽。有時候父親還會再追問:“重一點兒還是輕一點兒?”我覺得既然犯錯誤了,輕一點兒是不應該的,就總是說重一點兒。尺子抽在屁股上,有一種麻麻的感覺,甚至忘記了疼——許是抽得過于重了,連疼痛感都消失了。因此當父親問我“痛不痛”時,我就直白:“不痛。”父親說:“不痛?那就再來兩記。”后來我就知道了,不痛也要說痛。
除了打我,父親有時候還讓我餓肚子。抽三四下,痛感或許很快就過去了;不讓我吃飯,真要了我的命。中午,父親打完我之后,就把我晾在一邊,等他們吃完,就把飯菜一股腦兒都放進高我一半身子的菜櫥里。即使父母離開了,我也不敢自己爬上去偷吃,否則父親知道,一定還會打我。有一次姐姐看我可憐(因為是她把我犯錯誤的消息帶回家的),就偷偷把飯菜從櫥子里拿出來給我吃。父親知道后,還打了姐姐。從此她再也不敢幫我了。于是,我就只能餓著肚子去上學,這樣的下午我都是在眼冒金星中度過的。這樣的次數多了,親戚朋友有知道的,就勸父親,別把孩子的胃餓壞了。父親說,他們小時候經常有一頓沒一頓的,也沒生什么胃病。
父親打我最兇的一次,是母親的手臂被繅絲機軋斷之后。本來家里的活兒基本上都是母親包攬的,但是因為手軋斷后,生活自理都有些困難,母親就把我和姐姐叫到跟前,給我們分工家務活兒:姐姐負責掃地,我負責洗碗。我覺得吃了大虧,當場就不同意。因為地可能不用每天打掃,碗卻要每天洗三回。母親說,男孩子應該多做一點兒,干干活兒,力氣就來了。無論好說歹說,我就是不答應。一直到父親下班回家,我還是沒答應。父親一怒之下,就打了我兩記耳光。那天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死倔一根筋,不論軟硬兼施就是不肯。父親實在氣不過,就把我捆綁著吊在單位白場上一棵樹上狠命地打。父親單位同事走過,都勸阻父親。父親居然拉下臉,對勸解的所有人說:“今天誰要是把他放下來,就跟誰打。”據說那天我始終沒答應,父親無奈,最后只好把我放下來。以后幾天,父母親理都不理我。可能我慢慢覺得自己理虧,就悄悄把洗碗的活兒接了過來。后來每次說起這個事,父親都會笑著說:“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父親打我的歷史,一直到我小學畢業才告結束。父親長得矮,只有一米六幾的樣子,我一上初中就超過父親身高,他就再也不打我了。他知道他打不過我了。工作以后,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提到父親打我的事,不小心被父親讀到。他小心謹慎地問我:“這些事你還記得這么牢啊?”我笑著對父親說:“別怕,只是寫寫的。”那時候我已經高出父親一個頭。按照父親的說法,我比他高之后,他有點兒怕我了。
在父親那一代人觀念里,總覺得棍棒底下才能出孝子,雖然他們并不知曉“子不教,父之過”的古訓,但確確實實在行動上這樣踐行著。好多看我長大的人都說,我真的就是給父親打出來的。我的一位后來做了領導的老師就是這樣評價我的。她說,小時候那么吵的一個人,怎么現在好像完全變了一個人?言下之意,要不是我父親那樣打我,今天我可能早就犯下大錯,更別說像模像樣地做人了。
如今,父親早已離去。在我印象中,父親除了打我,一輩子似乎再沒有別的對我產生重大影響的教育方法——我的童年時代似乎只記得是在父親的棍棒底下生活著的。但是現在若要我說出父親打了我那么多次究竟有什么過錯,我卻一樣也說不出來,好像所有錯的都在我,而不是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