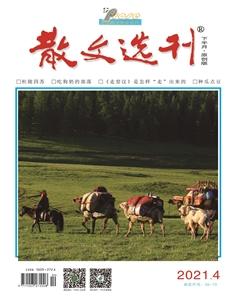魚販子
林嬌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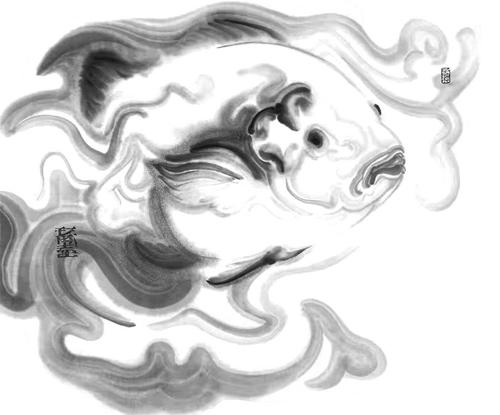
周末的中午,我到一個光顧了20 年的魚販子家去買黑魚。
這家魚攤兒位于菜市場門口,魚販是50 歲出頭的小老頭兒,20 年的片魚技術,他早已爐火純青。他先麻利地剖好魚,沖刷好魚鱗和內臟,用干凈的抹布搽試干凈,他如雕花般的片魚技藝即將精彩紛呈。一般來說,片魚前,他會有個儀式,像是給魚做個短暫的禱告或默哀,接著慢慢地片魚。那動作輕緩,像是蜻蜓點水,那么慢,慢得串不起光陰的線。好在午后,買魚的顧客并不多,經得起他的精雕細琢。倒是我著急起來,我見不得魚那樣的痛苦。但人就是這樣虛偽,明明見不得那樣的殘忍,最后還是要吃了它。
等待很漫長,我分散了注意力,上秤看自己胖了沒?住在海邊的人,吃海鮮較多,吃河鮮便少了許多。我通常一兩個月吃一次酸菜魚,去他家殺一條河魚,來一次,便會稱一次自己的體重。冬天來的時候,一次比一次重,夏天來的時候,一次比一次輕。似乎也是說得過去的。我說秤不準。魚販急了,怎么可能?圍觀的人都上來稱,笑出了眼淚,說秤是真的不準呀!魚販更加不悅,黑炭色的臉,織著一片死氣沉沉如陰霾的天。玩笑也開夠了,魚,還沒片好。魚肉與魚骨分離了,那副魚骨架,瘦巴巴的,露出尖銳的刺。魚骨除了熬出濃白的骨頭湯,好像沒有其他作用了。魚販毫不猶豫地把魚頭、魚骨丟進垃圾桶,用心片魚片。午后的陽光透過透明玻璃,我看見一朵朵玉芙蓉般的魚片從他那雙水腫又開裂的手掌里變出來。一朵兩朵晶瑩的水晶花,飄若浮云,慢慢升入上空……
果然,他片的魚很漂亮,如白色雕花。這時候,有人來買鯽魚,他是來不及上秤的,他用手一掂,伸出幾個指頭,顧客會意,欣然付款。我注意到他家有兩臺秤,一臺是電子臺秤,擱在桌子上,一般稱些散賣的河魚。另一臺是個老古董了,是大型的電子臺秤,秤身沾滿了歲月的灰塵,是為早上批發商計量的。這么多年了,我不曾細細觀察過這臺秤,總是一來就上來稱一稱。沒有電子秤前,我是不認識那種帶有星點和錐度的木桿或金屬桿的桿秤的,去買東西,商販總是把秤桿橫到我面前,說:“看看,看看夠不夠秤!”我是不懂的,總是假裝自己能看懂。有了電子秤后,就能一目了然。但更多的時候,商販稱重的速度過快,常常讓我還沒看清,就神速地打包。我不喜歡斤斤計較,也不會討價還價,更多時候說多少就給多少,很多商販就很自然地把零頭抹掉了。那些把零頭抹掉的商販,心里也有一桿秤呢。這個魚販子,我光顧他20 年了,他大兒子今年26 歲,小兒子今年8歲。這20 年,他買了兩套房子和一個店鋪,說起來那個自豪,魚腥味撲鼻的小小鋪子里,洋溢著他喜形于色的滿足感。他除了片魚很慢,還很健忘,常常是稱過的價格,與片過魚后的價格不一樣。但只會往多了說,從沒說少過。只要我提出異議,他就會淡淡地說:“哦,我忘了。”說多了,大家都叫他“呆進不呆出”。
但是這次,我一向佩服的黑臉魚販子,居然把我的魚,片得厚薄不一。那條活潑亂跳的魚,白白挨了那千刀萬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