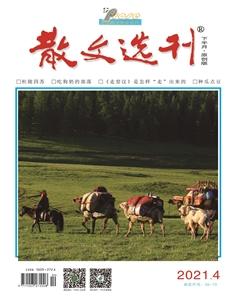老家的土炕
萬有文
我的老家是一個處在祁連山下的小村莊。說起老家,讓我倍感溫暖和記憶猶新的就屬老家的那方土炕了。
那一方土炕,曾承載了一代又一代老家人的愿望和夢想。無論是人生的暢想,還是生活的歡娛。
一個個幼小的生命從那里誕生,然后在土炕上一天天長大,像大地上的小樹苗一樣茁壯成長著。有了土炕的保護,有了土炕提供的溫暖,幼小的生命便成長得特別快。土炕似搖籃,在夢鄉(xiāng)里我們聽到母親的搖籃曲,看到母親那張慈祥的臉一次次浮現(xiàn)。就在那方土炕上,我們第一次笑,第一次做夢,第一次尿遺,第一次感受到一個人溫暖的懷抱。
土炕似懂人情。夏天它讓自己變得清涼宜人,有了疲憊則可以整個地將身心放松,躺在它堅實而平硬的后背上,疲憊頓時消散,不一會兒便可進入夢鄉(xiāng)。而冬天,在麥草和些許的煤炭灰的熏燒下,土炕便一點點兒地溫暖起來,進而整個土炕都透著人間的大暖。從小我們都有賴床的毛病,就是有土炕嬌慣著,像我們的長輩一樣寵愛著我們。我們當(dāng)然更不想過早地從那溫暖中脫離出來。因為鄉(xiāng)村的冬天有著刺骨的寒冷,土炕成為我們躲避和防御這些寒冷的唯一去處。我們趴在被窩里,整個身體都被土炕的熱量拱著,熱得整個臉都紅彤彤的。看著地下忙碌的母親,為我們做飯、打掃房屋。
而在冬天,老人們也在這里找到了最終的歸宿,幾乎一整個冬天,他們都將自己的身體和命門交予土炕,似乎土炕可以給予他們生命的力量。在生命一天天垂危的狀況下,土炕讓他們減輕了日漸感覺到的冷。一整個冬天,老人們不是在暖墻彎下,就是在土炕上度過著他們慘淡的剩余時光。
而年輕人在土炕上找到的卻是更多的歡樂。新婚宴爾,一場酣暢淋漓的人生大戰(zhàn)和愛語、糾纏,與人生的矚望,直到數(shù)月后,一個小生命呱呱落地,落在那方土炕上,那人生的幸福和歡樂才真正地打開門。多好!添丁的熱望被土炕的溫暖包裹著,從此一家三口在土炕上升起的月光下幸福著。也許歡樂的極致就是幸福,而土炕正是這幸福誕生的搖籃。
兩筐紋子、一筐麥草就可以保持一夜的溫暖。為了讓溫暖更長久一些,再熱烈一些,母親還要將爐子里沒有著敗的煤灰,或和泥煤留下的碎塊扔進炕洞里。這樣,直到第二天,再填坑時,炕都是熱的。那時候冬天太冷了,又沒有更多的煤加熱取暖,將整個房屋都燒得熱火朝天。而大地上,那些麥草秸稈是富裕物,拿來填炕。在炕上的被窩里取暖,要比在房屋的火爐旁取暖更加愜意一些。因為在炕上當(dāng)身體暖洋洋的舒服勁兒升起的時候,眼簾會不由自主地合在一起。那便乘著土炕的溫暖,睡上一覺吧。這種自由、天性、自然、舒服的舉動,是對當(dāng)時鄉(xiāng)村生活的一種詮釋。在土炕上什么也不想,就那樣睡著,直睡得天昏地暗。連睡夢中都能感覺到土炕絲絲的暖流正一點點兒地浸入身體,富裕權(quán)貴又如何?王侯將相又如何?那不過都是虛無縹緲的東西,還不如在這土炕上一夢長起,夢柯南山。
這多少有點兒像希臘斯多葛主義者的想法了,我想,那個時代的農(nóng)村人大多都是斯多葛主義者吧。
歲月靜幽。鄉(xiāng)村生活已離我們漸漸遠(yuǎn)去,土炕仍沉靜在故鄉(xiāng)一隅,但它給我們的記憶是美好的,也是長久的。當(dāng)我們拖著疲乏的身體,每天奔波于生活當(dāng)中時,我們便想起了它;當(dāng)更多的病痛糾纏于我們的時候,我們也會想起它;當(dāng)人生失意落敗的時候,我們多么希望找到一方土炕,能躺下去,就像我們剛出生不久,在父母和土炕的懷抱里一樣再撒一回嬌。
只是,只是啊,時光已不再了,我們只能將記憶埋在心靈深處,一點點兒地品嘗、回味、感慨,那一方土坑給予我們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