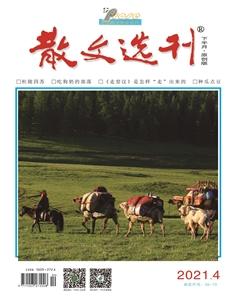《走窯漢》是怎樣“走”出來的

《北京文學》是我的“福地”,我是從這塊“福地”走出來的。1985 年9 月,我在《北京文學》發表了短篇小說《走窯漢》,這篇小說被文學評論界說成是我的成名作。林斤瀾先生另有獨特的說法,他在文章里說:“劉慶邦通過《走窯漢》,走上了知名的站臺。”汪曾祺先生也曾對我說:“你就按《走窯漢》的路子走,我看挺好。”
我的老家在河南,1970 年7 月,我到河南西部山區的煤礦參加了工作。我一開始寫的小說,在河南的《奔流》和《莽原》雜志上發表得多一些,一連發表了八九篇吧。時在《北京文學》當編輯的劉恒,看到我在河南的文學雜志上發表的小說,寫信向我約稿。我給《北京文學》寫的第一篇小說《對象》,發表在《北京文學》1982 年第12期。大概因為這篇小說比較一般,發了也就過去了。但這篇小說能在《北京文學》發表,對我來說是重要的,難忘的。我認為《北京文學》的門檻是很高的,能跨過這個門檻,我的寫作自信增加不少。劉恒繼續向我約稿,他給我寫的信我至今還保存著。他在信中說:“再一次向你呼吁,寄一篇震的來!把大旗由河南移豎在北京文壇,料并非不是老兄之所愿了。用重炮向這里猛轟!祝你得勝。”劉恒的信使我受到催征一樣的強勁鼓舞,1985 年夏天,在我寫完了長篇小說《斷層》之后,緊接著就寫了短篇小說《走窯漢》。寫完之后,感覺與我以前的小說不大一樣,整篇小說激情充沛,心弦緊繃,字字句句充滿內在的張力。我妻子看了也說好,她的評價是,一句廢話都沒有。這篇小說我沒有通過郵局寄給劉恒,而是趁一個星期天,我騎著自行車,直接把小說送到了《北京文學》編輯部。那時我家住在建國門外大街的靈通觀,《北京文學》編輯部在西長安街的六部口,我家離編輯部不遠,騎上自行車,十幾分鐘就可到達。因為那天是休息日,我吃不準編輯部里有沒有人上班。我想,即使去編輯部找不到人也沒什么,我到長安街遛一圈兒也挺好。我來到編輯部一間比較大的編輯室一看,有一個編輯連星期天都不休息,正在那里看稿子,而且,整個編輯部只有他一個人。那個編輯是誰呢?巧了,正是我要找的劉恒。我們簡單聊了幾句,劉恒接過我送給他的稿子,當時就翻看起來。一般來說,作者到編輯部送稿子,編輯接過稿子,會說,稿子他隨后看,看過再跟作者聯系,不會立即為作者看稿子。然而,讓我難忘和感動的是,劉恒沒有讓我走,馬上就為我看稿子。他特別能理解一個業余作者的心情,善于設身處地地為作者著想。劉恒在一頁一頁地看稿子,我就坐在那里一秒一秒地等。他看我的稿子,我就看著他。屋里靜得似乎連心臟的跳動都聽得見。我心里難免有些打鼓,不知道這篇小說算不算劉恒說的“震”的,亦不知算不算“重炮”,一切聽候劉恒定奪。在此之前,我在《奔流》上讀過劉恒所寫的小說,感覺他比我寫得好,他判斷小說的眼光應該很高。小說也就七八千字,劉恒用了不到半個小時就看完了。劉恒的看法是不錯,挺震撼的。劉恒還說,小說的結尾有些出乎他的預料。我的小說結尾出乎他的預料,劉恒的做法也出乎我的預料,他隨手拿過一張提交稿子所專用的鉛印稿簽,用曲別針把稿簽別到了稿子上方,并用刻刀一樣的蘸水筆,在稿簽上方填上了作品的題目和作者的名字。
1985 年9 月號的《北京文學》,是一期小說專號。我記得在專號上發表小說的作家有鄭萬隆、何立偉、喬典運、劉索拉等,我的《走窯漢》所排列的位置并不突出。但在上世紀80 年代,人們主要關注的是作品本身的文學品質,對作品排在什么位置并不是很在意,看作品也不考慮作者的名氣大小。對于文學雜志上出現的新作者,大家帶著發現的心情,似乎讀得更有興趣。
小說發表后,我首先聽到的是上海方面的反應。王安憶看了《走窯漢》,很是感奮:“好得不得了!”她立即推薦給上海的評論家程德培。程德培讀后激動不已,隨即寫了一篇評論,發在1985 年10 月26 日的《文匯讀書周報》上,評論的題目是《這“活兒”給他做絕了》。程德培在評論里寫道:“短短的篇章,它表現了諸多人的情與性,愛情、名譽、恥辱、無恥、悲痛、復仇、恐懼、心緒的郁結、懺悔、絕望,莫名而無盡的擔憂、希望而又失望的折磨、甚至生與死,在這場靈魂的沖突和較量中什么都有了。這位不怎么出名的作者,這篇不怎么出名的小說寫得太棒了!”當年,程德培、吳亮聯袂主編了一本厚重的《探索小說集》,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小說集收錄了《走窯漢》。后來,王安憶以《走窯漢》為例,撰文談了什么是小說構成意義上的故事,并談到了推動小說發展的情感動力和邏輯動力。說實在話,在寫小說時,我并沒有想那么多。王安憶的分析,使我明白了一些理性的東西,對我今后的創作有著啟發和指導意義。
北京方面的一些反應,我是隔了一段時間才聽到的。有年輕的作家朋友告訴我,在一次筆會上,北京的老作家林斤瀾向大家推薦了《走窯漢》,說這篇小說可以讀一下。1986 年,林斤瀾當上了《北京文學》主編。在一次約我談稿子時,林斤瀾告訴我,他曾向汪曾祺推薦過《走窯漢》。汪曾祺看過一遍之后,并沒覺得有什么特別的好。林斤瀾堅定地對汪曾祺說:“你再看!”等汪曾祺再次看過,林斤瀾打電話追著再問汪曾祺對《走窯漢》的看法。汪曾祺這次說:“是不錯!”汪曾祺問作者是哪里的,林斤瀾說:“不清楚,聽說是北京的。”汪曾祺又說:“現在的年輕作家,比我們開始寫作時的起點高。”在全國第五次作家代表會上,林斤瀾把我介紹給汪曾祺,說這就是劉慶邦。汪曾祺像是一時想不起劉慶邦是誰,伸著頭瞅我佩戴的胸牌,說他要驗明正身。林斤瀾說:“別看了,《走窯漢》!”汪曾祺說:“《走窯漢》,我知道。”
可以說,是《走窯漢》讓我真正“走”上《北京文學》,然后走向全國。將近四十年來,我幾乎每年都在《北京文學》發作品,有時一年一篇,有時是一年兩篇。在《北京文學》創刊70 周年之際,我專門統計了一下,迄今為止,我已經在《北京文學》發表了35篇短篇小說,5 部中篇小說,一篇長篇非虛構作品,還有七八篇創作談,加起來有60多萬字,都夠出兩本書了。
走窯漢,是對煤礦工人的稱謂。我自己也曾走過窯。煤還在挖,走窯漢還在“走”。我持續不斷地寫作,與走窯漢挖煤有著同樣的道理。“走窯漢”往地層深處“走”,是為了往上升;“走窯漢”在黑暗里“行走”,是為了采掘和奉獻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