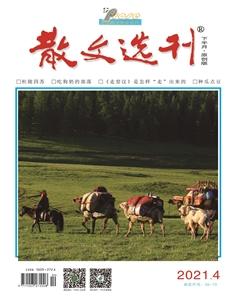吃狗奶的部落
海拉提別克

幾個世紀以來,有關我們家族的傳說是這樣傳過來的:我們大部落的祖宗架得克成家立業后,他的老婆生個不停,可生出來的嬰兒死個不斷。
有一年,她老人家終于生了個活嬰兒,就是我的祖先“吃狗奶的”那個。按哈薩克人的習俗,遭遇這種情況時,要么給嬰兒起個不順耳的名字,譬如:裹腳布巴依、屁股巴依、柴火巴依等等;要么起個祈禱含義的名字,認為這樣才能保住嬰兒性命。我的祖先生下來以后,在給他起名的問題上,人們商量來商量去拿不定主意,最后一個長者建議,不但要起個不好聽的名字,而且要把嬰兒過一下母狗腹部下面,這樣做的意思是這個嬰兒能活下來的同時,他后面會和狗崽一樣生出很多很多的孩子。當時,人們按長者的意思照做了,給嬰兒起了個“吃狗奶的”(iytemgen)名字。果不其然,從那以后,架得克有了十二個兒子,包括我的祖先“吃狗奶的”。再后來,架得克老人家建了大部落,他的十二個兒子建了分支小部落,我的祖先“吃狗奶的”是長子嘛,雖然他的名字有些刺耳,可在十二個分支小部落中還是挺有面子的。
雖然傳說是這樣講的,可沒有任何記載,所以,我們只能把這個傳說作為依據,對付那些說三道四的家伙。他們歪曲歷史真相,誣蔑我們的身世。有的說:“你們的祖先是吃著狗奶長大的,并不是人家說的那樣只過了一下母狗腹部底下。”還有的說:“你們部落的人無數,因為天下的狗兒都是你們的近親……”
連我三歲的外孫女一見到狗兒就說:“外公,你看看,又是你的親戚……”有一次,我帶她在城市的繁華地帶玩兒,她說要吃東西,我們走到一家小館子門口時,躥出一個卷毛的、白色的哈巴狗,立馬站在我面前搖搖尾巴,水汪汪的黑眼睛望著我。看到此景我的外孫女拍手蹦跳著喊:“外公,你的親戚多么可愛,它一眼就認出你是它的同胞,你給我買一只……”
那么,狗兒就成了我們家族的“祖先”嗎?完全不是,雖然我的鼻子像狗的鼻子一樣靈敏,雖然我在領導面前像狗一樣搖尾討好、搖尾拍馬屁……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雖然部落的名字不順耳,可令我自豪的是,我的祖先是十二個小部落的長子,是架得克老人家的大老婆生的,像是皇后生出來的皇長子啊!
原先的哈薩克族是純粹的游牧民族,新中國成立以后才慢慢地定居下來,他們的生產方式離不開狗兒,因為狗兒們保護他們的牛羊,他們不管條件允不允許,家家戶戶都要養狗,而且不止一只。可憐的狗兒們為護著他們的牲畜,與自己的近親同類狼兒們生死搏斗,有的還犧牲自己“寶貴”性命,而贏得了敬重……不過,狗兒在哈薩克人心目中的地位很低下,還不如駿馬,他們認為駿馬是男子漢的翅膀。駿馬死了,他們會把駿馬的頭顱放在懸崖峭壁上,這樣做等于厚葬。但再好的狗兒死了,不管它在活著的時候為他們付出了多少代價、在保護主人和牲畜過程中被狼咬死了或咬死了狼,也得不到這樣的待遇。他們還常說:“好狗不見尸。”這句話充分說明他們對狗兒的態度。可憐的狗兒們活著時候,不惜一切代價保護他們的羊群,而死了之后,他們還不愿看到它們的尸體,這實在不公平,實在不人道,這樣做和過河拆橋、卸磨殺驢有什么區別。所以,我一直想不明白我的同族為什么對我的“祖先”這樣的不公平。更不用說他們,連我們“吃狗奶部落”的人們也是和他們一樣的看法,對自己的“祖先”扯著“好狗不見尸”的看法,真不可思議,不肖子孫!
雖然我是“吃狗奶的”后代,但對狗兒也不太感冒,雖然我的耳朵和鼻子與狗類的耳朵和鼻子比沒那么敏感,但感應程度比一般人的好幾倍。平時,我能感覺到一般人絕對感覺不了的氣味,也能聽到一般人不一定聽到的聲音。這點我以下面的兩件事來證明:
第一件事,是我在山東的臨淄區掛職的時候發生的。有一天快到中午的時候,我的鼻子突然聞到了被割掉的青草氣味,我像狗一樣伸著下巴頦兒,把鼻子對準敞開的窗戶聞了又聞就說:“這個區城的某個地方開始打草了。”當時,我的同事們不信我的話。到了下午,我為了證明自己鼻子的敏感程度,帶著他們在區城里轉著圈兒找了半天,終于見到打過草的地方。果不其然,因進城的綠化地帶的草長高了,已經開始用機械打了。我的同事們到了跟前才感覺到被割的青草香味。
第二件事,發生在我當兵回來放牧的那年的秋季。那天,我和合伙放羊的伙伴們一起在伙斯里(簡易氈房,蒙古包哈薩克人叫作氈房)準備吃肉,肉已經下鍋了,我的耳朵愣了片刻,就聽到了玻璃瓶相撞的“叮當”聲,聲音很脆弱。我說:“等一會兒吧,有人馬上送酒來。”他們不信,也不理會我的話,我們就開始吃手抓肉。肉快吃完了,他們才聽到馬蹄的“嗒嗒”聲和玻璃瓶子輕輕相撞發出的“叮當”聲,在座的人目瞪口呆,驚訝的眼神望著我……
我一直在想,我的這種特點是不是“返祖”現象呢?但后來我的鼻子出現偶爾不通氣的毛病,就去醫院看病,醫生檢查完了對我說:“你的鼻子輕度鼻炎,對草類等植物特別敏感,和你的祖先‘吃狗奶的沒有任何關聯。”但他也說不清我耳朵的敏感原因,就說:“一般萬分之一的人會有這樣的現象。”我認為這個醫生也是個傻瓜,這樣的診斷能讓我心服口服嗎?等于一半兒的問題沒有解決嘛!
雖然心里對“祖先”抱著幾分敬意,但我這一輩子殺死了很多“同胞”。
那時候,我在喀爾交鄉工作。冬天大雪封山的期間,高山區的牧民反映有一群狼時不時攻擊他們的牛羊。書記鄉長商量后決定,派我和武裝干事去消滅那些黑心的家伙。
我們騎著馬往高山區走著,正好路過一個山口處的冬窩子前面。突然間,冬窩子的房前房后躥出一群狗,直向我們沖刺過來。平時,騎著馬的人遇到這種情況是不會恐慌的,因為牧區的狗一看到陌生人就像看到敵人一樣沖上來,但它們一般圍著騎馬的人狂吠轉圈兒,騎馬的人走遠了,它們就顯出很得意的樣子,昂著頭停下來,這樣做的意思就是把陌生人給嚇跑了,它們看到陌生的牲畜也會這樣做。可這次情況大不一樣,一只白頭黃狗沖過來毫不客氣地咬了我的馬腿一口。鄉里的領導騎的都是好馬,有的脾氣還很烈,我騎的馬也是。我的馬瞬間跳了幾下,然后猛地彈伸后腿踢了過去,那個白頭黃狗尖叫一聲連翻了幾滾,然后又站了起來搖了一下頭,就是不肯認輸,繼續沖。我的馬受了驚嚇,認輸了,一縱身跳起來就跑,跳得很高,差點兒把我甩下去。我好不容易才勒住韁繩并跳下馬立定,馬立直雙耳顫著身響著鼻轉圈兒。那個白頭黃狗看到我下馬了,就后腿間夾著尾巴雙眼盯著我也停下了。
這時,武裝干事在馬上揮舞鞭子,便嚇唬著其他的狗向我跑來。白頭黃狗偶爾吠叫幾聲盯著我站著不動。剎那,我突然想起童年時代咬傷我的那個黃狗:那天我跟媽媽到另一個山溝里的牧羊人家串門,大人們在石頭房子里聊天,我和那家的孩子在露天羊圈里玩耍,一只小黃狗也在跟著我們跑來跑去。不可思議的事發生了,那個小黃狗撲過來咬住了我的腿肚子,還不肯放嘴,不知為啥,那家的孩子不但不救我,還哈哈大笑看熱鬧。我邊尖叫著,邊拿起一塊小石頭砸著狗頭……那狗的四個尖牙留下的痕跡還在我的腿肚子上非常顯眼。那時候,牧區被狗咬傷的人不打狂犬病疫苗,傷口上抹些爐灰就完事了。
我心底冒出了報仇的火焰,嗆在喉嚨里,就到武裝干事跟前大聲喊:“槍,把槍給我!”武裝干事沒下馬,把挎在肩上的半自動扔給了我。我接過搶站穩腳,拉了一下槍栓,子彈上膛,就慢慢地舉起槍,瞄準了黃狗的頭……
黃狗的頭開了花,腦漿噴濺到雪地上,槍聲在山溝里回響了好一陣,其他的狗四處逃竄。我心里立馬充滿了報仇雪恨的滿足感。我把槍扔給武裝干事,摸了一下馬頭安慰它。就在這時,從冬窩子的房間那面跑來一個老婆子,她望了一下我們和躺在雪地上的黃狗,然后蹲在死狗旁邊就尖叫:“你們不得好死,為啥要打死我的好狗?”
武裝干事不作聲,我瞟了她一眼說:“你的狗咬傷了我的馬腿,是我打死它的。”那個老婆子向我撲了過來,大聲喊:“你,你,我的狗咬傷了你褲襠……哪家的狗看到陌生人不叫啊!我的狗到底惹了誰?你把護院的衛士給槍殺了,以后誰給我護羊群?你替它看家嗎?深更半夜的時候,你替它吠叫嗎?”
她沖過來想要揪住我的衣領,我把她推開說:“你趕快回家去把你的臟嘴洗干凈!”
這時,武裝干事下馬跑過來攔住她說道:“夠了,你這個毒蛇的舌頭咋這么長?這位是咱們鄉的副鄉長啊,滾開,滾得遠遠兒的!”
他這么一說,等于火上澆油了,那老婆子抓住武裝干事的衣領說:“我跟你拼了……”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我變成了拉架的,我從后面過來抱住那潑婦,小聲說:“好嫂子,狗是我打死的,你有什么話沖我來,我們給你賠個狗還不行嗎?”
那個老婆子一轉身,左手抓住我的大衣領子,右手指指我的眼睛說:“你,你能給我賠個抓狼的好狗嗎?”
雖然她這樣說,但聲音比剛才緩和了許多,武裝干事氣得在那哆嗦著站著,一時半會兒不知干啥。這時,跑過來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他揪住那老婆子的脖頸拉開了,然后和我們一一握手問候。那時,我當副鄉長時間不長,鄉里的好多人還不熟面,但這個男人我見過,他是沙爾布拉克村的牧民哈畢,而且和我都是那個“吃狗奶的部落”的。他把我們請到家里喝了個奶茶,非要我們吃個飯再走。比年齡,他老婆該當我嫂子。我們邊聊天邊喝茶,其間,肉也下鍋了。我的那個嫂子一直愁著眉,苦著臉,一言不發,不高興的樣子。我想試探一下她的想法,就說了一句近乎話:“嫂子呀!還在生我的氣嗎?你那狗咬傷了馬腿,而我也在馬背上差點兒被甩下來受傷,要不我也不會打死它,你大人大量,不管怎么說,我向你賠個不是……不應該打它……請原諒小叔子的過錯吧!”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她好不客氣地說:“你們‘兄弟互相殘殺,作為嫂子的我能不氣嗎?我心疼,疼得要命。”
她的意思是說,我和她丈夫哈畢都是“吃狗奶的”子孫嘛,殺死了狗就等于殺死了自己的“兄弟”……
我那個喀爾交鄉的有些女人就是這樣的毒舌,而性格又剛烈。有一年,我鄉的牧民和鄰鄉的牧民間發生草場糾紛。鄰鄉的牧民把我們鄉的牧民打散了,打得他們跑進氈房不敢出門。緊接著,鄰鄉的牧民揮舞馬鞭轉著氈房揚威。看到男人們縮頭烏龜的可憐相,有幾個老婆子手持樺樹杵子,沖出氈房騎上馬就參與了打架。當時,牧民打架一般都用馬鞭,可女人們揮舞著杵子上了場并和對方的幾個男人打上了。當然,對方的男人也不一定對女人們下狠手嘛。我們鄉的男人們看到女人們的勇敢行為,邊受到鼓舞邊羞愧無比,就都騎上馬拼了命地打過去。結果把人家趕跑了,爭議的草場給奪回來了。總的來說,我故鄉的人們性格溫和,而且好客,講義氣,為朋友肯把心窩子都掏出來。好,不說這些也罷,還是講講我殺“祖先”的第三個故事吧!
1995 年的夏季,我們鄉的部分區域發生了狂犬病。一個牧民在打草期間被患狂犬病的狼咬傷,雖然及時送到縣醫院救治,可不到一個星期就死了。這下麻煩了,地區領導過問事情的來龍去脈,縣上的領導蹲點兒督促工作。那時候,快要滅絕的狼們就在牧點的周圍出現,狐貍沖入牧人的房子。出現狂犬病區域的牧民中產生了恐慌…… 摸清情況后,鄉里決定開展消滅狗類動物活動,包括家養狗。鄉里還是安排我和派出所的所長負責此工作并具體落實。最后,我們分成兩個組:一個組由我帶隊,另一個組由派出所的所長領隊。我們兩個組都帶上槍支出發了。這一次,作為我的“祖先”或我的“同胞們”的狗兒,對它們造成危機的不是別人,就是像我這樣的不肖子孫。
我們在發生狂犬病的區域搜尋整整半個月,被我們槍殺的狗兒不計其數。我們越打越來勁兒,連狗崽都不肯放過。我槍殺的狗比他們槍殺的多得多,這也難怪,因為我畢竟是當過武警的人嘛,而且年輕,性格又急躁,虛榮心也較強,再加上執行命令是軍人的天職嘛,現已復員幾年了,可部隊上養成的好習慣哪能丟棄啊!
隨著年齡的增大,人常會回憶一生中經歷過的往事,我也不例外,常常會回憶自身經歷過的一些大事。想到那些做得對的事時,心情就會舒坦;可想起那些做錯的事時,總是心里不安起來,覺得于心有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