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印瞿秋白遺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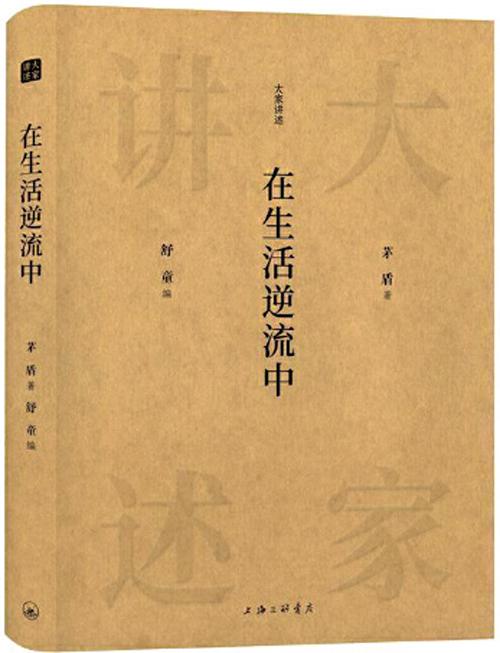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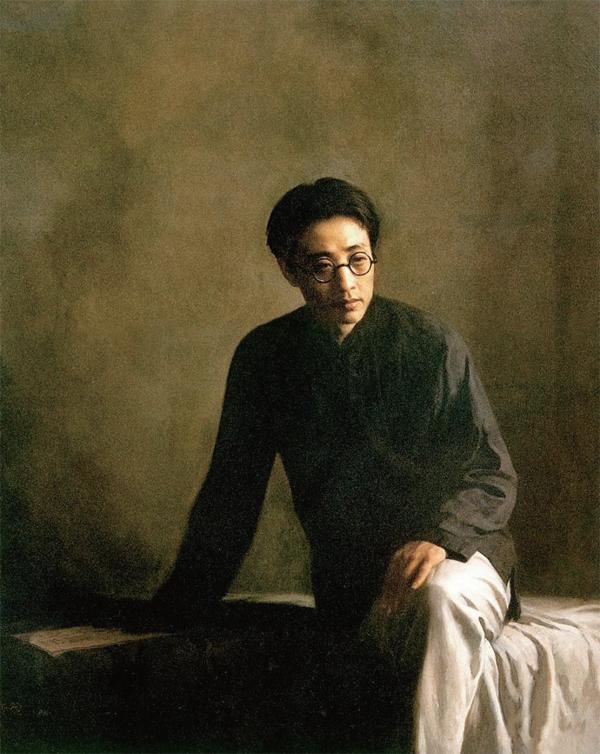
《大家講述:在生活逆流中》茅盾 著
上海三聯書店
2020年9月版
定價:39.80元
在搬往信義村的前一日,我去向魯迅告別,因為住得遠了,往后非緊要的事情只得靠書信來傳遞了。我們談了一會兒,我覺得魯迅的心情不好,就站起來告辭。魯迅卻拉住我,壓低了聲音道:“秋白被捕了!”我大吃一驚,因為我們總以為秋白是隨著紅軍主力離開中央蘇區西進了,莫非他所在的部隊給打散了?國民黨倒是天天在報上吹噓江西“剿匪”的勝利。我問:“這消息可靠嗎?”魯迅道:“他化名給我寄來了一封信,要我設法找鋪保營救。看來是在混亂中被捕的,身份尚未暴露。”我又問:“之華知道了嗎?”魯迅道:“告訴她了,她是干著急。你也知道,這一次上海黨組織被破壞得厲害,所有關系都斷了,所以之華也沒有辦法,不然找一個殷實鋪保還是容易的。現在要找這樣一爿店,又能照我們編的一套話去保釋,恐怕難。我想來想去只有自己開它一個鋪子。”我沉吟道:“就怕遠水救不了近渴。還是要靠黨方面來想辦法。”我們木然對坐,想不出更好的辦法。后來魯迅果然打算籌資開一個鋪子,但在尚無頭緒之時,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就登出了秋白被捕的消息。他被叛徒出賣了。從報紙上的消息,我們知道秋白未隨紅軍主力西征,而是二月底在福建長汀被捕的。同時被捕的還有兩個女的,也就是后來向敵人告密的叛徒。大約又過了一個月,在六月二十日前后,傳來了秋白同志高唱《國際歌》從容就義的噩耗。那時,秋白才三十六歲。
秋白犧牲后,就有人提議出紀念集,也有主張出秋白的全集。但只見口說未見行動。我與楊之華(由于黨組織遭到破壞,之華那時隱蔽在一個工廠里當女工)、魯迅也交換過意見。魯迅說:“人已經不在了,但他的著作、他的思想要傳下去,不能泯滅了。這也是我們還活著的人對他的最好紀念。不過,秋白的遺作究竟怎樣編印,我還要再想一想,大概只有我們自己來印。”
過了半個來月,魯迅約我到鄭振鐸家中去商量編印秋白遺作的事,他說:“我們都是秋白的老朋友,就由我們來帶個頭罷。秋白這本書,書店老板是不敢出的,我們只能自編自印。自編容易,只要確定個編選范圍,明甫兄和我都可以編。自印卻需要解決兩個難題,一個是經費,書的印刷、裝幀必須是第一流的,而印數又不可能多,所以成本一定高,將來書售出了,也許能收回成本,但目前先要墊出錢來。另一個是印刷,要找個肯印刷的地方。”振鐸接口道:“經費可以在朋友熟人中間籌集,將來再還,也可以募捐。印刷問題容易解決,找印刷所的事就包在我身上。”魯迅說:“一些年輕朋友倒是很熱心,但他們口袋里沒有錢。”我說:“秋白當年的老朋友不少,他們現在大抵都有點名望,也拿得出錢,他們雖然不愿出頭露面,但暗中幫助是一定肯的。不過也要先估計一下大致的字數、印數及印刷費用。秋白的遺作大概有多少萬字?他早期寫的政論不少,是不是都要收集進來?這樣恐怕字數相當多。先要定出一個編選的范圍,然后可以計算出需要多少錢。這件事要聽聽之華的意見。”魯迅說:“我手頭有秋白的一部分手稿,主要是文學著譯方面的,政論文章要看之華那里是否保存得有。不過這部分文章恐怕印刷所不敢排印,也沒有書販敢賣。有兩部秋白的譯稿在杜衡那里,前年拿去的,說是現代書局要出版,稿費也預支過了,卻一直扣著不印,這次可以把它贖回來。”又說:“我是不贊成出紀念集的,太小氣了,出全集還沒有這個條件,我的意見還是出選集。至于籌款,范圍不要大了,年輕人就不必去驚動他們了。”我說:“籌來的款能不能歸還,先不要說死,這部書印數少,成本高,弄不好還要倒貼的。”魯迅點頭道:“先不說死也好,將來每位捐款人送兩套書是一定辦得到的。”最后決定,由魯迅與楊之華商定遺作編選的范圍,并由魯迅負編選的全責。由鄭振鐸去聯系印刷所,等到有了著落,再由振鐸出面設一次家宴,把捐款人請來,既作為老朋友聚會對秋白表示悼念,也就此正式議定編印秋白的遺作。捐款人由振鐸去選定。我不負具體的責任,只規定我從中協助和促進。另外,我捐了一百元。
鄭振鐸聯系印刷所并不順利,最后還是通過章錫琛找到了開明書店的美成印刷所。這也有他的難處,因為太小的弄堂印刷所排印不了這樣考究的書,而大印刷廠(譬如商務的印刷廠)振鐸怕里邊的走狗告密。八月六日,振鐸在家中設便宴,到十二人,都是當年商務、開明的老同事、老朋友,也是秋白的老朋友,記得有陳望道、葉圣陶、胡愈之、章錫琛、徐調孚、傅東華等。大家回憶起秋白當年的音容笑貌,不免凄然。談到籌款事,一致推定振鐸為收款人,并相約推薦新的捐款人。
九月四日,魯迅約我去他寓所。我趕到那里已是掌燈時分。魯迅捧出兩大摞原稿放在桌上,用手輕輕拍一拍道:“都在這里了。”我估量了一下問道:“有一百萬字罷?”魯迅微笑道:“也許還不止此數。”又指著原稿道:“這一摞是著作,那一摞是譯文。當然不全,不過之華已經盡了全力了。現在的問題是究竟怎樣編?全部出版恐怕要編四巨冊,經費有困難。之華的意思是先出著作,因為這些是秋白的心血結晶,比譯文重要。我則認為譯文收集得比較全,編選也容易,著作則編集困難甚大,非短時間所能完成,不如先將譯著出版,一面繼續收集作品,等到將來譯文集售出若干,經濟可以周轉時,再考慮出續集。兩種意見,要請你來裁決。”我笑道:“裁決不敢當,還是商量個最好的方案。”又說:“之華說得有道理,著作與譯文不同,著作更重要;不過我還是贊成你的意見。秋白的譯文比較單純,主要是文藝方面的,而他的著作就復雜,大量的是違禁的政論,現在恐怕不是出版的時候。”魯迅道:“我大致翻了一下,有不少文章是講國共兩黨的斗爭的,收不收進集子,最好由黨方面來決定。文藝方面的著作是可以編的,不過還是放到第二步好,作為續編來考慮。”又說:“現在既然你同意了我的意見,之華就不會再堅持了,她說過,最后由你和沈先生決定。她不久就要去蘇聯,已經把編印秋白遺作的事完全托付給我了。”

